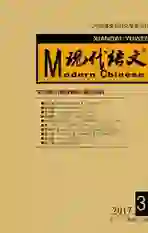永远的返乡与命运之思
2018-01-17梁芬奇
摘 要:《望春风》作为格非继“江南三部曲”与《隐身衣》后的最新长篇力作,它的构思巧妙意蕴丰富,尤为突出的是作品饱含了作者深沉的归乡情结和厚重的生命积淀。小说勾勒了为数众多的人物群像,他们每一个人都承载了作者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作为故乡与乡村题材的收官之作,《望春风》从故事层面到精神层面都围绕“返乡”展开,同时作者对于个人命运的变幻无常也有独到的感悟。小说以主人公赵伯渝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儿童被父亲独自抚养长大到失去父母双亲,从年少到老去,从儿童的天真的叙述到成人审慎的自白,在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我”得以重返故乡,重拾生命中的温暖与希望。
关键词:返乡 文本分析 互文性
一、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构成的时空对话
格非的《望春风》与鲁迅的《故乡》一样,在叙事上均选择了以第一人称来叙述自己返乡路途和情感经历。热奈特在《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指出:“第一人称叙事是有意识的美学抉择的结果,而不是直抒胸臆,表白心曲的自传的标记。”[1]这段话表明,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是作家匠心独运的表征,不可以随便等同于作家自传,应承认其艺术运思的存在。《望春风》用第一人称叙述,采用的是内聚焦的叙述模式。在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中都可以出现内聚焦叙事。然而,第三人称内聚焦与前者还是有着细微差别。如“第三人称内聚焦叙事文一经叙述者传达,则存在着两个主体,既有人物的感觉又有叙述者的编排。并且,运用内聚焦的第三人称叙事文在视野范围上有一定自由度,即使作品中的叙述者悄然移动一下角度,也不至于像第一人稱叙事文中那样明显生硬。”[2]但是作者坚持选择第一人内聚焦这一颇受限制的叙事方式实际上别具匠心。以“我”的口吻贯穿全篇,自然所叙述之事都是“我”的选择,包蕴了“我”的思索,浸润了“我”的情感。这样一切叙事都是在“我”的选择下进行的,主观体验性较第三人称内聚焦更强。对于这个文本内聚焦可以做以下细致分析。
与鲁迅的《故乡》不同,格非的《望春风》并没有采取倒叙回忆的方式勾勒故乡曾经的图景,而是以顺序的方式,开篇即以还是孩子的“我”叙述了“我”和父亲去半塘走差的经过以及窑里赵村和儒里赵村数十年的见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由儿童成长为少年,并离开故乡逐渐成人再到逐渐衰老,叙事者“我”也悄然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在回顾往昔故乡的人和事时,“我”已经由懵懂无知的少年变成历尽沧桑的老人。这便是整部小说中的两个第一人称。申丹在《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说:“但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事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以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3]比如“我”对唐文宽的了解就是如此,“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对着孩子说怪话,一直是唐文宽让他们大笑不止的法宝。”后来知青小付听出了唐文宽的“怪话”实际是流利的英文,才从此牵连出唐文宽不为人知的身世经历。再如父亲的身份,童年时我一直认为父亲是南货店的伙计,后来却迷上了算命行当,土改时回到农村戴上富农帽子。后来德正在医院向我透露了父亲真实身份实际是上海特务组织的成员,他的死可能是畏罪自杀,但是他选择自杀的时间又颇为可疑。确实,《望春风》中双重的第一人称“我”在叙事过程中的悄然变换也营造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感。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叙事从第一章、第二章的线性叙事,到第三章余闻时以人物列传的方式将拆迁之后儒里村人物的命运一个个娓娓道来,同时解答了“我”童年时对许多事的疑惑。这样的叙述虽然依然没有脱离第一人称内聚焦的方式,但是却打开了叙事的视野,让读者对人物的理解更加深入,也很自然地将人物们融入了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但是,小说的双重第一人称“我”在叙述过程中依然承担着回忆和现实的两条线索。
记忆中清新质朴的故乡在现实中凋敝了。小说中曾经提到王曼卿精心打理的花园:“曼卿家的园子,不过是用蔷薇花枝密密匝匝地编织而成的篱笆院落。桃、杏、梨、梅,应有尽有;槿、柘、菊、葵,各色俱全;蚕豆、油菜、番茄、架豆,夹畦成行;薄荷、鸡冠、腊梅,依墙而列。花园外,就是一望无际的桑林和麦田,斜斜的坡地一直延伸到弯月形的波光水线。”多年后儒里赵村拆迁的废墟上,王曼卿的花园“早已不复旧观,时移物换,环堵萧然。同彬站在当年王曼卿为他翻眼皮的那处墙根下,目光追逐着一只黑翅的大蛱蝶,看着它在瓦砾上翩然翻飞,神情漠然,若有所思。”[4]两个叙事主体所叙述的出来的生活场景,来自两个时间空间的人,自然会有差异,以致形成两个时空的对话。如今故乡的萧索代替了当年故乡的明丽景象,“我”的语调也从天真变作伤感无奈。横亘在两个“我”之间无法逾越的时空,通过过去和现在的转变形成了“宽阔时空的对话”,我们在阅读中产生的诸如思乡、乡愁、凄凉、落寞等诸般感受,正来自此对话的效应。
二、中外文学交映下优秀的互文小说艺术
采用互文性方法分析《望春风》,是探寻这个文本艺术价值的另一条路径。“朱力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出的互为指射(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echo)其他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互相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或隐蔽的引证和隐喻;较晚文本对较早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5]
1.题目与互文性。小说中互文的现象频繁出现。克里斯蒂娃关于互文性的思想启发了我们:“互文性超越于国家和民族,各民族国家的文学相互借鉴、互相借鉴、互相指射的空间是无限的。格非作为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又有多年在大学任教的经历再加上他的中外文学修养都非常深厚,因此《望春风》与中外文学的互文性都格外明显。题目《望春风》借用了题记中《诗经·小雅·节南山》“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之意。小说结尾处的一段话更可以作为题目的注脚。“我”在失去所有亲人后站在破败的故乡面前向东、西、南、北四方瞻望,“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节南山》是周孝王之子家父为了讽刺执政者尹氏所做的诗,时过境迁,家父当年讽喻的暴政已是昨日黄花,但是忧时忧世之情依然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面对乡土的失去,故乡的精神之根在现代文明急速推进中被无情斩断,“我”的痛苦,无奈和悲凉之情与《节南山》中“我”的四顾茫茫的又是如此的相似。小说再次引用《诗经·王风·黍离》中“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诗句对人终极意义发出振聋发聩的拷问,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题目《望春风》的注解。可以说“文学作品的客观世界,这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以及‘形而上质(崇高的、悲剧性的、神圣的)”[6]等层面。那么,散落在作品中的互文现象又在形成作品的艺术价值上起了怎样的作用呢?endprint
2.还乡模式与互文性。互文本身并不简单指文本中直接对过去文本的引用,文学文本中固定模式的引用也同样可以构成互文。显而易见,《望春风》中“还乡”的主题明显借鉴了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纪》。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十年,历经种种艰辛,最后回到家乡与妻子重逢,这和我1977年离开故乡,历经三十年又重返故乡和春琴结为夫妻非常相似。小说为读者构架了主人公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还乡之旅。失去父亲的赵伯渝离开故乡踏上了去南京寻找母亲之路,却又迎来母亲已经去世的打击,这让“我”产生了无限的孤独和思乡之情。后来,人到中年的“我”和春琴在同彬的帮助下回到重新修缮的变通庵居住。在某种意义上,叙述者是在几十年后亲眼目睹故乡彻底消失时,才开始追溯自己的生命之源。这样重返故乡又重拾生命意义的模式可以说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中几乎可以作为一种母题的存在。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地。”无论是诗人荷尔德林的《返乡——致亲人》,哈代的《还乡》,还是鲁迅的《故乡》都和《望春风》一样思考着现实的故乡与精神的故乡之间的联系。但不同的是《望春风》用循环往复的圆形来隐喻命运的轨迹,具体分析会在本文第三部分详细说明。
3.古文诗词与互文性。本文中穿插在情节中的诗词、古文、书画、曲名,对人物的性格的刻画起到了暗示作用,也同样营造了一种优美深沉的古典意境。“我”的老师赵先生的书房里“有一幅《溪山狩猎图》。旁边还挂着一幅字,据说是周蓉曾的手笔:
履霜坚冰所由渐
麋鹿早上姑苏台
我们每天上课都看着这幅字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幅字引用的是王国维《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这首七古中的两句,上下文为“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履霜坚冰所由渐,麋鹿早上姑苏台。兴亡原非一姓事,可怜惵惵京与垓。”[7]从引文来看其中又另有出处,“履霜坚冰”是《周易》坤卦初六的系辞:“履霜,坚冰至。”比喻危险的事情即将到来。而“麋台”的典故出自《史记·淮南山列传》:“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用来比喻政治腐败,国家威危亡。王国维作为前朝遗民感慨大厦将倾,生民涂炭,无人能力挽狂澜。我的老师赵先生在私塾教书,思想守旧,也颇有些遗民思想,他的书房挂有王国维的诗在合适不过。但是,深究起来,如果不单单把这两句诗看做前朝遗老的悲叹之作,而看成对淳朴自然的故乡终将失去的预言就更有深意,那姑苏台上荆棘丛生,麋鹿遍布的景象几乎可以当作多年后我回到已是砖瓦满地,走兽出没的故乡的写照。沈祖英一章,沈祖英“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谚中,我们可以隐约看见她对生活的基本看法: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桑田生白波。”这一句出自八仙之一的蓝采和的《踏歌》道尽世事无常,人事变迁之感,但洒脱随性也呼之欲出。一辈子没有结婚隐居在图书馆的沈祖英就是如此性格。这句诗歌的大意是:早上乘着凤凰飞到天上,傍晚就见到桑田升起白波。一“朝”一“暮”即见沧海桑田,人一辈子的兴衰荣辱在仙人眼里不过一朝一暮罢了。书中也提到人一生的轨迹总会有辉煌的时刻但是最终还是会复归卑琐与平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皆是如此,从而伤感的叹息除了故乡的失去还伴随着青春年华的一去不返。
三、命运之谜的阐释空间
《望春风》在叙事上采用循环往复的圆形隐喻命运的周而复始。叔本华说:“除非运用寓言和比喻的方法,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最深刻最隐秘的真理。”[8]格非笔下人物的“宿命”就是叔本华所说“最深刻最隐秘的真理。”对命运的不可抗力,中外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红楼梦》警幻十二仙曲预示了金陵十二钗各自悲惨的命运,莎士比亚《麦克白》三女巫也在一开场就预示了麦克白的命运,《望春風》将命运更强化了生与死的联系。“在死亡的一刻,一切神秘的力量(虽然它们植根于我们自己)就聚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它们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这些力量角力后的结果就是这个人即将踏上的道路:这个人的再生、轮回也就准备好了,连同其所有的痛苦快乐。” [9]格非设置了变通庵连同生死的地点。父亲的生命在这里结束,我回到故乡与春琴结合又重新生活在这里意味着生命重新的开始。如书中所说“其实,我和春琴的童年时代,我们过的这样的日子。我们的人生在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在快要走到它尽头的时候,终于回到了最初的出发之地。或者说,纷乱的时间开始了不可思议的回拨,我得以重返时间黑暗的心脏。”而这个连同生死的“变通庵”,“或许真的是我那料事如神的父亲留给我的神秘礼物。”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提供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父亲葬礼的时候天上下着大雪“梅芳站在我身后,用手紧紧地箍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泪水掉落在我的额头上,顺着我的鼻梁往下淌。我能感觉到,她怀有身孕的大肚子紧紧贴着我的脊背。”眼前是触手可及的死亡,背后是安静孕育的新生。生与死之间仿佛有在那样一个时刻悄然流转。巧合的是梅芳那个孩子出世后就叫做新生,梅芳离婚后万念俱灰的生活也因为这个孩子而“新生”。小说还多次运用重复的笔法隐喻生命的回归:赵伯渝父子走差的过程中,“我看见他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坡的顶端,然后又一点点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变大、变高。”给父亲送口信的陌生妇人走时,“她的身影在风渠岸的大坡上一点点变小,一直升到坡顶……又自对面的土坡赏一点点变大。”赵伯渝和春琴回半塘扫墓的路上,“我看见她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土堆的顶端,然后一点一点地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春琴又在另一个突破上一寸寸地变高、变大。”格非对“重复”有自己的理解:“我所着迷的‘重复源于我对生活自身的思考。我们对‘重复源于我们对生活自身的思考。我们对早年的经验会在生活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对于同样的时间感受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当每个细节在不断地重复过程中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10]小说用三次几乎重复的笔调描述了三个不同的背影,分别映射了主人公经历的三个人生重要阶段:第一个背影是小孩子崇敬的目光看高大的父亲,还未尝涉世,天真懵懂;第二次已经隐隐感受到命运的一位,初尝世事,虽内心有感,但还只是些初浅的感性认识;第三次的凝望是中年人的目光,在经历人世的沧桑变迁之后将生命看得透彻。结尾处“望春风”三字画龙点睛,是绝境逢生,面对人生起起伏伏终归平静的释然,这里的“望”是对未来的眺望,无论草木荣枯、繁华衰败,“春风”都在吹着。endprint
除了命运的反复循环之感,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孤岛”理论是命运之谜的另一个方面。小说中沈祖英一章中提到:“她(沈祖英)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过,每个人都是海上孤立的小岛(这个比喻来自《奥德赛》),可以五香瞭望,但却无法相互替代。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书中的沈祖英就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与“我”在图书馆工作十几年,她“从未请我去他们家做客,也从未提及她的任何一位家庭成员”还“一直可以避免谈她的身世”。即便是与“我”朝夕相处的童年伙伴,父亲的自杀,母亲的死,几乎书中的每一个人都怀有秘密,而他们的真实心意我也永远不能知晓。这些情节的安排又与题记之二蒙塔莱《也许有一天清晨》的诗行遥遥呼应“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默默走在人群之中,他们都不回头。”在叙事手法上,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也增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可知。“我”只能记叙“我”所看到的,或是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人和事,因此很多事情发生的第一现场“我”是无法经历的。这样的叙述方式似乎也在模拟我们每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对于世界未知的部分远远多于已知部分。小说的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在梦境描写和命运书写上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学关于梦与生命轮回的命运冠;同时,小说被包裹在农行元的神秘气氛中,从儒里赵村这个村庄的虚幻色彩到整个故事的扑朔迷离都有鲜明先锋色彩。作者借以传统和先锋这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命运的神秘与不可预知。
注释:
[1]王文融译,[法]热拉特·热奈特著:《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2]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3]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4]格非:《望春风》,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352页。
[5]朱金鹏译,[美]艾布拉姆斯著:《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页。
[6]刘俐俐:《一个有价值的逻辑起点——文学文本多层次结构问题》,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
[7]王国维:《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519页。
[8]韦启昌译,[德]叔本华著:《叔本华思想随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9]同上165页。
[10]赵振杰:《文学永远是一个变數——专访格非》,新文论,2016年8月25日。
(梁芬奇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院 03000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