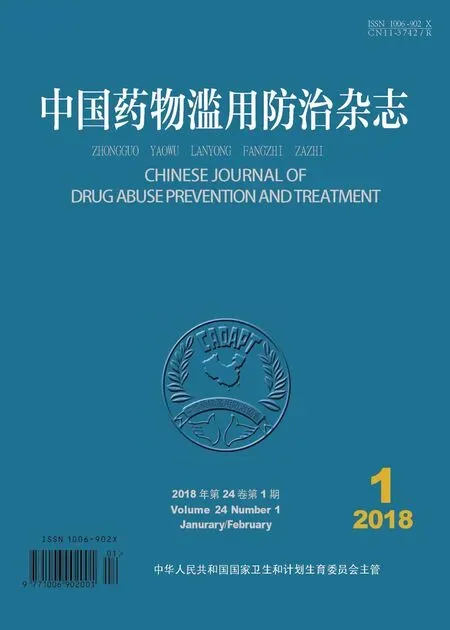接纳与承诺疗法在物质依赖中的应用*
2018-01-17吕知璐蒋京川
吕知璐,蒋京川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
物质依赖(Substance Dependence)即成瘾物质依赖,是指一种不正当的使用物质的后果,由于机体对某种成瘾物质产生了依赖性而无法控制地反复使用某种或某类物质[1]。比如阿片类药物、酒精、尼古丁等物质的使用,这类问题戒治的复发率很高,第一年超过60%,第二年超过75%[2]。长期使用成瘾药物可导致吸毒者认知功能的损伤,表现为行为抑制缺失、注意力受损以及记忆力减退等,严重者会危害家庭和社会[3]。戒治者在戒断后虽可有效抑制对毒品的生理依赖,但并不能完全祛除心理依赖,这成了成瘾者高复吸率的重要原因。能否消除心理依赖也是防复吸的关键[4],而对于心理干预层面的工作模式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近些年,在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系列新兴疗法,其中典型代表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Hayes等人创立,被誉为“认知行为疗法第三浪潮”的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相较于其他的认知行为疗法,ACT在理论和实践技术融合了很多东方文化的概念,更符合了中国的文化背景[5],对国内物质依赖领域的干预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 ACT的理论基础与模型内容
1.1 ACT的理论基础
ACT是以功能性语境主义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 为哲学背景,以关系框架理论 (Relational Frame Theory, RFT)为理论基础[6],旨在削弱人类在痛苦时所使用语言的破坏性,这对于物质依赖患者在生活问题中产生的自动化的负性思维和自我评价很有价值。
关系框架理论是一种行为语言学习理论,揭示人们如何将经验和语言结合,来改变和影响内部和外部行为。作为ACT独有的模式,它探讨人类如何在想法与想法、经验和经验之间进行操作和安排,并创建一个关系框架网络,进一步发展语言学习过程。例如,当谈到“考试”一词时,一个人可能会想到试卷、学校、课堂等和考试接近的东西。然后他可能会进一步感知到与考试经历有关的体验(包括焦虑、懊悔、得意、怀念等正负性情绪),从而通过感知产生出与考试相关的一个关系框架。由此可见,关系框架是由想法和相关的经验所组成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人们不自主地将思想同语言跟过往经验(包括了痛苦经验)相联结。
理论研究表明,人类在分析与整合刺激相关因素,并将其置于任意情景控制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这些分析和整合后的刺激关系也能反过来改变事件的功能,这是一种受情景控制的过程[7]。ACT不仅关注到了特定情境下的关系网络及属性,它还注意到改变这种关系网络及其功能的情景。可见,ACT的目标并不是去改变困扰心理事件的内容、形式或频率,而是通过改变这类事件的功能以及个体与事件的关系,以此来提升个体的心理灵活性,解决各类心理问题。
1.2 ACT的模型与内容
国外在各领域应用ACT技术时都发展了自己的特定咨询技术,这些技术都是在Hayes等人所提出的六种核心技术上发展,下面介绍下六要素的具体内容和操作:
(1)接纳(acceptance)。接纳是要来访者用一个真正开放的方式来经历正在发生的事情(往往是痛苦的情形),而不是回避模式。物质依赖者的生活中往往有诸多痛苦的经历或问题,酗酒、吸毒等是一种回避现实问题的行为方式。实际操作中治疗师通常先在谈话收集来访者的过往经历的问题及反应或处理方式来评估其接纳的准备水平,逐步引导其接纳当前在回避的痛苦经验。如一个离异女人可能会通过全身投入事业(或吸毒玩乐)来回避对婚姻不幸的挫败感,咨询师可以通过让来访者将一个痛苦情景视觉化(如看见朋友夫妻的和睦有爱场景),并注意观察此情景引起的想法、情绪、回忆和身体语言,从而精细描述出回避的内容。最终在对待痛苦上,来访者能够看见它、承认它、且愿意不抗拒地体验它。
(2)认知解离(cognitive defusion)。是将自我从思想、意象和记忆中分离,客观地注视思想活动如同观察外在事物,将思想看作是语言和文字本身,而不是它所代表的意义,不受其控制[5]。咨询师的主要目标就是让来访者有意识地将感受体验为感受、思维体验为思维、记忆体验为记忆。比如物质依赖戒治中可能产生“我是个失败者”的评价,这里就在“我”和“失败者”上产生了“认知融合”(cognitive fusion)。应通过引导让其意识到:此时“我”只是产生了一个“我是个失败者”的念头(但“我”不是念头本身),并进一步理解这个念头的来源去解离“我”和“失败者”的对等关系,意识到“我(只是)曾在戒烟这件事上失败过”(而不是所有事)。具体的训练操作上ACT有一些经典的活动,比如“牛奶牛奶”训练(通过快速大声重复词语或语句达到将意义与语音解离);或用像“公交乘客”一类的经典隐喻,让思维能够变成具体的人或事从而达到认知解离。
(3)体验当下(being present)。即“关注你在这一刻的经验,而不是被你的思维掌控”[8],将注意力放在当下,以一种非评价的方式体验一切,而不是思虑过去或将来。对于专注于当下,可以通过使用一些简短的正念练习,通常会在治疗的开始阶段先做一些类如“观察呼吸”练习、“身体扫描”体验,或通过关注当下的五种感官(“我听见/看见/闻到……”)来帮助来访者从里到外地培养对当下的关注。咨询师也会在互动过程通过观察来访者当下的反应给予及时的注意和反馈,帮助其更好的培养当下的觉察。
(4)以己为景(self as a context)。是将一种被评价的概念化的自我转化成一种作为各种心理事件的载体的自我。也就是在治疗过程中培养来访者发展处一个“观察的自我”,比如要求来访者站在更“明智的将来”回头看看现在的自己。其实,前几项要素都是通过综合干预让来访者发展出“一种灵活和即时的自我意识”,鼓励其以一种正念的状态对自己的思维情绪保持觉知,使来访者回到与更广泛知识的接触中——而不是僵化于语言语境设定的狭隘牢笼里。
(5)价值(values)。即一个不断被实践的方向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可实现的目标[9]。例如,“找到伴侣”是一个可以通过结婚完成的目标,但“成为一个更好的爱人”却是一个没有完成时的实践方向,它需要个体在日常选择中不断选择和创造。“为伴侣倒一杯水”,“倒水”或“解渴”不是单薄机械的目标,“爱”的意愿(价值)是引导在整个过程中的。因此,价值指导的问题并不是具体要做什么,而是如何做。僵化模式下的来访者往往会展现出某种“自己无法掌控生活”这样一种似乎“别无选择”又“无法实现目标”的状态。比如,婚姻关系不满的来访者可能在家庭中做着一切“应该的”“正确的事情”,从而能够与配偶维持着一段和平疏远的关系,而这并不是其“真正想要的状态”。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价值追求时才会蕴含出巨大的生命力,这需要咨询师带来访者一起探索并澄清来访者所重视的价值内容,帮助其理解行为、目标价值的不一致性。在具体操作上,ACT会应用一些活动,如“观看自己的葬礼”,“我的墓志铭”“价值评估工作表”等方式,剥离冗杂的生活信息追问其最深处的价值意义。
(6)承诺行动(committed action)。是指“在某一时刻发生的以价值为基础的行为反应,并与服务于价值的行为模式紧密关联。”作为认知行为疗法,ACT的底线是要落实在“行为”上的,其疗法的名字——ACT(也是缩写)也正是对“行为改变”的重视。承诺行动是表达个人价值的途径,最终是发展出与价值深层的联结的一套新的、灵活自主的行为模式。咨询师的任务是辅助来访者根据价值做出行动的承诺和实施步骤。需要澄清的是,在实际中,来访者可能会发生行动失败(如毒品复吸、失控对孩子打骂),咨询师需要让来访者明白价值(“想要成为一个好父亲”的愿望)依然是永恒未消减的,除非来访者自己改变了价值。对于价值和行动的关系,可以通过ACT一些经典的“园艺隐喻”“滑雪隐喻”等帮助来访者更好的理解,也有助于其更坚定持续的投入价值的行动中。ACT对价值与行动的关系理念,对于物质依赖者生活中,由于“偶然复发”引起来自我全盘否定的破坏性后果可能具有重要的心理建设意义。
从ACT 的心理灵活性模型看,六大基本过程是相互影响和联系的,它试图打破以往通过具体心理病理过程导致特定心理问题的传统模式,认为六大基本过程是同时对特定的心理问题产生不同程度影响[10]。模型总体又可看做两大过程:正念和接纳、付诸行动(或承诺和行为改变)。
具体操作中,ACT注重练习或实验的直接体验,较少采用直接说教的方法,干预过程中会使用各种隐喻来帮助来访者理解各种技术的具体技巧及其原理[11]。ACT本身强调灵活性的重要,在治疗实践中它也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治疗手段,治疗师不用拘泥于某种形式、流程,而是可以从任何一个核心过程切入,且能够与传统的其他行为疗法技术很好的兼容。为了维护这一疗法的灵活性防止治疗师在治疗中过于僵化和集中,ACT团体甚至不再认证 ACT 临床咨询师[11]。
总之,整个模型的目标并非是建立一个手册化的治疗工具,而是一种以过程为导向的综合模型。
1.3 心理灵活性测量工具
目前为止,研究者主要使用认知融合和经验性回避作为心理灵活性的量向,也就是认知融合和经验性回避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灵活性水平就越低[12]。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2nd Edition,AAQ-Ⅱ) 是评估心理回避的主要工具[13],另一问卷是认知融合问卷( 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CFQ)。国内学者引进量表并分别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验证性分析和修订,得到接纳与行动问卷(AAQ-II)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重测信度0.80[14];认知融合问卷( 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CFQ)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重测信度0.67[15]。中文版量表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ACT价值的有效工具。
2 ACT在物质依赖中的应用及效果
2.1 ACT在物质使用障碍的应用研究
一项针对用ACT疗法干预物质成瘾领域(包括吸烟、酗酒、吸毒)的元分析报告了ACT较于其它疗法的表现出更显著的效应[16]。Lanza等人(2014)通过ACT工作坊对物质成瘾障碍者的自我污名进行干预,后测结果现实干预显著降低了自我污名感[17]。Heffner等人(2013)使用ACT团体干预在女性吸毒人员中进行了对照组研究,发现ACT不但能降低毒品使用,且显著提升了心理健康水平[18]。在ACT治疗方法的创新推广与实际应用方面,Bricker等人(2017)甚至将ACT的治疗理论与当下智能手机的使用相结合研发出一个针对烟瘾人群戒烟的APP(SmartQuit),从2014年到2017年的先后三份研究报告显示,这种与新媒介手段结合的戒烟手段具有良好的戒断成果,通过观测追踪戒烟用户使用该软件的持续参与度以及实际的戒烟率来实现[19-21],这为ACT理念在物质使用障碍甚至未来更广阔的干预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一些参考。
2.2 ACT在团体干预中效果的持续性
ACT本身并不关注症状反应或消极认知,更多的是去引导个体认识痛苦的普遍性,认清接纳与改变的辩证关系,这对大多数物质成瘾者的生活和所经历的内心冲突的化解过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ACT是通过让个体从认知的纠结转向当下的事实并于此时此刻紧密连接,遵循自己的价值观念努力行动来产生实质的转变,这种理念意味着个体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领悟与练习,它的效用会随着时间积累而日益凸显[22]。
Luoma等人(2012)在冰毒成瘾干预研究中就发现ACT和CBT相比在治疗参与的持续性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ACT组的冰毒成瘾者(病理学评价和自我报告)的成瘾严重程度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降低[23]。另外一项针对降低物质成瘾障碍群体的羞耻感团体干预研究也发现ACT不仅能有效降低羞耻感,且4个月后所表现出的效果比刚结束干预时要更加显著[24]。西班牙一项针对监狱背景下的物质成瘾女性的对照组干预研究发现,ACT干预小组的戒断率达到27.8%,在干预结束的6个月追踪效果达到43.8%[25]。针对女性戒毒人员的团体干预中将ACT和CBT做对照干预,同样发现ACT组的心理健康水平在追踪效果中比CBT组和ACT组自身直接后测的结果要提升更多[18]。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支持了前人研究,Smout等人(2010)用两种认知行为疗法对照干预了抑郁症群体发现ACT在即时效果和长期效果方面都显著高于CBT组[22]。这些研究结果都显示出ACT在效果中的持续生命力和临床应用价值。ACT的作用机制不像CBT 那样激进,它以一种温和而渐进的方式,使症状与负性思维呈现平稳而持久的线性下降[22]。因此,相对于传统的认知行为疗法,ACT疗法的优势可能主要体现在干预结束后在自然生活中产生的持续影响力。
3 小结与展望
ACT并不是一种针对特定问题去分析原因的干预方法,而是通过关注功能实现转化,并通过价值的探索落实到现实的行动中。这造就了ACT在诸多临床干预领域的丰富成果,也在物质依赖领域中显露出特有的应用潜力。
未来在物质依赖这一社会性心理问题领域,ACT的研究前景广大,更多的干预研究可以不断展开。同时,对于影响心理灵活性的过程影响因素也需要进一步探析。在测量工具方面,国内对于心理灵活性的工具量表的信效度资料还比较少,还需要更多本领域的研究提供支持[15],尤其对于成瘾人群,现有量表的适用性如何还亟待考察。最后,如何将ACT这一灵活的技术和我国的社会环境、文化心理相结合,发展出针对不同物质依赖人群的具体干预方案也是未来需要不断思考和校验的方向。
[1]刘毅,路红. 变态心理学[M]. 广州市: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2]Brewer, J.A., H.M. Elwafi , J.H. Davis. Craving to quit: psychological models and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mindfulness training as treatment for addictions[J].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Psychologists in Addictive Behaviors, 2013. 27(2): 366-79.
[3]Lu, L., Y. Fang and X. Wang, Drug abuse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Cellular & Molecular Neurobiology, 2008. 28(4): 479.
[4]陈磊,王学廉.药物成瘾脑深部电刺激术研究进展[J].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 2015(10): 782-789.
[5]张婍,王淑娟,祝卓宏.接纳与承诺疗法的心理病理模型和治疗模式[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05): 377-381.
[6]Mccracken, L.M., F. Mackichan , C. Eccleston. Contextual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severely disabled chronic pain sufferers: effectiveness and clinically significant change[J]. European Journal of Pain, 2007. 11(3):314-322.
[7]王淑娟, 张婍,祝卓宏. 关系框架理论:接纳与承诺治疗的理论基础(述评)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11): 877-880.
[8]Russ, H., H. Steven. ACT Made Simple : An Easy-to-Read Primer on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M]. 2009: New Harbinger Publications.
[9]曹婧,王凤兰,闫晓丽,等.239例女性戒毒人员应对方式与自我接纳的相关分析[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14(03): 190-192.
[10]Weeden, M. and A. Poling, Learning ACT: An Acceptance & Commitment Therapy Skills-Training Manual for Therapists[J]. Psychological Record,2010. 60(3): 549-552.
[11]曾祥龙, 刘翔平,于是, 接纳与承诺疗法的理论背景、实证研究与未来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 2011(07): 1020-1026.
[12]Hayes, S.C., K.D. Strosahl and K.G. Wilson,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mindful change (2nd ed.). 2012.
[13]Fledderus, M., et al., Further evaluation of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II.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12.24(4): 925-36.
[14]曹静,吉阳,祝卓宏.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中文版测评大学生的信效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3(11):873-877.
[15]张维晨,吉阳,李新,等. 认知融合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4(01): 40-44.
[16]Lee E B, An W, Levin M E, et al. An initial meta-analysis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for treat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J].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2015. 155: 1-7.
[17]Luoma J B, Kohlenberg B S, Hayes S C, et al. Reducing self-stigma in substance abuse through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Model,manual development, and pilot outcomes[J]. Addiction Research & Theory,2009. 16(2): 149-165.
[18]Lanza P V, García P F, Lamelas F R, et al.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Versus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ubstance Use Disorder With Incarcerated Women[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4. 70(7): 644-657.
[19]Heffner J L, Wyszynski C M, Comstock B, et al. Overcoming recruitment challenges of web-based interventions for tobacco use: The case of webbased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for smoking cessation[J].Addictive Behaviors, 2013. 38(10): 2473-2476.
[20]Bricker J B, Mull K E, Kientz J A, et 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pilot trial of a smartphone app for smoking cessation using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J].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2014. 143: 87-94.
[21]Bricker J B, Copeland W, Mull K E, et al. Single-arm trial of the second version of an acceptance & commitment therapy smartphone application for smoking cessation[J].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2017. 170: 37-42.
[22]赵文,周雅,刘翔平,等. 接受与承诺疗法干预抑郁的效果追踪[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01): 153-157+169页.
[23]Smout M F, Longo M, Harrison S, et al. Psychosocial Treatment for Methamphetamine Use Disorders: A Preliminar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and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J]. Substance Abuse, 2010(No.2): 98-107.
[24]Luoma J B, Kohlenberg B S, Hayes S C, et al. Slow and steady wins the race: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targeting shame in substance use disorders[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12. 80(1): 43-53.
[25]Villagrá, L.P, M.A. González.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for drug abuse in incarcerated women[J]. Psicothema,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