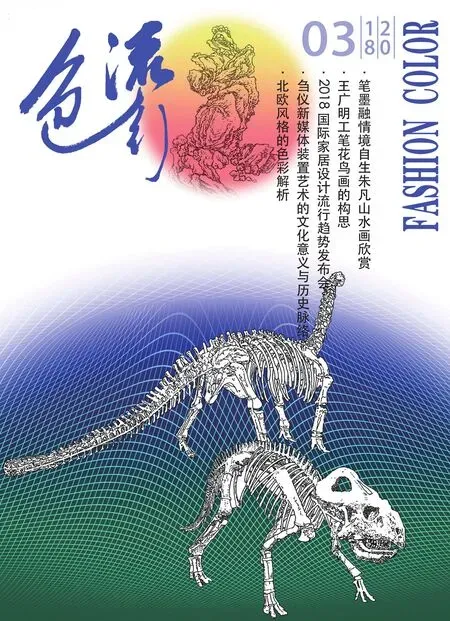如何做到“隔而有味”
——解读冯至《蚕马》中的“转述”与“创作”
2018-01-16张盛长治学院沁县师范分院
张盛(长治学院沁县师范分院)
冯至(1905-1993)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自上世纪20年代初便开始诗歌创作。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于1927年4月出版,铭刻了他在诗歌创作生涯起点之际的摸索与经验,同时也是中国早期新诗的硕果之一,曾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这部诗集分上、下两卷,冯至早期的四首叙事诗,即《吹箫的人》、《帷幔》、《蚕马》和《寺门之前》,均收在下卷。鲁迅先生曾盛赞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不过,除却“抒情”的面相,作为诗人的冯至,可谓十分多面。比如,与《昨日之歌》上卷中幽婉细腻的抒情立场相比,下卷中的抒情长诗便显得冷静而克制。而且,这些叙事诗还有更为明显的特征,亦即这些诗歌并非直接咏叹冯至的个人经历,而是转述已有的经典故事,通过重新叙述“经典”而构架成诗。
这一创作路径让人很自然地想起中国诗歌创作理论中的“隔”。具体来说,“隔”是指诗歌内容不是直接来源于创作者的生活经验,抒情方式也不是直抒胸臆,而是通过化用典故、传说、歌谣,做出拉开距离、看似冷静的陈述,让读者不容易直接从文字的表面“看穿”作者的感情。这就到了考验创作者能力的时候了,优秀的叙事诗可以做到“隔而有味”,在叙事“别”种故事时,还能透露出专属于自己的色彩。同时,读者也可以对照原有故事叙述与诗歌的改编,体会到创作者深沉的情感与取舍立场。冯至的四首叙事诗,或取材于民间歌谣,或改编典籍故事,在现代叙事诗史上“堪称独步”。而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蚕马》,更是经历了两重转述,因而更具解读价值。
改写经典故事:有希望的绝望
叙事诗《蚕马》的故事脱胎于“女化为蚕”的传说,冯至在诗末附有小注:“传说有蚕女,父为人掠去,惟所乘马在。母曰:‘有得父还者,以女嫁焉。’马闻言,绝绊而去。数日,父乘马归。母告之故,父不可。马咆哮,父杀之,曝皮于庭。皮忽卷女而去,栖于桑,女化为蚕。(见干宝《搜神记》)”如果结合干宝《搜神记》中“女化为蚕”的传说来细读《蚕马》,会发现其中有很大的改动,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母”的角色消失了。此处必须引入《搜神记》中的原文来加以分析。《搜神记》卷十四载: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末及竟,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竟种之,今世所养是也。言桑蚕者,是古蚕之余类也。
叙事诗《蚕马》的成形,经由了两次转述,一次是从《搜神记》的原文本到诗末“附注”(“附注”虽然列于诗歌末尾,但在创作过程中却相当于作者的“腹稿”与基础的故事架构);另一次则是从“附注”到骨肉兼具,落笔成诗。可以说,《搜神记》中的传说,“附注”的简要概括与《蚕马》的敷衍成诗,同一个故事有了三种不同的面目。在这一过程中,冯至显然就是那个“造物主”一样的存在。第一步便是调节角色和情节,或增删,或改造,或颠覆,以适应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在《搜神记》最初的叙述中,“母”的角色是不存在的,《蚕马》诗中也未提到“母”,但偏偏在附注中强调了“母”的存在:“母”是许诺者,直接导致了悲剧的产生,而“女”是无语的,只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在冯至的理解中,“母”在《搜神记》中是存在的,而他在诗作中将“母”的角色抹掉。从附注到正文, “母”的角色从“有”到“无”,悄然消失。在《蚕马》中,“女”成为许诺者,具有了话语权和行动能力,摆脱了“母”的控制,从而可以自由选择、自我安顿。于是,整个故事的关注点便转向了个体的真实感情,而非封建礼制的“老故事”。这与“五四”之后,追求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相当吻合。其次,“马”在干宝的文字中,兽性较强,比如“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附注中仍有“马咆哮”之语,但在《蚕马》中,“马”始终是任劳任怨、痴心苦恋、温柔细腻、占有欲不强的形象,相对于“父亲”甚至具有了某种比较健全自由的“人性”。“母”的消失,“女”的凸显,“马”的人化,在角色和情节上的调整都体现了冯至作为转述者的用意。
在《搜神记》和附注中,蚕女和白马自然地分属人和畜两类。人畜之恋违背伦理常识,“马”对于恋人的渴望,只能是违背天地大伦的痴心妄想,因此结局的悲剧性在大家的接受范围内,富有传奇性但在情理之中,作者干宝的主要职责是讲述这个“情理之中”的故事,落实某种伦理观念,而整个故事也配合了读者脑中固有的伦理观念和生活经验。但在冯至的《蚕马》中,白马的身份不只是“畜类”,而是在“亲爱的青年”与“马”的两个身份中变换着、矛盾着、挣扎着。蚕女一人留守家园,日日思念父亲,然而父亲的归日就像“汪洋的大海”,浩渺无期。她自然地把希望寄托给相依为命的马儿,问道:“马,你可能渡我到海的那边,去寻找父亲的笑脸?”由此幻想到“如果有一个亲爱的青年,他必定肯为我走遍天边!”,面前荡漾着这位想象中的“含笑少年”。骏马听到了少女的心愿,踏上征程,姑娘的幻影也随即消逝了。“马”和“青年”,在此都成为孤弱少女的寄托,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蚕女》中“马”和“青年”总是相伴出现的,作者似乎暗示着某种联系,“马”有着蚕女幻想中“青年”的真诚感情,并且成功地履行了“青年”的职责将父亲带回,但是自己“兽”的身份却从根本上否定了“马”追寻的幸福。“刹那间是那个青年的幻影,刹那间是那骏马的狂奔”,两个影子纠缠着,无限接近理想又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悲剧就在这种身份困扰中萌生。“女”和“马”的感情由于“马”的人化而具有某种爱情的性质,而这种“爱情”,天生就是有缺陷的。
最大的绝望,莫过于有希望的绝望。这种处理显然要比简单的人兽处理要深刻得多。“马”的困境具有普遍性,有希望、有深情、有着理想的世界,而自己也具备部分条件,似乎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然后事物从本质上就切断了这种可能性,永远无法完成,我们所做的只能是无限地逼近但永远无法到达,在某一瞬间必然会承受断裂的痛楚。主题的改造,诗境的升华,都是冯至个人气质和精神困境的体现。
冯至是位诗人、学者,更是一名“否定型”的精神斗士。“他是一个真正否定型的精神探索者,他一生都在审省,都在寻找精神的故乡,都在和自己身上的孤独、怯懦作斗争,不断克服,使他总是从人生的一个境界达到另一个境界,正像他自己讲的‘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 ,冯至敏感多思的性格必然会折射在他的写作中,不断地否定,然后再不断地否定这些否定,正像他的《自传》中写到的“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这种否定不是矫情的表演,而是对生命负责任的思考,沧桑而有力,充满绝望而又不放弃努力。冯至一生都有着阶段性的渴望完成的自我,引领着自我奋斗的航向。从诺瓦利斯、里尔克、歌德到伍子胥和杜甫 ,他试图超越自己,抵抗绝望。一层层地脱落,最终形成一个最本真的冯至。《蚕马》是冯至青年时代的作品,此时他已经踏上了“否定之旅”。
诗人的抒情主体身份在《蚕马》中隐匿了,但人化的“马”正是诗人的象征,他们都渴望完成一个崭新的自己,获得满足和超越。然而,他们的共同命运却是在可能性的蛊惑与必然性的失败间挣扎,永远不得圆满。这是命运的残酷,天生的残缺,也是这首诗的动人气质所在,从根本上改变了原作的精神内核,从角色、情节到主体和内涵,都成为冯至自己的叙述。
神话境与人间情:两重叙事的对话
转述仅仅完成了一步,《蚕马》中除了“马”与“女”的动人故事之外,还有另一个故事同时展开,即现实中的“我”苦恋着一位姑娘,感情由“火焰”到“燃着余焰”,从充满希望到归于残缺和不圆满。这两个故事在情感上是“同构”的,只是显隐不同。然而这三段中“我”的叙述绝不是多余的,而是与蚕马的主体故事相互推动,具有互文性与对话性,共同将感情推向高潮。对话是“在各种价值相等、意义平等的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而这种对话性是叙事艺术的生命之所在。” 除了显性的对话之外,这两个平行的结构紧密互动,在角度的不断切换中,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叙事。显性的“我”只是“我”的一部分,现实故事与神话故事共同承载着创作主体的意志与情感,“我”与“马”共同形成了冯至。
首先,现实与神话具有某种同质性,表现着同样的困境。《蚕女》分为三部分,每部分都是从现实中的故事出发,以景物起兴,从“春霞”、“红花”、“火焰”到“柳絮”、“蝴蝶”、“正燃着的火焰”到“黄色蘼芜”、“黑色的燕子”、“还燃着的余焰”,蚕儿从“初眠”到“三眠”到“织茧”,象征着故事的起点、发展和结局,一唱三叹,富有节奏性,反复渲染着悲剧的气氛,配合着主干故事的推进。
其次,现实故事与神话故事之所以能够进行对话和统一,整合到一篇诗作中,“茧”的意象起着重要的作用。“茧”的困境一步步织出,是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挣扎之后最美丽的结果,是现实和神话的共同结局,殊途同归。马儿成为马皮之后,还不放弃对可能性的追寻,它对蚕女哀诉道“我生生世世保护您,只要您好好睡去”,紧接着“马皮紧紧裹住了她的全身”,“月光中化作了雪白的丝茧”。茧是反抗绝望的结果,同时也象征着彻底的结束。现实故事中“燃着的余焰”与神话中马皮最后的温情形成对话,这种真诚是至死不渝的,也是冯至讴歌的对象,同时也体现着冯至的的矛盾:一方面,他肯定爱情和理想世界的存在,而且有着同情之理解,温情和敬意。另一方面,他又对结果有着必然的悲观主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毁灭一方,获得平等的身份,“同化”为“蚕马”,以毁灭完成爱情。伴随着“茧”的形成,两个故事逐步展开,相互呼应。
同时,“女”与“马”的故事在作者的视野中仍是神话故事,最多具有情感上和逻辑上的真实,所以他要在结尾做出附注说明其出处,突出其传说的性质。现实的故事则将这种感伤的氛围弥漫到人间,使希望与绝望的矛盾面向人事。作者在每段之首,都提示着读者在神话故事中寻见人间情怀,在人间情怀中又获得某种超越和形而上的思考,真实性和现实感进一步加强。因此,冯至在早期的叙事诗中不仅是要写一些不是人间烟火的僧侣、尼姑和艺术的守护者 ,去叙述一个虚构的时空进而阐释某种哲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人间情怀,植根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切观照和痛苦思考,体会到了比常人更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因为有了幻想的羽翼,不断地扩展它的边界,因而形成了这些超凡绝世的故事时空。虚构的根基恰恰在于真实,幻想世界来源于人间情怀。
总之,增添一层故事而不显得突兀,而且能与主要故事想成良性对话,同时对读者加以适当提醒,使得整个故事“隔中有透”,有了人间气,己之情。
简短的结语
《蚕马》是冯至在干宝《搜神记》和附注基础之上的二重改编,成功地将经典传说叙述为“自己”心中、眼中和思想中的新故事。他通过角色的重置和调整,将“马”人化,赋予“女”和“马”的感情以爱情的内涵,然而结局却展现出否定型探索下悲剧。“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冯至的精神象征。同时,故事在结构上演变为二重叙事:现实和神话并行不悖,形成对话,相互配合,完成叙事,使整部作品具有了人间情怀。转述乃至拟作在文学创作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转述必然会体现着转述者的身份、立场、趣味、情感和目的,也是最见功力之处。《蚕马》是冯至作为转述者的一次成功尝试,完成了他的“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