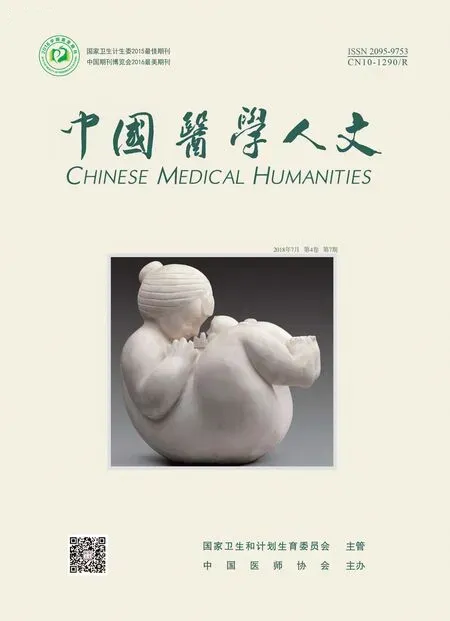生命伦理“有利”原则之重新检讨
2018-01-16何裕民
文/何裕民
今年五月中旬在太原召开的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上,笔者针对生命伦理的有利原则,结合自身临床事例及诸多现实之分析,认为其缺头掐尾,且本身只是功利性导向,故常引起一些混乱、争执与迷茫,需重新进行检讨……一语激起波澜,与会者纷纷展开激辩。笔者应邀就此再作窥探,发些议论,以求证同仁。
医学的“悖论”与生命伦理的“塌陷”
谁都知道,20世纪医学成就斐然。但人们却对临床医学日趋不满,批评声强烈。罗伊·波特在《剑桥医学史》开卷便说:“在西方世界,人们从来没有活得那么久,活得那么健康,医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1很显然,医学陷入了“20世纪悖论”。而这悖论,不仅仅是人们的感受不佳,更体现在多方面:如执现代医学牛耳的美国,半官方的自我反思后认定:美国医疗科技全球最发达;医疗保健投入全球最高(超过发达国家人均2-3倍);期望寿命却在16个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里倒数第一,最短;健康状况更差(且各年龄段的健康状态均差)。该报告共405页,系统引用第一手资料,十分权威,揭示上述明显悖论的报告标题就很刺目:《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健康情况:寿命更短,健康状态更差》2,3。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70年代生命伦理学的诞生,涵盖并超越了传统医学伦理学。按规范的界定:生命伦理学指生命领域的一个伦理框架,评价约束医学领域各种行动的合理性,同时规定了操作者和施受对象的权利义务;生命伦理有著名的四原则:有利、尊重、公正、互助;其中,尤以有利原则最为基础。其核心可简单概括为“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美国医学尴尬现状——高科技、高费用、低效用(人均寿命、健康状态两大主要指标都出大问题),至少说明根本症结不是出在技术层面,而是规范层面。例如,是不是恪守了“不做不该做的事”“做该做的事”之信条?就是说,起约束规范作用的生命伦理“塌陷”了,没起到约束之功,甚至,反向而为之?至少,医学权威韩启德院士的警句:“总之,人们对现代医学的不满,不是因为她的衰落,而是因为她的昌盛;不是因为她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她不知何时为止!人们因为成就生出了傲慢和偏见,因无知而变得无畏,因恐惧而变得贪婪。常常忘记医学从哪里来,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缺乏对医学的目的和要到哪里去的思考……”4这,点到了问题症结,也道破现代医学之“悖论”,很大程度是源自生命伦理“塌陷”。
从后续效果谈起:何谓“有利”
某一行为的真正意义,往往要结合时间因素考量。例如,根据疗效评估疗法。笔者主要从事肿瘤诊疗,认为对规范临床行为的生命伦理,结合临床事例讨论才彰显意义。行医40余载,很多案例对笔者触动很大。
我的一位农村来的研究生,毕业回老家工作多年,家境一般。七年前请我帮她母亲治病。原来,她50多岁的母亲因严重腹胀,查体确诊为晚期卵巢癌伴严重腹水。因为该研究生曾在肿瘤临床侍诊多年,深知晚期卵巢癌之难治。故在北京大医院确诊后,没有告诉母亲实情,毅然带母亲回家,仅行保守治疗。并告诉没有文化的母亲,是因为太劳累所患的“鼓胀”,已让上海老师开方治疗;老师说会恢复的,但叮咛千万别再累了。从那时起,就纯以中医药内服外治。当时我们都以为能拖2-3年就很幸运了。最初几年,她频繁要求给母亲转方调整,后来次数逐渐稀少。今年四月,她又联系我要求续方。因为较长时间没联系,我顺便问她母亲情况,告知一切都好。我很纳闷,反复盯着问:最近检查情况如何?她直说:不敢给母亲查体,反正母亲没觉得不适,也许忘却了自己的病,天天陪外孙玩或打打牌,没有任何病理述说。这,让我陷入沉思:也许,不经意中她真的用了“上上策”:病人不知情,认为是累的;女儿的老师、上海专家给治的,一定不错……轻松中逐步恢复常态,无忧无虑中快乐地活着!这,不是最有益的结局吗?而这结局可是什么“有利”的治疗措施都没有采取啊!
千万别理解为这只是孤案个例,笔者亲历过的类似情况成百上千。也许,举些公众人物更有说服力。先锋派作家马原从肺癌魔爪中逃离后,写下自传体的《逃离》一书5,颇令人深思。嗜烟的他,2008年春因肺上6-7公分大的结节,并伴有前驱症状(剧痛的带状疱疹),被高度疑为肺癌,在病床上他苦思冥想,思考结局:明确肺癌后又怎么样?手术、化放疗,无休止,按常规,治疗后平均能活16个月……他越想越不对。文人的感性促使他大胆决定:“我要逃离”!他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大城市/大医院,回归淳朴的山野生活,在大自然中呼吸着没雾霾的空气,接触阳光,喝着纯净水,自在地活动着,没做任何治疗却日趋康健,且生了孩子……一晃十余年过去了。大难不死促使他写下了《逃离》5,以生死之体验,倾诉着清晰的伦理观。
数据表明:肺癌现是第一大癌,中国每年新发病人84万例,包括很多从不抽烟的女性,北方尤多。笔者在北京有不少女性肺癌患者,不少人属于磨玻璃阴影(GGO或GGN)。如果没有抽烟史(或另一半抽烟史)者,笔者一般只主张先观察,不行,再行手术也不迟。一家有姐妹三人,先后都出现磨玻璃阴影。大姐2008年出现,奥运会前夕急忙赶来上海求治。因为双肺有十余个磨玻璃阴影,部分较致密,有咳嗽但不剧烈,已没法手术,只能保守治疗。但患者不想用化疗与靶向。故嘱其不妨先观察,只行中医药治疗。至今十年,一切皆好。因为心理放松了,天天在公园里快乐地活着,状态似乎比病前更好。其两位妹妹都一样,但结节较少,故更是从容。京城一位文化界大腕,其年过六旬的夫人因咳嗽查体见双肺多个磨玻璃阴影,一个有呈毛刺状(是明确恶性之征兆),且粘到胸膜。纠结于是否亟需手术。因为有身份及地位,遍求名医,除天津一位主任外,几乎所有医师都极力主张尽可能手术,能拿掉多少是多少。笔者力排众议,建议她先观察,因为一则已不可能行根治术了,二则粘到胸膜手术创伤很大,术后多数会出现胸水。夫人不愿意手术,接受笔者意见,仅以中医药调治为主,定期观察,闲着周游世界。不久前笔者去北京,她兴冲冲拿着刚拍的CT片,高声嚷道:五年整了,拍片医师说肺内情况很好,病灶没任何变化。而她这五年的生活质量则是近几十年来最好的,因为既未行创伤性治疗,又减负荷换了一种活法,自在多了。
类似案例很多。在此陈说并不想炫耀诊疗水平,只是强调这些诊疗同样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如性质/或后果未明确时,不妨先行观察,避免盲目创伤所致损害;治疗后果利弊难辨时,不妨缓行激进措施,且力争活着,“以平为期”;这些措施背后,也有生命伦理引导,也许,此后果是最“有益”于患者的。
动机“有利”,结局不一定“有益”
为清晰界定伦理的指导性和约束性,现代生命伦理学在有利原则基础上,细分出“有利”及“无害”等,以便临床掌控。然而,即便如此,临床依旧难以具体评定其伦理价值。上述各真实案例在“有利”伦理原则引导下,完全可以/而且通常都会更多地做出另类抉择:如对已确诊为晚期卵巢癌者,都会尽快实施化疗方案,或再配合姑息手术。结果会怎样?其实大多数肿瘤医生心知肚明——通常,晚期无法手术的卵巢癌患者中位生存期2.5-3.5年。而且,一定伴随着十几次/几十次痛不欲生的化疗。不止一位医生对卵巢癌患者直言:“只要你想活着,就需要不断化疗……”潜台词是,除非死了才能免除。肺癌谁都知道当先手术,手术不成可用化疗或靶向药……如此诊疗指南指导下的各项积极治疗措施,“创造”了中国肺癌患者平均16-17个月的中位生存期之“奇迹”。当然,这些都符合伦理“有利”原则的!但你也无法反驳笔者建议他们所接受的姑息性治疗方法加观察(甚至只是苟且活着)违拗了伦理基本原则。因为多年后结果表明:如此姑息苟且,也许综合且长期效果是最有益的,那可是结果导出的结论,最有说服力的啊。
可见,笼统强调生命伦理的“有利”原则,既可导出全然不同的治疗对策措施;而且很多情况下动机“有利”,治疗结局(包括长期综合效果)不见得“有益”;况且时常还需付出极高的身心代价及巨额成本。前面提及的20世纪医学之所以有“悖论”,这层因素也需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我们疑虑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尴尬,破解对策又何在。或换句话说:同为有利原则,显然还受背后的价值尺度之掣肘。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背后的价值尺度是唯一的吗?如果不是,又还有哪些,它们的价值取向何在,意义及适用范围如何,落实到临床治疗,又应该怎样具体抉择呢?
确立“基准”和基于效果的评估,令“有利”原则有前后掣肘
众所周知,行动受动机支配,动机为价值尺度所左右,后者受制于自然观等更高层次的认知系统。显然,生命伦理的“有利”原则本身并没错。但它更多是功利性的,并非价值尺度,多数情况下充其量只是种表浅的行为动机;其背后还受制于相应的价值观,以及对自然/世界本然状态之基本认识;后者也就是通常说的自然观/世界观。可以说自然观、价值观、伦理观形成了完整的认知行为链。多数时候,自然观是价值观基础,价值观是自然观延伸,伦理则受制于这两者。
笔者落笔写初稿时,美英法三国正因“化武疑云”而对叙利亚进行狂轰滥炸。叙利亚是世界文明最早的发源地,后世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粮食畜牧业主要驯化地。落得此番境地,令人唏嘘不已!我们不谈国际政治,也不论地缘势力角逐;仅就事论事——按美英法的价值观,其如此野蛮打击,自有其自洽的伦理“有利”逻辑:站在他(基督-神教)立场,“我”是天下唯一正确的;异教是另类,是错的(自然/世界观);有我没你(价值观);你有罪(哪怕只是可疑),狂轰滥炸就是对的/有利的(伦理观)。只不过这“有利”,是美英法的人利益,还是叙利亚人的安居乐业,又当别论。其实,若干年前美国轰炸伊拉克,举国上下赞同,同出一理。这,用来说明“三观”间的隶属关系,还是比较贴切的。
其实,验之临床,可以说所有医师都认为自己最初给出的治疗措施是“有利”的,对的。没有人会承认是不利的,错的。哪怕是严重的过度治疗或错误措施,也都可以借此以搪塞。而且,别人无法据理反驳。就像是无法以佛教教义反驳基督教一样。因此,缺头掐尾地讨论有利原则,显然不得要领。而这个“头”,需建立最低“基准”线;这个“尾”,相对好说些,就是“基于效果”的评定。
这个“首”“尾”,很多人会联想到循证医学。然而,也许创立者初衷的确如此,但学界已发出严肃的声音:“循证医学体系正走向崩溃,它常常迫使医生做未必正确的事情”。“过度诊疗之风愈演愈烈,循证医学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6循证医学讲究的是证据,但“统计学有句名言:只要你拷问数据,数据就会招供”。国外有两本畅销的名书:《数字是靠不住的》和《统计数字会撒谎》,作者诙谐地说“统计数字就像美女身上的比基尼,露的部分引人遐思,没露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6。因此,循证医学证据作为“首”,不太可信;作为“尾”(评价尺度),事件已发生,对该患者来说于事无补,但聊胜于无吧。
“有利”原则的进一步“追问”
我们认为伦理的“有利”原则充其量只是种动机选择。且其过于原则性和笼统性,在缺乏具体约束细节情况下,人们对何谓有利之理解,可大相径庭。就具体医疗行为言:有利原则只是方向性指导,尚不能提供具体的行为指南。而且,动机之“有利”,结果不一定“有益”(化疗对胰腺癌缩短寿命就是例证7),短期之“有利”(如幽门螺杆菌用抗生素),不一定长期后果“有益”(有证据表明:HP乱杀是后续很多病的根源8),局部之“有利”(如过去时兴的动不动因炎症而切除扁桃体、阑尾)被证明对全身综合状态不见得“有益”,临床指征的“有利”,不见得就是患者自我感受之“良好”(空鼻症患者频发杀医事件是反面教材),故对生命伦理的有利原则,需深刻且深入地追问及反思。
笔者认为:贯彻伦理“有利”原则的前提,首先需考虑站在谁的立场:谁有利,医,患,还是家属,厂商?谁(医生还是患者)做出的抉择?是以何者为尺度或准绳做出的:是“自然”而本原性的,还是“科技”而人为的(对此另文细究)?底线何在?尺度如何把握?
其次,需考虑时间及疾病性质。急病(危急状态)相对单纯,保住他的命就是有利,且绝对是以医师为主导,甚至来不及征询患者意愿!但如今面对的大都是慢病,治疗决策没那么急迫。《纽约时报》2011年曾配发社评强调:即使患了癌也无须匆忙走进手术室9!我们倡导:刚确诊为癌也不妨“一停、二看、三通过”,以便有充裕时间权衡,综合评估9;可听听多方意见,确保决策更理性;可让患者从容捋出头绪,听听内心真实意愿。如此,才能尽量做到遵循不伤害/或不加重伤害原则,包括兼顾患者长期、综合效益最佳,自我感受良好……
以癌症临床为例,笔者自认为下列情况时可先如此试行:无奈时,规避加重损害原则(积极调整为主,期待并力争“雨过天晴”);恶果未明了时,努力争取伤害最小原则(别急吼吼地一次次创伤性治疗不已);很多情况下,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师,不妨先行保守治疗,同时严密观察;两难选择时,优先考虑长期综合效益最大化原则,而不是刻板地死守指南;最积极、最有效的措施,是调动自我内在“本然”力量(尊重“本然”原则)。因为笔者认为自然(身体也一样)充满“智慧”,本然存在着康复力(就像希波克拉底的“自愈力”),笔者针对癌症治疗阐发了每个个体内在的“抗癌力”,写下了《抗癌力》10一书。
在人为与本然,科技与生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且尽可能把后者放在重要考虑的位置,努力创造有利于本然(包括自我身体)恢复的生态环境……
这些,体现着生态医学原则与思想;也许,我们需要呼唤医学的生态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