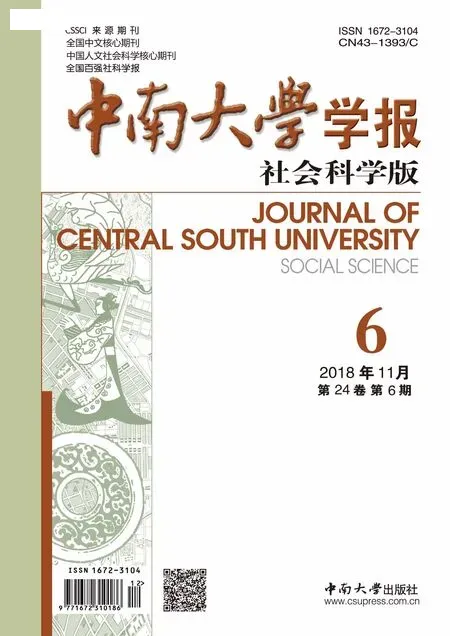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取向的二元统一
2018-01-13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8;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一、引言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发展文化软实力是加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1]。政治话语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政治话语的外宣翻译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因此,探索适合政治话语的外宣翻译模式,对于加强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伴随着近年来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研究也日益成为我国译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学者们主要根据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实践和经验对相关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进行了探讨。如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结合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实践提出了“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并强调译者应按照国外受众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化习惯进行翻译[2]。南京大学博士后杨明星通过对比分析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方针的不同译法,阐述了政治话语翻译中应遵循“政治等效”的翻译标准[3],而不宜盲目借用西方媒体的表达。新华社高级编辑王平兴从几个政治术语的翻译问题出发,探讨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的政治考量问题,指出政治考量要高于语言考虑,译者不能为了顺应目的语的表达方式而损失原词的政治内涵[4]。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鲍川运结合“中国关键词”的翻译过程指出,政治话语的翻译既要注重原文的政治准确性,忠实于原文的政治内涵,又要照顾到受众的语言文化习惯,使用地道的英语表达,使国外受众易于接受;当语言的地道性与政治的忠实性相冲突时,选用表达以忠实原文的政治内涵为主[5]。中央编译局资深翻译贾毓玲通过对《求是》英文翻译案例的分析,从话语构建和话语翻译两个角度探讨了提高原文的外宣适应性和译文的连贯可读性的翻译手段,从而构建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6]。已有研究成果为我国政治话语的外宣翻译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反映了两种基本的翻译取向:或采用目的语取向,或采用“以我为准”的取向。但总的而言,目前的研究理论性探究较少,多是经验性的总结,且缺乏系统性。为此,本文结合我国权威机构的政治话语英译实践,探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取向的二元统一模式,认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时,在语言层面要侧重目的语取向,在文化与政治层面要侧重“以我为准”取向,两种取向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实践。这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符合我国外交政策的现实要求。
二、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取向的二元统一依据
英国翻译家纽马克(Newmark)曾经谈到,翻译方法的选择取决于文本的类型。他认为,“呼唤型文本”的功能核心是读者,其目的是要“唤起”读者去“思考”,去“行动”,强调读者的认同,翻译此类文本应以目的语为导向,在保证译文与原文信息一致性的基础上根据目的语的表达特征对原文作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注重译文在目的语群体中的可接受性;“信息型文本”的功能核心也是读者,重在向读者提供信息,因此翻译时也应以目的语为取向,方便读者理解并接受原文的信息;“表达型文本”的功能核心是作者,作者的个人语言风格和原文独特的韵味构成了翻译的中心,此类文本的翻译应尽可能使用贴近原文形式的表达,忠实再现原文的意义和风格,彰显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异域文化色彩[7]。
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翻译理论对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的政治话语常常是三种文本功能兼具。许多政治文献,如党政文献、政治人物的讲话,一般认为属于表达型文本,作者在文本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作者的个人语言风格、话语目的和原文独特的韵味构成了文本表达的要素。根据纽马克的理论,此类文本的翻译应侧重“以我为准”的取向,使用尽可能贴近原语的表达形式,以彰显原文的独特风格。此外,政治文献还往往兼有“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的功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是为了对外宣传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让国外受众了解我国的发展现状,了解真实的中国,从而认同中国的发展理念,由此在国际社会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所以,政治话语外宣译文具有显著的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为了保证信息的传播效果,同时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还应以目的语为取向,让目的语受众接受译文内容,使用符合目的语语法规范和表达惯例的语言形式,使译文语言通顺流畅、明白易懂且具可读性,译文的语言表达符合目的语受众的期待。因此,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坚持以目的语为导向和“以我为准”的二元统一的翻译取向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
从我国外交政策的现实情况来看,坚持二元统一的外宣翻译取向也是必需的。加快实施国际话语权战略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话语的影响力与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对外政治话语体系还远未达到国外受众想了解、愿接受的程度。因此,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亟待加强。习近平同志曾多次提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关键是要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既要注意话语体系的转换,运用国外受众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宣传当代中国的价值理念,又要融入中国特色,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对外话语体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倾听中国声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经发行,即好评如潮,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畅销书籍。该书的译稿定稿人王明杰在谈及翻译要求时说到,译文既要忠实原著,译出原文风格,也要让国外读者看得懂,有可读性。作为该书译者之一的刘奎娟认为,对于许多中国特色的词汇,中国译者肯定是把握得最准确的,由他们来译可以保证翻译忠于原文、符合政策,由外国专家来润色语言,可使译本易于被国外读者理解和接受。可见,在语言层面侧重目的语翻译取向,在政治与文化层面侧重“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将二元取向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实践是符合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工作现实要求的。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日趋完善,让国际社会真正听到中国的声音。
三、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取向的二元统一实现
“以我为准”和以目的语为取向是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取向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各有侧重,辩证统一,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实现其二元统一。
(一) 语言层面的翻译,侧重目的语取向
1.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侧重目的语取向的理据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目的语读者意识一直是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西方许多著名学者基于目的语读者意识提出了一些影响很大的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最初将读者反应纳入翻译研究的是美国翻译家奈达(Nida)。他认为目的语读者是翻译的服务对象,因此,译文质量的评判标准应该以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为主[8]。此后,以姚斯(Jauss)和伊瑟尔(Iser)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也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关注读者的审美经验。该理论认为,作品的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体现出来[9]。接受美学充分承认读者对作品意义的作用,给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翻译过程中应对译文读者审美特征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审美特征,因此,译者应熟悉译文读者的语言表达方式和阅读期待,使用译文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进行表达,否则,译本的价值将很难实现。上世纪 80年代,英国翻译家纽马克将所有文本按其功能分为三大类别: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各类文本可采取的翻译方法。他认为,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均强调目的语读者的主体地位,应使用符合目的语规范的形式来表达原文意义[10]。为了使译文容易为目的语读者接受,有时甚至要对原文进行改写。上述理论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文本中心范式,引导译者更多地关注目的语读者。可见,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侧重目的语取向是有一定理论基础的。
在国内,许多外宣翻译专家从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现状出发,并结合自身的翻译经验,也提出了侧重目的语读者取向的必要性。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对外宣传我国的发展状况、内外政策和价值理念,以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同,构建积极的中国形象,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政治话语外宣译文的表达是否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对我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黄友义认为,外宣翻译只有超越了简单的字面对应,使用外国受众能够理解的表达方式,才能真正传达原文的含义,实现对外传播目的[11]。贾毓玲通过反思《求是》中一些重要政治术语的翻译,指出译者应在一定权限内尽量使用准确地道的外语表达,从而消除外国受众的理解障碍,提高译文的通透性和域外接受度,增强我国政治话语的传播效果[12]。要让目的语读者准确理解译文信息,译者首先应设法化解英汉语言在语法规范、表达特点等语言层面的差异,以目的语为导向进行翻译,使译文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
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二者在语法规范和表达特点上有显著的差异。在汉英语言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无视差异和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而一味追求与原文的字面对应只会使译文晦涩难懂,让目的语读者产生抵触情绪,影响译文的接受度和对外传播效果。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融通中外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13]。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翻译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与译者在语言翻译层面侧重目的语取向不无关系。可见,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有必要侧重目的语取向,按照目的语的语法规范和语言表达特征进行转换,超越中西语言障碍,以实现与国外话语体系的对接,增强对外传播效果。这既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也是实践经验的启示。
2.语言层面的翻译侧重目的语取向
王平兴主张,对外宣传所用的语言形式必须以目的语受众为主,也就是说外宣翻译在语言形式上应该以目的语为取向,这样既可以达成政治话语对外翻译的目的,又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14]。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译者应充分考虑两种语言的差异,顺应英语使用惯例,采用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进行翻译。
受汉语表达的影响,现有的中国政治话语在译为英语时往往存在不合语法、逻辑缺失、表达累赘、用词欠妥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妨碍目的语受众对译文信息的有效编码。因此,在翻译中国政治话语时需顺应英语语法规则和表达特点,在遵循英语语言惯例的前提下合理运用多种翻译方法进行翻译,使用目的语受众熟悉的语言进行表达,以提高译文的地道性和可接受性。下面笔者将从遵循英语语法规则、简化表达、区分词义内涵、增加信息注释、拆分长句等五个方面探讨以目的语为取向的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方法。
第一,遵循英语语法规则。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应遵循英语语法规则。汉语语义兼容性强[15],词语搭配方式灵活,英语语义兼容性则较弱,搭配有一定的限制。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译者应遵循英语惯用的搭配方式,保证译文的准确性。我国政治话语中包含大量的数量结构,如“两个一百年”“三个代表”“四个全面”等。汉语数量结构槽的语义兼容能力特别强,无论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都可装进数量结构槽。而英语中数量结构的搭配限制则比较强,数词后面一般只能跟名词性成分。在翻译数量结构时,译者应以英语搭配特征为导向,使用能被英语受众所接受的搭配方式。如 “四个全面”的翻译,国内一些双语网站直接将其按照原文的字面形式译为“Four Comprehensives”,这在译文读者看来可能不仅离奇,且不达意,因为英语中并没有类似的数字化表达。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译者使用英语中常见的“数词-pronged+名词”结构来表达,将其译为“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不仅顺应了英语数量结构的搭配规则,同时通过在数词后面添加-pronged这一英语中常用的表达形式译出了原术语的内涵,表明四个“全面”是相互依存、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16]。因此,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译者应遵循英语的语法规则,使用英语受众熟悉的语言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使译文容易被英语受众接受,达成对外宣传目的,主动掌握话语权。
第二,简化表达。
英语和汉语的行文风格有较大的差异:英语表达崇尚简洁精炼,文风质朴,追求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和实用性;汉语则讲究声韵对仗、节奏平衡,为渲染气氛、强调语气,常使用强调副词和四字结构[17]。我国政治话语中常用到一些强调副词和四字词语,这种表达风格与英语迥异。因此,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过程中,应根据英语表达特点,作适当的删减,简化表达。例如:
原文(1):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译文(1):We will unite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lead them to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in the drive to secure the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原文(1)使用强调副词“奋力”,旨在突出党带领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坚定决心。如果将该副词译出,不仅不能强调语气,反而会弱化表达,显得累赘。因为在英语受众看来,“夺取”一词已包含“奋力”的语义内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语气强调副词的使用非常普遍,如“大力”“牢牢”“紧紧”等。在外宣翻译中,这些副词基本都省略不译,以顺应英语简洁精炼的表达特点,贴近英语表达风格。
第三,区分词义内涵。
由于中英语言文化的差异和社会背景的不同,英汉两种语言中有的词语或表达方式尽管字面意义相近,词义内涵却相去甚远,它们所引发的文化联想也截然不同。这就要求译者熟悉英语中相关词语的词义内涵,能够对两种语言中一些字面意义相近的词语进行区分,选择内涵最贴近汉语政治术语的英语词汇进行翻译。“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政治术语,官方最早提供的译文是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随后,国内外宣机构又相继提出了两种译法: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和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尽管汉英词典中针对“命运”一词给出的英语词条的确包括“destiny”,但“命运共同体”这一术语中“命运”的内涵与“destiny”并不一样。现代汉语中“命运”有两个主要的含义:①指天命,如生死、一切遭遇;②比喻发展变化的趋向。“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其提出旨在树立和谐的人类发展整体观,可见这里“命运”一词实则比喻美好的未来,带有积极意义[18]。而英语中“destiny”一词带有一种宗教色彩,指天命、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带有中性色彩。故此处以“destiny”来译“命运”似有不妥。而shared future通常含有积极、正面的语义内容,在英语母语国家的正式文件中也经常用到。中共十九大报告的译者采用的是最后一种译法: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符合英语母语使用者的表达习惯。
第四,增加信息注释。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外宣传我国的政策纲领、政治主张等方面的信息,这就要求译者应对国外受众可能难以理解的语言内容增加相关的注释信息,以排除受众在语言理解上的认知障碍,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黄友义认为,好的外宣翻译应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和信息需求对原文进行加工,适当地增加注释内容[19]。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许多政治术语的表达含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如果完全直译,国外受众可能不易理解。因此,译者们通过增添注释的方式将必要的背景信息融入译文中,对原文相关表达进行补充说明,这有助于国外受众的理解。
如“坚持大扶贫格局”这一政治术语如果完全直译,国外受众可能不太理解。因此,译者使用分词短语对“大扶贫”进行了解释说明,将其译为“continue to advance poverty reduction drawing on the joint efforts of government,society,and the market”,使国外受众接收到准确的信息。
由于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存在较大的差异,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形式如果直译很有可能引起国外受众的误解,难以实现外宣翻译的对外传播功能。因此,译者应以国外受众的认知背景为导向,采取灵活的方式增加相关注释信息,以便于受众理解和接受。
第五,拆分长句。
与英语相比,汉语句子的信息容纳能力较强,一句话可以包含多层意思,长句使用频率较高,有的句子就是一个段落。在政治文献中,尤其如此。经常一个句子套着另一个句子,一句话多达数百字。而英语的句子结构一般比较简单,句子短小精悍,往往是一句话只包含一层意思,即使表达相对复杂的意思,句子长度也很有限,一般不超过五十个单词,且英语长句使用并不常见。因此,为了使政治话语的外宣译文方便国外受众理解,译者应恰当拆分长句。例如:
原文(2):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译文(2):We will pursue a more proactive,open,and effective policy on training competent professionals.We should value people with talent,be good at identifying talent,have the foresight to employ them,be earnest to keep them,and welcome them into our ranks.This will better enable us to attract bright people from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Party and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o join us in pursuing the great endeavor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We will encourage and guide people with talent to work in remote poor areas,border areas with mainly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and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as well as in communities and on the frontlines.We will work to foster a positive environment in which everyone wants,strives,and is able to excel themselves,and can do full justice to their talents.With this,we aim to see that in every field the creativity of talent is given great expression and their ingenuity and expertise flow freely.
上面的译文将原文的一个长句拆分为六个独立的句子,由于第三个句子和第六个句子与前面的句子存在紧密的关联,因而分别使用代词 this和过渡成分with this承上启下。这样,在化长句为短句的同时,也体现出英语的层次,避免了拆分长句可能导致的连贯缺失问题。
中国人对长句的使用习以为常,但英语世界的读者却觉得难以接受。中央编译局的外国专家 Graham Faulkner曾经提出,“能断则断,不能断也要想方设法去断”应作为处理汉语长句的一般原则[20]。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译者们深刻理解英汉语的这一句法差异,在翻译时以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句子表达特点为导向,仔细分析句子层次,化长句为短句,利于英语读者理解。
(二) 文化与政治层面的翻译,侧重“以我为准”取向
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目的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增强话语权。要实现这一目的,在外宣翻译的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应该侧重“以我为准”的取向,将中国的价值观念完整介绍出去,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
中国政治话语一般具有鲜明的汉语言文化特色,其中有许多来自汉语中的成语、俗语和典故,还有很多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表述。在翻译这类政治话语时采用“以我为准”的取向有助于保留汉文化意象,同时有利于对外传播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念,满足国际受众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和价值理念的愿望。因此,译者应将我国政治话语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和政治内涵原汁原味地介绍给国外受众,而不是改头换面,套用英语中字面意义相似的表达,或是盲目借用西方媒体的表达方式,翻译成文化内涵或政治内涵失真的符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提出了“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的原则。该《公约》指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关系人类文明存续的根本问题,是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尊重、和平共处的基础[21]。可见,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也是符合文化多样性原则的。
1.侧重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传播中华文化
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采取“以我为准”的取向翻译文化信息是可行的。由于近年来我国外宣力度不断增强,某些直译成英语的政治术语已为国际受众所接受。如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再次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对外报道的过程中被直接翻译为“Two Centenary Goals”,《经济学人》《今日美国》等国外主流媒体也沿用了这一译法,可见,“两个一百年”的概念已为许多境外受众所理解。事实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时代》等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中对中国特色词句均采取由汉语直译的翻译方法,这样做并不会增加国外受众理解上的困难[22]。这也表明了在对外翻译政治话语时采取“以我为准”的取向是可行的。因此,译者应在保证语言地道性的基础上遵循“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传递政治话语中包含的汉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坚持必要的文化自信,并通过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宣传介绍中国政治话语,使中国政治话语得到广泛的接受。
使用中国历代名言及成语典故是我国政治话语的独特语言风格。这些成语典故和名言名句生动形象、内涵丰富,体现了汉语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使用不仅有利于说话者意图的形象表达,而且保留了汉语文化意象。中国领导人讲话中一贯有援引历代名言名句的传统,这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语言风格和个人魅力。在翻译这些名言名句时可大胆地运用中国英语,在忠实于汉语意义的基础上保持形式上的对应,展示领导同志独特的文风和魅力,增强话语感召力。2013年3月,李克强总理首次会见中外记者,一句“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传递出其锐意改革的决心。当时的现场翻译版本为:Talking the talk is not as good as walking the walk.尽管这个习语能够表达原句的基本意思,并且这种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更容易为国外读者所理解,但如此转换为英语后,汉语原句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已消失殆尽。实际上,就在国内翻译工作者千方百计地探寻在语言上、文化上更接近英美国家受众接受的表达的同时,外媒却更乐于原汁原味地展现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表达。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处理李克强总理用到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这句名言时,并没有使用英语中常用的习语,而是直接将其译为:“Screaming yourself hoarse”was not as good as “rolling up your sleeves and getting to work”.这种直译加注释的翻译法不仅译出了原句的意义,同时又保留了原句独特的表达形式,在英语表达中融入了中国元素,丰富了英语表达,有助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对外传播。黄友义认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展示汉语言文化魅力是现阶段对外翻译的一项重要任务[21]。当今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和发展思路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中国古代的名言诗句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和文化特色,具有独特的影响。在翻译这些名言诗句的时候不可仅仅满足于意义上的忠实,还要尽量做到在形式上与原句保持一致,充分尊重国际受众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愿望,恰当运用中国英语进行翻译,展示中国领导人的语言魅力,呈现中国元素,使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
2.侧重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凸显政治意识
政治性是政治话语的重要属性。政治话语的翻译不仅要求语言准确,更注重政治准确性。政治准确性要求译者必须注意把握用词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分寸。译者在翻译政治话语时,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坚持中方的政治立场,坚决抵制外媒在言语上的政治攻击。在外宣翻译中坚持用本国文字及称谓来指代本国事物,不仅有助于宣传本国语言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同时也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扩大政治影响,维护国家利益。在对外交往中,经常会涉及一些有关领土、主权等政治性较强的内容,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准确传达其政治含义。比如,在对外宣传“南沙群岛”时,就不宜将其翻译成西方人所称的“the Spratly Islands”或“the Spratlys”,而应该采用汉语拼音翻译成“Nansha Islands”,以表明我国的国家主权利益。实际上,利用本国文字及惯用称谓来表达本国事物和主权的做法已成为国际惯例。因此,在我国政治话语英译过程中,译者应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凸显一定的政治意识,坚持用中方称谓来表达政治诉求。
盲目借用英语现成表达是目前我国政治话语英译中的一大问题。西方媒体话语往往打上了自身意识形态的烙印,是为其左右国际舆论、掌握话语权服务的。而国内很多英文媒体尚缺乏文化自觉意识,为了迎合所谓的国际话语规则,直接套用西方媒体所用的表达,而不探究其使用根源,这样,不利于我国的话语权建设。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首次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大国关系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主要特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理念、新主张,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将“新型大国关系”译为“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23]。一些国内英文媒体也纷纷仿效此译法,殊不知“power”一词与习主席所强调的“大国”并非一回事,“power”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控制他国权力的国家,其标准是强权政治、军事实力和战争能力[24],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强权政治或霸权主义。西方媒体将此术语中的“大国”翻译为“power”是别有用心的,不利于国际受众准确地理解我国的外交立场。
作为对外介绍我国政策纲领的官方网站——外交部英文网站,基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以“major country”译“大国”,符合新型“大国”外交理念和和平共处、合作双赢等独特的价值观,有别于西方国家追逐权力的“大国观”。
现阶段,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它们的对华报道中存在着很多歪曲事实的成分,国际社会对中国仍然充满着诸多不解。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翻译工作者如盲目地借用外媒所用的表达,就会导致国外受众难以听懂中国声音。因此,为了让国外受众了解真实的中国,获得“原汁原味”的中国关键信息,在翻译政治话语中一些体现政治内涵的词句时,应该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并加强对外宣传,使国际受众准确理解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
四、小结
“融通中外”是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加强文化软实力的系列讲话中,特别强调融通中外的重要性。融通中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国际社会准确理解原文所传递的信息,尤其是中国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追求,内容上不能有偏差。因此,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坚持目的语取向和“以我为准”取向的二元统一是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提高我国对外话语的可接受性、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必然要求。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时学所指出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本质就是中国如何对外“发声”,既要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积极地对外宣传中国成就,传播中国理念和中国文化,又要注重与国外话语体系的对接,最大程度地弥合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25]。由于中国政治话语反映了党和政府的治国理政理念,因此其翻译既要坚持目的语取向,顺应英语语言规范和表达特点,与国外话语体系对接,又要采用“以我为准”的取向,忠实地传递政治话语的文化信息和政治内涵,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就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而言,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用这两种翻译取向,将其统一于翻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