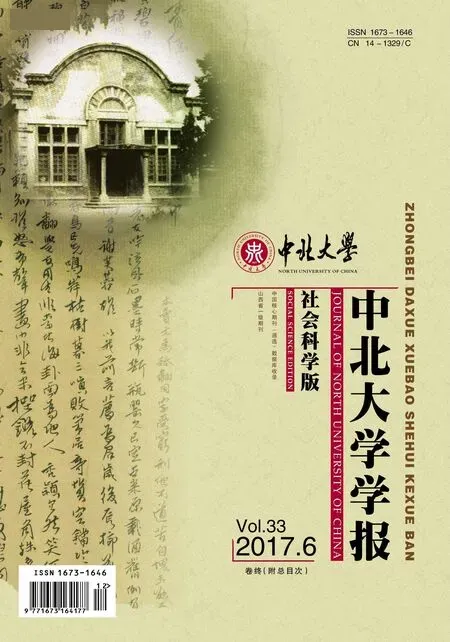自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公共交往之现代化转型
——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
2018-01-07洪榕蔚
洪榕蔚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文史教研部, 四川 成都 610000)
自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公共交往之现代化转型
——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
洪榕蔚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文史教研部, 四川 成都 610000)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 他主张通过语言的有效沟通来构建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 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主要作用于行动者之间, 交往的工具是语言, 语言的作用在于理解, 即通过运用充足的论据说服他人, 最终达成行动者之间的共识。 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转向, 自媒体时代下政府与公民的公共交往实现现代化转型, 需要从交往空间、 交往关系、 交往方式三个维度来考量。 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对当下我国政府公共形象的建设、 行政职能的转变及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正确行使、 参政热情与文化素养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 公共交往; 自媒体时代
1 哈贝马斯的理性范式转向——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
工具理性和感性关怀是衡量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社会的整合需要二者的协调与平衡。 然而, 由于站在工具理性与人文关怀、 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立场,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 阿多诺等对工具理性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哈贝马斯在研究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批判理论、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理论、 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以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之后, 并没有完全排斥现代理性, 而是在扬弃了前人的观点后, 提出现代社会的理性既是批判的又是可规范的论断。 在他看来, 现代理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 现代社会关系的构建, 既不能走向工具理性的极端, 也不能单纯依赖于人的主体意识, 二者应努力实现共存与融合。 哈贝马斯在工具客体与人的价值主体之间, 搭建起一座桥梁, 将两者进行沟通并进行规约, 这座桥梁就是交往理性。 由此, 他的理性范式转向了交往理性, 这种转向可以从认识论、 方法论和空间转向三个维度来考察。
1.1 交往理性的前提认识: 客体性与主体性对立转向主体间性
古希腊理性集中体现在对客观世界的关注, 认为世界的本源在于实体形式的物质, 经院哲学将本体论转向了上帝, 客体理性占据了人们的世界观, 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下, “我”这个主体尚未引起重视。 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 人的理性获得启蒙, 它所开启的现代社会最初是以承认人的理性自由发展为前提的, 但是随着它逐渐被资本理性所替代, 人的理性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成了对人进行控制的理性, 甚至企图对“他者”进行征服, 成了为确立理性霸权地位而绝对排他的理性。 主体理性只关注自我, 而忽视了他者的“在场性”, 在人人皆为真理、 皆为衡量价值尺度的逻辑中, 永远无法自愿达到共识, 最终背离了文艺复兴初衷。 到了后现代主义, 更是片面强调主体认知和价值判断,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去中心化’的立场有其合理性, 也符合日益分化的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但是这意味着社会很可能走向相对主义、 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面临解体之虞。”[1]对主体性的强调原本是为彻底否定工具理性, 摆脱科技对人的“奴役”, 但这种否定到最后却过犹不及, “我”这个主体成为他者眼中的“他者”之后, 也不复“存在”了。 资本的现代性取代了启蒙的现代性, 人们刚摆脱了科技物质客体的剥削, 又陷入了人的非理性的奴役之中。
主体间性的提出, 摆脱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状态。 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主客体关系, 而是在交往和对话中共在; 主体间性在涉及自我与他人、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 不是把“我”看作原子式的排他性个体, 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 因此, 可以看出主体间性并不是反主体性、 反个性, 而是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和超越, 是个性的普遍化和应然的存在方式。 主体间性的提出给了哈贝马斯很大启发。 在哈贝马斯看来, 主体间性在实践中体现为交往, 它是在交往的双向互动中达成的“公意”理性, 进而使得在商讨和对话中制定出社会规范成为可能。 主体间性更像是一种平衡主体与客体、 主体与主体、 此在与他在之间关系的张力, 最后达到共识, 实现社会的有序整合。 以主体间性作为交往行动理论的前提认识和逻辑起点, 社会整合的基础就在于这样一个过程: 处在公共领域的行动者之间既可以进行交往, 也可以发展相互间的理解和认知。
1.2 交往理性的方案: 意识哲学范式转向语言学范式
意识哲学范式将主体性捧到了本体论的高度, 因而也导致它的价值主体成为了具有排他性的认知个体, 后现代主义者更是将主体的非理性发挥到了极致, 背离了建构现代性的目的与初衷。
实现现代性不能仅仅依靠个人头脑中的主观意识, 哈贝马斯看到了这一点, 故在现代理性实现方案的制定中, 他开始转向了语言学。 语言, 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 以及对此时此地的直接感知形成的经验的距离化媒介。 它必然意味着主体间性, 或者交往”[2]189。 语言学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 在公共领域, 对语言的理性使用是实现交往理性的主要手段和工具。 哈贝马斯构建批判理论的目标就是揭示造成失真交往的条件以及那些阻碍理想语言情境得以实现的条件。 也就是说, 哈贝马斯想要构建这样一种理想社会: “在那里行动者能够不失真地进行交往, 获得彼此间主观状态的认识以及没有外界强制力和威逼的争论来公开调解他们的分歧。”[3]202交往理性下的语言行动应符合三种效度: 第一, 陈述是真实的, 或参照外在客观世界的陈述是真实的; 第二, 有关既存规范的情景或社会世界的陈述是合理的; 第三, 陈述是表里如一的, 应显示行动者意图和经验的主观世界。 “基于理性的共识, 即主体间可批判性的效度要求, 通过协商对语言的情景定义达成理解。”[4]137由于语言是交往、 互动的基础, 也由于社会最终要靠交往和互动来维持, 所以通过实现交往过程的内在动力机制, 创立一个较少限制性的社会系统便指日可待。
1.3 交往理性的空间转向: 公共领域与日常生活世界的重建
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在于他要建构和发展一种允许重建日常生活意义和信任机制的理论视野, 这一目标将通过进一步理解行动者在何种场域下沟通、 互动和发展符号意义而得以实现。 行动者之间的交往既离不开一定的公共场所和意义世界, 又不断创造着新的公共场所和意义世界, 即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世界。
公共领域是一个社会生活领域, 介于国家和个体公民之间, 是可以将国家意志和公民原子化的诉求实现协调的过渡空间。 在那里, 人们可以讨论有关公共利益的事情, 可以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和争议而不必求助于传统教条及外在强力, 可以通过合理的争论来解决观点的分歧。 哈贝马斯从历史观层面追溯了公共领域的产生, 在18世纪的西方社会, 当时各种公共讨论场所(如俱乐部、 咖啡馆、 杂志和报纸等)像雨后春笋般涌现, 公共领域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交往的物理场所, 同时, 愈加频繁的交往也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产生的交往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
交往理性在公共领域中得以实现需要以语言为媒介, 而语言使用的前提是“必须要先有一套情景假设和知识库”,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就是一个理想的日常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日常生活世界是一种“由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知识库”。 日常生活世界有三种不同的解释性范式, 即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的解释范式、 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的解释范式, 还有关于个性取向或自我及其存在的解释范式。 因而, 日常生活世界的功能就在于对社会的整合: ①通过交往行动, 对文化知识的传播、 保存和更新达成理解; ②协调互动的交往行动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 ③使行动者社会化的交往行动满足形成个体身份的需要。 也就是说:“通过主体间性相互可批判的效度要求来协调他们的行动, 他们一方面依靠群体的成员, 另一方面又重新强化整合。”[4]208因此, 完成交往理性的转向, 必然要重建日常生活世界并在交往之中进行日常生活世界的再生产, 从而实现现代社会的整合。
2 自媒体时代下实现政府与公民现代化交往的四维度
交往, 在一定意义上是指行动者建立契约和规则的过程。 传统交往行为通常是发生在同一空间下共时的交流与互动。 所谓现代型交往, 不同于传统空间意义上的沟通与互动。 随着社交媒介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传统交往行为的时空界限逐渐被打破, 几乎每位网络公民在哈贝马斯语境下都可以在虚拟空间随时随地掌握科学型知识、 解释型知识、 批判型知识等大量信息。 这种趋势影响到公共政治生活领域, 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信源, 政府与公民的交往行为, 客观上逐渐向现代型转变, 而交往的现代性可以从交往空间与生态、 交往关系、 交往方式三个维度来解读。
2.1 交往空间的共融化与交往生态的多样化
交往空间的共融化体现在物理空间上的相互交融, 即公域与私域的融合。 哈贝马斯认为: “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意见的交往网络; 在那里, 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 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 像整个生活世界一样, 公共领域也是通过交往行动——对于这种行动来说, 掌握自然语言就足够了——而得到再生产的; 它是适合于日常交往语言所具有的普遍可理解性的。”[5]445自媒体时代下, 网络作为一种 “消灭空间”的信息技术, 有益于公众独立人格的构建, 有益于消灭传统媒体造成的差异, 有益于达成共识的“公意”。 “互联网成为公共领域最理想的沟通媒介, 网络空间成为一种理想的论辩环境。”[6]现代的社交网站就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下的公共领域, 人们在那里将自己的“私域”有选择地展示或分享在“公域”之中, 而“公域”也在影响着公民的私人领域, 二者是相互交融的。 因而, 在空间共融的网络平台中, 政府与公民的交往与互动一定要以一种公开、 自由、 开放的状态进行。 这种交往空间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交往空间更具有现代性。
交往生态, 可以被界定为人们交往行为的意义空间。 进而, 交往生态的多样化就是指公民在自媒体社交中对意义世界的追寻而呈现出认知、 经验和价值观等等的多元趋势。 网络空间的隐秘性使得个人语言文字的表达更富有真实性和自由性。 社交网络空间中的公民“在场性”是交往生态多样化的前提, 在自媒体时代, 个人、 群体和机构都可以把有关自己的信息和表征放进信息流, 以维持自己的公共存在。 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指出, 社交网站的“公共”维度产生于“私人领域的聚合”。 “在场”不等于邀约三五好友讲新闻, 也不像在公告牌上发通知, 其受众并不确定。 “在场”指向一个公共空间里永久性的网站, 其显著特征是信息的生产者展示自己, “它是为了回应日常生活世界里正在出现的一个需要, 即身体在他所处的物质空间之外寻求它在公共领域里的存在, 去建构个人的对象化(objetification)”[7]52。 公民作为自媒体在生产和展示信息时, 更多地是希望自己的存在得到关注、 诉求得到回应、 文化需求得到满足, 而政府发布信息如同工作汇报总结展示, 两者互动呈现“意义”的差异性(非对立性)会比现实世界更加明显, 而现代型的交往生态要达到的境界应该是“和而不同”, 是找到两者价值评判的最大公约数的和谐共存, 这样的生态圈才是健康的, 有生命力的。
2.2 交往关系的平等化
一方面, 精英走向了大众。 人人皆为信源, 信息的共享导致在信息资源上精英曾经的绝对优势相对削弱, 大众掌握了信息, 更加愿意行使监督权与参与权, 政府的角色也随着自媒体的不断开放在发生变化, 从传统的管理者到服务者, 再到寻求伙伴的合作者。 角色的转变必然引起行政思维的转化, 例如在决策方式上, 从传统社会的经验决策、 惯性决策、 秘密决策、 专制决策的单方控制转变为主动收集和听取公民的意见和建议等等双向互动性决策。 这意味着, 精英要想获得大众的支持, 必须站在大众的立场, 考虑大众的诉求和需要。 因而, 精英与大众、 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一种不断趋于平等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 个体从集体中走出来。 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时期, 社会不断涌现出新的阶层和社会群体, 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也呈现多样化趋势, 而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往往会将个体的声音淹没在集体之中, 导致个体在集体中的“在场性”被忽视, 个体的情感未被及时关怀, 这也不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和稳定, 而体现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正是对个人与集体的全方位关照。 传统社会中, 政府代表集体“公意”去行使政治权利, 公民往往难以表达私域中的诉求, 现代化的官民关系更应该通过平等友好的对话与互动来协调个人与集体、 公意与私意, 既体现集体利益, 又关照个人的合法权利, 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2.3 交往方式的效度化
交往方式的效度化, 是实现交往操作层面现代化的体现。 语言是交往理性的操作工具和媒介。 交往行为正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的相互作用来达到相互理解和承认的行为, 它蕴涵着主体间平等、 真诚、 和谐互动与正当交往的理性, 弥补了工具理性的弊端, 为话语政治提供实践运作的可能。 政府与公民的现代型交往行为根据哈贝马斯的语言三效度理论, 可以窥探出以下衡量交往方式现代化的维度。 如图 1 所示。

图 1 政府与公民现代型交往方式示意图
政府和公民作为网络政治交往中的行动者, 必须通过有效语言进行理性对话:
第一, 信息表达机制。 从政府层面, 确保发布的信息是真实的, 符合该地方现实情况和社会道德规范。 从公民层面, 可以自由发表利益诉求, 发表符合自身主观世界的见解和自身真实意图且合乎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法律规范; 第二, 信息交换机制。 回应与互动, 在发生分歧时, 能够根据客观实际情况, 通过理性论辩和商讨, 不断调整双方日常生活的认知图式、 价值观、 规范、 主观经验来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 这里可采取投票、 评论与回复等征集意见的形式来进行交往互动; 第三, 信息反馈机制。 调查公众对某件事情处理的满意度, 总结并改进不足, 不断提高自身行政的专业化水平。 20世纪60年代, 凯伦·特伦波姆—韦因布拉特(Keren Tenenboim-Weibatt)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 如今, “互文性”不再潜藏在传统文本中, 不需要学者去抽象演绎, 我们日常的评论习惯就随时演绎着“互文性”行为。 信息“互文性”的增强也是一种现代性交往的体现, 公民发送评论和信号的能力和范围被数字媒体大大拓展了。 这是对政府网络与现实行为的一种反馈形式, 是现代型交往的一种体现。 满足了以上要件, 才会有创造一个更公正、 更开放、 更自由的社会理性交谈的潜在可能。
3 自媒体时代实现政府与公民关系现代化的启示
哈贝马斯一方面批判理性, 特别是理性在历史中扭曲、 片面的实现, 即狭隘的工具理性的张扬; 另一方面又重构理性, 肯定理性所取得的成就, 扩展理性的维度。 哈贝马斯构建的社会潜在动力——交往行动的概念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且单纯依赖语言进行交往互动, 也具有一定的狭隘性。 但不得不说, 他提出的交往理性方案对规约公共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 随着移动客户端和社交媒体的融合发展, 论坛、 贴吧、 微博、 博客、 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应运而生, 这对官民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政府如何应对、 公众应以何种姿态和角色参与其中及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实现政府与公民关系向现代化转变, 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对当代我国实现政府与公民现代型交往有很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3.1 政府层面
政府作为自媒体时代下公共交往的行动主体, 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可以获得三点启示。
3.1.1 政府的角色应逐步从办事员、 管理员、 服务者向共商伙伴式的合作者转变
政府的角色定位决定着行政方式的转变, 即从传统的政府向公民单向输出管理和服务, 逐渐向双向的沟通协商、 共同治理转变, 这就要求政府要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等政治权利, 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而非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对待公民。 现代治理理论认为, “基层政府要实现多元主体协商治理, 加强多元主体之间的交流沟通, 明确各自职责所在, 协力促进社会和谐有序, 经济稳定发展”[9]。 因而, 在网络平台中, 政府通过沟通和激励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政积极性, 耐心听取公民的意见和建议, 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及时了解和实现公民的诉求和需要, 另一方面有利于构建起信任机制, 树立政府良好的公共形象。 相信群众参政议政能力, 依靠群众集思广益, 决策从群众中来, 服务到群众中去, 这样的行政方式是政民现代化交往关系的体现。
3.1.2 转变网络舆情处理思维,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网络舆情是指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对社会问题不同看法的网络舆论, 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 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 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 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公开、 透明地还原事件真相,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如果舆论危机源于谣言, 政府部门就需要及时向公众澄清事实真相; 如果舆论危机是由政府失职造成的, 则政府部门更应该勇于面对, 不回避, 不推卸责任, 找到问题源头进行补救并及时反馈于公众, 这样才能够在公众心中树立一个勇于担当的政府形象。 “公众最渴望的就是政府第一时间站出来还原事情本质, 如果政府不能开诚布公的将信息公布出来, 而是隐藏、 封锁、 捏造舆情相关事实真相, 那么公众就自然而然对政府不再信任。”[8]哈贝马斯的有效语言理论构成之一就是信息的真实性, 这也是公共交往的前提所在, 即公民可以接受有失误的政府, 但不能容忍有失误却逃避责任、 隐瞒真相的政府, 且一旦真相被纰漏,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会走向对立甚至对抗的境遇中, 所导致的结果是政府之后发布的任何信息都不为公众所相信和支持。 少数网络暴民的出现, 也会左右舆论倾向, 为了避免造成“塔西佗陷阱”, 政府除了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以外, 也要健全规约网络言论环境的制度。 政府还应注意对公众进行适当引导, 获得绝大多数的舆论支持。 总之, 政府要提高对政策和事件处理的解释力, 并在实施过程中保持言行一致的作风, 与公民真诚对话, 提高政府公信力。
3.1.3 完善信息沟通与对话机制, 营造良好的公共交往生态
一方面, 政府要积极广泛地搭建官员在线访谈、 政府网络政务平台、 官员个人微博、 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线调查和网络提案等等政府与公民合作平台来实现交往主体间有效的沟通, 保证政府部门与公众沟通渠道的畅通, 以增强互信感, 并进一步使之常态化和制度化; 另一方面, 政府要鼓励公民发声, 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和利益诉求, 从而营造一种自由、 开放、 平等的言论场。 同时, 也要善于引导, 在传播正确价值观中激发公民的责任意识, 对网络造谣者等网络暴民进行惩戒, 但不能因为由于网络交往生态的多样化催生了少数网络暴民, 就使原本应该自由开放的网络交往环境变成“一言堂”。
3.2 公民层面
“主体的本质在于参与”[9]167-168, 公民应充分利用网络这种新媒体技术效应, 提升参政水平, 培养网络参政的理性和公共性、 批判性品格和独立人格。 既要维护自身的基本政治权利, 也要树立责任意识。 要从“吃瓜群众、 围观群众”向现代公民转换, 主动投身于构建公共政治生活理性秩序的事业上来, 提高参政能力与水平, 关心国家命运, 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献言献策。
3.2.1 增强公民参政意识
主体间性作为交往理性的前提和逻辑出发点, 必然要求交往的双主体同时“在场”, 缺失了一方, 便无法构成平等交互的交往关系。 “没有参与, 就谈不上政治民主, 更谈不上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10], 公民作为公共政治生活的重要行动主体, 要培育自身的问政参政意识, 关心国家事务和民生, 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在与政府进行沟通和合作中达成共识。 在积极投身于问政参政的过程中, 公民不仅可以了解政府的运作和政策, 解答涉及切身利益的疑惑, 还可以增强对政府的理解, 在与政府共同治理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政治效能感, 实现公民价值。
3.2.2 提高公民参政能力
公民只有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分析, 形成对政治系统的理性利益诉求, 使社会情绪和舆论趋于理性, 才能促进社会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公民政治参与需要激情和勇气, 但是与政府进行理性对话和依法独立判断的能力更加不可或缺。 自媒体时代, 虚拟化、 隐蔽化的网络解构了现实人伦秩序, 解除了对个体自由自主的禁锢和制约, 激发和强化了我国公民的独立主体和权利意识, 网络成为构筑公民主体性的全新平台和开阔的精神空间。 但由于网络的隐蔽性与复杂性, 网络公民很容易受情绪化的非理性言论左右, “网意”天然具有群体极化的特点。 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指出: “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 在商议后, 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 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11]这要求公民要提高自身文化素质、 政治素养和法律责任意识, 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不制造谣言, 不散播谣言, 不做网络暴民。 因此, 有文化、 有教养、 有纪律、 有责任意识的公民才是公共领域的真正参与者, 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必须拥有独立人格, 能够就普遍的利益问题开展理性的辩论。
总而言之, 实现良好的政民关系与公民与政府交往的现代化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1] 宋晓丹.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J]. 西北大学学报, 2016, 46(1): 153-160.
[2] [英]安东尼·吉登斯. 政治学、 社会学与社会理论[M]. 何雪松, 赵方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3] [美]乔纳森·H·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邱泽奇, 张茂元,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4]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1.
[5] [德]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童世骏,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6] 许英. 论信息时代与公共领域的重构[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3(5): 50-58.
[7] [德]尼克·库尔德利. 媒介、 社会与世界: 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 何道宽,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8] 岳佳, 曾庆亮.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分析[J]. 中北大学学报(社学科学版), 2016, 32(2): 40-43.
[9] 张文显. 法哲学范畴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10] 周庆智. 基层治理: 一个现代性的讨论——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历时性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53(5): 19-28.
[11] 陆学莉. 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和传播影响[J]. 新闻记者, 2016, 20(10): 41-49.
OntheModernizationTransformationofPublicCommunicationBetweenGovernmentandCitizensintheWe-mediaEra——BasedonHabermas’s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
HONGRongwei
(Literature and History Department, Party School of CPC Sichuan Provincial Committee, Chengdu 610000, China)
Habermas, the Frankfurt School’s second-generation head, proposed to construct a neo-mode of deliberative politics through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ased on hi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language, as a communication tool of actors, plays a role in mutual understanding, that is to say, convincing others by showing sufficient arguments in order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basis of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s turning,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in the we-media era can be measured by three dimensions (communication space,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ways). Hi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s valuable for constructing the public image of the governme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he correct exercise of fundamental political rights of citizen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nd cultural quality.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public communication; we-media
1673-1646(2017)06-0025-06
2017-09-24
洪榕蔚(1993-), 女, 硕士生, 从事专业: 社会治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学。
B089.1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