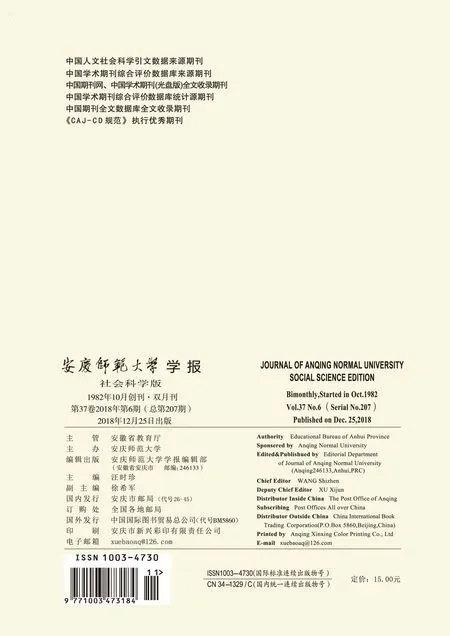《威弗利》中的情感与共同体建构
2018-01-02张秀丽
张秀丽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44)
在第一部苏格兰历史小说《威弗利;或六十年前 的 事 》(Waverley; or,'Tis Sixty Years Since,1814)中,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以充满浪漫幻想的英格兰贵族爱德华·威弗利的苏格兰高地旅行为轴线,以1745-1746年詹姆士党人最后一次试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威弗利逐步与苏格兰贵族露丝·布雷德沃丁建立婚姻关系的故事。国内外学者很多都指出,威弗利与露丝的婚姻象征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盟①国外学者如伊恩·邓肯(Ian Duncan)、艾娜·费里斯(Ina Ferris)、凯蒂·特鲁姆佩纳(Katie Trumpener)等,国内学者如石梅芳、高灵英、苏耕欣等都对婚姻和政治联盟之间的关系有过论述。。然而,在这一婚姻关系中,就威弗利的主动性问题,学者们普遍持否定观点。威弗利在与露丝确立婚姻关系之前,狂热地爱恋着高地伊沃族首领弗格斯的姐姐弗洛娜。弗洛娜充满激情和神秘色彩,而露丝却温柔贤惠,二者之间强烈的对比使得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威弗利后期转向露丝并非主动。此外,威弗利虽向往激情四射的生活,充满浪漫幻想,但却不谙世事,表面上看来总是处于左右摇摆状态(正如其名字waver所暗示的那样)。他逐步参与到1745-1746年事件中也被解读为“受到诱使”②乔治·纽文汉姆·莱特(George Newenham Wright,1794-1877)早在1836年就指出,威弗利的高地之行是受好奇心所使。后来有学者指出威弗利还受到了弗格斯等人的诱使。,体现出学者们对威弗利行为主动性的充分不信任。威弗利高地之行主动性与否的问题对于理解英格兰-苏格兰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双方的情感信任至关重要。若从身体促发情感,进而建立关系的角度来看,威弗利的高地旅行是充分自主的行为,反映出司各特在建构英格兰-苏格兰共同体过程对情感的重视。
一、情感与运动
在西方思想中,情感(affect)③本文采用affect,而非emotion,feeling,mood等词,主要是因为前者含义更为丰富,指向更为宽泛,而后者更多指的是具体的情绪。参见KeLLY J R.,N e.IANNoNe & M K.MccARTY.“The Function of Shared Affect in Groups”[M]//VoN ScHeVe c,M SALMeLLA,eds.collective emotions: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ogy,philosophy,and Soci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176-188.的含义并不明晰。一方面,情感被认为是无序的、偶然的,具有潜在的破坏力,必须加以控制;另一方面,情感被认为是一种对社会“有组织的反应”,一种动机,一种“激起、维持,并引导行为的过程”[1]17。这个定义强调了情感的社会属性,对于我们重新阅读司各特作品中的情感书写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情感之所以具有社会性,对个体的社会身份进行规定和调整(emotional regulation),在于情感能起到触染作用(emotional contagion)。在珍妮丝·R.凯里等人看来,情感触染是一种“不自主地模仿他人,在神色、举止和行为上与他人保持一致,以在情感上与他人趋于相似的倾向”[2]176。诸如神色、举止和行为上的一致会导致共同情感的产生,而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的共同情感也会引起诸如神色、举止和行为上的类似。
运动在情感触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珍妮丝·R.凯里等人指出,“群体的情感起到了一种重要的沟通功用,其目的是为了促使群体成员行动起来,同时又将成员粘合在一起。”[2]176而与笛卡尔齐名的哲学家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则将情感定义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3]97。在这里,情感涉及两个元素:身体、感触。由于身体总是被外界感触,或者感触外界,情感于是与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身体运动(move)时,它同时也在感触(feel),感触时也在运动,二者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个体情感向集体情感转化的过程中,身体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这个视角重新阅读《威弗利》,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部关于身体运动的小说。威弗利离开处于静止状态的家庭生活,进入苏格兰低地参军,来到图莱-维俄兰拜访叔父在低地的故交布雷德沃丁男爵。因高地抢劫事件进入高地,见到高地伊沃族首领弗格斯,被其浪漫的气质深深吸引,同时爱上其姐姐弗洛娜。在归途中被劫,被陌生人救治,被送往已经起义的荷里路德宫,被弗格斯引荐给“摄政王”查尔斯·爱德华,威弗利向“摄政王”效忠,加入到起义军中,随起义军南下撤退。在撤退途中遭政府军追击,在混乱中与高地军分散。在农民家中躲避政府军,一番坎坷后回到伦敦,得知高地兵败,返回苏格兰营救布雷德沃丁男爵和露丝。与露丝两情相悦,前往卡莱尔城堡见弗格斯最后一面,返回图莱-维俄兰,与露丝结为夫妇。在结构上,除了首尾的家庭生活外,小说的大部分是由威弗利的旅行连接在一起的。可以说,整部小说是借助于威弗利的身体和运动将宏大历史事件与个人爱情经历联系在了一起。
威弗利参与1745-1746年高地事件的行为是由其情感倾向所决定的。威弗利性格内向,耽于浪漫的幻想,不喜户外活动和社会交往。姑妈曾经给他讲了许多家族英雄故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面对“英俊、端庄”,“神态威严、高贵”的王子时,他被后者身上的英雄气质所打动。他甚至认为,“尽管他身上没有表示身份的标志:胸前佩戴星章,膝上系绣花袜带,单凭他那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风度,他也能看出他的高贵出身和地位”[4]192。当弗格斯正要介绍威弗利时,王子打断了他,说“英国最古老、最忠诚的世家之一的后代”[4]192不需要引荐。他表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与威弗利的祖先尼杰尔爵士曾经致力的事业有相同之处。“要是威弗利先生像他的祖先尼杰尔爵士那样,决心拥护这一正义的事业,并追随这位依靠人民的爱戴,致力于夺回他祖先的王位或者为此牺牲的王子,要是这样,我只能说,在这一英勇的事业中,他会发觉这些贵族和士绅是值得共事的朋友,他所追随的王子,也许不幸,可是绝不会忘恩负义。”[4]193高贵、忠诚、英雄、正义等字眼对威弗利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查尔斯王子的“仪表、风采,以及他在这一异乎寻常的冒险事业中所显示的气概,无不符合他想象中的传奇英雄的形象”,于是威弗利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便向王子跪下,“为维护他的权利而奉献他的心和剑!”[4]193
由此不难发现,威弗利参与到1745-1746年高地事件是出于本性中的浪漫情感倾向,表达出的是他对正义的事业,浪漫的英雄,高贵而忠诚的世代传承的深厚情感,而正是这种情感促使了他的运动。情感与运动之间处于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之中。假使威弗利本性并非如此,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并没有给予他这种情感,那么他很可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追随汉诺威王朝了,而不会与高地扯出如此复杂的纠葛。而伴随着他一步步深入到高地,深入到高地人之中,了解到高地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化背后所蕴涵的关于忠诚与秩序的理念,亲身经历高地的风俗人情,威弗利对高地的情感也在不断加深。这是两种作用于威弗利身上的力。那么,这种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力量呢?
二、同情的力
同情是一种重要的情感动力,它能够促进情感的联系,起着一定的社会黏合作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1756)中指出了同情对于建立情感关联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同情的存在,我们才关心他人所关心的事物,才感动于他人所感动的事物,并且不至于对人们所作或所经受的一切事情无动于衷,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5]41威弗利并非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一步步参与到高地的军事行动中,正是基于对高地人民的同情和对高地文化的热爱。这种同情的动力在《威弗利》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力量,可以说是司各特借此以连结苏格兰人民与英格兰民族情感的艺术手段。这种同情的内驱力并不是理性的,其核心是激起人们心中对于不幸事件的适度欣喜。
对于不幸事件的愉悦感情并非出于理性的观察,而是“身体的感官结构”,或者“心智的框架与组成”[5]41。伯克指出,在考察社会交往关系时出现的上述现象,“理性的影响力或许没有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广泛”[5]41。对于苏格兰,尤其是高地社会、诗歌与文化的行将覆灭,无论是威弗利还是作者司各特都表达了深深的同情。深受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等人的影响,司各特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所谓进步论,对于在现代资本文明包围下苏格兰封建氏族社会的发展困境深感无力。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对于苏格兰社会和文化的向往就像是试图抓住必然逝去的东西一样徒劳无益。但是,威弗利对苏格兰的浪漫幻想,以双腿丈量了苏格兰高地的崇山峻岭,以眼睛观看了苏格兰文化的展演,本质上是一种对于感官和心智的张扬。在理性大行其道的现代资本社会,对落后的,野蛮的,行将或已然逝去物的想象,可以说是一种对理性的抵制,更是对身体与情感的弘扬。
之所以说是不幸的,使人震惊的事件能够让人产生很高程度的愉悦感受,在伯克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当想到如此忧伤的一个故事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作品时,我们感到满足”;其次,“当想到我们远离作品所描写的罪恶时,我们感到愉悦”[5]41。1745-1746年的苏格兰高地事件以卡洛登战败画上了句号。它同时终结的是苏格兰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可能性,至少在当时可预见的未来。对于苏格兰民族情感来说,这次事件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创伤事件,对苏格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因不幸事件所产生的愉悦感受使得人物和读者在面对他人苦难时生出同情之感,促使人们做出行动的激情,并联合起来,建立情感关联。伯克指出,在灾难面前,人们会被同伴的感情所影响。这种影响引诱我们走向这些事件,如同阅读高贵民族的灭亡或伟大人物的不幸一样去切身体会苦难者的感受。正是这种切身的感受与行动,促使人们“通过同情而联合起来”,而“运用来加强这种联合关系的东西就是某种适度的愉悦(delight)”[5]42。因他人苦难引发的情感上的适度愉悦加强了不同个体之间的情感关联。这种欣喜之情“并非是一种不掺杂其他的欣喜,而是混杂着某种无法释怀的感情”。“面对此类事件时的愉悦,使我们无法置不幸的事于不顾;而我们感觉到的痛苦,则使得我们在宽慰他人的时候,也顺带宽慰了自己。”[5]43对于19世纪的读者而言,司各特所展示的一阵令人痛苦的民族伤痛虽然已经遥远,但却并没有消失。重新阅读历史事件给读者创造了旁观过去的机会,并使得人们在隐隐存在的民族之痛中感受愉悦,获得解脱。这种解脱之感对于重新建立新的民族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苏格兰人民来说,这种阅读与旁观将自己从创伤中解脱出来,而不是陷进历史的泥潭无法自拔。对于英格兰人民来说,在这次不幸事件中以威弗利、塔尔博特上校为代表的英格兰人对苏格兰的友情与同情,在很大程度上宽慰了自己。这对于重新建立英格兰-苏格兰的民族关系是十分有益的。
三、情感共同体
在身体运动中引发了感触,在不幸事件中生出同情的力量,都有助于建立情感的关联。情感的这种关联又进一步促进了共同体的建构,甚至大不列颠的想象。在《威弗利》中,司各特从英格兰-苏格兰经济一体化、印刷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情感关联的内在驱动三个维度建构了情感共同体的动机与内涵。对19世纪的大不列颠而言,共同体指的是在共同的区域所有人因共同的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概念。1814年《威弗利》的出版距离1707年《联盟法案》的颁布已有百年余。在这一百多年的冲突与融合中,英格兰与苏格兰已经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司各特在《威弗利》中所建构的共同体可以说是一种情感共同体。在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和印刷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内在驱动下,它可以说是建立情感关联的文化需要和表征。无论是在大不列颠,还是全球各地,英格兰与苏格兰因资本全球扩张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司各特在这种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强调英格兰-苏格兰之间虽有分歧但依然相互关爱的历史友情,反映出建立情感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需求。
英格兰-苏格兰的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情感共同体的建构。17世纪后期,英格兰已经为海外领土扩张建立起了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基础。从1650年开始,英国开始了全面经济和军事扩张的步伐。苏格兰也渴望在海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17世纪90年代末期,苏格兰集全国财力,试图在位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的巴拿马地峡中的达林海湾(the Gulf of Darién)建立殖民地。但是这次努力并未成功,苏格兰银行全面崩溃,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想要成为世界贸易中心的苏格兰不得不放弃独自寻求海外市场的企图,转向英格兰政府。虽然1707年《联盟法案》的颁布充满了政治阴谋和欺骗,对于苏格兰的民族情感来说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但是若从当时的经济格局和政治形势来看,苏格兰加入英格兰经济,共享英格兰在海关、税收、制造业等方面的经济利益和市场,是大势所趋。在小说中,也即联盟之初,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在经济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当威弗利来到图莱-维俄兰村庄时,所见一片萧条。与“整洁宜人的英格兰农舍”相比,这里“简陋不堪”。一群小孩赤裸着身体在路上玩;一二十条“饿得半死”的狗跟在马匹后面嚎叫,咬着马的后蹄;一些老头“由于长年劳累,个个都弯腰驼背,又因上了年纪,烟熏火燎,两眼泪水模糊”[4]48-9。这表明,苏格兰低地的经济处于十分落后,甚至停滞的状态,与英格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英格兰人威弗利十分同情。他说:“那些人的脸绝非一副木呆呆的傻相;外貌虽粗,但显然很聪明;虽严肃,却不蠢;从这些年轻姑娘当中,画家可以不止挑选出一个面貌和体态都像密涅瓦的模特儿。那些皮肤晒得黑黑的、头发晒得发白的孩子,也有自己的神态、生活方式和兴趣。”[4]49-50而到了小说发表时的19世纪初,英国打败殖民对手法国“为大规模的领土夺取定下了基调,而苏格兰人十分适时地从中获取了大量物质益处”[6]4。此时,加强情感的关联是必然趋势。
其次,爱丁堡印刷业的繁荣及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英格兰-苏格兰情感共同体的建立。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提到了印刷业对于想象共同体的重要作用。由于书籍出版业对资本的无限渴求和趋利,印刷资本主义开始形成。它促使印刷语言逐步替代地方性的语言,尽可能地扩大读者群体。《威弗利》虽然是以苏格兰历史为背景,小说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苏格兰人,使用的是苏格兰低地或高地各氏族的方言,但小说却是以标准英语写成,只穿插了很少的苏格兰对话,并不影响读者的接受。可以说,英语成为印刷语言为英格兰-苏格兰创造了统一的交流工具,促进了文化的沟通和情感的加深[7]38-46。伴随着爱丁堡印刷业的全球扩张,司各特的27部威弗利历史小说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对于世界各处的大不列颠人而言,小说极大地加强了英格兰与苏格兰对于共同家园的想象,促进了大不列颠性(Britishness)的形成。人们会为威弗利与弗格斯之间真挚的情感所感染,会被浪漫化的苏格兰高地深深吸引,不断地建构着共同的文化记忆。
最后,资本的全球化也促进了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在19世纪,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和资本的全球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再像传统的社会关系靠近亲血缘关系维系,传统价值开始分崩离析,社会的向心力也逐渐消失。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建构共同体的呼声。此时的联盟与百年前的政治结盟已有很大区别,更重视人的情感因素。威廉斯也指出了18世纪之后的共同体有一个更重要的特征:“不像其他所有指涉社会组织(国家、民族和社会等)的术语,它[共同体]似乎总是被用来激发美好的联想。”[8]76借助于激发联想,特定人群实现了对于共同体的想象,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情感关联。这里所说的联想与想象可以说是同义。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论述了想象对于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而亚当·斯密也指出,“只有借助想象,我们才能形成有关我们兄弟感觉的概念。……通过想象,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因而形成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法,甚至体会到一些虽然程度较轻,但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9]2-3可见,想象促进了情感的关联,进而加强了共同体的建构。
司各特在《威弗利》的引言中称,小说是以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在战争冲突时超越政治偏见,相互保护的友情为基础写成的。他称,“我决定仰仗人物性格和感情本身的说服力,以尽量避开那些不利因素;——那是社会各阶段中人所共有的情感,就像人类的心不论是在十五世纪的铠甲下,或在十八世纪的绣花外衣下跳动,还是在蓝罩衫和白细布背心下跳动,都一样为这种感情所激动。”[4]5情感在《威弗利》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司各特借以建构共同体的重要策略。这种超越时间、区域,甚至文化差异的情感,在建构英格兰-苏格兰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