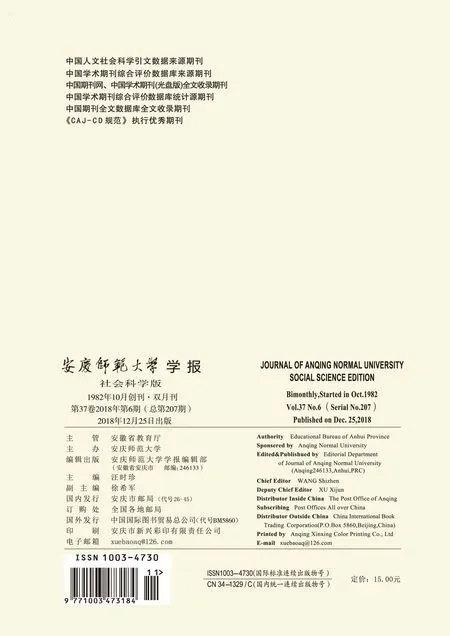“当代文学史”的莫言书写
——从陈晓明两版《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说起
2018-01-02梅向东
梅向东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246011)
从1985年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陈思和倡导“新文学的整体观”,1988年到1989年陈思和、王晓明倡议“重写文学史”,直至2012年,近30年的当代文学研究,持续处于“历史化”的冲动和热潮中。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便“已出版三十几种”[1];到2012年则猛增至七十多部[2]。然而,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犹如一声棒喝,让喧闹一时的“当代文学史”沉静下来。
“当代文学史”陷入某种自我反讽的尴尬境地。它们大多写于2012年之前,出版时莫言除《蛙》之外的重要作品均已问世,然而其莫言书写,却显然不能匹配于莫言的创作成就。其固有的问题暴露无遗。正如有学者所言:“不啻是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潜隐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和潜在危机的一次引爆。它首先表明的是我们的文学史观是多么‘无形',20多年来我们‘重写文学史'的热情是多么‘无力',我们的话语谱系是多么‘没谱',而我们评价文学的标准又是多么混乱。”[3]莫言的获奖无疑让这变成了现实。唯其如此,如今检视和反思“当代文学史”的莫言书写,就显得尤有必要。
一
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先做出反应的“当代文学史”,是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以下简称《主潮》)。它原本出版于2009年4月,当莫言2012年10月获奖,《主潮》第二版便于两个月后的12月修订完稿[4]598,2013年9月年出版,这不禁让人疑问:陈氏何以反应如此迅速?这种兴奋和急切意味了什么?
考量第一版《主潮》的莫言书写,不能不乐见它有相当的前瞻性,这在所有的“当代文学史”中应该是最为显著的。这当然是见于其关于1980年代莫言的书写中。它是把莫言置于第十三章《应对西方潮流的现代派与寻根派》和第十四章《先锋派的形式变革及其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中去述及的。它注意到莫言创作从一开始就显露的独特性:其一,在一个从观念出发的文学时期,莫言却是凭着个人经验进入文学的。1980年代正是文学突破教条桎梏,在“应对西方潮流”中观念纷呈的时代,而莫言的“写作总是从个人经验出发,他可以控制他笔下的文学,而不是被文学拖着走”[5]340,这充分显示出与当代作家尤其是80年代“寻根”作家的不同。他“从来不作形而上的思考”[5]335,“只凭着他的本真经验”切入文学,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表达文学”[5]334,就显得独特而可贵。其二,莫言拓开出的文学世界,具有独特的文化和美学意义。1986年,莫言发表《红高粱》等系列作品,“具有中国当代小说少有的家族自我认同意识”,正是在同自我本源性的血脉相连中,它触摸到“原始生命力”这一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它是混合了“尼采的生命意志特征”和“本土(民间江湖)的侠义精神”的壮丽形态[5]334,而这是现当代文学中罕见的。其三,莫言的小说叙事具有形式变革的重大意义。《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的独特叙述视点,是将民族、家族“与‘我'的经验和生命本体联系在一起”[5]334的方式;莫言“大起大落的笔法,粗犷凌厉,涌溢而出,无拘无束,洒脱豪放”,“为小说叙事向着个人经验、向着语言和感觉层面转向提供了一个杠杆。”[5]335总之,陈晓明较为敏锐地把捉到1980年代的莫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莫言“使当代中国小说从思想意识到文体都获得了一次彻底的解放”[5]335。这一判断,应该是所有“当代文学史”中不见的。
然而,陈晓明从一开始却也流露出对于莫言固有的认知困惑。在对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历史化”处置中,如何确立莫言在其中的方位?他一面以莫言为先锋派形式变革的“前行者”[5]342,一面却将莫言置于“寻根派”中去叙述,这种体例处置,本就显得吊诡;不仅如此,又说:“莫言并没有明确的‘寻根'的意图”“1986年,莫言发表《红高粱》等一系列作品,这是‘寻根'的一个意外收获,却又仿佛是它的必然结果。”[5]334这是一种既难以确定又不无矛盾的判断。这表明那种体例处置,其实是一种认知犹疑的选择,是将莫言置于“寻根派”“现代派”“先锋派”“新写实”“新历史”等等概念化运作中,都显得似是而非的结果。更为遗憾的是,陈氏不仅没能把其前瞻性眼光延伸到对1990年代后莫言的审察,相反,倒是延伸了先前的认知困惑。面对90年代后的莫言,第一版《主潮》更多表现的是无所适从、无法有效阐释的危机。也就是在其第十三章述及1980年代的莫言之后,紧接着有这样的后缀:
若回到个人体验的生命本体,回到叙事语言的本体,莫言为新的小说意识打下了坚实基础。莫言几乎已经挥霍尽了文学叙事在历史文化和生命认同方面的想象力,因而,在个人的生命体验意义上,不得不给后来者剩余下个人的乖戾感觉,也就是说,那种狂热的、自我确证式的认同,只能向着个人的狭隘感觉方面变化。就莫言本人而言,经历80年代后期的宣泄式的写作,他的想象力和激情也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终结了。莫言后来依然在写作,作品有《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等。这些作品显得更加自由洒脱,似乎胡作非为而能出神化[5]335。
它不仅把“个人的乖戾感觉”“个人的狭隘感觉”维系于莫言,而且宣布了莫言的意义随着1980年代的过去而终结了。这一看似武断而草率的判断,恰恰透露出陈晓明对于莫言潜在而真实的感知。如果参之以陈氏这之前的言论,更见不虚:
就莫言本人而言,经历过80年代后期的宣泄式的写作,他的想象力和激情也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终结,莫言后来依然在写作,作品有《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等。这些作品不能说不好,但相对莫言过去的成就和现在的名气来说,这些作品就不能说非同凡响[6]。
它出自于陈晓明2002年出版的《表意的焦虑》,而这一著述即是《主潮》的前身。这至少表明,陈氏是将莫言的意义定位于1980年代的当代文学,而对1990年代后的莫言小说却无法进行“历史化”的意义阐释。尽管在第一版《主潮》最后一章《乡土叙事的转型与汉语文学的可能性》的第四部分“新世纪的乡土叙事与本土化问题”中,有“莫言:历史反讽与戏谑的叙事”,述及《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三部小说,但那里关于莫言的历史叙事的讨论,不仅比不上对刘震云、铁凝、贾平凹、阎连科的阐释那么富有底气,而且显得勉强而含混,既见不出它们与1980年代的莫言有何精神上的内在关联,又显得单薄无力;与其说是意义阐释,不如说是一种后现代式的解构性阅读;似是价值中立,又似有价值诉求;与其说是价值肯定,不如说是价值否定:“莫言本人并不是一个对历史多么眷恋的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而是一个要在文学中找寻快乐、创造快感的人。……莫言摆脱了重建历史的责任,他从历史中拾掇起人性的碎片,不时地打击这些碎片。叙述一段历史,却又能避免重新历史化,莫言似乎保持着‘去历史化'的游戏精神。莫言更感兴趣的是用他的叙述制造戏谑,在这里,游戏精神使他的语言表达获得了最大的解放。”[5]588
因此,随着莫言的获奖,修改《主潮》就显得紧急而必要了。事实上,这也是最主要的动因,第二版《主潮》修改的主要内容,正是有关莫言的部分。第二版在对1980年代莫言的书写中,引入了“在地性”概念:“他的寻根并没有知青群体的那种观念性的文化反思态度,他只有与乡村血肉相联的情感和记忆——这就是他始终的‘在地性'。”[4]336“他给寻根文学提示了另一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本身,回到个人的生存事实中去,这个根不是文化观念意义上的‘民族之根',也不是文化典籍积淀下来的生存态度或价值。莫言的寻根有一种在地的直接性。”[4]337显然,这一“在地性”解读,强化了陈晓明从一开始就赋予莫言的那种“根”性上对于本土文化生命体验的血肉本体性,唯其如此,就使得莫言后来走向世界的独特艺术经验,就有了更坚实的本源:以回归本土的方式迈向世界,抑或说以现代性方式回归本土。如果说这种增补性修改是对1980年代莫言的锦上添花,那么,大尺度的删改,则当然集中在对1990年代后莫言的书写上。第二版《主潮》将最后一章第四部分的标题,由原来的“新世纪的乡土叙事与本土化问题”,改为“新世纪乡土叙事的‘晚郁'气象”,把原本第一版属于这一部分内容的“莫言:历史反讽与戏谑的叙事”删去,专门独立另辟第五部分“莫言与汉语文学的坚实道路”。这一结构调整和标题改动,其目的可想而知,这不仅是要重新书写1990年代后的莫言,而且要对这一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学重新考量,或者说既要实现前者,就要实现后者。第二版将前述第一版第十三章述及1980年代莫言之后的后缀,删改为:
回到个人体验的生命本体,回到叙事语言的本体,莫言为汉语小说意识开启了一个极其广阔自由的空间。在他的身后,崛起一批先锋派作家。他们在莫言的险径上一路狂奔,迅速抵达极地[4]338。
原本对莫言的“个人的乖戾感觉”“个人的狭隘感觉”、莫言作品的价值随着1980年代的过去而终结等等判断,自然都被删除了,而且把“莫言为新的小说意识打下了坚实基础”改为“莫言为汉语小说意识开启了一个极其广阔自由的空间”,由此,莫言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80年代,而且也是其90年代后作品的意义之源。当然,对于莫言最大的改写是最后一章中关于《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的叙述。陈氏一改在第一版中对前三部小说勉强而含混的解读,而拓展出它们独特而广阔的文化与美学意义空间。他建起了它们的历史文化意义逻辑:前三部构成“20世纪中国现代三部曲”,是莫言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苦难历程”的书写[4]587,莫言从一个“从历史中拾掇起人性的碎片”者,变而为“在地性”地“抓住历史的痛楚”者,从“‘去历史化'的游戏精神”者变而为“始终把握住历史正义、人间正义以及人性正义”者,从“创造快感”“制造戏谑”者,变而为“以戏谑、反讽以及语言的洪流来包裹他的强大的批判性”者[4]591。莫言创造了一种属于他的小说艺术的根本特质——“解放性的修辞叙述”,它“意味着对汉语文学的一种基础性和方向性的开启”[4]595。通过改写,两版《主潮》中的莫言显然有了绝大差异。
二
然而,正是因为陈晓明的修改是在莫言获奖之后,所以不管反应多迅速、修改多完善,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因为第一版《主潮》中的问题,与其说是会随修改而消失,相反不如说是随之而彰显。更为深重的在于,它远非仅是《主潮》的问题,而是“当代文学史”的普遍问题,而这却是谁也无法修改的。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将莫言从1980年代到90年代后的全部创作历程,置于“80年代中后期小说”的寻根文学之后简述的[7]289,这一非常牵强的体例处置,无疑显示了洪著的书写态度。这意味着它把莫言定位于80年代中后期“表现了新锐和革新精神”的“风景”之一[7]195;而这既是对莫言整体文学经验的轻忽,更是无法完整认识和判断其文学史意义的结果。这使得莫言“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此前少见的乡村天地”“表现了开放自己感觉的那种感性化风格”“天马行空、不受拘束的叙述方式”“突破艺术成规”“转化‘民间资源'”“‘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探索”[7]289等等艺术经验,缺少了“历史化”的成色,更谈不上“世界化”的认证。伴随于此,洪著甚至有不该有的失察:它把莫言建构“高密东北乡”看作是其小说的早期行为;莫言90年代后的“叙述方式有了朝着内敛、节制的方向演变”[7]289。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建构一个文化地理学的“高密东北乡”,如果说这在莫言早期还属于一种不自觉,而到后来则是越发自觉并强化的行为;莫言那种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叙述,在90年代后也非但没有收敛、节制,相反,更是朝着文无定法突进。洪著之所以有这种失察,显然是因为对莫言90年代后小说的轻忽。事实上,在洪著整个对于1990年代文学叙述的部分,几乎不见莫言作为重要作家的“在场”,这种巨大盲视,不能不是伴随了对这一时代莫言长篇小说宏伟建构的极度失语。在洪著对于莫言的“既令人惊讶,受到赞赏,也引发争议”[7]289的交待中,1990年代后的莫言,几乎成了一个无法判断的意义缺失。
陈思和说:“我把莫言的小说作为一个自觉的民间艺术形态的探索者和创造者的文本来解读。”[8]然而在其《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却并未贯彻这一宗旨。而是一面把莫言作为“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9]291,一面把莫言置于“新历史小说”中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对待,而在专列一节“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审视:《红高粱》”的重点讨论中,解读的却是其“民间立场”及其价值[9]317。尽管这三者互有交叉,但毕竟有大不同。这起码透出两个信息:一是对于莫言,不无认知错乱。陈著似是将莫言小说置于形式上的“先锋性”、内容上的“历史性”、意义上的“民间性”三个维度上考量,但却既没能凝合出莫言独特而完整的艺术经验,又在“先锋性”的历史虚无、“历史性”的文化寻根和“民间性”的自由精神三种价值取向上,对莫言难以进行价值判断和文学史定位。二是推重1980年代以《红高粱》为标志的莫言。在陈著中,莫言就是《红高粱》的莫言,《红高粱》就是其“史”的意义所在,而《红高粱》的价值就在于拓开了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叙事。陈著所有的莫言书写,都限于1980年代范围。它从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一章三章讨论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却不见莫言任何踪迹。而倒是在附录二“当代作家小资料”的莫言介绍中,提及《天蒜薹之歌》《十三步》《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并附简评:那些小说是感觉和形式上“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回归现实和民族传统,文字上激情勃发,画面五彩斑斓,语言无节制、夸诞等”[9]409。由此倒是可见它们不入陈著法眼的书写立场。尤为不可思议的是,以建构“民间性”著称的陈著,在其关于1990年代“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的专章叙述中,竟然只字未及莫言。这不禁令人生疑:陈著是以什么意义上的“民间”看待莫言的?它是在人类文化学意义上?还是在特殊历史语境中作为一种对抗“主流”的策略?是因为其“民间”概念具有暧昧性还是莫言的“民间”具有暧昧性,导致陈氏对90年代后莫言的失语的?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则以莫言为先锋写作的代表类型之一[10]258。在董著的书写语境中,莫言1980年代中后期的《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爆炸》等,离“文化哲学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特色较远,更多地指向叙述变革的形式层面”[10]260。也就是说,莫言的“先锋”意义在于“某种特殊的叙述感觉的追求”“独特文学审美感觉的体悟”,而“远离存在意义上的哲学深思”[10]260。它同样重点述及的是《红高粱》,但却是将它作为先锋小说的形式范式,解读其“非线性、非逻辑的循环复叙结构”的形式意义的[10]315-316。董著中莫言的“在场”,是作为1980年代先锋小说家的“在场”,而且其“在场”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董著以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两章的篇幅叙述1990年代后的小说状况,论及陈忠实《白鹿原》、张炜《九月寓言》、张承志《心灵史》、贾平凹《废都》、阿来《尘埃落定》等诸多文学,却几乎完全忽略了莫言,竟然只有一处这样言及:“在精神探索方面,90年代并不比80年代呈现出更多、更独特的光彩。一些作品对过去流行的价值观念进行彻底颠覆的同时,并未为我们重构新的价值理想。如莫言的《丰乳肥臀》。”[10]422对1990年代后莫言的价值态度,可想而知。
洪著、陈著、董著无疑是“当代文学史”的力作和富有代表性的文本,然而从中却不难见到,它们的莫言书写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阐释危机——或是认知混乱,或是极度失语。这是一种无法有效阐释的危机。三种文学史都聚焦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莫言及其《红高粱》,而焦点各有不同。洪著以其为寻根文学,陈著以其为新历史小说,董著以其为先锋写作。这不能不是认知混乱的征验,而其阐释的有效性就不能不令人生疑。这延续到了后出转精的《主潮》中。如前所述,《主潮》既把莫言视为先锋派的“前行者”又将莫言置于“寻根派”中去叙述的体例处置,对《红高粱》既是“‘寻根'的一个意外收获,却又仿佛是它的必然结果”,是“对‘寻根'的反叛和超越”的似是而非判断,都体现了这一点。这表明,对于莫言文学在原初的形态及其艺术经验,它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新历史文学等等的众声喧哗中跳出三界外的独特性,“当代文学史”并没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和有效的“历史化”。莫言在《红高粱家族》自序中说到的“伟大文体的尊严”“不但同情好人,而且同情恶人”的“大悲悯”“笨拙、大度,泥沙俱下”的“庄严气象”[11]1-6,这些属于《红高粱》系列作品、也是莫言原初的内在精神气质和文化美学价值,“当代文学史”却未能有效阐释并提取为文学史的意义。这即便是到陈晓明的第二版《主潮》中也没有根本改变。当然,更为深重的是,对于莫言1990年代后的文学,“当代文学史”几乎陷入了一种无所适从、无法进入、无法阐释的集体失语。莫言《酒国》《食草家族》《天蒜薹之歌》《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诸多长篇小说,都问世于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可以说这一时期正是莫言取得巨大成就的黄金时期。而它们的问世,也都在洪著、陈著、董著第二版出版之前,然而却似乎被后者集体盲视。如果说对1980年代莫言作品的基本意义及观念方法,“当代文学史”尚有基本把握和阐释,那么面对90年代后莫言的“声色大开”“泥沙俱下”、千汇万状而又文无定法,它们便陷入了一种无措的境地。它们没能有效阐释它的艺术发展与创新,没能有效给出1990年代后莫言作品的历史意义。这种失语,不仅使得莫言成为一个巨大的意义缺失,也让他永远匍匐于当代文学史的1980年代。当然其代价也是很大的,正是这种失语,让它们随莫言的获奖而显得岌岌可危的。或许正是意识到这种严重性,让陈晓明迅速临机决断,重新改写而自我救赎的。
三
陈晓明在第二版《主潮》中说:“今天我们来总结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多年的历史,重要的是要看到是否有几位或十几位有分量的作家为时代留下几部或几十部过硬的作品。当然,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来说,关键是我们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这些作品,是否有能力阐释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汉语文学的艺术价值。”[4]573问题在于,这些言论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因而不无透着一种自我反讽。这不啻为对“当代文学史”的集体反讽。我们有理由问,假如没有莫言的获奖,陈晓明会有那样的改写吗?进而质询:在当下作家中,还有没有由于不能获得诺奖而其作品蕴涵有重大价值,但却依然无法被有效阐释而处在意义遮蔽状态的吗?缺乏对当代文学的阐释能力,这一根本性问题会因为莫言的获奖而有本质性改变吗?
“当代文学史”不仅建构知识谱系,也建构文学经典,而且无论是从“史”的学术水准还是传承传世的道德责任来说,都要求它具有更富历史感的文学批评。什么样的文学现象进入“史”的视野,哪个作家作品能够被“经典化”,这既是对“文学史”价值判断的考量,也是对其理论阐释力的检验。然而,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学史”,却同时患有严重的失语症。其最大的症候或许就是对莫言的无法阐释和极度失语。所以,陈晓明的莫言改写,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发现问题;与其说要改正观点,不如说要更新观念。这表明,对莫言的阐释危机就在于无法有效阐释的危机。甚至于陈晓明迅速修改这一行为本也是这一危机的表现形式。“当代文学史”应该回答却没能有效回答的是:莫言给当代中国文学带来了什么、有什么文学史意义?
这与其说是因为没有理论话语的失语,不如说是由于面对中国原创文学经验却没有原创理论话语的回应。1980年代的文学,或是意识形态价值的诉求,或是启蒙精神的表达,或是仿效于现代西方,角逐于各种主义而迷恋观念化写作;莫言却是依着生命本身的原创冲动和自由精神,在竭力呈现他所看到的世界的样子,这种“大悲悯”,从一开始就把那种观念化写作抛得很远。在1990年代后当代文学对这个空前多元化时代的言说中,莫言不仅是佼佼者,更是进入属于他的黄金时期。在他展示“长篇胸怀”[11]2,把长篇小说推向“庄严气象”时,也把其原初的生命冲动展现为历史生命形态;历史的苦难与面对苦难的狂欢化精神、现实质感与魔幻怪诞、了别善恶与浑默不识、历史暴力与人性温情、文化批判与悲悯情怀、在地与越界等等,构成他极其饱满而浑涵的巨大叙事张力,充分彰显出当代中国艺术经验。面对于此,“当代文学史”却显示出无法概括的理论苍白,当用各种概念去描述莫言而都不无扞格时,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自我反思和理论调整,甚至似乎丧失了谋求活水之源的内在冲动。此其一。其二,“当代文学史”没有建构起世界性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语境,因此也就无法真正确立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经验。“当代文学史”的价值诉求,让自身既无法真正进入世界性语境,又无法真正认同中国当代特殊的艺术经验。纷纷扰扰的“当代文学史”为建构自身的整体性和合法化逻辑,确立了各自为阵的文学史观,而执念于各自急切的价值诉求和文学史意义阐释方式,这不仅使得作为一种“史”应有的相对稳定的意义沉淀,不复存在,而且唯其如此,更是让真正进入世界性语境从而真正认同和确定中国艺术经验,变得不复可能。如洪著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观念,重在文学的“历史的产生”,而偏于“意识形态”的文学;陈著“民间”的观念重在文学的“历史的遗漏”,而偏于历史遗漏的“民间”;董著“现代性”的观念重在文学的“现代性的生成”,因而偏于文学的“现代性”;《主潮》“中国现代性”的观念重在文学的“中国现代性”特殊经验,而偏于文学的“现代性激进化”。如此的文学史书写语境中,莫言也就成了一个平面化的意义缺失。
而这一切都根源于“当代文学史”的中国文学焦虑。其实近30年的“历史化”不竭冲动,本身就是这一征候。尤其是其中的“启蒙情结”和“中国情结”,让“当代文学史”对中国文学的关切,变得急迫而焦灼,从而往往丧失了应有的历史理性、价值理性和学术理性。它让“当代文学史”那种回返“历史现场”的“历史化”,变成一场“历史化”焦虑。在这一症候中,难以建构富有原创性的理论话语,难以感知、理解和把握富有原创性的中国艺术经验,难以真正确立世界性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语境,就显得难以避免了;在失去历史理性、价值理性和学术理性的视阈下,当代文学扭曲为畸变形态——或是历史时空的肿胀,或是历史存在的虚脱,或是文化意义的遗漏。不能有效地阐释莫言文学经验及其重大意义,就势在必然了。
“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特征是未完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愿意把它的莫言书写看作是未完成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带给“当代文学史”的,不仅仅是反讽、反省和反思,还有启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在于本土本源性的现代性出现的地方,而这既在于作家的创作,也在于文学史家的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