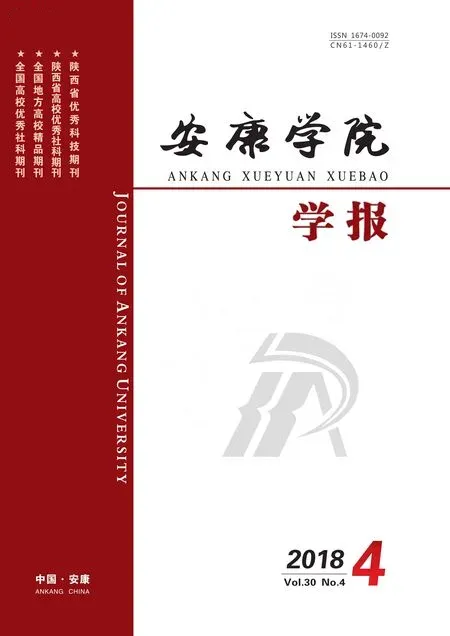父权宰治下的母亲
——《心经》中许太太的形象内涵分析
2018-01-01牛宇娟
牛宇娟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前人就张爱玲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传统父权压抑女性这一主题已多有论述,但很少有论者深入分析《心经》中父权对女性的宰治与压抑。说起《心经》,多数论者着重分析小寒和许峰仪父女的不伦关系,甚至有论者认为《心经》仅是张爱玲写的“一则幼稚的‘厄勒克特拉’故事的摹本”[1],往往很少论及许太太。且在少数对许太太的专论中,论者也多将许太太看作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表现母爱温情的女性形象,而忽视了许太太这一形象本身的矛盾复杂性。《心经》中,看似新式家庭里也不乏父权对女性的宰治与压抑。本文即着重分析父权宰治下许太太的形象内涵。
一、母亲与妻子身份的双重缺失
中华民国的成立,意味着封建帝制被推翻,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并没有随着清王朝一同灰飞烟灭,封建的伦理纲常仍对中国的社会和家庭有着深远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女性。尽管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浮出了“历史地表”,但女性的生存处境并非就此明显改善,封建的伦理纲常仍禁锢并压抑着中华大地上的多数妇女。在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社会定位下,多数女性只能生存在家庭婚姻之内,扮演男性主体的他者,屈从于丈夫、父亲或男性家长的权威之下,家庭婚姻生活便成了妇女一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心经》中的许太太便是如此。
在《心经》的开篇,张爱玲为许太太设计的出场方式就极有深意。作为许家的女性家长,许太太是在小寒之友的问答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连小寒之友都产生许太太是否在世、是否是小寒的亲生母亲这样的疑问,不禁使人纳罕许太太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而以小寒之友的眼光来看,许太太显然“不怎样,胖胖的”。其后小寒之友又误将客厅内的一张“女性”照片认作是许太太的照片。也难怪,明明是三口之家却只摆放了小寒和许父的照片。小寒澄清说许太太是为了不使大家拘束才没有现身。这便完成了许太太的第一次“出场”。从这一借他人之口的出场中,已经暗示出作为许家的女性家长,许太太在家中并没有多少存在感。其后,大概是在小说的三分之一处,许太太才真正现身。许太太的这一真正现身是从生日宴会结束、众人去后,她开门打扫房间开始的。许太太的身形正如小寒之友所言,确实“胖胖的”。在这样一个新式家庭里,相较于小寒的年轻活泼、许父的风神俱存,许太太就显得太平凡普通了。且通篇小说,在许太太多数出场中,她都是和家务琐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不是在打扫房间、侍弄花草,就是在提醒丈夫吃药、做女工等等,许太太的存在类似于女管家或保姆。显然,虽作为许家的女性家长,许太太却被囿于家庭之中,并非是家的主人而是变成了家庭奴仆,其自我主体身份匮乏。
许太太的自我主体身份匮乏,不仅表现在她被困于家庭生活的各种家务琐事中,在家中存在感低,还表现在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她必须忍受丈夫和女儿多年来的不伦恋情。在许太太和小寒的第一次争吵中,小寒提醒许太太注意许峰仪可能在外面有人了,许太太只是叹息道:“那算得了什么?比这个难忍的,我也忍了这些年了”[2]135。可知,许峰仪和小寒的不伦恋情,许太太不是不知情,而是只能选择隐忍和沉默。而许峰仪外面有人,身为妻子的许太太也只能忍受。但许太太的沉默与忍受并非来自小寒的压制,而是来自许峰仪。小说结尾处,许太太和小寒推心置腹的谈话中,许太太说:“有些事,多半你早已忘了:我三十岁以后,偶然穿件美丽点的衣裳,或是对他稍微露一点感情,你就笑我。……他也跟着笑……我怎么能恨你呢?你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孩子!”[2]144此话乍听好似一切都是小寒的错,但如果不是许峰仪也跟着嘲笑许太太的话,许太太不会感到如此自卑。正是许峰仪的纵容,小寒才会在母亲面前如此放纵任性,许太太才会愈加卑微。也因此,不敢管丈夫、也不能管女儿的许太太,其妻子和母亲身份双重缺失了。
妻子和母亲身份的双重缺失正是许太太在许家的现实处境。即便许家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在民国时期,但仍旧是一个父权统治的社会。像许家这样的“新式”家庭里,整个许家没有摆放一张许太太的照片,并结合许太太和许峰仪的平常相处以及许太太对待许氏父女的不伦恋情、许峰仪外面有人的沉默和隐忍来看,许太太在家中的存在感极低且没有话语权。正如许太太自己所言,她是一个“不要紧”的人。“不要紧”三个字,不仅道出了许太太内心的酸楚与无奈,也反映出在强大的男性家长许峰仪的权威之下,许太太作为一个女性自我否定的认命心态,而这种认命心态使得许太太未能真正尽到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
二、母亲身份的“复归”
《心经》的后半段,许太太的出场次数明显增多。尤其是在小说的结尾处,许太太和小寒在大雨中推心置腹的谈话,许太太的母亲身份好似因为许峰仪和小寒的决裂而复归,但并非完全是主体性的复归,小说中还有些细节需要深思。
一般将许太太解读为“温情”的母亲,主要是从小说结尾处许太太和小寒大雨中推心置腹的谈话而得出的结论。在段家门口,许太太将小寒骗上车后,母女俩展开了一场真诚的对话。作为母亲的许太太先是严声呵斥小寒不要发疯,阻止了小寒去段家告状,然后诉说了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的悲楚,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解小寒不要再做傻事,并决定将小寒送到其三舅母家住一段时间,好让小寒冷静下来。在许太太的深情告白中,小寒终于明白这么多年来自己所犯的罪,是“她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2]145最终母女二人达成和解,小寒也同意去三舅母家住上一段时间。小说至此看来,许太太和小寒确实复归到了各自的本位上,且许太太的母亲身份也得以复归。在这场煽情动人的对话之下,使读者不禁被许太太的隐忍与牺牲所打动,许太太这样做是为了保全家庭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女儿,并认为她是一位温情的母亲。在这场父女不伦恋情中,许太太俨然是最可怜之人,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心经》中,许太太和小寒一共发生过三次对谈,且这三次对谈都发生在小说的后半段。在小寒和许太太的第一次对谈前,小寒已经知道许峰仪在外面有了人,而且是自己的同学绫卿,所以小寒提醒许太太注意丈夫的动向,许太太反倒劝说小寒不要管太多。显然许太太已然知道许峰仪在外面有人的事实,但她就像对待许峰仪和小寒的不伦恋情一样,选择不闻不问。等到许峰仪和小寒摊牌后,小寒在许太太面前使气,责怪她不管丈夫,使得许太太大怒,给了小寒一个嘴巴子,并斥责小寒“犯了失心疯了”。这是小寒和许太太的第二次对谈。由这两次对谈可知,许太太显然已经知道许峰仪找到了小寒的代替物——和小寒长得很像的绫卿,而许峰仪肯定要抛弃小寒了。所以许太太对待小寒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第一次还是略带酸楚的劝说,第二次就变成了大怒、打嘴巴子和斥责。而在二人的第三次交谈前,是小寒赶去段家欲向段老太太告状以期能够拆散许峰仪和绫卿。正待小寒敲门,许太太突然跨出车来以许峰仪出车祸入院为由强行将小寒带上黄包车,离开了段家。这一处可谓是小说中最惊心动魄也最富张力的情节,可在此也不禁让人纳罕许太太如何得知小寒是去段家告状。其后小寒和许太太在黄包车上展开了第三次交谈,小寒怪许太太不及早管她,许太太却说自己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儿和丈夫有不伦之恋的事实。但从前两次的谈话来看,许太太并不是完全不知情,难道仅凭“不敢相信”,许太太就能对此不负一点责任吗?况且,以许太太知道许峰仪和绫卿同居的事实为分界的话,显然后半段中许太太的母亲身份逐渐显现出来,但这种显现值得怀疑。
虽然许太太口口声声说自己的不管不问、沉默、隐忍都是为了保全家庭、保护女儿,但她的这些做法却纵容了丈夫和女儿的不伦之恋,纵容了丈夫在外与别的女人同居,还使得女儿差点陷入疯狂,不禁使人发问:这样“完整”的家庭是否应该保全,许太太的委曲求全是否值得?笔者认为许太太之所以采取委屈求全、隐忍的方式保全家庭,也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家中的女主人地位。身为正室,许太太显然清楚自己在许家身份的尴尬难堪,然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真正的“弃妇”和“寡妇”又要比许太太凄惨[3]。所以许太太即便是知道许峰仪和小寒的不伦恋情也选择默不作声,即便是知道许峰仪在外有人也是不管不问,甚至阻止小寒去拆散许峰仪和绫卿。从这一角度来看,许太太阻止小寒告状,实际上是在帮丈夫解决麻烦,以防许峰仪和许家母女撕破脸皮,抛弃许家母女。而在许太太和女儿小寒的冲突中,作为整个事件的主导者许峰仪,却时常隐身在幕后,掩饰其在事件中的主谋身份,让许太太帮他解决麻烦。这也是小标题中“复归”二字要加引号的原因。许太太的母亲身份“复归”并非是完全主体性的复归,其间与男性家长许峰仪有着复杂联系。
三、“温情”母亲的破灭
张爱玲一贯认为:“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4]作为一个以善写女人见长的作家,张爱玲显然是不屑于写母爱这一题目的。但在《心经》中,许太太却一再被解读为“温情”的母亲,也因此在很多对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的专论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很少论及许太太,许太太这一女性形象也因之在张爱玲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显得尴尬而暧昧。对此,笔者认为将许太太称之为“温情”母亲值得商榷。
如前文所言,在父权的压制下,许太太面对许峰仪和小寒的不伦恋情,只能选择沉默和隐忍。但时代已经是中华民国时期,而且这又是个新式家庭,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许太太竟然能够八年如一日地无动于衷,许太太自身也值得怀疑。许太太能够一忍就忍八年之久,除了父权的压制之外,其实也指向了另外一种可能——许太太默认了许峰仪的做法。所以直到许峰仪没有找到合适的小寒的替代品之前,许太太对女儿小寒和丈夫的不伦恋情,只有沉默和无动于衷。而当许峰仪找到能够代替小寒的绫卿并与其同居后,许太太便不再对小寒保持沉默、无动于衷。如若许太太真的是一位温情的母亲的话,她怎么会一点办法也没有呢?“不敢相信”不代表不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直到事情发展到难以控制之时才去阻止、劝说小寒,如此来看,许太太是“温情”母亲令人怀疑。
小说的高潮也是小说最富张力的情景,即许太太冒雨阻拦小寒并将其骗回家。许太太的确是在保护小寒,保护家庭的完整。但许太太的热情举动、煽情话语,如从第二部分的分析来看,她阻止小寒告状不仅仅是为了保全家庭的完整,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太太地位。可许太太为何如此急促地做出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将小寒送走?在和许太太的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小寒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了罪,并渐渐平静下来。按理说就剩她们母女两人可以相互依靠,那许太太为何一定要将小寒送到远在北方的三舅母家呢?小说中第一次提到三舅母是因为小寒刚生下来时算命的说女儿克母,所以打算将女儿过继给三舅母,却未成型。第二次提到三舅母则是许峰仪主动提出将小寒送到三舅母家住些时日,好减轻三个人的痛苦,小寒不同意。却没想到小寒最终是被许太太劝说送去三舅母家。许太太竟和许峰仪的想法如此相似,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小寒能否再回到许家都需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中国的宗教》中,张爱玲明说中国的“父亲是专制的魔王”[5],此话一点不假,看看许太太在许家的现实处境便可明了。但张爱玲笔下的母亲也绝非好人,借用《第二性》扉页上所引用萨特的话:“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像所有人一样”[6]。《心经》中的许太太虽然是父权压制下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父权的同谋者。许太太并没有真正尽到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屈从于男性权力之下的她已失掉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资格,许太太的“温情”母亲一说便难以成立。
将家庭和闺阁中的女性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张爱玲,其笔下成功塑造了多对母亲和女儿形象,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和姜长安、《倾城之恋》中的白太太和白流苏等。表面上看,《心经》讲述了一个父女乱伦的故事,但张爱玲并没有将《心经》写成是一个仅仅表现父女不伦之恋的小说,其间也有对母女关系的深刻探讨。有论者言,张爱玲的小说里“罪恶的母亲无所不在,理想的母亲则是缺席的”[7]。诚然,在许家,“理想的母亲”也是缺席的。父权压制下,许太太被囿于家庭之中,既是可怜的受害者,也变成了男性家长的同谋者,其妻子和母亲身份双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