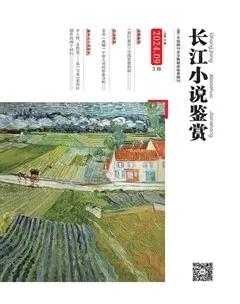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2024-06-21金芷娴
金芷娴
[摘 要] 与五四时代众作家的作品相比,张爱玲笔下的母亲似乎很少以正面形象示人,传统的母亲形象在她的作品中给予了不一样的描述。精神扭曲、虐待子女者、如曹七巧;无所作为、束手无策者,如许太太;早逝却给后代留下一生痛苦者,如冯碧落。她们经受种种迫害,又将命运延续到儿女身上,书写着一出出代际的悲剧。而张爱玲之所以创造出一个个不一样的母亲形象,与她年幼的经历和特殊的母女关系息息相关。
【关键词】 张爱玲 金锁记 心经 茉莉香片 母亲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47.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9-0023-04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被称为“不世出的天才”,其作品语言风格独特细腻,以冷静而锋利的笔调书写男女情事,字里行间处处透着时代的苍凉与人生的荒芜。在语言风格与感情基调之外,张爱玲的人物塑造也是值得细究的,她塑造的一个个经典形象,至今深刻影响着后代的写作者。本文试分析张爱玲笔下的一类人物“母亲”的形象特点,及其与传统母亲形象相比而产生的差异。
一、张爱玲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分析
1.曹七巧:从受虐者到施虐者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成为母亲前,便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作为麻油店的活招牌,她原本是健康的、自由的,可以与顾客和路人说笑,却因为兄嫂的贪欲不能选择一个喜欢的男子过终生,相当于是卖给了给大户人家残废的儿子做姨太太。后来被老太太扶了正,却无非是让她死心塌地侍奉残废的丈夫。家里的小姐少奶奶瞧不起她,连佣人都认为她不配服侍。在爱和性上都得不到满足的曹七巧对小叔子动了情,得到的只是被无视和奚落。长期压抑的、没有爱和尊重的环境,如同黄金的枷锁虐待着曹七巧的心灵。这正是曹七巧母亲形象与传统母亲形象
产生脱离的成因。尚未散去的封建婚嫁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宗族内腐烂僵死的空气对人性的迫害,使曹七巧从“人”被折磨成了“非人”。
如果说分家前的七巧是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媳妇,处在宗族制度的受害者的地位,那么分家后,作为一家之主和母亲的曹七巧,对待儿女又是如何?对于女儿长安,她可谓是“要什么不给什么”,却自以为尽心尽力,“送她上学,还替她裹小脚”。后来长安与童世舫的婚事被曹七巧百般阻挠,订婚后,她对着女儿酸溜溜地说:“这些年来多多怠慢了姑娘……这下子跳出了姜家的门,称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别这么摆在脸上呀——叫人寒心!”这是什么心态?是嫉妒,却自以为是不舍。七巧嫉妒女儿这一辈子有一个正常的男人,凭什么她自己却没有[2]。这种母亲形象和心理的偏离,造成之后她对女儿的抹黑与迫害,也是情理之中的。
长安曾怀揣梦想,渴望踏足洋学堂,甚至勇敢地体验过住校的生活。她内心深处对美好爱情充满憧憬,期待与留洋归来的童世舫共赴爱河。然而,每当长安试图展现出丝毫的生机与活力,七巧总是设法将其无情扑灭。每当长安提出住校的念头,七巧总能找到各种借口,大闹学校,迫使长安退却,回到家中。更令人痛心的是,长安的浪漫幻想被七巧与童世舫一句“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的轻描淡写彻底击碎。七巧一想到女儿可能拥有她未曾享有的幸福,心中便充满了嫉妒与恨意,她决心拉着女儿一起沉沦[3]。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安逐渐蜕变成了年轻版的七巧,变得善于挑拨是非、言辞刻薄,令人避之不及。在七巧离世后,长安似乎重新找回了些许生活的热情,但长期积累的负面情绪已难以逆转。就如同那双被七巧束缚的三寸金莲,长安错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少女时光,恐怕再也无法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经属于自己的幸福渐行渐远,将早已枯萎的灵魂深深埋葬。
对女儿,七巧是嫉妒的。再看七巧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子长白。长白是她生命中唯一完全属于她的男人,她对自己的儿子产生了极端的爱和占有欲。七巧为了阻止儿子去寻花问柳,还让他染上了鸦片烟瘾。七巧随随便便为儿子寻了一门亲事,却阻止儿子同儿媳圆房,每夜让儿子给自己烧烟泡。儿媳芝寿一进门,就遭到了她的百般挑剔和讥讽。如同儿媳芝寿所说,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不像个婆婆。他们议论她的隐私,当面羞辱她,把她活生生逼死了。之后扶正了侍女绢儿,她也很快重蹈芝寿的覆辙,吞了鸦片膏自杀。于是儿子长白不敢再娶亲,只是逛逛窑子抽鸦片。七巧一双儿女的人生,也是被她彻底毁坏。
七巧临终,知道儿子恨她、女儿恨她。“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1]曹七巧并非全然无情,尽管她偏爱儿子,但其扭曲的爱却导致他的人生支离破碎。她的嫉妒与对女儿幸福的抗拒心理,不仅使女儿的幸福化为泡影,更酿成了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随着命运之轮的冷酷转动,曹七巧自身也不幸沦为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她亲手摧毁了自己家庭原本应有的幸福与光明前景,进而引发了一连串新的悲剧。命运之轮无情转动,曹七巧自己竟也沦为了破坏者,摧毁了她家庭应有的幸福与未来,从而造成了新的悲剧。曹七巧的母亲形象是受虐者和施虐者的统一,被害与害人的疯子。她是张爱玲笔下一个最彻底的人物,却不是一个全然虚构的人物。七巧的悲剧甚至延续到了下一代,本应是慈爱子女的母亲,却将孩子也变成了牺牲品。在古中国封建制度半死不活的空气里,如同张爱玲所说,这故事不会完,完不了。
2.许太太:情敌还是母亲
在《心经》这样一个父女不伦恋的故事里,许太太作为母亲仿佛一直是个背景板一样的角色,从头至尾甚至连名字都未曾提及,仅以许太太这一称谓贯穿全篇。作为小寒的母亲,她更多的是女儿与丈夫畸形恋情中的陪衬。她与丈夫之间缺乏真正的爱情纽带,仅存的或许只是占有欲。
许家是一个阳盛阴衰的家庭,连照片都只有父亲和女儿的。生日会,母亲也没有出现,许小寒满口的只是“我爸爸”。许太太的存在最初仅在小寒同学的对话中隐约被提及,而后在她为丈夫服务的日常中逐渐显现。然而,她真正的自我觉醒是在小寒持续的提点与引导之下慢慢复苏的。觉醒后的许太太,在这场错综复杂的畸形恋情中,扮演了至高无上的角色,既是冷静的观察者,又是深刻的见证者,更是富有洞察力的预言家。她不仅见证了这场爱情,更重要的是深刻理解了其中的复杂情感——“你爸爸不爱我,又不能够爱你”[1]。尽管父女之间的情感纽带使母女间的关系变得微妙,但她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却依然坚韧。许太太的善良让她一直回避面对这种错乱的恋情,最终她选择了原谅与包容自己的孩子。为了女儿的未来,小寒的母亲毅然决定让她离开家,避免她再与父亲相见,因为她深知女儿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不可否认,许太太在《心经》中并非是一个完全负面的母亲形象,她甚至是这个畸形家庭中女儿小寒少有的温暖。她维系着家庭表面的完整,知道自己和丈夫已经不存在爱情,便选择去维护与女儿的亲情。在后半部分,母女间的力量平衡出现了显著的转变。女性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分裂到觉醒,再到再度分裂的艰辛历程。然而,在故事的尾声,这两位女性的形象最终实现了真正的整合,她们回归到了各自原本应有的正常地位和价值。在关键的时刻,许太太以不知何来的勇气,勇敢地站了出来,以一巴掌唤醒了迷惘的女儿。女儿在痛苦中向母亲发出质问:“妈,你早也不管管我!你早在那儿干什么?”这不仅是对母亲的呼唤,更是对母性的深切渴求。在母爱的驱动下,许太太毅然决定承受女儿的痛苦,甚至不惜牺牲自我来拯救女儿。她深情地说:“我一向就是不要紧的人,现在也还是不要紧。要紧的倒是你——你年纪轻着呢。”[1]这样的言辞在张爱玲的笔下极为罕见,尤其是出自一位母亲之口。她坚决地做出了决定,为女儿的未来安排了一条出路。
许家并非表面的“美满得少见”,实际上存在着母爱的缺位。小寒从出生就被算命指为“克母”,甚至一开始打算过继出去。小寒从懂事开始就将母亲作为性方面的竞争对象,其中必然有母女亲情疏远的原因。母爱的淡薄造成母亲的形象在小寒心中产生偏差,矛盾在这个家庭最终爆发。在小说结尾,母女得到了和解。但是这不能补偿十几年来许小寒母爱的缺失。许小寒爱父亲,因此更加痛恨自己的母亲。许太太一直没有干预他们的畸形感情,母女的对峙造成亲情的悲剧。许太太母亲形象的反差在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失败,然而这已经是张爱玲笔下较为温情的母亲形象了。
3.冯碧落:屏风上的鸟儿
与许太太一样,《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聂传庆早早过世的母亲,似乎不是一个戏份突出的角色。但是她在儿子聂传庆对教授言子夜病态的恋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聂传庆年仅四岁的时候,他便失去了母亲,对于她的模样,他的脑海中已无法勾勒出清晰的轮廓。然而,他耳中却时常充斥着关于母亲的种种传言,这些声音来自他的继母,来自家中的佣人。聂传庆逐渐洞察了母亲曾历经的悲惨命运——那段与言子夜间绝望的爱恋。这也让他终于领悟,为何母亲结婚前的照片中,她的面容总是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忧郁。
然而,对于母亲的过往,聂传庆却知之甚少,他的了解大多源于泛黄的照片、陈旧的杂志以及旁人的片言只语。在小说中,由于信息的稀缺,聂传庆逐渐形成了一种对母亲既神秘又深沉的认同和依赖。他时常在内心构建母亲的形象,试图在有限的记忆中重塑她与言子夜那段未竟的情缘,并幻想着自己与母亲能够拥有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于母亲,聂传庆深知她未曾全心投入于与父亲的感情;而对于自己的家庭与父亲,他则怀着深深的厌恶。得知母亲曾经深爱着他人,甚至可能与言子夜共筑爱巢,聂传庆的心中涌现出无尽的遐想——倘若母亲当年能勇敢追求真爱,无所畏惧;倘若她为了子女的未来,做出更为理智的抉择;倘若自己成为言子夜之子,生活在一个充满爱与完整的家庭中,自己的人生又将如何展开?然而,这些遐想终究只是空中楼阁。母亲已然离世,过去的一切无法改变。在现实中,聂传庆只能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之中,通过对母亲所爱之人的认同,寻找心灵上的慰藉。这种认同,实质上是一种想象中的占有,他将自我与母亲融为一体,将母亲的渴望转化为自己的追求。那种绝望的爱,如同母亲心中的利刃,如今也在他的心头留下深深的伤痕。因此,在迷恋母亲的同时,聂传庆也不得不怨恨她。他将母亲的形象定格在一张旧照片上,只能在想象中与她重逢,在不可能的生活中寻求慰藉。而他的命运,也如同母亲一样,无法自主选择,仿佛一只被困在屏风上的鸟儿,无法展翅飞翔。他的母亲虽然做出了清醒的牺牲,但他自己却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4]。
在小说中,聂传庆对言子夜的畸形倾慕,以及对妨碍他欲望实现的言丹朱的憎恶,都在不断加剧。这些被虚幻所迷困的欲望,在现实中注定无法实现,只会给他带来无尽的痛苦和压抑。最终,这些积累的痛苦和压抑,使得悲剧成了他的必然命运。于是在《茉莉香片》中,母亲成了主人公同情和仇恨交织的对象,母亲当年的选择,似乎是令聂传庆痛苦不堪、精神变态的原因。因为母亲的爱,他狂热地倾慕母亲曾经的恋人言子夜;因为母亲的退缩,他嫉妒言子夜的女儿言丹朱,幻想取而代之。母亲的形象在他心中产生的偏差成为他儿子一生痛苦的根源和指责的对象。
二、母亲形象发生偏离的成因
纵观张爱玲诸多小说作品,“母亲”从来算不得一个正面的形象。她们或像曹七巧一样虐待子女,或像冯碧落造成孩子一生的痛苦,或像《花凋》中郑夫人自私自利不惜子女,或像更多作品中的母亲,对儿女的困境束手无策,甚至干脆缺席。究其原因,自然得关注张爱玲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得到的是怎样的亲情。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也是高官后裔,美丽而思想先进,不能忍受张父的颓废落后,在张爱玲四岁时便出国。在散文《私语》中,张爱玲回忆:“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1]
母亲没有在年幼的张爱玲心目中占据多大分量,以致于一次次分离时,她总是显得冷漠,也怀疑母亲的冷漠。后来母亲终于回来了。与母亲一同回来的还有钢琴、外文、淑女,许许多多崭新的科学的事物。黄素琼无疑是位洋派女子,独立生活,有外国的男朋友,可是回来后要照顾一个逃出家门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在散文《童言无忌》中,作家回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译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5]
张爱玲的母亲,一位极具勇气的新式女性,因对婚姻的不满,毅然决定抛下两名幼子,远赴英国游学四年,并最终选择了离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父亲,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沉迷于鸦片、纳妾,甚至对叛逆的女儿实施禁闭。这种独特的家庭背景,使得张爱玲在受到西方新女性思想熏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文化的深刻影响。如同许多青春期的少女,张爱玲内心深处也渴望着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然而命运却并未眷顾她。童年时期,母亲的离去与父亲的再婚,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故。张爱玲被父亲和继母虐待,后逃向母亲家。她倾慕母亲的独立自主、摩登美丽,又希望得到母亲的亲情和关爱。
与其说张爱玲抗拒描写伟大的母爱,不如说张爱玲更关注母亲角色作为女性、或者说作为独立自主个体的丰富的生命体验和人性。例如,曹七巧的受虐转为施虐,许太太在无爱婚姻中的退避和最后的觉悟,冯碧落作为早逝母亲曾经的爱与悲欢离合。这与张爱玲母亲的特立独行,以及她们母女关系中特殊的,既独立逃避,又渴望依恋的拉扯是分不开的。尽管有人认为张爱玲对母爱和母性持否定态度,但她实际上并非不崇尚母爱,而是不推崇贤妻良母或孝顺女儿的形象。在她的作品中,她常常超越传统的女性社会角色定位,深入挖掘女性更深层次的本能特质,着重展现她们的人性光辉。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并非仅仅是母亲或妻子的身份,而是作为独立的女性个体来被描绘。因此,在她精心编织的小说世界里,一系列真实且充满生命力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她们并非总能迎合社会既定的角色期待,甚至勇敢地与之抗争。尽管她们可能不符合传统观念中的理想妻子、母亲或女儿形象,但她们无疑是真实、鲜活的女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女性身处延续了千年的父权制度之中,内心充满了困惑与挣扎。她们承受着女性特有的痛苦与挣扎,这些痛苦和挣扎或许不为外人所理解,但她们却默默承受并试图在困境中寻找自我与出路。她们的故事,不仅是她们个人的奋斗历程,更是对女性身份与地位的深刻反思与探索。通过张爱玲的笔触,我们得以窥见这些女性在困境中依然坚守自我,展现出她们独特而坚韧的女性魅力。
三、结语
不同于五四作家中普遍的对母性罗曼蒂克式的讴歌,张爱玲对母亲形象因特定原因产生的差异和偏离,进行了冷酷到残忍的揭露和入木三分的剖析。许子东先生曾经与阿城拜访北岛在台湾的寓所。北岛问:“你们这么多人喜欢张爱玲,张爱玲把人性写得这么恶有什么意义呢?” 阿城回答说:“写尽了人性之恶,再回头,一步一光明。”[2]或许,这正是张爱玲解剖母性——或曰女子被忽视的人性——的深远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2] 许子东.《许子东细读张爱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20.
[3] 冯梦秋.由《金锁记》浅析张爱玲的女性意识[J].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5(12).
[4] 严纪华.弃儿的家庭传奇——论张爱玲《茉莉香片》[J]. 华文文学,2009(4).
[5] 王源.从其个性心理结构解读张爱玲的文学创作[J]. 山东社会科学,2009(10).
(特约编辑 杨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