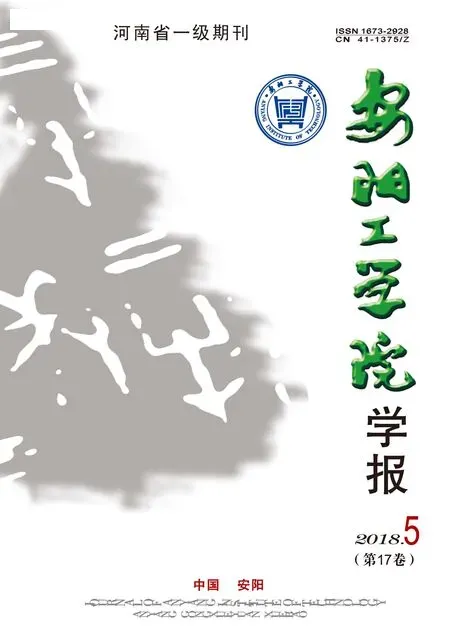冯梦龙情教论与“三言”婚恋题材研究
2018-01-01张园园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安阳45000
张园园(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安阳45000)
冯梦龙的情教论不仅是他的文学创作观,也是一种世界观。这种观念主要集中体现在他的《情史类略》中,也渗透在他所收集、编辑、创作的拟话本——“三言”之中。本文通过分析情教论和其在“三言”婚恋题材的体现,立足哲学层面,阐释这种思想在当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从而为读者了解晚明时期的文学风尚提供一个窗口。
一、情教的特点
(一)情教的本体性
傅承州认为,“冯梦龙‘立情教’,就是要创立一种与佛教、道教一样的宗教。”[1]不可否认,情教的确有一种宗教的成分融入里面,但其思想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冯梦龙在《情史类略》中指出: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法。”[2]1
冯梦龙认为,情是世界的本源,是世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万事万物由情构成,万物因为情而生生不息。这虽然含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是他却把情这一理念提到了对世界本质认知的高度。这在明代以理统治人们思想的时代,确实是一种振世之音。他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即是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开展的。
情的内涵是极其抽象的,那么冯梦龙是如何找到立足点,使得情能够变得具体形象的?冯梦龙是从“六经”经典出发,总结出其中的规律:“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以情始于男女……”既然“六经”在整个社会中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从男女开始,那么情教由男女之情生发,自然也不会受到统治集团猛烈抨击。这样他的情教论就有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当然,他提出的情教与“六经”之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两者不能混淆,否则就失去了冯梦龙思想上的创新性和突破性。正如宋克夫指出:“冯梦龙提出道德修养正是基于对情的因势利导。没有‘情’,也就谈不上纲常和秩序,社会就将失去一切行为规范而处于混乱之中。”[3]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情的发展脉络,他从男女之情出发到家庭人伦,继续向外拓展,编织成一个情组织网络。这样,情的内涵就逐渐丰富起来,由单纯的男女之情衍生出整个社会伦理以及宇宙世界。因此,他的一部《情史类略》是“情的法典”。他在“三言”中,塑造了众多的爱情男女,婚恋主题也成为“三言”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情教的教化性
冯梦龙树立的情教世界观,一个重要的用途是用情来教化百姓。他试图把情教提高到与传统儒家经典同样的高度,从而起到教化育民的作用。在《情史序》中,他强调:
“我死后不能忘情世人,必当作佛度世,……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虽事专男女,未尽雅驯,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善读者可以广情,不善读者亦不至于导欲。”[2]1
在这段话中,冯梦龙鲜明地表明了要用情来矫正当时的浇薄世风。无论是谁,当看到他的作品时,都能够变无情为有情,变私情为公情,最终形成一个“有情”天下。这种推广情教的途径是由内而外,由小变大,由男女到家庭再到国家。与当时统治者统治人们思想、行为的手段的强制性、被迫性截然相反,冯梦龙更多地采取依靠唤醒个人的意识,最终达到整个人类道德的觉醒,这种观念与他在“三言”中的创作意图殊途同归。《警世通言·序》十分鲜明地表明了冯梦龙的态度。
“《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于是乎村妇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4]
冯梦龙主张通过通俗文学向愚夫愚妇、村野农夫进行道德教化,发挥通俗文学的力量,把通俗文学这种文学样式提高到了和儒家经典同样的高度。嘉靖年以后,通俗小说的刊刻印发在读者群中受到了强烈的反响,冯梦龙继续发力,充分发挥通俗小说的长处,扩大其影响力。
冯梦龙认为,通俗文学能够很好地发挥其启迪百姓、教化风俗、规范道德的作用。如果我们把通俗文学看作是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冯梦龙的情教就是通俗文学的主体内容,二者相辅相成。基于这样的目的,他所倡导的情教论,面向的读者群是社会基层民众,他们具有学识水平不高、喜奇好猎的特点,而冯梦龙的作品在题材上大都是反映市民阶层生活,贴近普通民众的,二者在手段、目的上具有一致性。
(三)情教的自然性
冯梦龙的情的内涵是丰富的。由男女之爱情逐渐扩展到世界生灵万物。他总结出一切万物都来源于情。但是,冯梦龙的情与“六经”所讲的情是有很大区别的。罗宗强认为“六经于情,是约之以礼;而梦龙要导的情,是本性之真情”[5]。
情是发自人心中的一种无意识。情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无所不在,遍布在整个自然界中,万物都有情。情是无影无形的,它可以幻化成任何事物,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情还具有穿越生死的力量,能打破生死的界限,这又与汤显祖的“至情观”一脉相承。冯梦龙在《情史类略·白女》中提出:
“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又能生之。……夫男女一念之情,而犹耿耿不磨若此,况凝精翕神,经营宇宙之魂玮者乎![2]310
情是世界的本源,它不会因为某物的灭亡而消失,它永久存活于这个世上。情既然是万物的根源,是生灵的主宰,而人之情也是不可磨灭的天地生灵之物,那么就不能用客观存在的“天理”对人之情进行约束。理学把理和欲对立起来,利用外在的理实现社会统治,压制甚至摒弃人们内心的欲,实现所谓的社会伦理道德。这并不符合人的本性,长此以往,只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变质。而情就不同,它是在尊重人的自然情感基础上,适应人之情并对其进行引导。冯梦龙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理学引导下的道德规范的不足。
冯梦龙以为,情是判断人们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的标准,只要是以自然为纽带或者是真情,都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所以他在《情史类略》中收集了各种类型的情,例如“情贞”“情缘”“情仇”“情侠”等。但是,实际上,他所提倡的情仍然处在封建礼教的框架内,比如“女性守贞”“一夫多妻”等一些内容,按照现代家庭观来看,具有一定落后性。这与冯梦龙的身世、当时的社会思潮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情教论在“三言”婚恋题材中的体现
(一)追求真情,抨击纵欲
“真”是冯梦龙情教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是判别是否有情以及是否达到“至情”的最大前提。在“三言”中,冯梦龙收集整理编辑了众多的青年男女在追求情的道路上的众生相,反映了晚明时期市民阶级对于婚恋这一重大问题的观念。
《卖油翁独占花魁》描写了妓女莘瑶琴对真爱的追求和选择。莘瑶琴见惯了风月场上的虚情假意,卖油郎秦重的出现,让她感受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当吴大公子对莘瑶琴人格尊严进行侮辱,逼得莘瑶琴走投无路时,秦重的出现不仅挽救了她的性命,也温暖了她的心,于是她主动选择了秦重。秦重没有钱、没有门第,甚至连他的职业也是不齿的,可是他有一颗尊敬他人善良之心。正如莘瑶琴所说:“以后相处的虽多,都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看来看去,只有你是个至诚君子。”[6]莘感受到了秦对她人格的尊重,不比其他浮浪子弟玩弄她,才使得她最终要“真从良”。
《卖油翁独占花魁》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尾,可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的命运却是爱情的悲剧。杜十娘当初在那么多的“风流少年”之中选择李甲,主要是因为他忠厚赤诚,两人也是相谈甚欢,情投意合。结果,由于李甲的性格懦弱,最终在家族和爱情之间,辜负了杜的“真心”,引发了杜十娘悲惨的结局。
冯梦龙在追求真情的基础上,鲜明地反对纵欲。由色生情,由情生淫,情与色、欲联系非常紧密,但不是一个概念,他们的界限就是是否有真情。冯梦龙歌颂的是在爱基础上升华出来的情,而对于由情滑向欲则表示明确的批判。纵欲和妒色都是没有情的因素或者没有情的基础,他们是“假情”“虚情”,贪图的只是肉体的欢愉。他在《情史类略·情痴》指出:“夫情近于淫,而淫实非情。今纵欲之夫,获新而置旧,妒色之妇,因婢而虐夫,情安在乎!惟淫心未除故耳。”[7]《小夫人金钱赠年少》《蒋淑真刎颈鸳鸯会》《明悟禅师赶五戒》《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乔彦杰一妾破家》都是对于虚情、纵欲的反映。
(二)倡导专情,尊敬移情
贞洁是封建时代对女性的一种强制性要求,它在宋代理学盛行的时代兴起,一直延续到清末。明朝时,程朱理学成为统治百姓的一种强硬手段。遵照封建礼教行事,是当时大众女性普遍的心理,她们讲究女子的“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在情感上,追求“专情”,她们的情感固定,不可转移,哪怕要付出后半生艰辛的生活甚至珍贵的生命。冯梦龙在“三言”中也是大加赞赏这种行为。《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阿秀被梁尚宾哄骗,认为违背了人伦,最后选择了自缢身亡。《范鳅儿双镜重圆》中的顺哥因“烈女不更二夫”而自刎而亡,保存了自己对范希周的贞洁。无论是阿秀、顺哥还是金玉奴等,他们为了贞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把成就贞洁烈女作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即使自己遇到了薄情郎,也还会委曲求全和对方一起生活。
虽然冯梦龙对妇女守节表现出赞赏,可是,在“三言”中,冯梦龙对那些已婚妇女再嫁、婚外恋情也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这也是“三言”中光辉的一点。这些妇女能够摆脱封建礼教对她们的束缚,在一段婚姻之上再次追求自己的幸福,远远要比那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追求婚姻爱情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勇气。这些妇人能够再嫁、再恋,冯梦龙并没有苛责他们,而是给予理解。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在丈夫蒋兴哥外出经商之时,结识了小商人陈商。面对三巧的出轨,蒋兴哥不是一味地埋怨、责骂。他试图站在三巧的立场,反思自己:正是由于他常年不在家,留三巧独守空门,不能给予家庭的温暖,才使得她偷情。这种丑事,责任不完全在三巧。最后二人破镜重圆。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娘子,第一次向许宣介绍自己时,就说自己死了丈夫,是个寡妇,主动表明心迹,想和官人有宿世姻缘,而许宣也认为“真个好一段姻缘”。白娘子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寡妇就不敢再追求自己所爱的人,许宣也没有因为爱上自己的人是个寡妇而不接受,他们都认为寡妇再嫁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可见当时很多女性摆脱了“一女不嫁二夫”“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羁绊,开始自主自由地追求爱情婚姻生活。
(三)歌颂自由,谴责专制
爱情作为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之一,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礼赞。歌颂爱情的作品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封建婚姻的基本模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的结合最终是为了宗庙之事和家族的繁衍生息。父母与媒妁为对方选择对象的标准主要是从本家族的利益出发,很少考虑青年男女的感情。在“三言”里,冯梦龙歌颂的是青年男女自主选择的爱情婚姻,对那些阻碍青年男女爱情的势力给予了批判。
《乐小舍拼生觅偶》中的乐和本与邻家句顺娘青梅竹马,可乐家母亲却认为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最终乐和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力量赢得了顺娘的爱情,成就了美好的姻缘。冯梦龙也评价“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的素香身为女性,勇敢机智,主动追求爱情。她青睐的是舜美的才,而不是钱,为了避免两地相思之苦,她竟主动提出了和舜美私奔。
三、冯梦龙情教观的哲学阐释
冯梦龙生活的年代大概是明代万历二年(1574)到清代顺治三年(1646)共72年。历史上称这段时间为晚明时期。晚明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资本主义潜滋暗长,不断发展壮大。政治腐朽、经济繁荣,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极大的不协调性,影响到了哲学、文学领域,很多文人拿起笔杆开始对那个时代进行抗诉。禁锢的理学思想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姿态。通俗小说创作的兴盛,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文化娱乐方式。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冯梦龙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一)理学的继承与传播
冯梦龙出生在苏州,从小学习“四书五经”,致力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然而他一直到57岁还是位秀才。在1620年至1627年间,他陆续编纂完成“三言”。《情史类略》大概成书于崇祯初年。作为一个士人,他自然受到传统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明太祖即位后,就把朱熹作注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教材,各种伦理规范被提升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必须遵照执行,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对女性的约束到了极致。明史中,《烈女传》记载的人数是最多的。
明朝建立之初,朝廷通过政治手段对女性婚姻、生活等方面进行了强制性约束。当时女性通过守贞洁既可以获得精神性的表彰,又可以获得一些物质性奖励。因此在明朝,仅有史册记载的女性就有上万人。冯梦龙作为受到传统教育的文人,自然也会受到理学的影响。他逃脱不了他生活的时代,无法超越那个时代,当然也不会彻底突破统治思想的藩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理学的继承传播者。
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婚姻问题时,青年女性一般以守贞作为处理婚姻问题的重要手段。《大树坡义虎送亲》中,勤自励在外当兵,与未婚妻潮音一直没音讯。当潮音父母劝她改嫁时,她义正词严道:“爹把孩儿从小许配勤家,一女不吃两家茶。勤郎在,奴是他家妻;勤郎死,奴也是他家妇。岂可以生死二心。”[8]只认作丈夫真死,在家守孝三年,整日素衣蔬食。《陈多寿生死夫妻》中,朱世远夫妇的女儿也具有相似的认识:婚姻都是命中注定的,坚决反对改嫁。这些女子,从未与自己丈夫见过面,双方根本不知道对方的样子、脾气、性情,可以说是“无情”,他们立志守贞不是出于“真情实感”,仅仅是成就自己的名节而已。这样的婚姻命运,以现代眼光看来,令人唏嘘,可是冯梦龙却仍对她们给予称赞,“三冬不改孤松操,万苦难移烈女心”。
冯梦龙以一个道学家身份,向他的教导对象愚夫愚妇宣扬礼教,一方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与从小受到的教育、浸染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二)心学的传承与发扬
在理学盛行的明代,陆九渊创造的心学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哲学思想颠覆了理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冲击了人们的思想,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轰动。生活在其中的冯梦龙和心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冯梦龙的家乡江苏是王阳明心学的繁荣之地,包括唐顺之在内的一大批心学学者在这里曾经居住。泰州学派是王阳明心学最大的分支流派,其创始人王艮祖辈也曾经在苏州居住。可以说,江苏之地是心学学者聚集之地,也是心学交流传播的重要根据地。生长于苏州府的冯梦龙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冯梦龙对王阳明特别推崇。在《三教偶拈》中,他指出了对王阳明推崇的原因:
“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9]
在此,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王阳明的推崇备至。
影响冯梦龙思想的另一个心学大家是李贽。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振聋发聩的言论,尤其是童心说。李贽认为童心是人类天生就具有的能动性,凡是人生来就具有的能动性,都是属于童心的范畴,只有出自真情实意才是童心,否则就是假意。这样的说法与冯梦龙的情教论如出一辙。李贽主张人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有追求欲望的权利,每个人都应当受到尊敬。作为李贽思想的接受者,冯梦龙在“三言”中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
冯梦龙所展现的市民阶层的婚恋生活形态,不仅仅局限于传统,还塑造了许多青年男女自由追求爱情、寡妇改嫁的人物形象。男女在择偶标准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性强化了对男性的品格、才学、相貌的要求,淡化了对门第、财富的追求,而男性弱化了对贞洁的约束,强调了对性欲、情欲的肯定。幸福美好稳定的家庭生活方式是以男女双方相互尊敬、深厚的感情为基础的。“三言”中的风尘女子,她们虽沦落风尘,但一旦遇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就誓死守护;她们常处于男人世界中,更懂得男人品性,在选择配偶时,会变得更加谨慎小心;她们与良家女子一样,有对爱情的追求,对家庭的渴望,所以他们一旦看中了某个男人,就会倾其所有,付出全部真情。当然,这与冯梦龙对风尘女子的倾向性、时代对女性约束性的逐渐松懈有关。冯梦龙对这类女子寄予了深厚的感情,并且用非常细腻、真实的手法表现了妓女的婚恋生活,对她们的命运深表关注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