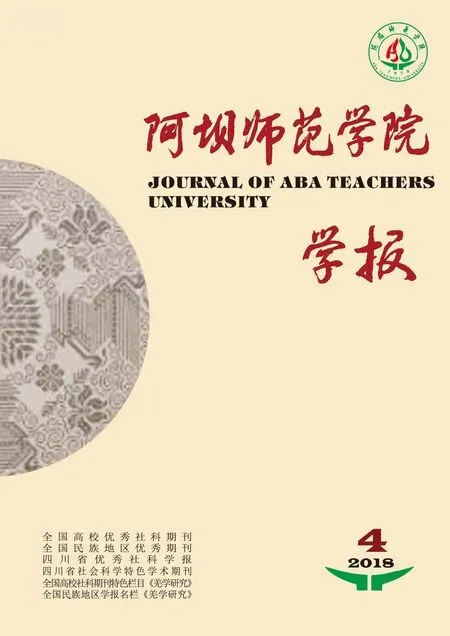1980年以来“《周易》与中国文化”研究述评
2018-01-01何则阴张飘月
何则阴,张飘月
《周易》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之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今人研究《周易》之“文化”向度的成果甚丰。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喜忧皆有。喜的是,一些研究成果能够在新时代阐发《周易》文化精神原貌,可以给当代国人带来多维的文化影响或积极的心理启发;忧的是,一些学人自己未能读透《周易》,认识片面,阐释粗浅,推出了一些违背《周易》之文化精神原貌的论述。笔者忧后者之背离,虑背离之误传,更忧虑此类成果会对今人或后人带去精神层面之贻误。于是不惜耗费精力、笔墨,梳理诸多研究成果,分析得失,力求阐述当代研究《周易》文化精神之应有方法①。
《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易经》为64卦之卦象、卦辞、爻辞介绍。爻辞含有古人蓍占记录或阐释。《易传》即常说的《十小传》:《彖传》《大象传》《小象传》《文言传(乾坤)》《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与《杂卦传》。《彖传》阐释每一卦的经文,以断一卦之义。《大象传》解释卦辞,《小象传》阐释爻辞。《文言传》包括《乾文言》与《坤文言》,它们专门对乾坤卦爻之文、理之意进行阐释与引申。《易辞传》通论《周易》之作者、成书年代、创作过程、运用方法、八卦起源、《周易》意蕴、功能与筮法情况。《说卦传》论述圣人创立八卦的方法、作《易》的初衷与目的、八卦的对错、方位、本象、引申象等内容。《序卦传》解释《易经》通行本何以如此排序。《杂卦传》以错卦、综卦相对应的方式来阐述64卦。虽然《易经》之中没有出现“文”或“化”字,但是不能因此认为《易经》就没有阐述“文化”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易经》的每一卦都从某一角度蕴含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由此产生的“《周易》与文化”研究成果较多。
张岱年先生先后两次对《易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张先生肯定了《易传》所揭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永恒之变等文化精髓,也肯定了天道论等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深远影响。1984年,张先生撰文指出:《易传》因依托孔子,而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易传》之中,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思想虽然交错并存,但其中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才是《易传》思想的价值所在;《易传》之中提出的那些精粹深堪的观点,启迪了秦汉以后的进步思想;《易传》的辩证思维与变易观念,是中国文化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思想基础[1]。1991年,张先生又论述了《周易》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周易》不仅为汉、唐、宋、明文化学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还能给当代以深刻启迪。由于张先生阐述《周易》与传统文化关系时,是立足《易传》来论述的,因此该文实际上也可看作是论《易传》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成果。他分析,《周易大传》十篇提出了博大深微的天道论,其中的一些精粹思想具有历久常新的义蕴,具有令人赞叹的感染力,因而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2]。当然,张岱年先生认为《易传》依托孔子的观点,目前学界对此是有争议的②。
一、《周易》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述评
关于“《周易》与文化”的研究,成果丰富。择要归之为三类:一是论及《周易》对中外文化的影响;二是主要论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及未来的影响;三是对研究方法的反思。
纵观相关成果,关于《周易》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学科学角度来讲,学界主要立足于文明史(蒙培元)、符号学(苏智)、文化发生学(张立文)、文化学(程建功)、文化史学(余敦康)、比较文化学(孙尚扬)、存在主义(尹旦萍)、现象学(苏状)、政治学(谭德贵)、宗教学(张泽洪、张悦)等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另有王新春、刘光本立足《易传》的“人道”,撰文分析了《易传》论“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提出人的本质特征在于人文,社会人生的真正希望在于人文精神[3]。此外,还有从思维方式方面进行研究的。如:整体思维或系统论(邢媛、王胜国)、思维模式(施炎平)。这些成果引导我们对《周易》展开进一步的学习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方法。若从研究本身是否立足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语境而言,以上研究成果大致又可分为三类,即:立足于传统文化本身的研究、借鉴西学立场的研究、立场不明确的研究。
一般来讲,具有明确的中国文化语境立场的研究,比较容易得出符合中国文化、周易文化事实与特征的成果;而依于西学立场,就比较难于做出尊重中国文化或周易文化自身的成果;而那些立场不明确的研究,其成果就更难体现中国文化或周易文化的本真面貌。大致说来,若立足纯粹的西学文化立场进行研究,由于它们只能借助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参照体系来解读中国文化,多半会带来误读。若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比较容易做出较有价值的,或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因为,它至少尊重了中国文化的本真精神。如若能够进行中西合璧式的研究,当然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期待。中西合璧式的研究是指,在研究时可以借鉴西学研究方法,但同时在研究前,必须将某种研究方法,进行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改造。所以,这种研究方法难度很大。因为,它对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学术方法、学术积累等都要求很高。文以载道,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引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可能性,值得学人关注。
(一)立足于传统文化本身的研究
就《周易》与文化做出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张立文、蒙培元、张泽洪、施炎平、王胜国、邢媛、程建功、罗炽、孙尚扬、余敦康、刘大钧等学者③。张立文先生先后于1988年、2010年研究介绍了《周易》的时代、作者以及符号情况,立足文化发生学角度,探讨了《周易》与中国文化之根的问题,从《周易》与儒家、《归藏》与道家、《连山》与墨家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他阐述了《周易》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周易》与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两大内容[4]。他指出《易经》既是卜筮经验记录,又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5]。蒙培元、张泽洪等从中国文明史、中国文化思想史等角度,分析了伏羲“始作八卦”的意义、《周易》八卦符号的来源等。蒙培之先生撰文指出:中国的“人文始祖”伏羲“始作八卦”,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八卦揭示的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整体思维,“始作八卦”是中国文字创造的开端[6]。张泽洪、张悦以道教和西南少数民族禹步为例,分析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周易》,是道家道教思想的重要来源,认为《周易》的八卦符号,揭示了先民对自然界阴阳运动规律的认识[7]。这类研究是基于《周易》本身的,提出的认识、观点确实可信。施炎平先生主要立足儒学,阐述了《周易》对国人内在文化基因的塑造及深远影响,以及对国人“顺天而应人”思维方式的塑造。施先生认为,立足“经典周易”(《易经》—孔门儒家—《易传》),遵循“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路径,发展出国人“顺天而应人”的思维方式,凝结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种基因性因素。长期以来,它们对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思想特质起着深远影响[8]。《周易》对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还塑造了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如王胜国与邢媛。王胜国文概略地提及了整体思维。邢媛的论文不仅分析了整体思维,而且还阐述了洋溢在整体之中的“交泰”智慧。王胜国分析并反思了《周易》整体系统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9]。邢媛等通过阐明《周易》的宇宙论和天人观,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系统智慧,并对其文化学意义作了尝试性阐发。《周易》认为,宇宙是一个森然有序、变化日新的全息开放系统,天与人是一个休戚相关、双向互动的交泰和谐系统。《周易》的这种宇宙论和天人观所显示的系统智慧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10]。这些成果都把握住了《周易》文化的根本精神。其实,可以认为,程建功的研究与王胜国、邢媛的研究一脉相承。因他强调《周易》的整体性、《周易》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一体性,与前两成果相类。他提出,应从文化学角度对《周易》进行研究,故宜从《周易》的整体思维方式、“经”“传”“学”关系、研究的方向及方法等方面,对《周易》与传统文化的互相渗透及影响,从整体上进行基本梳理和探究[11]。正因为《周易》阐释的是整体思维、系统思维,是有关天道、地道、人道的全方位的内容,也正因中国传统文化是整体的,所以,《周易》才会对后来各个学科带去深远影响。罗炽先生就论述了《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全方位多角度影响。罗先生指出,《周易》是一部经过长期积淀的“圣典”,中国文化中的各种观念,甚至各个领域,如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宗教迷信等,都有《周易》的遗传因子。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决定性的影响[12]。按照《周易》,圣人作爻画卦,首先是为体认天地人三道,但更是为启迪蒙昧、教化人文,实现人文化成。孙尚扬先生对《周易》之中化成人文的人文精神,认识深刻。他立足“人文主义”视角,以《易传》为例,提倡以具体、细致的比较文化学方法取代笼统、大而无当的研究,比较分析中西人文主义的异同。他认为《周易》经传中的教化理想(目的)、内容是圣人意识,与古希腊重培养人的公民意识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不同的[13]。诚然,《周易》也有对万民教育的层面,但都是以成圣、成贤、成君子为旨归。即教育平民不是让他安于平凡,而是要志在圣贤。这确实与西方文化教化世人安于凡俗,乐于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有很大的不同。
也许是对以上这些分学科研究之弊有预见的缘故,余敦康先生提出,提倡超越学科学的研究。余先生指出,要以一种广义文化史角度,即能够超越卜筮、哲学、科学(天文历法)、史学的角度,来把握《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14]。这是一种不为现代学科所囿的研究方法。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本来文史哲不分、人文与科学不分、社科自科不分、文理不分。余先生的观点更为切合中国传统文化实际。此外,刘大钧先生提出“中医”并非“中国医学”的简称,而是医、《易》结合的概念,这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当做一个整体进行思考、研究的典范。刘先生进而提出,以“中”这一思想来医疗、平衡人体,以恢复健康[15]。这很符合中国传统医学的实际情况。
(二)借鉴西学立场的研究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借用西方文化、哲学的研究方法,对《周易》之文化精神进行研究与揭示。这其中,大致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得出的结论不够全面,如尹旦萍的成果;二是论述不够深入或易带来误会,如苏状、张立文、苏智的研究成果。尹旦萍发掘了《周易》的生存智慧,分析了这种生存智慧对中国家训文化的影响[16]。该成果揭示了《周易》对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个方面。苏状力图对《周易》的文化智慧进行现代解读,他发现《周易》背后潜行有一种文化智慧特质,即“一种日常性”,他认为,正是这种日常性,是真理存有和发生的场,促成了中华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的持久张力[17]。这一研究成果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它阐释了《周易》所揭示的天道、地道、人道,已内化于国人血脉之中,达到了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境界;另一方面,若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这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提倡的要“行”“履”“习”的实践性,或言强调修身养性的“修”与“养”,即学问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书本里、文字里。苏智利用符号学理论,引入“文化中项”概念,分析了“文化中项”在《周易》价值建构之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周易》所倡导的儒家“中庸”思想,实际上也是在向中项所认同的正项价值靠拢的表现。《周易》从价值观念到实践方法,都体现出了文化中项对其价值建构所具有的重要作用[18]。该成果借用“文化中项”这一西方文化理论,肯定了《周易》具有的理论建树特点,同时淡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貌。张立文先生2013年撰文论述,《周易》与《圣经》、《吠陀经》、《古兰经》被誉为世界“四大经典”。该文观点丰富,影响深远。该文认为,《周易》第一次把文明与人文联系起来,具有“保合太和”精神,天地万物由“和实生物”而来;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精神;思维方式的大智慧,如太极思维、变通思维、道器思维;民族精神大智慧,如与时偕行精神、忧患精神。最后,他提出,要让《周易》智慧在我们生活中继续“活着”[19]。张先生梳理了《周易》中潜藏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其论述也有一个致命的不足,就是把现代“文明”植入了《周易》“文化”精神内涵的论述之中。具体详见后文分析。
(三)立场不明确的研究
有些成果,研究立场不够明确,没有顺应中国传统文化、周易文化本身的具体情况,从而对《周易》本身把握不深、不准,进而得出了一些违背《周易》文化基本精神内涵的结论。这些结论无疑会对《周易》经典之阐释带去一些不良影响,如王志跃与谭德贵文。王志跃撰文认为,《易传》抛弃了《易经》的宗教神学内容,继承了《易经》的符号系统,并保留了《易经》以天道切合人道、天人贯通与神人合一的基本精神,认为《易传》的基本精神属于吸收了道家天道观的先秦儒学范畴,是儒道思想文化合流的结果[20]。该论述有自相矛盾之处,《易传》既然保留了《易经》的“神人合一”,又如何是抛弃了《易经》的宗教神学内容呢?也有认识不够准确之处,如关于天道切合人道的论述。如若深入研读《周易》全文,我们会发现,《周易》阐释的是中国古圣先贤,对天地、宇宙、人生规律的认识、模拟与顺应,以及在顺应天道、地道的前提之下,充分发挥人之主观能动性,而实现化成天下的人生理想的一种模式。因此,只能是人道切合天道,而不是相反。而且,即使其中描述有我们今人难以理解的神秘的一面,但也不能遮蔽古人对于人之理性、主观能动性充分信任与发挥的主流思维模式。谭德贵立足政治思想视角,分析了《周易》的政治思想及其影响,认为《易传》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传统专制的理论基础,与《易经》的先天平等思想有着重大冲突,提出这是中国政治传统文化的秘密所在[21]。从《易传》中读出“专制”,应该说是一种不全面的、望文生义的误读。《周易》的本质强调阴阳和谐。如果是“专制”,怎能还有和谐呢?此外,《易传》强调人文化成,即使是圣贤、明君等可能成为“专制”主,但他们也必须顺应天地人之道,必须是顺势而为、顺性而为。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怎么可能会有提倡“专制”的思想呢?
二、《周易》对当代文化及未来影响的研究述评
研究《周易》与当代文化之关系的有张崇琛、向达、张烦烦、赵玉强等。张崇琛探讨了《周易》的文化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他认为《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与发扬运用。如其中蕴含的整体意识、变化发展思想、相反相成意识、和谐意识等文化价值,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等[22]。这些精神价值,值得当代人进一步挖掘与发挥。而向达、张烦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作是在这一方面所做的深入研究。因为,该成果特别强调了《周易》的和谐思想,从宇宙观层面、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层面、实际操作层面分析了《周易》的和谐思想,认为其和谐理念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思想财富,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启迪良多[23]。《周易》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对当代带来积极影响,也有对人未来生活的激励与引导,如赵玉强论述的《周易》的希望品格及其文化价值。他认为,《周易》的希望品格是指《周易》在时间之维中展现出的,对未来昂扬自信、积极乐观的精神气象与文化面貌。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开掘《周易》的文化内涵具有基础性意义。他分析,《易经》卦爻辞中,吉辞多于凶辞,并且多有凶转吉的论述,这也传达出一种对未来的自信与希望。《易传》进一步在哲学理路上,从天道、人事、愿景等方面系统展现出了希望品格[24]。这说明,《易传》不是仅仅关注一件事情在某一时间点的吉凶祸福,而是更为提倡人之主观能动性的把握与发挥,更注重人之修养的养成。有关《周易》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论述对世界文化的深远影响或伟大贡献的,如张立文、蒙培元等。张立文认为,《周易》数千年来,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5]。蒙培元认为,《周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命的和谐,既是古老的,又是很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文化,具有永久的价值,他认为这是伏羲所开创的周易文化对人类所做出的伟大贡献[6]。纵观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发现,研究方法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研究观点。所以,反思研究方法,是研究展开之前应当完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三、《周易》研究方法反思
研读、反思以上研究成果,取用何种方法来研究《周易》,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方面,笔者非常赞同李学勤先生的观点。他指出,“应该按照中国文化本身的结构、途径和方法来看易学带给它的作用,由之进一步论述了易学对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25]。只有这种立足《周易》本身之内涵的研究才是《周易》式的研究。到哪儿去寻找中国文化本身的结构呢?笔者以为,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依凭原典文本;其次是不能离开古人的实践背景、生活背景与认知体系。笔者注意到,施炎平先生对《周易》之“神道”的阐述,非常精到,可谓是一个依循文本解读传统的成功典范:
何谓神道?《易·说卦》确立“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的命题,依据八卦观念作出解释,强调在乾坤定位、阴阳辩证互动的条件下,通过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易传》中有多处关于“神明”、“神化”、“神无方(无形)”等的表述,也主要是从彰明天地万物变化之神妙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总体上看,《周易》讲的神道,即神化之道、神妙之道,不同于神意或神灵,更多指的是自然界孕育、化生万物的奇妙莫测的功能[8]。
诚然,在他之前,很多人都把“神道设教”误解为原始的神灵崇拜。但若据《易传》原文,即使当时古人崇拜“祖先神”,但崇拜的非为“祖先”之“神”,而是辞世“祖先”之“神奇”伟业。产生此误解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不加区分、不予说明地套用西方宗教学的“神学观”来研究《易传》中的“神”字;二是或许没有读通、读透《易传》文本,臆想论断。
施炎平先生撰文多年以后,仍有学者远离文本依据,论述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如有学者从《贲卦·彖传》“文明以止,人文也”出发,阐述了一段“文明”与“人文”的关系,认为该论述背离了《易传》文本关于“人文”“文明”的基本含义,完全移入了现代人的“人文”、“文明”观。如:
《周易》的《贲卦·彖传》里讲到“文明以止,人文也”,第一次把“文明”和“人文”联系了起来。“止”,朱熹解释为各得其分,指性质、性分。观察天时和时势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刚柔和谐,教化天下。人文与文明是天下普遍价值。《周易》讲人文和文明相辅相成,人文以文明为内涵,无人文精神,就没有文明的行动;无文明的行为,也没有人文的精神。一个文明的社会一定是人文的,一个人文的社会一定是讲文明的。人文精神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关怀,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把握,体现为人对价值、理想、社会、人格的追求,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把握,即是对人的尊重[19]。
以上关于“文明”与“人文”的论述,如若不放在《周易》这一古籍文本的平台之上,看上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若说这是《周易》本身内含的精神,那就很成问题了。因为,若据《贲卦·彖传》全段,哪有现代“文明”“人文”含义的影子呢?“文明”与“人文”可以联系起来,但此“文明”非彼“文明”,此“人文”非彼“人文”。比如,其中讲“人文与文明是天下普遍价值”。那么,这是指《周易》论及的“人文”与“文明”精神吗?是论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与“文明”精神成为当今天下的普世价值呢,还是指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与“文明”精神成为当今天下的普世价值了呢?在这里,是值得仔细讨论与分梳的。如果回到《周易》文本,不难发现,《周易》中圣人法天则地、取象画卦,“人文”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象而已。比如,《周易》中关于“文”有“天文”[26]354、“天地之文”[26]355、“人文”[26]328、“鸟兽之文”[26]357、“文炳”、“文蔚”[26]347等种种“文”。而“文”的含义,《周易》也有明确阐释,为“物相杂,故曰文”[26]360。“物”“物”相间,“物”“物”之间杂然并存,乃“文”之本意。“文”的这一含义与《说文》释“文”为“错画也”含义一致[27]425。《周易》对“文”的用法与《说文》可以互相参考。在这种语境中,若将“文明以止,人文也”理解为“所有的象之中,最美的是人之象”似乎更妥。请看《易传》原文:
“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住”,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6]328。
而最美的“人文”有什么特点呢?“文”为“坤”[26]361,为“君子”之“文德”[26]332,这是在阐释人在天地面前,应当具有顺天应时的柔顺之德。而“文明”呢?按《周易》,可以为“天下”的之“文明”,“天下文明”的原因在于“见龙在田”[26]352。此处“文明”的含义为,普天之下各种纹理、交错现象,因为阳光普照,而全然显明。“文明”还可指代人之“德”。若“人”不与“天地”并论阴阳,人之“文明”之“德”的特点为“应乎天而时行”的“刚健”[26]327。此“刚健”之“德”与上文所论的“坤”德、“文德”相结合,即为圣人、贤人、君子等当具有内刚外柔的刚柔相济之德。此德即为最美“人文”。于是,贯通全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最早的“文”“化”用意,则是指圣人在观察天文地理之时,一方面,法天则地,自我教化、自我熏养;另一方面,依循人之象状、秉性,因势利导,教化世间,以形成新的人象、天象、地象,以致万物之象。圣人教化天下的目标当是“文明以说”[26]330,即是要追求、实现众人和悦的大同世界④。
综上而论,未能深入《周易》文本而进行概略性研究的成果比较常见;而离开《周易》文本,或离开中国文化语境进行剪切式、片段式、移植式研究的行为也较普遍。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甚至是该摒弃的研究方式。笔者认为,当今学人,应该站在当代中西文化的交汇口,融会贯通中国文化的思想渊源与西方研究方法,以提出新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古代典籍的研究。因此,在研究中国文化时,首先当深入古典、回归传统、承载传统;其次是洋为中用、融西入中;最后,方可能发扬传统,以实现返本开新、启迪国人、服务社会与国家、奉献于世界的宏图。笔者尝试从《周易》文本结合中国古文化背景本身去理解其文化内涵,拟另撰文阐释《周易》的文化含义、文化精神。
注释:
①本文研究参考文献主要集中于1984-2013年间,之后的研究成果拟另撰文论述。
②当代易学大家陈德述先生认为,学界史上认为《易传》全为、全非孔子所作,都是“太绝对”且“极端”不可信的观点。比较可信的观点是:即使其中也有部分内容由后人串入,但《易传》“基本上为孔子所作”。因为,无论其中是记叙前人遗文,还是弟子后来记录孔子之讲述,“其思想应属于孔子”。若此,用“依托”一词来表述孔子对《易传》的贡献,显然很不够。参见陈德述:《周易正本解》,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2年,第278页。
③此处的论述主要以成果完成时间为序。
④关于“人文”与“文明”的论述,参见何则阴:《周易与文化创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303-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