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艺品与教品
2017-12-29孙娟
孙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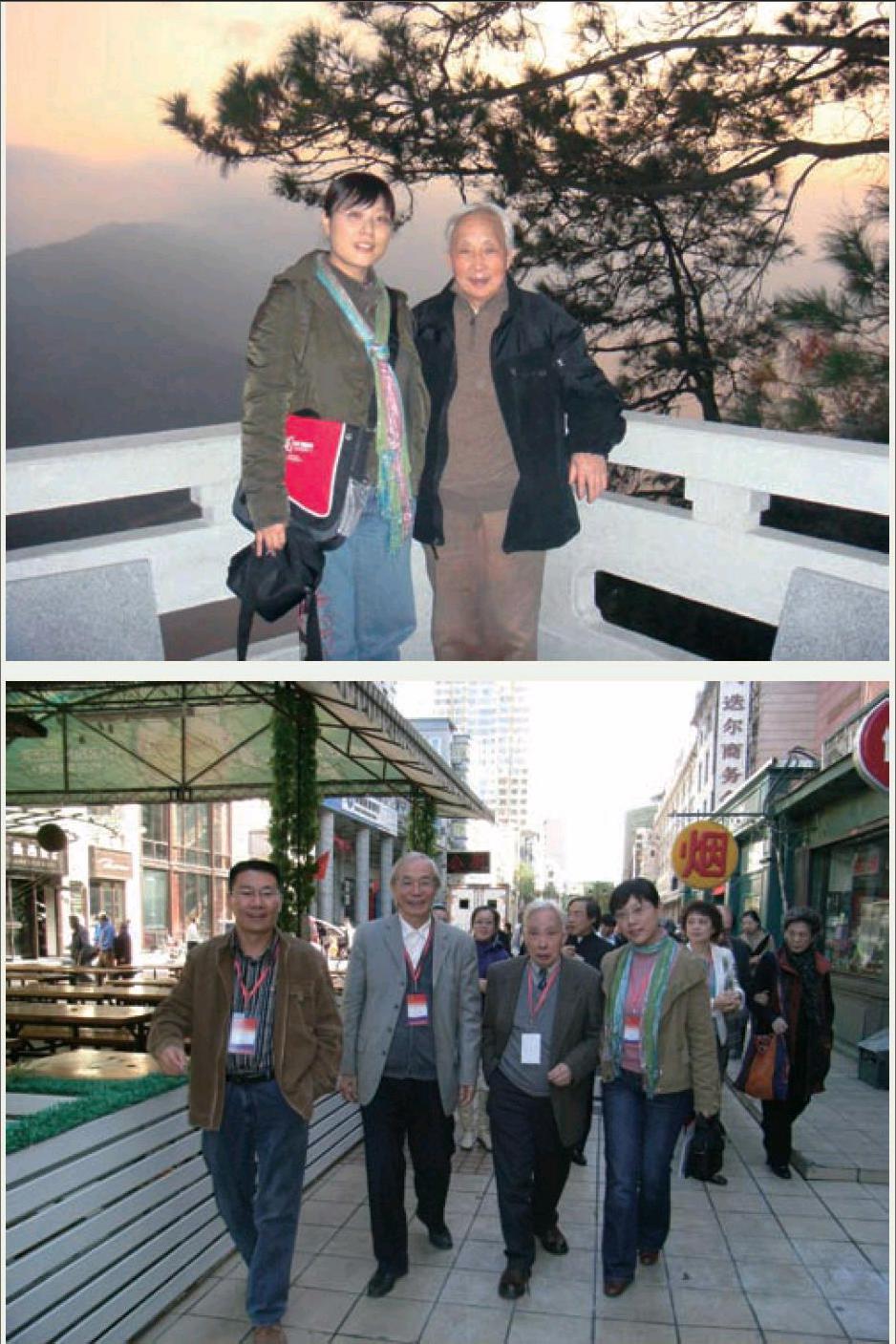

6月25日清晨,我收到了戴先生小女儿的信息,得知我亲爱的导师戴鹏海先生因病已于美国时间6月24日上午9时25分在纽约皇后医院逝世,噩耗传来,悲痛不已!虽然只有三年的博士后经历,戴先生却在诸多方面对我影响深远。这不禁使我思绪万千,往日与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伴随着泪水一一浮现……
初识先生是在2007年。当年我刚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第一件事就是着手完成一直以来的心愿——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跟随戴先生继续学习。早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就通过网络读到先生的一些文章,对他充满敬仰,心想如果能跟先生继续学习,并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该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同时,心中也有些许忐忑——戴先生是国内著名的音乐理论家,而我只是一名刚刚毕业回国的博士“小海归”,他是否能够同意我做他的博士后呢?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我鼓足勇气拨打了戴先生家的电话,戴先生那具有磁性的湖南普通话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询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后,便跟我说他两天后会前往北京到中国音乐学院开会。于是,在中国音乐学院的专家招待所,我第一次见到了戴鹏海先生。只见一位头发花白、严肃儒雅的老人走了过来,在简单的一番自我介绍后,先生直奔主题询问我对于博士后科研课题的想法规划。不知是因为先生略显嚴肃的询问还是他音乐理论家的身份给我带来的压力,我当时竟没有很好地去阐述我的想法,一时相当地惶恐和忐忑不安。戴先生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他有意压低了语调但也不失严肃地对我说,等我准备更充分一些再跟他联系。初初会面,我认为先生虽然貌似威严,但也隐约感受到他和蔼的一面。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准备,我于2008年的10月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的进站通知书。自此,我正式师从戴先生,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为了能提前了解一些博士后工作站的情况,我曾跟一些在其他高校读博士后的朋友们打听过,据说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之间只要把研究课题的大致框架确定好就可以了,不必再像读博士期间每周与导师见面。虽然这种状况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可想着还是得适应国内环境,不要过多地打扰导师。于是我便在办理完进站手续后,开始按照之前博士后面试时的课题框架收集资料,三天后才给先生打了电话。通话中能听出先生对我到上海后没能及时跟他联系有些意见,并表示他要为我在博士后期间的研究及各方面负责,以后最少每隔两天要跟他汇报一下研究的进展情况,若有写好的文字也要及时拿给他看。而且先生善意地提醒我,即使是博士后也要虚心、踏实地展开学习和研究,不得有浮躁之心。通话之后我的内心其实是欣喜若狂的,这正是我需要和渴望得到的教导。于是就这样,我开始了别样的博士后学习和研究工作,也逐渐走近了戴先生,了解了他的人品、艺品和教品,并亲切地称呼他为“戴老”。
戴老有着丰富的艺术经历,在此不再赘述。我想所有的这些创作、表演及导演经历都是他日后涉猎戏剧表导演理论并对歌剧艺术及理论潜心研究、热心撰写的主要原因吧。戴老一生精进,笔耕不辍,除了音乐创作外,1983年遵贺绿汀院长之命回上海音乐学院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后还在国内外80余家报刊上发表了近400万字的大量高水平学术成果以及音乐家全集和年谱长编,文章涉猎中国近现代及当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思潮及创作研究与批评、歌剧史论研究诸领域。
先生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酷爱民间音乐而且记忆力极佳,在他身边经常能听到张口就来的古人古训、警句名言以及满怀深情、饱含韵味的各地民歌。他生活俭朴、自重、崇尚操守、严于律己,面对任何事他都胸怀坦荡,爱憎分明,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讲真话。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拥有时刻心系祖国、心系人民的博大情怀。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传统美德,也是他经常跟我提及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士”的精神。
他的教品、艺品也如同人品一样。对于教学和理论研究与批评也一向一丝不苟,抱着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非常重视学生在研究中的第一手学术史料的掌握,他认为只有掌握了详实的史料,把案头工作做扎实,方能迈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因此,在我着手博士后课题写作之前,戴老给我布置的任务就是收集所有与课题有关的资料。戴老严于律人,更严于律己。有一次,居其宏先生到上海来看他时,还说起他当年为了挖掘某些被历史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曾多次不辞辛劳地往返于京沪之间,每日清晨扎进北大图书馆、中国音协资料室等单位仔细查阅资料的往事。戴老总是强调,要进行学术研究就必须能甘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不管结果如何,只要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潜心挖掘史料,总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戴老的两篇长文《惟史不可以为伪——秦启明(冼星海年谱简编)伪误实录》(《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1-2期连载)和《马思聪音乐活动史料拾遗——兼评叶永烈著〈马思聪传〉》(《艺术探索》1996年第3期)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成为后学重视学习史学研究中的“史料第一性原则”的代表性文献。
跟随戴老学习的几年时间,我注意到,无论是自己的朋友、学生还是领导等,戴老与他们相处都是直言不讳、刚正不阿的。先生在新时期所发表的6篇论文:《应当正确审视历史,估计形势——从吕骥同志的一次讲话和一篇文章谈起》(《人民音乐》1987年第12期,江苏江阴“当代音乐研讨会”即席发言稿整理),《从“王洛宾热”谈到“炒文化”》(《人民音乐》1994年第6期),《民歌岂能出卖》和《答王洛宾先生》(均刊于《人民音乐》1995年第3期)以及《“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说起》(《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和《还历史本来面目——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的“个案”系列之一:陈洪和他的〈战时音乐〉》(《音乐艺术》2002年第3期),不仅是新时期音乐思潮史上三次事件的“导火索”,引发了音乐界大批学者的争鸣,为音乐研究者如何面对不公正之事树立了典范;同时也为后学了解这些事件提供了鲜活材料和典型案例。在学生的学习和写作中,凡是他认为有不认真、不积极或因各种缘由出现的错误,他都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坦言自己是一位“六亲不认”的导师,如果学生不努力,后果要由自己承担,这些都是为了督促学生们更积极、更努力地把科研课题做好,对得起导师和学校的培养,也对得起自己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博士后期间,我非常荣幸地做了一些将老师的手稿录入为电子版的工作。每次录入完第一稿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修改好的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戴老会在原稿及修改稿的基础上添加、纠错甚至是调换段落的顺序。一开始我也非常不解,因为有的语句只是个别字的调换,对整个意思影响并不大,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发问,戴老便会爽快地解释道:换成另外一个字虽然对于整个语句的影响不大,但这个字却是最能体现出语句表达含义的那个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句杜甫的著名诗句就是告诉我们在写作中应该仔细斟酌、推敲你所要表达的意思,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写的文章。至于文章怎么样,那就交给后人来评判吧,但一定要对自己的文章负责。”他还经常教导我们要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一个严谨、负责的学者。我深深被戴老的这种严谨、认真的责任感所打动,并要求自己一定要向老师学习,做最好的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戴老在教学中非常重视音乐理论研究者的音乐实践和听觉积累,他经常给我们提供听音乐会的机会。每年的“上海之春”交响音乐会、“上海作曲家新作品音乐会”,还有一些国外著名交响乐团的交响音乐会我都没有错过,不仅是去听,而且听完之后还要跟他谈听后感,戴老也会对我的观点进行再点评。去上海交响乐团听交响乐排练也是必要的一门课。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次陪戴老一起去昕朱践耳先生的交响作品音乐会的排练。与之前所听排练不同的是,朱先生亲临现场并亲自指挥和讲解作品,那一次经历真的让我获益匪浅。
戴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教学严格的导师,同时也是一位大爱之人。他爱自己的老师,关心同学和朋友,对学生严格之外是关爱和鼓励。先生经常将他的文章、书籍等赠予我,鼓励我勤奋求学,并常忠告我们年轻一代意欲成就事业,既要苦学专业知识,更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学问要先做人,不媚俗、不见风使舵、不违背做人的原则,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记得居其宏先生在《猛士多情方呐喊,书生意气乃独行——为戴鹏海教授80寿诞而作》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更令我感佩的是,以戴鹏海的学识和修养,本可在创造性的学术平台上大展身手、著书立说,但他却偏偏钟情于为老一辈音乐家纂年谱、编文集和作品集——长期以来,独对洋洋史料,甘于默默无闻,翻检抄录、笔耕不辍且乐此不疲,在资料收集整理和实际写作中投入了难以计数的时间和精力。”当我读给戴老听时,他是这样回答的:“那些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做出贡献的老一辈音乐家,他们的功绩理应被翔实地载入史册,我们也该铭记这些音乐家,为此我甘愿付出自己的绵薄之力,這是我应该做的,也必须做好。”寥寥数语,彰显了如此的奉献和大爱!
戴鹏海先生的一生达到了人品、艺品和教品的和谐统一,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他具有中国老一辈音乐家、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独有的人格魅力,他的离世让我们无限痛惜。作为学生,谨以此短文表达对先生的深切怀念。但寸草岂能报春晖,我只有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断学习,充实人生,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