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可贵、可敬又可爱的歌剧前辈
2017-12-29满新颖
满新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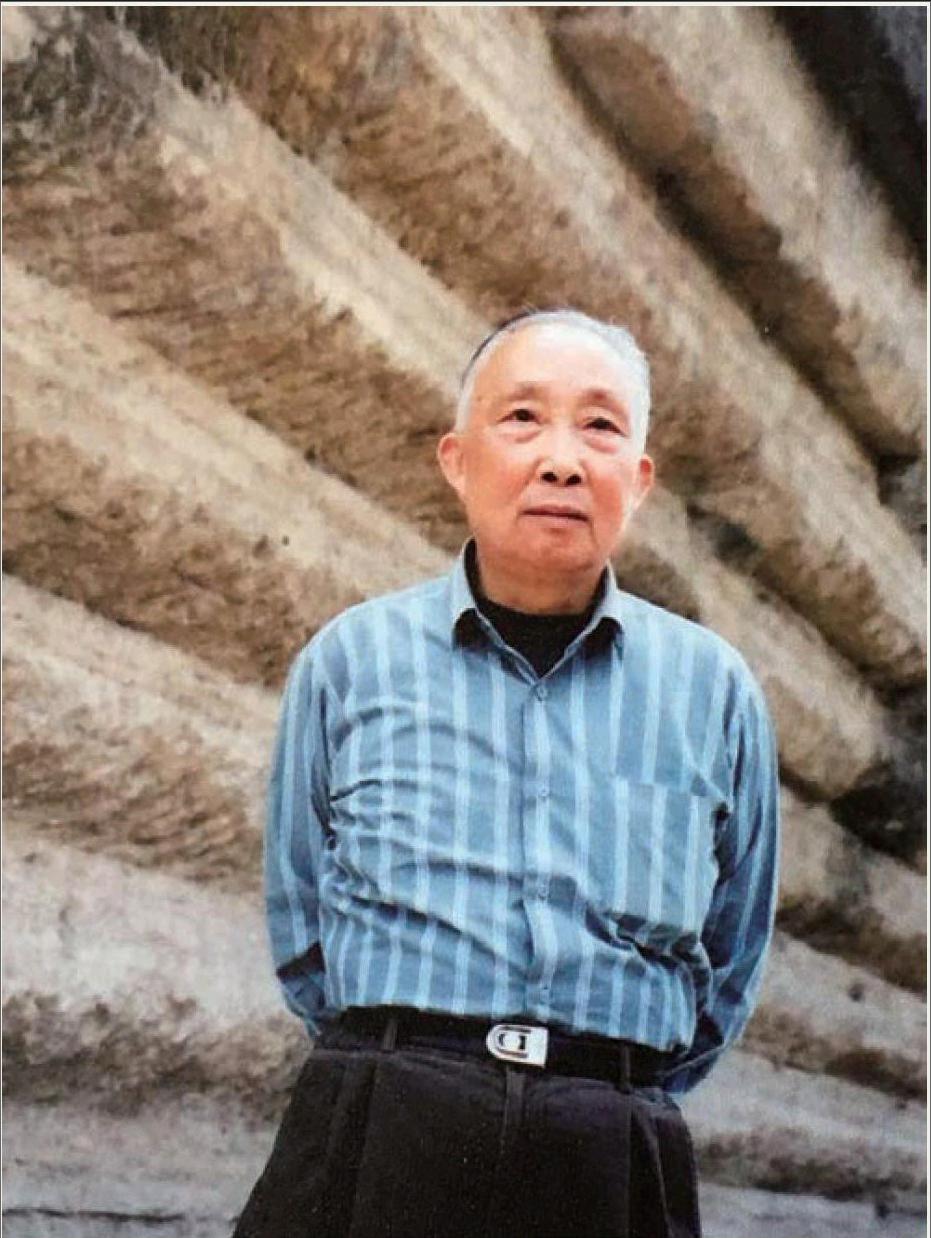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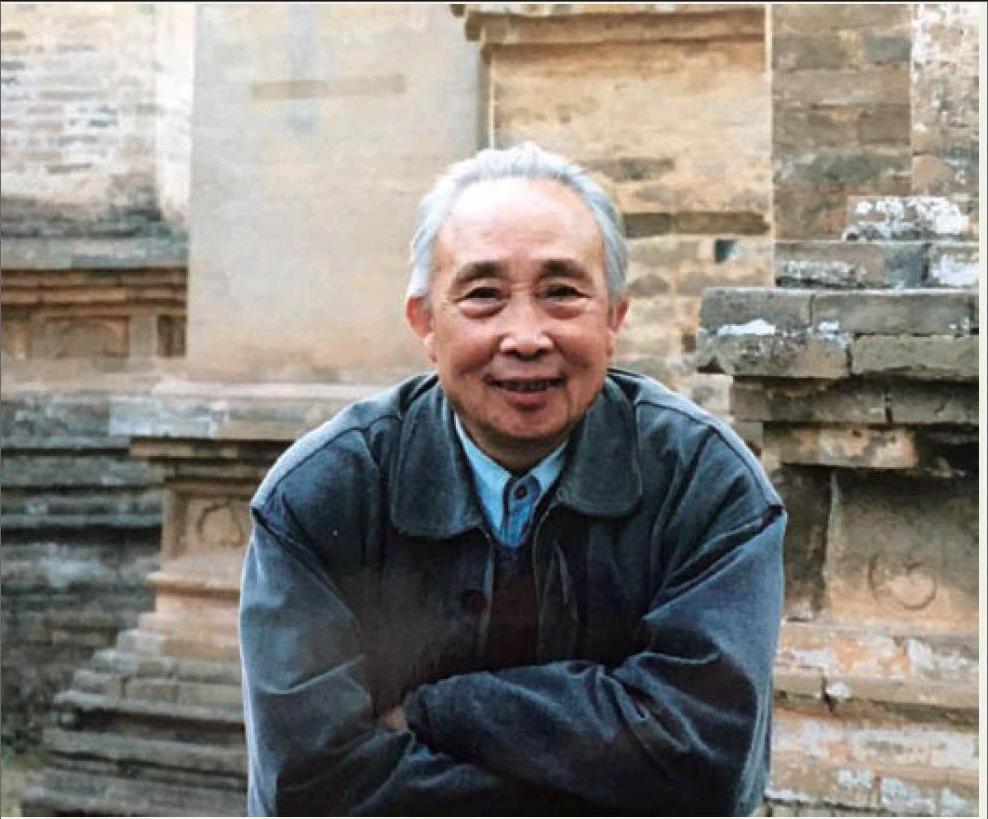
编者按:戴鹏海,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中国音乐史学家,因病于美国纽约时间6月24日上午9点25分在纽约皇后医院逝世,享年87岁。戴鹏海作为《歌剧》杂志前身《歌剧艺术》的编委之一,他与《歌剧》杂志有着特殊的渊源。本期我们特邀戴先生的朋友与学生撰写文章,以便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位大家,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引言
2017年6月24日,音乐学家、评论家,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1929—2017)研究员在美国仙逝。远隔重洋,无法吊唁,我点了蜡烛,把戴先生的书和一个空酒樽摆好,望着手机屏中他那安详的遗容,涕泪交垂。
5年前,我与居其宏先生赴沪为其饯行的情景历历在目。我问戴老,是否需要把他的书房“整饬”一下,他说他“去去就回,放在那里别动,回来好找也好查”。可他竟一去无回!那次,我把喝空的酒瓶带回了南京,如今每望酒樽,旧日里欢聚之声、其屋所飘出的烟气与书霉味一起袭来,每至思源枯竭,虽再也无法骚扰和求诸电话彼端的戴老,但他的神采却时刻浮现,总觉得戴老没走,就在那里。他的真知与深沉的爱,早就化作波涛,跃动在祖国的音乐潮流中。
1998年“上海之春”期间,我到上海歌剧院听导师吴培文教授演唱的歌剧《霸王别姬》音乐会,结束后赵升书教授介绍我去认识一下他的老同事戴鹏海。到了那里我才发现,这老前辈竟是在那样一问又小又黑的斗室里(后因建设需要而拆除)写出了那么多好文章!也就在那次,遇上了当时正欲向侵其著作权的娃哈哈集团讨要说法的、歌剧《阿美姑娘》的曲作者石夫先生。后来才知道,“小黑屋”曾是我博士后合作导师居其宏先生在京读研期间来沪时经常下榻之所。打那之后,直到戴先生去美国与妻女团聚前,我每到上海都要前去拜望。2008年,我来南艺做博士后搞课题的几年里,负责了上海地区的歌剧调研报告,常随居其宏或其他良师益友们往戴老的新居跑。在他屋里,总能见到来自全国各地音乐界名家和同行,还有我们这样去请教看望他的普通学生。
不论在上海,还是在各地论坛,我和戴老碰在一起的次数不算少。尽管常有人怕挨其批评而敬畏他,我却觉得戴老这人实在、可靠。他像块磁石、像座加油站,常给同道以鼓舞和方向。戴老并不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与居师在一起时,常是笑声不断。他谈论作家、作品,到情深之处,那笑到落泪的情景让我终生难忘。这位老人,或许到死都没学会世人最擅长的伪善,老于世故和他没关系。每至开会碰到一块,腿脚多有不便的戴老就得要有个人照应一下,特别是他要去地滑的洗手间时,男生们就有了请教的机会。居师不得空时,就大声疾呼:“小满,快陪戴先生上厕所。”于是我便成了戴老如厕的“护法”之一。而两位尊师又都有抽烟和沾点酒的“坏毛病”,我的确又与他们臭味相投。
戴老与我父同庚,我虽随着居师,但戴先生对我来说始终亦师亦友。出国前几年,他曾因大病而突然住进华东医院。居师闻讯后,立即电告,让刚从北京回南京还不到半小时的我火速赶往上海照顾他。博士后出站后,有一段时间我工作无着落,这可把戴老急坏了,他几乎每周都给我电话问情况如何了。后来才听他私下里对我念叨说,他曾希望我能到他那里做博士后研究。
近20年的交往中,我感到戴先生有着渊博的知识结构、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他做学问勤勉刻苦,对艺术时刻充满激情,就像个朝圣者。那种洞若观火、理性练达的分析与批判能力,是当下学人中罕见的。最特别的是他能一贯坚持真理,有人格、有气度、有文人的一副铁骨,让我倍加折服。即便有时我因为瞎说八道被他臭上一两句,也觉得“蛮爽”,他和居师说,要时刻好好敲打我成块“料儿”。
记得我有一次在大风呼啸的街边和他边抽烟边说事,我没在意他到底是把烟头扔出去了,还是顺手又带回他自己兜里去了(为了控制自己过量的烟瘾,他有时只抽半截烟,然后就立马用大拇指和食指直接捏死烟头,就是让任何人看了这“铁手”,都会担心他手痛,而他却浑然不觉)。我们太顾着讨论问题了,结果走了两步后我竟然发现他的羽绒服帽子开始忽忽冒烟,都快着火了(一定是他扔出的烟头被风吹回了他背后的连衣帽)!为了救火救人,我想都没想,“三下五除二”就把火给扑灭了。过了一会儿,戴老见了熟人他就开玩笑说:“小满刚才在街上打我。”害得大家既要拿我是问,又大笑不止!戴老在生活中是个老小孩!
作为音乐学家和评论家的戴先生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用我师弟的话说就是“你知道的,他全知道。而你不知道的,人家知道得多了去了”。
19g7年,以研究员身份退休后的戴鹏海并不像现在个别官学或博导那样,有大堆学生前呼后拥。我一直觉得,他内心孤苦而寂寞,音乐界好像只有爱读书且更关注当代音乐创作及理论思潮动向的卞祖善、金复载等一些艺术家和老师才对他这个人有兴趣,至于那些大牌演员,或者一向厌恶理论的所谓艺术家们,大多数压根儿就不知他是谁。新时期以来,音乐界读者一般是通过大量书报杂志、学术会议等大型活动和其所引发关注的音乐思潮了解他,但戴先生绝对是位名副其实、老当益壮的时代“弄潮儿”和乐坛宿将——他的影响是音乐界的那些“大官人”所无法企及的。他更是一位有着宏大的历史视野、多项独门绝技和博大真学问的一流理论家。他骨子里充满真性情,又敢于真担当。不少同人更这样认同他:音乐批评界的“当代鲁迅”,是受贺绿汀影响且一样有着“硬骨头”的大先生!
在我印象中,除赵、讽先生是个能过目不忘的理论家之外,其他能过目不忘又能仅听一遍音乐就过耳成诵的,所见甚少。但戴老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博闻强记简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让很多歌唱家不敢相信的是,这个幼年受过学堂乐歌熏染的老夫子,还能把很多意大利歌剧、原文艺术歌曲、俄罗斯歌剧选段信口唱来,别说什么旋律风格,即便是原文音节,他有时也能唱得一字不差!而至于近现代中国音乐家的代表作,他就更不在话下了。
记得戴老在80岁那年来南京开当代音乐学会议(2008年11月)时,我们到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去参观,那里有回声地貌,老人家歌唱的兴致一下子就上来了。当着众人面,他放声高歌两曲,且底气十足,满座不免惊呼这位“跨世纪的少年”。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每每在学术会议或者对着某个历史的片段进行观点阐述或大发自己的感慨时,令我常怀疑他是否修过“入定”法门,他那种气度和阵势,绝对不是硬装来的,而是从他炽热的心里迸发出来的浩然之气。这位理论家,一点都不像其他爱端架子、爱做样子或者一天到晚“装”高度的学者,他绝对是位情感型又兼具詩人气质的人,是“老夫聊发少年狂”。或许有人认为,平素他常给歌剧界一种高高在上的压力。其实不然,导致大家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大概出自两方面:一是我们早就习惯了虚于委蛇的表达;二就在于,他还最喜欢直奔真理而去,厌恶“顾左右而言他”。
这可能与他的家学渊源、一生爱学习、爱求知的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很大关系。
一、全面的素养来自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积累
80岁以上的歌剧圈老前辈中,常自称是“歌剧战线上一名老兵”的人已然不多!但常自我调侃说“早就遁出了歌剧圈”者中,一是戴先生,另一个就是郑小瑛教授。尽管他们嘴里这样说,却无时无刻不关心中国歌剧的发展。他们爱歌剧,早就爱到了骨子里。
“60后”“70后”甚至“80后”的歌剧界从业者,大多不太了解戴先生的歌剧人生,即便一些熟悉他却不太了解中国地方歌剧史的读者,也未必对其歌剧背景熟悉。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浩劫和“因言获罪”的三年大牢,如果不是80年代工作的需要让他转行做了理论,他对中国歌剧的贡献,也许不会仅限于在音乐学理论和评论上的成就。
戴鹏海的父亲戴望峰,是民国时期一位有名的文艺家,与其老乡贺绿汀是好友。而戴望峰曾与鲁迅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剧作家向培良一起,创办过青春文艺社,办过《青春月刊》杂志,还搞过轰动一时的“青春音乐会”。从小学开始,戴鹏海就耳濡目染于新文学、新音乐的文艺氛围之中,他早年的音乐戏剧意识离不开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儿歌表演曲和电影《野草闲花》中的插曲《万里寻兄词》(1930,孙成壁作曲)等作品,小学时他曾多次上台表演,到80多岁时,这些歌曲依然随口唱来。虽然有文学、戏剧、音乐的爱好,但是直到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前,他在表演、导演、作曲和音乐理论四个方面基本算自学。时代文艺思潮和现实生活的需要,让他从实践到理论一步步地积累,一连串探索的脚印最终使他成为了歌剧理论专家。
1947年夏,18岁的戴鹏海高中毕业后就在家自学作词和作曲,像独唱《窗外桐叶黄》(词出自《南京五四周》)和《你又站在窗前》(自作诗)就是当年的习作。1949年9月,他进入湖北省文联文工团(即创作了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湖北省歌剧团前身),1950年就在话剧《思想问题》中先后扮演了于志让和何祥瑞两角色。同年,他又被借调到“湖北革大二部文工团”担任艺术指导,先后导演了《思想问题》、独幕话剧《不能走那条路》,以及歌剧《赤叶河》(阮章竞编剧,1945)和《阴谋》(李鹰航作曲,:1948),这两部歌剧作品颇受当时的群众喜欢。随着这些工作的不断深入,他开始越发自觉地触及戏剧的表、导、演理论研究。除了从独唱、合唱到歌剧的作曲之外,他也注重从人物形象和内心和性格出发,来借鉴话剧的表演手段,同时也注重从传统戏曲创作美学(如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苏联斯坦尼理论体系中汲取营养。
后来,他越加喜欢上了作曲。1952年全国文工团整编时,他响应“下基层”号召,去湖北省恩施地区的鹤峰县文化馆辅导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同时,开始潜心收集民间音乐,进行音乐创作。他以诗人王希坚的词,谱写的一曲湖北民歌风格的《采山花》十分具有地方音调特色。自从1954年首次在刊物上发表曲作之后,戴鹏海更加注重练习大型声乐和器乐音乐体裁的技术理论的学习。1955年7月,社会主义阵营举办华沙“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创作竞赛的作品征集,为了响应上级号召,他与毛侠、刘隆平创作了大合唱《我们的歌声飞向华沙》(同年发表在《长江歌声》7月号上),该曲由华中师大合唱团录了音,被选拔为武汉地区参加申报的三部代表作之一。1956年秋,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本科学习。两年后,他作为编委之一与本系部分师生集体参加编写《中国现代音乐史》,而这一历史机缘和其中的各种问题最终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才被他道出。1960年,他与作曲班同学陈彭年、王久芳和郑碧英三人在邓尔敬教授的直接指导下,以闽西音乐和歌仔戏音调为素材,参与了校方与上海歌剧院联合创作的歌剧《赤胆忠心》(1962年首演)的创作。1961年毕业后,他被分到上海歌剧院创作组任专职作曲。至“文革”开始,歌剧被迫让位给“八大样板戏”之前,戴鵬海已经创作了歌剧《嘉陵怒涛》、小歌剧《借刀》(李林编剧,1964年首演)、《把关》《铜锣记》和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集体创作)、三人舞《新春乐》、独舞《送余粮》。
如今看当时他创作的这些歌剧、小歌剧,多属于民族歌剧的样式,题材上明显带有阶级斗争惯性思维和“运动”时代烙印,都是为当年的政治任务服务的。不仅仅是歌剧从业者,任何艺术家当时都无法从极“左”政治思维定势中抽身而出,每个人的美学思想和歌剧观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性、社会性、历史性及个人因素的局限性。这种情形与他的老乡、好友石夫先生多次慨叹自己《阿依古丽》《阿美姑娘》两部歌剧“生不逢时”,所遭遇到的历史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尽管这些创作有的在“文革”前就淡出了公众视野,戴先生本人也很少提及他的这些经历,即便偶有提及,也被其说成是“无效劳动”。可是,对后半生不断进步和反思的他来说,依然能从创作经验和教训中吸取营养,做个货真价实的中国歌剧理论研究专家,这些苦辣酸甜实属他的个人精神资产。“文革”袭来,一向坚持真理、心直口快的戴鹏海自然也难逃此劫,1970年他被错划为“现行反革命”,与大画家林风眠一起同囚一牢,整整三年失去了自由,受尽知识分子不该受到的各种凌辱。戴老曾多次向我提及,他在牢房里感受到了林风眠先生的人格魅力,他那种“绝不自杀,一定要活下去”的坚韧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和艺术家,需要有向死而生的勇气,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版的太史公。
二、转向歌剧、音乐学理论与批评
戴先生像一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活唱机”,一部“活词典”。他的理论建树绝非“假把式”,而是充满了对研究对象真情实感的认识,有着自己真知灼见的论断。或许这种能力一部分是天生的,可是当我们从其全部人生去领略时,就不难发现这更属于他个人修为的结果。其核心即是当今社会知识人最为欠缺的人生观——追求真理和真相。这是他们这辈民国出生的文化人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尽管大学三年级时的戴鹏海就参编了《中国现代音乐史》的教材,大学四年级时就在《音乐研究》发表了音乐学论文《试论〈幸福河大合唱〉》,从没有师长和同学怀疑其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潜质。但是,我认为他真正潜心从事音乐史理论研究,还在改革开放以后。因为这从其前后论文的比较中就能明显看得出来。这次思想的大转变,促使他对贺绿汀等师辈们的人品、艺品展开了深入研究,而他本人对这十年的各种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反思,“文革”后的斐然成就离不开他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反思与感悟。他因此多次提醒后学:“文章千古事”,文人能老来“不悔少作”,才算功德圆满。
戴鹏海高度总结了他最推崇的尊师贺绿汀的人生特点,即“人品与文品的统一,革命与创作的统一,理论与创作的和谐统一”。这“三统一”的观点不但影响了他本人的学术,也让他不自觉地用这样的标准来勉励和评价其他音乐家及其创作。也许有人认为,戴老对艺术评价的要求太高、太过苛刻。但如果大家静下心来,真正回头看历史,并以经典作品与当下大多数作品比较,就会发现,经典作品和优秀作家,绝大多数符合这个“三统一”。而艺品和人格的分裂,才是时代的大悲剧和个人真正的不幸。当下中国能出产那么多“毁三观”的“称颂体”作品,能传下去的究竟有多少,原因又在何处?这是他常常最揪心的地方。
时代不仅使戴鹏海先生再次成为新时期音乐界最有影响的音乐学家和批评家之一,而且,在中国歌剧理论思潮中,他所关注、参与和倡导的一些艺术和学术批评的理念,都非常具有前瞻性,也有很强的学术导向力。
从1984年开始,在培育《歌剧舞剧资料汇编》(1986年第1期始改名为《歌剧艺术》,现名《歌剧》)杂志走向国内代表性学术平台的发展过程中,戴先生与编辑部其他同事如商易、张汀等人一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此刊一跃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学术杂志。而整个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可谓是中国歌剧相对低迷的一个时期,经济大潮和极“左”的意识形态,从物质到精神层面导致中国歌剧发展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面对时代困境,《歌剧艺术》杂志编辑部长期倡导刊物的对话功能,倡导多元化、多样化和不同艺术观的交流与碰撞。1981年到1987年,国内一部分保守论者借提“三化”方针,试图把《白毛女》所代表的个体风格模式化为中国歌剧发展繁荣的样板,以“一元化”来排拒歌剧艺术的多样性与现代性。该杂志奉行了“只谈道理~不论左右”的办刊方针,分期、分栏目地发表了贺绿汀、商易、戴鹏海、焦杰和刘诗嵘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对歌剧新思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如沙梅的《向西洋大歌剧学习什么》、周枫的《歌剧,先天营养不足》、居其宏的《(白毛女)传统与当前歌剧创作》和谭冰若的《必须重视欧美歌剧的舞台演出实践》等重要论文也在同一时期得到歌剧界的深入关注。到1988年底,“极左”保守派歌剧论者基本上已偃旗息鼓。其间,“搭错车现象”和“沈话现象”以及歌剧《芳草心》所代表的“小草现象”也为音乐剧在中国的后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可以说,以戴鹏海和商易为核心的《歌剧舞剧资料汇编》和《歌剧艺术》编辑部同仁们,不失时机地发现了新生戏剧形态所代表的力量和价值,他们功不可没。做《歌剧艺术》杂志编辑的过程中,戴先生下大力气,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上海地方歌剧史《上海歌剧创作剧目初探(1930~1949)》,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它都算是中国乃至世界歌剧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其精神支柱
在历史的大是大非和艺术规律面前,文化人该如何坚守良知,做出正确的判断,并敢于担责?从表面上看,这当然仁者见仁,但在现实生活和个人利益面前,很多人是随波逐流、两面三刀的,有人为了某些个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而滥用权力,拿批评的大棒不顾一切地去封杀他人,更甚者刻意掩盖历史的错误。“文革”后,相对其他文艺领域,音乐界的拨乱反正并不彻底,历史遗留的很多深层问题长期被主流话语所控制,这种情况不但引起了全国广大音乐家的不满,也不利于中国音乐事业和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历史亟需富有强烈主人翁责任感的勇者担当大任。而就在这场深刻的思想变革中,戴鹏海先生从不推脱责任,他敢为天下先,给学界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思想宗旨和可贵的人文品质可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八个字来总体概括,这些重大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关注国人思想解放的难题之一——轻音乐
戴鹏海年轻时就有着敏锐的历史眼光和严正的学习态度,这种良好的素养贯穿着他一生的追求。大学毕业不久,在阶级斗争话语甚嚣尘上的时期,轻松愉快、易于普及又颇有生活情趣的轻音乐的“去留”竟成了严峻的历史大命题。在今天的青年人看来,可以说不是个问题,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空气步步升级的状态下,音乐的娱乐性和商业性等功能却成了咄咄怪事。有些作曲家、评论家们如高为杰、宋扬、时乐漾、高介云、李凌等人面对社会音乐思潮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更多的人们还在观望中。1961年5月27日,戴鹏海在《文汇报》发表《对轻音乐问题讨论的建议》一文,提议从理论上对轻音乐类型的概念、创作手法等问题及其对中国时代音乐发展的价值与意义要给予及时、正确的引导。这种以音乐多元艺术观为主导的思想在当时虽非其率先提出,但文章在发表后,立马引起了舆论关注。我国音乐理论界从此话题出发,逐步延伸到了后续的“流行音乐”“通俗音乐”等相關艺术形式的大讨论。寒溪、朱践耳、李刚、刘诗嵘、杨民望、于庆新等几十位音乐家参加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中,一直到改革开放还远没结束。如今看,假如当时的中国社会连个轻音乐都无法接受,如今的各种流行音乐、音乐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出头之日了。
2.要真争鸣
戴鹏海的学术特色,是他勇于为历史上被人为地搞成两个阵营而又始终处于被打压的“学院派”鸣不平。他善于运用毛泽东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作为行动指南,为其开言立论做研究作挡箭牌。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史学批评法,他找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大量音乐家多有爱国和抗日救亡作品的证据,向历史的冤假错案进行公开的学术“诉讼”,对史上“因人废乐”“因主义废乐”等冤假错案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重估与清理。这些调查研究多从当事人的个案出发,使“右派”们及其作品、学术思想的历史价值重新得到学界认同。如对被“拔白旗”的钱仁康、陈洪的“战时音乐观”、江文也的作曲“不讲定则”教学法,以及陆华柏、李抱忱、吴伯超、马思聪等人的历史贡献等。他秉承了讲真话的“贺绿汀精神”,对这些严重问题,敢于向当时的音乐界代表人物进行严正质疑,不避讳吕骥、赵讽等音乐界领导,带头履行“百家争鸣”,真正“解放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