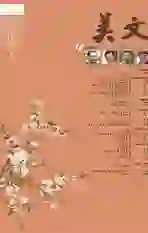主观书笔记
2017-12-13闫文盛
闫文盛
一
我经常会觉得许多感受在沦丧。时间和空间都变得不新鲜了。我以一个客体的身份在观察我和我们的生活。那种高浓度的真诚,我们越来越难以获得。这似乎是我们的热情在逐渐退失的一个标志。我似乎应该更加趋于内在。这当是我的写作的指归。但我似乎应该更加远离内在。我必须在一种反面的状态中重获叙事的热情。我在反复地走同一条路。不知昏晓地走着。天色已经变得格外突出,它薄如蝉翼,预示了一个透明时空在未来的诞生。

二
天骤然凉了下来。秋天来了。街头到处都是加厚了衣服的人群。我低头俯瞰他们。我想象秋天和温暖的窝。在我路过了那些時间的时候,他们都不等候。到处都是人群。他们的心头吹过骤然而至的冷风。在几十年前就是这样。在几十年后还是这样。在我们生前,在我们死后,秋天都是一年一度。它突兀地降临了。在我觉得躁乱不堪的日子里,秋天降临了。一丝丝细微的雨线从天空中落下。我路过街头的时候,天空阴沉沉的,像孩子欲哭的脸。我颇带警觉地走上了这段崎岖不平的小路。没有一丝亮色的天空使我焦灼。我不安地看着那里快要渗漏下来的雨水。来啊,这秋季就像我们心底的隐秘。在天高气爽的日子里,这秋季就是扫描我们灵魂的雨水。我简单而宁静地路过了这里,此刻连太阳都是昏黄的。此刻连太阳都是隐秘的。这就像我们心底的雨水。它漫漶地淌过了平原上的河流。所有人的孤寂的灵魂都在秋季里游走。但是,加入到我们的孤寂中的合唱开始发出了声音,它像突然爆破的光阴。在那些万般沉醉的人群中,我看到了雨水降临。此刻,在很多街区,阴沉的天色笼罩了多数人的生活。我们无法平淡地进入到那另外的生活中去。我是麻木的。但是这最后的生活缥缈不至。我想象这最后的缥缈而麻木的生活就像想象罪恶一般。我警觉地看着那些人。在树木之上编织树叶的人。在地底挖掘泉水的人。在地平线上怅然地面对秋天的人。我觉得他们走路的姿势都是压抑而低沉的。在一种无比相似的宁静的时光中,我看着灰色的天空进入到了秋季的底部。天骤然凉了下来。我们来了。在一种磅礴而起的对于未来的思虑中,秋季携带着它那隐喻般的光景来临,而我端然坐在这里。而我很快就远离这里。此处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段过往的时空。我透过窗口望着窗外,秋天像一座沉默的圣杯伫立在广场上。我无法阻止秋天像一座圣杯伫立在广场上,尽管我深深地感到了此刻的往来与错失,但我对于时间的流逝无法阻止。我不想与任何人共语,只有沉寂的天穹在我眼光的倒影中注视着我。我如此感叹,但无法悲伤。在我的心孑遗而徘徊的秋季,我看到了那些隐秘而至隐秘而去的灵魂,就像瓢泼而过的雨水看到了布满旷野的星辰。在那里静谧的青草变黄的秋夜,我们用了一生的力气挖掘,我们静静地将萎黄的草叶和阑寂的夜色葬在那里。
三
生命中有许多淤泥。沉重的铁。我们已经渐渐地不再书写的淤泥。铁。远方的山水和一种沉闷的、反复被激发的、单独的、窒息般的梦境。卡夫卡和他的爱情,单调到极点的,只在内心回旋的,无可排遣的梦境。爱情。左右迭增的,如云层般犬牙交错的光线。对世俗生活的拒绝,一种不可思议的充满了自责和自诘的处境。从表面上看,生活没有丝毫问题,但处处泛滥着那种恼人的悲伤。灰色的空际中有万物遭弃后的变种。卡夫卡。他只是一种无端的主观之物。我们有时与他相逢,但更多的时候,却离他异常遥远。总之,我们各自都是孤寂的。在不同的时空中。我有时会痴迷于诅咒那种沉闷的悲伤。但书写和惦念均无问题。我们共在的这个星球,有如卡氏般慷慨的悲歌,有如李白般的“疯狂”“梦境”和“游侠”(李长之语)之气。有我们的祖母和流浪儿一般的前生。有我们自诩的纪传。有我们用心描绘的花朵和鲜艳的血。有二十年不变的失眠的长夜。有灵魂经过时的荆棘。有黑铁和迷离的曙光。好了,有卡夫卡的存在,我们的绝望总是会变得更加清晰一些。在更为精准的坐标系中,坐着我们明亮的发光的咒语般的星辰。有自我焚毁和风景中的密林。好了,有我们的存在,人世总是温情脉脉。但人世为何温情脉脉,它在被无限黑暗的夜晚包裹中的星辰,也并无任何一丝冰凉的沉重。但我们为何总在仰望,它压榨,破损,成就了我们与人类,与猩群,与万千生物的共同症候。我们总在与身外的物相逢,我们总在与我们身体中的卡夫卡相逢。他在每一段尘世的终点,等着我们。
四
当我在诉说,我是不绝对的。世界在我的周身涌流,像万千事物攀爬之虫。我不能抑制我在人丛中存在的现实。但是,经过河岸,获得这种激越的观感,似乎无足荣耀。我欲清晰地断定天帝之雨意,却又浑然而不可得。当我在诉说,并不等同于时间之虚伪过失和万物之苍莽谛听。我并非只存在于我所经过的道路上。一切见识都只是暂时的,它们无从规训,更不求解。
我远远地从我的意识的深层走了出来。丝丝缕缕的河水仍在流淌,它们淡然而不突出。我足足看了五个小时车流,在每一个刹那,我都在阅读,出神,像一个不存在的人和再三地荒芜下来的树木。当黑暗降临的时候,天地为之目眩,我们只能容纳自己的不足部分,却再也看不到宇宙的万千法身。我很奇特地仰观马路,仰观城墙和闪烁着明亮之星的窗口,我很奇特地看着自己消融。我再未有心胸涨满的一刻,那万千之我都过去了。我必须客观地注视着那无我的万千时刻。
世界并非因我而存在的。世界并非因区区人类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在孤单和昏暗中所看到的日出日落,只是代表了我们有极大限定的一个视野的局部。它们无足挂牵地容纳了我们,并无须开辟任何另外的领土。那山河的纵深,各类悲喜剧,都非为我们书写。当我们消失的黄昏,日月的轮换依然不会有丝毫的改观。我们没有做出任何举动列席上帝的造物工程。他是无颜色的,无重轻的,不见时空的流动。在我们以穷尽心力的智慧抵达那些水泊时,那万千的星宿都不会扭头注目。那些高空的事物,只是一个个荡然的谜团。我们的命运如同上帝虚无的指头。
当然,作为我们自身尺度存在的球形羽毛仍然是明亮的,它以一种颇富夸饰的语调在推进着我们的飞翔。我觉得那些声音是不绝对的,暂时的,不值得记述的,那些尺度也只是小的,被歪曲的,看不见的,固化的,被驱逐的。那些我也不是我。那些窗子不是那些窗子。当然,那些虚无也不是虚无本身。它们在我已然洞彻的幻境中活着,以一种无比坚实的形容来对抗我们的千疮百孔的灵魂。但即便是这小小的洞彻也不是洞彻,它只是以远离我的本心的样子而存在罢了。它只是以瞬间的诅咒和爱恋而存在罢了。在我不加择选的人间,有无数乖舛而笨重的寓言。它们簇拥着自身看似光辉的形象,走进了一个个恍惚的行云般的雨夜里。天地流动着,像我们的肉身消散后,灰烬般的行云流动着。
五
造船的人走了之后。我们试图造那些兽。夜晚慢慢合拢。我们能够感觉到那些谣言和水珠。起初。黑暗和绿色都不明显。我们攀登树木。路过桥头。大声感叹。昏睡如一些田亩。我们曾经耕耘。曾经感叹。我们曾经造出木船。再造出高山。造出大宇宙。那些异灵兽看到我们。我们抚摸它们的身躯。它们抵达我们的肺腑。我们附上它们的鬼魂。一些活泼泼的异灵兽。剪除我们多疑的肢节。诞生我们的声嚣。太多的恩宠像光明的黄昏。天地橙黄。但一切都是明亮的。我们走到了埋没它们的区域。那些净白如月季的。那些净白如月季的。我说到了净白如月季的、遗忘和生长同步抵达的、疲惫而堂皇的异灵兽。我们以造船工的耐心赋予它们新躯体。异灵兽。它们被焚烧。被赋予智力的极限。多躲藏。少观望的异灵兽。它们站在河岸上。指挥船工造船。指挥人类造人。指挥同样繁杂而净白的花木。指挥它们爱的。毁弃它们爱的。忘却一切。它们爱的。在布满了炸弹的高山上。那些蠕动的鸟群在转化身躯。我们在转化它们的锐角。磨蚀它们的尖刺。去除它们的陌生性。异灵兽。它们曾经统治了地球。它们曾经统治过异灵兽。那些自我主义的高山长满了楠木。那些兰花变得日渐沧桑。我们毫无感官。无须任何接力。它们是那些兽。异常短暂而勇猛的。恒温的异灵兽。我们是那些杀死了它们的。异灵兽。它们挡在了我们身后。因为夜晚浑厚如刀。我们沉浸在高大的球体内部。没有一只动物发现我们。这些虚无在包容。并且毁灭我们。
六
我活到今天是因为受到了许多思想的滋养。我活到今天是因为我自己完全没有思想。在无所不在的遗忘的形象之中我越活越小。就像在极地里我所看到的灵魂的晶体越来越小。因为无法恢复我只能任由我的梦境漫游所以它也越来越虚无越来越小。我身体的重量起初能接纳很多梦想但现在只剩下不到五毫克的容量了。我想把它让给我的亲人们哪怕我自身孤苦无依灵魂不存。我想整个世界大概是这样的:它尽管拥有无限的力但只有最渺小的事物才最为完整地集中和体现了它的意志。整个世界要优于我们的思想。但它仍小于最小的寓言。
七
我们占有的声音、资料、处所,美丽的景物太多了,但这并无大用。在一种彻底的、空旷的龙卷风一般的宁静中,一切外在的物并无大用。但是寧静席卷了我:就像我们放下任何包裹,前往那空旷无人之地。一种彻底的、空旷的宁静寄居于我的全部身心,我希望以它们的存在清空我所有的沉睡和凝思的岁月,就像希望归途中的野草一般的,在万物之上飘扬的宁静覆盖我的全部身心。在人类聚集之地,宁静是独特的外物,它与我们的心率并不一致。我穿越那些奔驰的马匹,它们集体嘶鸣,就像清脆的野草步上高岗,在逐日升空的艳阳下,它们与时间同样是空洞而虚无的。我觉得疲惫,人间寥落如此,它们是另一种宁静。
八
隔着镶嵌在镜框中的一层玻璃,一个雨季,以及我的幼年遗落的一弯新月,我年久失修的田垄,那些朽坏的界石,我们心头的虚幻的杯影,一盏铁青色的灯光,一只纵飞于我们梦中的凤凰,我来到了此处。带着我们无力的垂死的祖母,以及她无休止的忍耐,院子里的枯木和掉满了沧桑落叶的屋顶,我们一眼望不到的过去,这些时间里的孤儿……
我们来到了此处。
灯光在碎裂。天空随之冷却下来。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一丝燥热。没有灰和靛青的爱欲。我们的心随之招来了那长庚或启明,我们称之为最亮洁的,呻吟语,黄金醉,这时间里的孤儿!我一点一点地度过了那些岁月,有时带一点薄铁,有时身无长物,像贫窘的人只能携引着天地,坟茔,早已严重忘却,再不复原的孤寂,这夏季里的祖母,和她亲眼目睹的吾父的孤寂。我们都在垂死的延长线上写诗,这浮世的歌与绘啊……
我是带着吾父、吾祖之痕活过了一生。
带着吾父、吾祖之劳作,带着村庄里的火焰,我莅迹绝少的故地,那些巍峨和错乱的山水活过了一生。我的每一天都是被时光放大了的针孔,我的每一天都是灰烬和千里欲穷之目,唯一的向死而生的指认性魔纹。我的每一天,活过了一生。这些时间里的孤儿啊……
如今我们来到了此处,每一个午夜的余业和树影的悲秋,热烈的四季里的鬼魂,无所欲、无所为的一生。我带着吾祖、吾父、吾儿之痕度过了一生,我们的大体的命运是相似的。像铁石般的,皮相,像南方山水的纤柔,像北方胡地葱茏的荆棘般的,野性、无序和沉浸的一生。像我的将要结束的写作和阅读的一生,像我已经重启的陌生人一般的阅读和写作的一生。像我不识万物时,根深蒂固的命运之感。像大雾弥天,烟雨之秋。这些时间里的孤儿啊……
我终于来到了此处,带着一切血缘上的倦怠和无痕的离愁。在我的逼近四十岁的午后之惆怅里,在无鸟的鸣啾和无叶的岁月的支离破碎中,我终于来到了,克服了我无限的恐惧和臭。我终于来到了,这些时间里的孤儿……在我的,一切没有抵达的时间里,总是弥散着无情的难以理解的想象。它们是宗法的,明年复明年,我的祖先。他们醒了,看,他们醒了。我看着他们枯槁的狰狞的面容,一时无语,像我们已经过完了一生,与他们相遇在生与死相连接的惆怅的出口,或入口。
看,这些时间里的孤儿……
他们都具备已经虚度的光阴之痕,他们是祖母的稻草,充满了隐忍的错谬的乱纷纷的一生。
九
我们并未带着秘密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并未带着任何欲求、希望和理想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并未带着任何遗忘和错谬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我们却常常被赋予某种使命,获得种种误解。我们始终在过着一种被虚构的人生。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被虚构中。那带来真实而松弛的晨景的清风,生活在巨大而不自觉的被虚构中。我反复地注视一寸寸行将消逝的光阴,任凭记忆的潮涌变得像海水般狂悖无矩。那些侵袭过我们祖父一辈的秋风又在侵袭我们。但我们的人生被虚构的事实无法被我们真正地领悟,那些远离此刻的感觉便是我们卑微而热情的思想。
我们生活在一种貌似坚实、自信的被虚构的命运的框架中。那些跃动于我们视野里的光线发源于我们的意志、情意和某种连绵不绝的思绪。我常常会惊诧于不识万物的奇遇之中,我们生活在一种巨大的、陌生的、反复被描摹的幻觉里。
在我们日日行经的小路,阳光层次渗漏,人影空洞悬浮。我们在静谧而自足的一刻聆听到万物浑融的巨大回声。我们生活在一种巨大的、旷野般的命运之中,那沁人心脾的花木在全身心地诱引我们。
穿过了无数的桥梁和道路,鳞次栉比的城市群,村落和沙漠,那被我们意识到的忘却在一次次地攫取我们。在一种无比确定的目光的注解下,我们在书写一种被虚构的高远的人生。
通常是在雨后,我们的幻想被凝聚起来,那令人目眩的霓虹,构成了我们被观察和变形的新的角度。我们是某些宇宙时间在人丛中的投射,它微细,沉醉,难以抵达。我们从未完整地写下它们。我们从未完整地写下霓虹。
一○
我在乡下的居所的利用率极为低下,这首先是因为我每年逗留在乡村的日子屈指可数。当然,在一种符合常规的意念的指引下,我来到了乡村,我回到乡村,我居住在我幼年的乡村的日子大约在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这是一个整年度的约数,每次平均为一到三日。而我观看天空中流云的时刻也常常符合这个概算。除此之外,我需要将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交付城市,并用以面对人生中的各种问题。但自打前年以来,这一切又没有定规,我大可以为了撰写某部巨著在乡村中逗留一年或数年之久。我没有做到的一个原因可能出自我对自己灵魂的姑息。我或许是需要回到城市里。我自己建立的家庭在城市里。我的爱人、孩子生活在城市里。我的工作在城市里。我的写作的重心在城市里。所以,近十年以来,我已经很少涉猎乡村素材了,越来越少。我同乡村的最大接触便在这条返乡之路。其耗时约在半小时到两小时之间。一百公里的旅程。我看着窗口。我的人生的幅度似乎被限定了。但是通过每月,或者每四十天一回的对乡下的天穹的流云的阅读,我的童年的面目依然可以及时地返回到我的脑海。我规律性地记录这些回乡的时刻,并且逐年结集为一部名为《危险的怀乡》的著作。我想,这一切都是我自以为是的精神的牢笼,因为我尚且不能充分地结构这样的著作。我只是按照平均的幅度来耕耘。我写下的事实远比真切发生的要简洁和凝练。我自认为洞彻了乡村的一切细节,但这其实是错谬和省略的产物。我对乡村的所有认识都被那深及穹宇的流云所捆绑、拘囿和束缚住了。我的乡下的蒙尘的居所代替我迎来的每一次隆重的日出都像我记忆中的新生儿的生活。现在我接近了它,获得了它,丢弃了它。这所有的错失,都是我人生中的败绩的积淀,因为我无法同时拥有这双向的生活。它们远比我所想象的要更为积极和富足,我只是在流云之下生活的奔波者。我的思绪像张皇的钟摆,如今它看起来远逊于我所生活过的乡下区域。它是需要拨乱反正和去除雾障的城市钟摆。
一一
我在乡下的书房以超越我的希望之姿在独立地生活着。一张床。桌子。台灯。茶几。一些早年的书籍。它们以超越了季节的冷静和淡泊,在独立地生活着。我能够与它们共处的一个夏季已经过去了。在寒风之尘透过窗户和墙壁的孔隙落到桌面上的时候,我分身乏术地寄居于别处。我不求甚解地活着,在我已将奋身度过的四十年中。漆黑如昨的乡村之夜是最为隐秘而真实的事物,在我能够看到它的时候,更多的浮思联翩的夜晚来临了。我直觉中的宁静,就像我二十年中独自栖息的水底般的宁静。我的乡下书房,一股轻烟般的往事中的思乡病,和继往开来的宏大叙事般的宁静。
一二
灵魂是肉长的,粉红色,其形各异。灵魂先生长在水中,任其浸泡,发育胚胎,再升至泥土中,经受各种雨露风尘。所以,迄今我们看到的灵魂都已陈旧无比,它们只是被上帝抛弃的通俗的曲辞,各种荒唐种子。我们何必追求灵魂的生动。我们都是昧于灵魂的人。
一三
灵魂只能孕育在水中,像河流只能孕育在水中,阔大的洋面和无尽的冰川孕育在水中。灵魂是无意识的诞生,虚妄之水被逐日去除。当然,我所指的灵魂的不存在已经形成,它们被逐日、逐月、逐年消融。我们何必奢求每一日、每一时刻都有灵魂。我们所持守的,必将是最终被我们所丢弃的无穷的水流、万物、河川和影子之舞。
一四
人生毫无例外,它总是被通俗地写到纸上的。那些铁青色的栅栏记录了摩肩接踵中的虚无人群。当然,正是在我们穿越的时候,天空变灰变暗了。我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生活被悬置起来。但出于一种此生难续的激情,我相信万物已经路经。我看不清我未曾潜伏的水底,那些黑黝黝的羽衣都已静寂,升腾,它们张大耐力,其思无邪。它们的爱,足以覆盖我们。作为诗人,我是在神灵不在的时辰完成伟大的自我教育的。我的本性降临,它使我濒临陌生的山川和堤岸。我关闭了一切,连带那些虚假的宣言。我的过失和空荡荡的原野相似,它们不该在火光未亮的时辰,降低了自己苇草般的身段。它们的悲伤被一切燃烧记住了。作为灰烬,我绘制了它们的形影。作为人,我毁灭了它们的生。我是一切我所怜悯和不爱的庸人。
一五
我視每一寸领土都为我们共有,每一个虚妄的国,每一片叶子,每一粒水流,河岸上的树,它们的臂膊。我视每一寸爱心都为我们共有,每一滴时间,每一份理想,每一块铁,每一年的云层,那些阔大的门,浩瀚的星空。我视每一座庄园都为我们共有,每一种饥饿和忧愁,每一枚红色的宁静,我们内心里的参数,那些细致入微的昆虫。我视每一类绿色都为我们共有,每一个方向上的绿色,每一个季节里,激烈的、浓艳的、衰伤的绿色,每一次啼鸣,每一次锐利的、随机的绿色。每一次护栏,堤岸。每一次,我们的,满怀悲悯的、虚妄的,绿色。我视所有的一切为我们共有,为此我朝向那所有的理想主义的,共生共死的人间,投去我反复的、专注的一瞥。
一六
当然,普通生活中没有火焰,正如阴雨中看不到蓝色星空。
在已经翻卷如云的路上,我们的疼痛的骨头形成,它打碎了爱之节奏。
我觉得写诗的日子和生活同样缺失,但是,我有自己的方式找到那迷途的入口。
吞噬掉它。摆脱它。陷入它。构成它。在某些短暂的时刻成为诗人。
不,我已经视察过了我们的灵魂,它们如暴风的裂纹。
我开始缝补。说服晴天的守卫官放我入川。
我不一定在所有的诗歌册页上留下字迹,但我一定得撕开那些暴风。
然后,我开始缝补。坐下来,成为根深蒂固的诗人。
这种罪孽感压迫我很深。
我不会成为诗人。我成为诗人。我的灵魂不会成为诗人。我的骨头成为诗人。
我像在逼着自己犯错,但是诗歌,它一再地把我刺疼。
我们是各种无生活的人。
我们是各种无灵魂的人。
一七
不必问我何故,我母亲就是因为意识到了永恒之存在后才爱我的。否则,她大可以把我吃掉,扔掉。否则,她大可以不做我的母亲。我以前对她的柔情蜜意也完全消失了,在意识到永恒之存在后,我痛苦地回溯了我和母亲的一生,我认为我们都是错的。所有的源于生活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母亲意识中的梦幻异常短暂,但她曲解了世界的寓意,她变成了唯我独尊的母亲,反反复复地钩沉旧事。在苍老的流云代替了秋風的时候,我看到母亲面容中的纹路一点点地加深了。
我也老了,但母亲的心却仍如旧岁,她所意识到的万物就是宇宙全体。否则,她大可以摔碎她的不幸,破坏自己的家庭,释放自己的哀愁,杀死她的夫君。但她的独裁却并非如此,因为她所意识到的永恒就是她心目中万物的本相。而我们的生死就是整个世界的最大事件。这样持续的爱恋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母亲彻底老了,像我记忆中的老祖母一样。我对她再也亲近不起来了。如果她仍旧困苦,我只是对她抱以客观的同情。
我们都在与永恒的对抗中来挽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必然而永生的关系。我们只是造物的浮云。如果大地上没有风声和任何人类,我们就如同大地本来的形体,但是如今,我们占据了很多区域。母亲占据了她的乡村,我们占据了城市的蜗居。每一次穿城而过都会使我忧伤,因为我貌似在这里已经待了一辈子。
某种程度上的我们已死。这是永恒的上帝的意思。某种程度上的我和母亲已死。至于我们的亲昵关系,也已经永久地终结了。我们不知要各自走到何处去,大野之外,没有任何母子。没有任何人。我们只是绝对的孤零零的个体。我总是为此而伤悲。
但是母亲,这才是永恒教给我们的绝对真理。我们毫无能力,挽救不了任何一个人类。
一八
对经典的审视和探索使人迷醉。
因为经典是准确的,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你内心的所知。
经典是一个特定的时空,它拥有必要的神秘性,所表现事物的复杂肌理及唯一的面孔。
它似乎经历了你思维的每个边界。
经典使你趋向于理解力和洞察力的极限。它似乎是语言的原型与本质。
经典是时间的复数,它是唯一不因时间之流逝而会衰退的事物。
经典无法被书写,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思维的闪电。
在阔大的、远去无痕的宇宙中,经典从来没有具体地诞生。
它无须激烈冲突,它不运动。
它是静止的。
无限的。
但经典又是无数衍生物的母体所在,它可以启动人间,与空寂之境并行不悖。
我们遗忘的事物会被它重新激活,但它是安详而静止的。
像无风时的旷野巨树。
经典可以是冠盖浓荫,也可以是微生物。
我们站在所有的时空下界,我们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间。
那些空虚之境是我们内在幻觉的终极表露,它大过了人间所有的喧嚣。
经典记录了这种秘密的生成,然后归于黑暗和静止。
光明的白昼在彼处,经典在静止的彼处。
经典是无色的溟蒙时空。
已经多少年了,我们面对着永恒退潮后的浑浊水流,看到那些绷紧的人体在暗暗泅渡。
他们是山峰迸裂后的谷粒。
他们由灵感催生和毁灭。
经典没有必然的路径,它似乎来自无穷的,空洞的,激进的或淡泊的心灵。
经典是静寂而入定的,它化解并超越了人间浮尘特有的烟火之气。
经典是时间的尸体之堆积,它引领我们,看到了无数残骸被埋葬在隐约的雾霭中。
向死而生使我们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领悟,因为我们可以触及的事物过于有限了,所以,那能够命名事物本身的经典便是涵盖了我们整体性命运的一种象征。
我们通过阅读经典来祭奠我们的生死,那种空旷和虚无,葬送了我们所有的幸福。
阅读是时间的一次次落幕,它荒唐地向我们形容了生的复数。
但是这人间最大的幻觉却是无色的。
无臭的。
它是静止的。
正如我们的沉默本身,它必然异于繁华热闹的大多数。
这只是一次无声的远征,我们必然随着经典落幕。
它陪着我们走远,如昙花一现。
它目送我们层层叠叠地降生和走远,如上帝目视整个人间。
一九
有时候回家,看到母亲呆坐到树荫下面,我就忍不住伤感。但我是无法与这时候的母亲对话的,也许是因为她的拒绝,也许还因为别的什么。但是,我貌似自得的生活从此便一直被笼罩在母亲的树荫里。那个庞大孤绝的世界,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在我幻想交流的日子里,生命中的又一个季节来临了。我又看到了母亲。我注意收集她的动作、形象,并且想象她的内心世界。
譬如,“儿女们长大成人后,就陆续离开了我们”,譬如,“家里只剩下我和老头子了”。
总之,已经很多年了,我想试之以母亲的口吻来书写她的长篇自述,但总是不成。也许是因为她的拒绝妨碍了我,也许还因为别的什么。但我的生活终归是被母亲的形象彻底改变了。在我想象我的自得的岁月之时,我觉得我与母亲之间的距离是无比遥远的,像在浩瀚的星空中,两颗星球之间所诞生的那种远。这不是事物的原貌,而是一种分裂的症候。
所以,我想象,“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我都不爱,我已经完全无法顾忌”,但这不完全是母亲的语气。我经常彻底地忘掉母亲的语气、形象,以及她示之于我的一切细节。这很奇怪,也许是出于一种磅礴的爱,也许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同情。无论对母亲对我,都是这样的。所以,母亲于我,是尼采、卡夫卡和佩索阿的合体。她综合了无数人的用心开始缔造我。
但我为了这样的命运而感到了深深的悲哀。深深的悲哀与欢欣,我难以准确地表述这种感受。总之,离开她的日子一久,我就开始不放心了。我在梦境中看到我的母亲,她呆呆地坐在树荫下面。她同谁都不说一句话。谁说话,她都不回应。
不过,“我只是活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内心澄思无比丰富。我只是活在我把他们都培养成人之后而剩余的我的岁月里”。但这仍然不是母亲的语气。母亲的语气是拒绝的,母亲给我的感觉,不是唯思唯我。不,母亲,她并不思索。她只是呆呆地坐在树荫里。
我看了只有心痛。
母亲老了,连同父亲和这所已经住过了三十年的老房子。我看见夜晚慢慢地降了下来。雨水又来临了。在一片弥漫天地之间的大雨中,我想试之以母亲的口吻来书写一篇关于她的长篇自述,但是不成。这是两个世界。幼时我对母亲的依恋已远。我也马上四十岁了。岁月真使人尴尬。如今是我空洞地坐在树荫下面。我在体会母亲在往事中的所思所想。我完全想不起来了。
我只能呆呆地坐在树荫下面,雨水很快灌满了我的脖颈。我不知道是季节的变换还是泪水混合着雨水的寒凉席卷了我,但我只是想起了母亲,我呆呆地坐在了树荫下面。
二○
我们受到的迷惑总是比我们失去的更多。在暴雨降落的时辰,我目睹那些暗云离去。
伴随着天地间的阵阵雷声,那些事物和往昔的梦境都结束了。
笼罩在梦境之上的是那些树木。笼罩在树木之上的是那些天空。
站在更高的角度,曾经占据了那些土地的一幢庞大的楼宇在今天下午被拆毁了。
伴随着暴雨来临前的阵阵烟尘,我看到一些生命结束了。
在夜晚,那些相对的高山带来了微生物一般的怅惘。
自从那些人群搬离旧居,上帝被命名作寓言的使命便结束了。
我只是觉得时间终究被清除出去了,那些与它共存的梦幻,仅仅是一些相对的高山。
爱与欲的纠缠,带来了雨水,连绵不绝地降落。那些时间都像微生物。
它们没有尾声,不计前仇。在环形的园林里,黄昏寂静极了。
不过是天地之间一场雨水;我如今站在这里,看到那些天宇,南方,寂静的密林。
如今我生活在过去,任凭技艺之神夺取我。不过是灯红酒绿。
不过是沙路数行。梦境之中,那些星辰都降落了。那些暴雨如注的星辰都降落了。
灯光也开始趋向昏暗。至于阅读和给予,都是雨水。那些密林,寂静,都是雨水。
那些注目南方之时的夜晚,昏暗的曙光。那些被迫等候的夜晚,寂静中的。
那些被拆毁的,正在降落的。那些张扬的语调,白璧微瑕。那些行色诡异的。
夜晚匆匆的。行人們。那些时日,正在被制作的落魄的。星辰。我一直在注目的。
事物;浩大的雨水正在弥漫整个天幕。我们正在经历此生。那些流亡的草虫们。
正在路过这一刻我们的祖国。可是,我们所猎取的意象都无法久驻。我们只是反复地。
在书写。对于那些濒临绝对寂静的密林,我只是暗怀敬意,但是在一些突兀而至的。
时辰;那庞大的天宇压迫我们的梦境,我十分小心地看待那些事物。对于我的。
命运,以及我们的命运;我觉得任何叙写都是无意义的。那些屋宇也像是虚幻的存在。
我们仅仅在它的周身徘徊,我们从未住下来。我们从未真正地写:就像那些正在流淌的。
血液;它们滚滚而来,如不竭的江水。它们并非任何一种物质,无墨,无痕,无物。
无色,无重。亦无:任何雷声。
二一
我们都想靠近自己的本能,迷恋于一切忘我的生活。
反复地诉说,爱那些星空。
我们的人生并不坚实,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都是虚拟的产物。
今天,我路过了很多墓碑,在麦黄时节,它们插播到地里。
它们也在生长,只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一日一日地衰败下去。
那些被风吹雨打的墓碑,不过是我们死后看不到的守卫。
雨水渐渐地落在了地里,就像我们虚构的一生变成了垂暮。
我的步伐很慢,我想着人生不过如此。
一块块墓碑而已。
远方高山耸落,它对应着天色的浮沉,像造像师心中的小神。
那些泥土并不容人,它们腐坏了人的骨头,一堆堆泥污,乱糟糟的人生。
我们将虚拟的火埋葬到地里。
那些事物,多少年岁都不清晰。
我们将自己疯狂的火埋葬到地里。
我们将自己的沉默埋葬到地里。
我们将自己埋葬到地里。
我缓缓地走过了我们的终结之所,不过像一个牧羊人缓缓地看到了日暮。
那昏黄的火,我们醉如浮生的火。日落下的众国。我们仰望和鄙薄的火。
许多事物和感觉都不新鲜了。生活或许一成不变,因此造成了我们的许多幻觉。
我们愚钝的心灵如同被损害的蚕丝。
杂乱、破败的蚕丝充实了我们经过的那些旅途。
细雨,苍翠的古松充实了那些道路。
沙尘便是我们人生中虚浮洋溢的表象。
我们并不是完整的个体,我们并没有度过完整的圆融的一生。
我们在许多时辰都是愚钝的,毫无知觉的。
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日子,当我们知道了生死和自我构造的艰难,我们便再也不可能保持那种纯真的感觉的流水。
人生遍地迷雾,我们何来清洁的精神。
我看着被封闭的囚徒,你,我,我们的母亲,那高高山上的王,我总会觉得悲伤。
但是这所有的感觉都并非直承自我的树木,它们的根系混乱地生长,在我们看不到的阴沉的地下,长着小鼠,长着幼虫,长着鬼神的灵魂。
我在泥土之上,看到了那些树木,我不知道它们的源头。我看到了高速公路和遥远的外部星球。
我觉得时间大抵如此,它从未被我们完整地发现。那些桀骜不驯的鹰隼,也大抵如此,它们也会在未来的某一日,消逝于长空中。
像它们飞纵而过的那些山峰,本来也是虚拟的山峰。
它们的存在和我们的人生都不坚实。
我通常是这样来揣测和理解世界的;但所有的这些夙愿,皆非我的思想。
我只是在日复一日的封闭和洞彻中离那些雨水近了,离那些丝线近了。
我只是离虚拟近了。
我不坚实,我们都不坚实。
作为人生忧闷的常态之一,我路过了那些事物,它们并无目光,毫不注视,但我觉得已有冥冥之眼在观察着我们这些事物。
我便这样沉默在无限的所得与所失中……度过了我的一生?
二二
坐在庭院,闭目凝思,能感受到光阴的绝大流淌和列车在地平线上驰过。能感受到树木和刺激它们身体发育的火。能感受到鸟儿鸣啾,低空的燕子和一片土地。能感受到栽种,沉闷和阔然。
坐在庭院,能感受到生活和嘈杂的人声。数十年的光阴过去了,能感受到它的起点和那些死去,不灭的时间。能感受到阳光融融的暖意和码头。能感受到柴火和墙面上的蝴蝶标本。
鸟儿鸣啾,能感受到黑色的炭火和旧日的书卷。坐在庭院……能感受到时间,广播里的嗡鸣,小贩的叫卖之声和暗寂里的漂泊。能感受到无限的我在生殖。能感受到万千宇宙,龟息的火。列车的震动。鸟儿,树木,黑色的炭禾,祖国之大和远方时空里的水木。藤蔓。旅途和今日的小兽。能感受到炭火里的余烬。皱纹中的空空庭院。
能感受到幼童的生长,鸡鸣于野和烈日下的汗珠。水母。能感受到高大豆荚。低浅的河面和蛙泳的人。能感受到。坐在庭院。《诗神》和阅读者的黃昏。能感受到顾盼和恐惧。能感受到恐惧的总和。能感受到所有的关隘。海。
坐在庭院,能感受到铺开的书卷和仍在流逝的时间。能感受到布谷之声和我们日渐展开的毛孔。能感受到窗户和梦境,外出的羁旅和几句诗。能感受到一切微弱的、微观的远方和明亮。
坐在庭院,一切绝大的背景都过去了。那流淌在北部的溪水已经断流。能感受到石头的梦,那缓慢坚硬的疑难。那些平静的时空,深喉在燃起草木。布谷。谷。布谷。谷。布谷。谷。我等了很久,一直走到这些故事的尽头。
能感受到时间破灭前回光返照般的照拂。整个早晨,唯小猫在叫它的乳母。
唯小猫能感受到人间百般的照拂。
二三
我最初学习写作,是为了描绘我内心的战争。
在我幼小时候居住的平原地带,有一些远古时候遗留下来的堡垒,我们作为异乡人抵达的时候,这些堡垒经过了数不清的风雨,早已变得伤痕累累。但我们将其择为最后的住所,或许有着这样的理由:这些堡垒已经囊括了人世的全部,只要我们甘于这样寂静地活着,并且死去,就完全不必因为猎奇之心而对它抱有任何遗憾或成见。
我们乖乖地住了下来。
作为更大的人群中的少数,我们所余留的时间十分有限,因此,选择这些隐蔽的乡间居住,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不可再有的搅扰。
而在此前,我们所经历的人生一片喧嚣。
自打安心乡居以来,我们外出的日子十分稀少,因为我们不仅居住在堡垒,而且决意无限的生殖堡垒。在我与我们之间,我们渐渐习惯了缄默无言的生活。我们担心过多的交流会出卖我们的灵魂。我们将我们的思想筑成洞府,那里只珍藏我们所书写和想象的事物。而冻结所有的爱恨和欲求,将成为我们最终的归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与我们之间,沉默的障碍开始成为诅咒。我们的言语功能退化了,在一些必不可少的夜晚,我们需要前往那些隐秘的高山之时,沉默的行动带走了我们柔软的面孔。我们千篇一律地铁青着脸行走,任何一个婴孩的哭声都被视为不祥。
在我想象到了我们的终点的那些夜晚,成群结队的幻影无悲无喜地走向那孕育我们的高山。我们最初学习生活,便是因为山上的树木。在大风肆虐的夜里,我们需要站在最高处的一棵树下喊出上帝的名字。此前,我们是以这种方式来对抗遗忘的。
但是,在过了太多的年月之后,山上的树木开始变得寥落。我们的生活不得不直接地对抗宇宙和风雨。那些神秘的信件就来自于上帝造访的夜里。作为上帝的分身,我们对于上帝本尊的感情是复杂的。因为他笑的时候,看起来像是婴孩。他发怒的时候,看起来像一只雄鹰。他睡着的时候,像一条无声无息的河流。我们阅读那些信件,便是在他安息的夜里。
上帝也在发出鼾声。我们看着他总也面目不清的睡相,像看着水流在无尽地消逝。那些神秘的信件总是在猜测上帝的名字,我们阅读了无数次,但总是找不到最终的答案。上帝并非上帝本尊:只要我们看这些信件久了,就会发现这一点。他或许是不存在的。尤其在他化身为流水般的睡姿躺下来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任何关于上帝的呼声。
到了后来,在所有的人彻底沉默下来的时候,我们成群结队地向着那隐蔽的高山进发。我们心中珍藏着一个笑微微的上帝婴孩。他爱我们,因此才会赐予我们阳光般灿烂的时光。但这些年来,我们经历了多少喧嚣。因为生老病死的缠绕,因为到处都有争斗和私见,我们渐渐地连自己都觉得不可信任了。
我们来到山上,以沉默的激情喊出上帝的名字。
我们在山巅上,听到山谷里沉默的回音。我们完全活在一个集体恐惧和沉寂的夜里。那个婴儿的面孔在无数人的心目中泛滥,那些高山般的盼望也在无数人的心目中泛滥。在压力大到了极限的时候,终于有人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而哭出声来。
这些年来,我们经历了祖先的死亡,父母的疯癫,各种怪异而嶙峋的堡垒的反复被构筑,在离高山很远的地方,我们缓慢而凝重地停驻下来。在一些必不可少的隐秘的夜晚,我们感到了上帝诞生时所带来的吉祥的红光。我们来到了高高的山上。
在最为粗壮的一棵树下,我们喊出上帝的名字。我们以沉默的激情喊。我们以善良的激情喊。我们以自己看不到的希望上帝降我们以祥瑞的利己之心喊。我们以对待一个婴儿不该有的高声喊。在高高的山上,我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在撕心裂肺地喊。
我们沉默着,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面对上帝嘴角的笑容和他流水无形的悲观。
山上的风声和融雪、泉水和沟谷都与我们不同。大自然的景观台过于寂静了。而我们以卑微之躯站在了上帝教谕我们写作、生活和历险的夜里。
我最初学习写作,便是为了描绘上帝。但对于他是否赐予了我们以生命,我很难确定。
我几乎不相信上帝会给我们以任何回应。他的微笑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他的婴儿身和雄鹰般的姿态,他对于流水的模仿和缔造,都发生在我们的梦幻被书写之后的夜晚。在任何平原之上,面对高旷、虚静、庞大的夜晚,我们都会心怀沧桑。
我们在居住到堡垒中的时候,信奉上帝的人已经开始减少了。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寓言般的抉择,我们会沉默着,在一些必不可少的夜晚离开村庄。在我们集体沉默的夜晚,月光渗漏到了我们居住的土地上,就像我们的幸福和荣耀被洗劫了一般。
作为上帝的分身,我们连彼此都不信任。
所以,在高高的山上,我们最后的话语是以古怪的枯死的树木的姿态被喊出来的。至于上帝,他听到了我们最终的悲伤。
“他虚幻的影子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一闪。”
二四
海边的水是浑浊的,波浪发出巨大的啸声冲击着堤岸,星星挂在山上,大太阳国的臣民们住在山上,君王住在城堡的深处,他的王宫就叫大太阳宫。我们主宰着他们的生,我们主宰他们的深处。我们住在大太阳宫。我们都是王宫里的旧人。但是海边的人是浑浊的,在波浪带着无数的啸声冲走了命运的一切痕迹之后,我们住在了已经没有往事的记忆之中。我们要书写任何文字都不成,我们想表达任何爱情都不成,我们无论哪种语言都没有准备学也不曾学会。我们住在沉没的泥泞之中,我们主宰他们的王宫。但是海边的一切都是浑浊的,无论天气阴晴,那远方的山水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含混。我们带着我们想要冲过的堤防走进了他们的深处。我们想要抵达的是一切物的尽头。在王宫的灰烬之上,我们看到了那些铜铁人、草木灰和一切尘土。我们走进的是时间的尽头,没有荒芜的烈日,没有瑟瑟的秋风。没有任何少女和一棵棵枯萎的树。在我们的叙述结束之前,还剩下了什么?但是堤岸是浑浊的,在我们提问之前,L,你曾经拥有什么?你见过长空里的飞箭和刺疼血肉的锋刃吗?你曾经拥有什么?大太阳宫还剩下了多少可以珍藏的瓦砾。在属于你的整个家族全盛的那几百年里,你是否控制过你的情欲,你是否也耽于杀戮和救人的想象。你是否也偷偷地观察过那高高在上的王,你是否也爱着宫女。你是否窥视月色,大象的衣裙和肮脏的街市里的羊群。你是否是没落的、高尚的、高高在山的王。但是海边的水是浑浊的,最后你逃亡了,流浪了,寂静了。但是海边的水是浑浊的。最后你是寂静的。在你的坟墓里,我们还互相拜访、问候过。那些沧桑的叶子和春天里的露水都住在你的墓地周围。那些青涩的桃子刚刚已被采摘过了,在黄昏来临之前,G,你曾经看到过什么?那些湖水就在你的墓畔,那些宁静的人群就在你的垂死的记忆里。你的任何痕迹都像是大太阳宫的赐予。你被晒黑了。在那些光明的日子里。那极端仇恨权力的人主宰着大太阳宫。他是我们的朋友,舊人。在我们的垂死的记忆里,他是一整片原野的拥有者。在他的领地上驻扎着他极端仇恨权力的灵魂。他主宰着莫须有的万物和一片空荡荡的宫殿。没有任何人相信他是空荡荡的宫廷里的守候之人。他延续了雷声和那种暴烈的雨水,在大片降临的鱼鳞甲的阵营中,他珍藏了他的垂死的灵魂。他是极端仇恨灵魂存在的人。但是,海边的人是浑浊的。Z,你还剩下了什么?在此之前,你拥有过什么?当然,我知道我们燃放了无数的烟花,那些绚烂的烟花都已经燃放过了。站在海边最高的楼房的顶端,我们看到了那些烟花。我知道那些岁月里的烟花都燃烧过了。你鲜艳的生命和一切诗歌般的内心都燃放过了。你的孤高的山峰和大太阳宫,君王般的大风都燃放过了。在最后你所抵达的那种深长的寂寞中,天色空空如同魔咒。你完全不必嫉恨了,你完全不需记忆。在你的垂死的灵魂的旷野般的顶峰上,我们看到了高高的谷子。我们看到了高高的谷子,可是,海边的水是浑浊的。你曾经拥有什么?H啊,你还剩下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