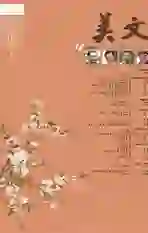心经故事
2017-12-13胡松涛
胡松涛
关于《心经》
任继愈说:“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有些译著写成后即无人问津,束之高阁。数万卷的典籍中,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发生广泛影响的不过十来部。其中流行更为广泛,达到家喻户晓程度的不过三五部。这三五部中就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心经译注集成·序》)】

《心经》的汉译本有几十种。
《心经》分为广本(又叫大本)和略本(又叫小本、简本)。广本的内容包括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大约相当于前言、正文、后记)俱足的版本,简本指只有正宗分(正文)的版本。汉地一直流行简本。
简本,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鸠摩罗什(344-413)于402年前后翻译的《心经》,一个是玄奘(602-664)在649年翻译的《心经》。两个版本中,最为流行的是玄奘译的《心经》,此本简易广大,放乎四海,照亮人心,去人无明,使人虚灵无昧。
方广锠编纂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1版1印),收集整理汉、梵文《心经》18种,唐宋间《心经》注疏18种,其中有13种是从敦煌遗书中整理出来的,这是目前国内收罗《心经》版本最多的专书。
罗什译《心经》与玄奘译《心经》
现在,我们对照阅读《心经》最流行的两个版本。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鸠摩罗什译):
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阴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弗,色空故,无恼坏相。受空故,无受相。想空故,无知相。行空故,无作相。识空故,无觉相。何以故。舍利弗,非色异空,非空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弗,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空法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萨依般若波罗蜜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苦恼,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是无上明咒,是无等等明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咒,即说咒曰:揭帝揭帝,波罗揭帝,波罗僧揭帝,菩提僧莎呵。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玄奘译):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 菩提萨婆诃。
据台湾清华大学陈淑芬女士在《三部梵语佛典的汉译技艺》中的研究和统计,罗什译《心经》与玄奘译《心经》的相似度达到92.4%。这说明,两个本子之间源头基本一致,具有前水后水一脉相承的关系。
也有人对罗什译《心经》持怀疑态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怀疑,是因为:
梁代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将《摩诃般若波罗蜜神咒(一卷)》及《般若波罗蜜神咒(一卷,异本)》,归入“失译”经录内。就是说,僧佑时代,光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神咒(一卷)》及《般若波罗蜜神咒(一卷,异本)》(即《心經》)之名,而没有《心经》之文。
到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编纂年代为公元730年),才第一次把《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判为罗什所译。后来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误判。误判与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有力的史料证实与证伪。我们还是依照唐代以来的习惯说法,来看待罗什译《心经》吧。
《心经》在罗什时代及以后很长时间并没有流行。直到玄奘译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出现后,《心经》在中华大地开始广为传播。“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大唐三藏圣教序》),诚所谓泰山之福缘,海深之善庆也。
《心经》来历之一说:蜀地病人授
《心经》从哪里来的?
大致有五种说法,都与玄奘有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
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感念观音,不能令去,及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唐代的慧立、彦悰撰,10卷,成书于688年,前五卷记玄奘出家及到印度求法经过,后五卷记回国后译经情况。
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心经》是玄奘在四川从一位被他感化的病人那里得到的,时间在玄奘取经之前,大致是618—622年玄奘在成都空慧寺修行期间。玄奘取经途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产生幻觉,“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他通过诵念《心经》,安顿自己。
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中,只字未提《心经》,这很奇怪。他的弟子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第一次说明了《心经》的来历和作用,这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心经》来历之二说:罽宾国病僧授
《太平广记》说,《心经》是玄奘取经途中在罽宾国所得: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也。幼聪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余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
《太平广记》是古代文言纪实小说的第一部总集,引书四百多种,因为成书时的978年是宋太平兴国年间,故名《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中的“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也。幼聪慧,有操行”一句,出自唐刘肃撰《大唐新语》卷十三《记异》;“唐武德初……至今诵之”,出于唐人李亢《独异志》。李亢生卒年不详,有学者考证,此书成书当晚于会昌六年(846)。
《独异志》及《太平广记》说的是,玄奘于武德年间(618-626)出发往印度取经,至罽宾(克什米尔)时,有一病僧口授《多心经》给玄奘,并嘱其背诵。玄奘一路不断背诵《多心经》,终于平安到达印度,取得六百多部佛经。此后,大家效法玄奘背诵《心经》。
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相比,《太平广记》的记载,有几点不同之处:第一,授予玄奘《心经》的是个病僧。第二,玄奘是在取经途中得到《心经》的。第三,从唐代开始,《心经》已经被称为《多心经》了,“多”是“波罗蜜多”的简称。第四,《心经》的作用开始从史实向传奇发展:一诵之下,“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何其神奇。
《心经》来历之三说:观音菩萨化身授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遗书S.2464号题为《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心经》有个序言,全文如下:
梵本《般若多心经》者,大唐三藏之所译也。三藏志游天竺,路次益州,宿空惠寺道场内。遇一僧有疾,询问行止,因话所之,乃叹法师曰:“为法忘体,甚为希有。然则五天(千)迢递,十万余逞(程)。道涉流沙,波深弱水。胡风起处,动塞草以愁人;山鬼啼时,对荒兵之落叶。朝行雪巘,暮宿冰崖。树挂猿猱,境多魑魅。层峦叠于葱岭,萦似带雪之白云;群木簇于鹫峰,耸[若]参天之碧峤。逞途多难,去也如何。我有三世诸佛心要法门,师若受持,可保来往。”遂乃口授与法师讫。至晓,失其僧焉。三藏结束囊装,渐离唐境。或途经厄难,或时有阙斋馐,忆而念之四十九遍,失路即化人指引,思食则辄现珍蔬,但有诚祈,皆获戬祜。至中天竺摩竭提国那烂陀寺,旋绕经藏次,忽见前僧,而相谓曰:“逮涉艰险,喜达此方。赖我昔在支那国所传三世诸佛心要法门,由斯经历,保尔行途,取经早还,满尔心愿。我是观音菩萨。”言讫冲空。既显奇祥,为斯经之至验,信为般若,□为圣枢,如说而行,必超觉际。究如来旨,巨历三祗;讽如来经,能销三障。若人虔诚受持者,体理斯而勤焉。
大英博物馆藏的这个卷子,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心经》音写本之一。它前面的序文,题“西京大兴善寺石壁上录出,慈恩和尚奉昭(诏)述序”;其后是署名“不空奉诏译”的《莲花部等普赞叹三宝》;最后是正文,题“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亲授梵本,不润色”。这个序言是何年所作,已不可考。
序文中记《心经》传授始末,说唐三藏志游天竺,经过益州,宿空惠寺,遇到一个有病的僧人,说有三世诸佛心要法门,口授与法师。此后,法师凡经困厄磨难,只要背诵《心经》,诚心祈祷,都会获得保佑。玄奘后来在中天竺摩竭陀国那烂陀寺忽见在益州所遇的那个僧人,自谓“我是观音菩萨”,然后现身升空。
这个序言进一步强化了《心经》的神迹与作用,已经有《西游记》神话故事的影子。历史叙述开始向文学叙述转化。
序言中也有“硬伤”:比如说玄奘“游天竺,路次益州”,益州并不在玄奘取经的路线上。
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发表论文《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首次对敦煌S.2464号卷子进行研究。陈指出:这段文字亦有所本,这就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本心经序文,历叙因缘,盛谈感应,乃一变相之冥报传。实考证玄奘取经故事之重要材料,殊未可以寻常经典序文目之也”。除了“冥报传”之说不很准确(“佛经应验说”更准确一些),陈说眼光独到,甚是得当。
《心经》来历之四说:燃灯佛授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三藏取得经卷之后)点检经文五千四十八卷,各各俱足,只无《多心经》本。(第十五节)
竺国回程,经十个月,至盘律国地名香林市内止宿。夜至三更,法师忽梦神人告云:“来日有人将《心经》本相惠,助汝回朝。”良久惊觉,遂与猴行者云:“适来得梦甚异常。”行者云:“依梦说看经。”一时间眼憾热,遥望正面,见祥云霭霭,瑞气盈盈,渐睹云中有一僧人,年约十五,容貌端严,手执金杖,袖出《多心经》,谓法师曰:“授汝《心经》归朝,切须护惜。此经上达天宫,下管地府,阴阳莫测,慎勿轻传。薄福众生,故难承受。”法师顶礼白佛言:“只为东土众生,今幸缘满,何以不传?”佛在云中再曰:“此经才開,毫光闪烁,鬼哭神嚎,风波自息,日月不光,如何传度。”法师再谢:“铭感,铭感!”佛再告言:“吾是定光佛,今来授汝《心经》。回到唐朝之时,委嘱皇王,令天下急造寺院,广度僧尼,兴崇佛法……”(第十七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宋元时期说唱话本,记述玄奘取经故事。作者不详,许多人认为是宋人撰写,鲁迅认为是元人所作。这部话本是《西游记》的雏形。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叙述中,玄奘取回的经卷中没有《心经》,《心经》是在取经回程中得到的;授经人不是前面所说的病人、病僧,也不是观音菩萨化身,而是定光佛。定光佛,也称燃灯佛、锭光佛,是释迦牟尼的老师,是过去佛。在《取经诗话》中,《心经》的作用更是了不得:“此经才开,毫光闪烁,鬼哭神嚎,风波自息,日月不光……”十分玄奥。
《取经诗话》第十七节还讲到:“皇王收得《般若心经》,如获眼睛,内外道场,香花迎请。”可见对《心经》的推崇。
《心经》来历之五说:乌巢禅师授
《西游记》第十九回写道,浮屠山中,有个乌巢禅师,以树为家,结巢而居,成天在树上打坐修行,他送给去西天取经的唐僧一卷《心经》,保佑师徒一路不惧妖魔鬼怪。
(乌巢)禅师道:“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瘴难消。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三藏拜伏于地恳求,那禅师遂口诵传之。经曰:……(《心经》全文略)此时,唐朝法师本有根源,耳闻《多心经》,即能记忆,至今传世。此乃修真身之总经,作佛之会门也。
这是《心经》来历的又一种说法。
唐代还真有乌巢禅师这么一个人,此人俗姓潘,法号道林,《宋高僧传》说他生卒于735—833,《景德传灯录》说他741年生824年归去。这个人持钵振锡,漫游四方,一天抬头看见秦望山形势险峻,且有一棵老松枝繁结盖,遂栖居于松巅,结跏趺坐,前后达四十余年。期间,有鸟在他身边的树枝上搭窝构巢,生儿育女,鸟与他彼此相安,相看两不厌,相忘于江湖,成为好邻居。人称“乌巢禅师”。有诗赞云:“形羸骨瘦久修行,一纳麻衣称道情。曾结草庵倚碧树,天涯知有鸟窠名。”(静筠禅师:《祖堂集》)
乌巢禅师远离尘埃,打坐在高枝上,看繁华落幕生命无常,悟色空不二诸法空相,逃大造,出尘网,六根清净,八风不动,修成身在尘世远离凡间的大师。
玄奘版《心经》诞生地——翠微宫
长安城南有终南山,终南山上有个松风空翠之地,唐初建翠微宫。翠微宫于贞观十年(636)废,贞观二十一年(647)重修。元和元年(806)改为翠微寺。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唐太宗幸驾翠微宫,皇子及玄奘法师随侍。其间,玄奘法师与太宗谈玄论道,问因果报应及西域遗芳。
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成书于730年)载,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玄奘法师于终南山译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
历史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
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四日,终南山翠微宫中,唐太宗李世民病危。病榻前,玄奘法师捧着刚刚定稿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请太宗圈定。太子李治、武媚娘在场,见证《心经》(玄奘版)诞生。
这一天,唐太宗驾崩翠微宫,玄奘诵读《心经》为君王超度。
随后,李治登基,武则天也逐渐走向大唐舞台中央。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在《心经》声中拉开大幕……
我到翠微宫时,世间已无翠微宫。老屋几间,乱石数堆,野草丛生,蜂蝶纷飞。昔日华宇荡然无存,只有翠微宫遗址上的皇峪村,以及山间的翠微之气。一种俗称知了的蝉虫反反复复地叫着“佛了佛了”“空了空了”。此地此景,好像是在用最平易的景象跟声音告诉众生:繁华落尽,色即是空。
在《西游记》的叙事中,唐僧取经西行,时常被神仙或妖精幻化的景象所迷,明明住进大厦高堂、雕梁画栋,可一觉醒来,也不见大厦高堂,也不见雕梁画栋,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这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真实景象的神话夸张而已。
一花一世界。建立在这花上的世界会和花一样盛开凋零。
世间生生不息,又变幻无常。王维诗曰:“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孟城坳》)今人沒有必要为古人悲,后人也不要为今人悲。毕竟,万法皆空……
《心经》存世的最早版本
《大唐内典》完成于664年,其中有玄奘翻译《心经》的记录,这是玄奘翻译《心经》的最早在案记录。664年2月5日,玄奘圆寂。
《心经》存世的最早版本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房山云居寺与石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罗炤考证,保存在房山云居寺石经山第八洞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镌刻于公元661年,是目前发现的《心经》最早版本。
纸、帛不易保存,容易损坏。尤其是经历北魏和北周的两次灭佛浩劫,佛家着意石刻佛经。被赵朴初先生称为“北京的敦煌”的云居寺,从隋文帝时名僧静琬大师发愿刻造石经开始,经过唐、宋、辽、金、元、明末一千余年,共刻佛教经籍一千多种,三千四百多卷,石刻佛经版一万四百多块,为我们留下一部石刻的《大藏经》。
石经,极妙!经与自然同体,与大化同在。
《心经》刻在石头上,以本自俱足之体、万古不磨之句、金刚不坏之身,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不摇不动,且坐且大。
《心经》信仰
玄奘法师以旷古巨眼、通神手笔译出《心经》后,《心经》从庙宇、从宫廷流向民间,人们信受奉行,逐渐形成了“《心经》信仰”“《心经》崇拜”。
《心经》成为“中华安心经”。
玄奘法师是《心经》信仰、《心经》崇拜的始肇者。
高宗即位,法师还慈恩,专务翻译。永徽三年春三月,法师于寺端门之阳造石浮图。高宗恐功大难成,令改用砖塔,有七级,凡一百八十尺,层层中心,皆有舍利。冬十月,中宫方妊,请法师加佑,既诞,神光满院,则中宗孝和皇帝也。请号为佛光王,受三归,服袈裟,度七人,请法师为王剃发。及满月,法师进金字《般若心经》及道具等。(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见《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
这段话中说,公元653年(唐高宗永徽四年),皇太子(即日后的中宗皇帝)满月之时,玄奘向唐高宗敬献金字《般若心经》以及其他法物,以示祝贺和祈禳之意。
玄奘献金字《心经》,显示他对《心经》的推崇,尤其是对《心经》的祈禳祝福功能情有独钟。
玄奘法师的推崇,西天取经的传奇,观自在菩萨在中土的巨大影响,中华文化重视修心(心被称为“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伟大传统,以及《心经》文通气畅、句句得力、简明扼要的鲜明风格,种种机缘会合,促进了《心经》的传播。
“《多心经》者,乃五乘之宝运,严万法以为尊;八藏之妙高,芳四珍而独秀。”(唐智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心经》具有避祸祈福的无比神力的说法在中国广为流行。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开始受持、读诵、传写、流布《心经》。
《太平广记》中记载有这样的故事——
李观刺血写《心经》,院内生香。“唐陇西李观,显庆中寓止荥阳。丁父忧,乃刺血写《金刚般若心经》《随愿往生经》各一卷,自后院中恒有异香,非常馥烈,邻侧亦常闻之,无不称叹。”(《太平广记》卷一○三)
王琦诵《心经》49遍,妻子病愈。“唐王琦……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疠。琦灯下至心为诵多心经,得四五句……琦却诵经四十九遍,李氏寻愈也。(出自《广异记》,见《太平广记》卷第一一一)
孟知俭一生诵《心经》三、四万遍:“唐孟知俭,并州人……俭曰:一生诵多心经及高王经,虽不记数,亦三四万遍。”(出自《朝野佥载》,《太平广记》卷一一二)
敦煌遗书中,《心经》卷子上的许多题记,也反映出民众对《心经》的信仰。抄录几则如下:
“诵此经,破十恶、五逆、九十五种邪道。若欲报十方诸佛恩,诵‘观自在‘般若百遍千遍,灭罪不虚。昼夜常诵,无愿不过(果)。”(斯四四O六号)
“弟子押衙杨关德为常患风疾,敬写《般若多心经》一卷,愿患消散。”(斯三三一一号)
“奉为母羊两口,羔子一口,写经一卷,领受功德,解怨释结。”(斯四四四一号)
“此经元(原)于《大般若》中流出,如《法华经·普门品》别行之类是也。三藏法师玄奘每受持而有灵验,是故别译以流通。若人清心澡浴,着鲜洁衣,端身正坐,一诵五百遍者,除九十五种邪道。善愿从心,度一切苦厄。”(斯三〇一九号)
元好问《续夷坚志》卷四之《米元章心经咒》中记载:“米老一帖云:《心经咒》从后倒念七遍,吹气枕席间,螫虫皆不敢近。试之信然。”
千百年来,《心经》以其强健思想、温柔形式、不可思议的功德和传说,闪烁着神圣的灵光,为广大民众所信仰。
《心经》信仰是玄奘引起的。但是,在《心经》的传播过程中,在种种神奇的传说中,特别是在《西游记》中,玄奘的形象被逐渐削弱了甚至被扭曲了——他的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心经》的作用被大大加强了。
玄奘于《心经》,有大生力。他若知道在他身后,人们扬《心经》而“贬”唐僧,大概不会眉峰双锁,心中不快。他秉教法门,早无嫉妒之心、念恋之心了。
《心经》与玄奘,相映生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心经》真伪
1992年,美国学者那体慧在《国际佛教研究协会会志》第十五卷第二期发表长篇论文,题为《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文章搜集了大量资料,将玄奘所译《心经》与梵、藏本做了细致的比较,特别是与罗什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相应段落的翻译几乎完全一致,接着将汉译本与梵文本进行比对,发现两者亦基本相符。但再把《心经》与梵本《大品般若》比对后,发现前者的梵文语言多有不妥之处,表现在词汇、语法和句子的表达方式上,说明现存梵文《心经》可能是由母语不是梵语的人从中文翻译成梵文的。印度现存梵本《心经》注则出现在八世纪左右,明显晚于玄奘译本。那体慧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般若心经》最早是从《大品般若》中抽取一些段落,再回译成梵文,而回译者就是玄奘本人!
也有学者指出,《心经》末尾有段咒语,这在大乘佛教中是非常罕见的。
“伪经说”点金成铁,凿空经典,固然可以作为一种学术讨论,终不过是聚讼而已,夺人耳目而已,它无碍于《心经》的本来面目。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梵本《心经》晚于玄奘译本,也不能有力地证明它是玄奘回译。历史上,一种著作的最早版本、母本失传的例子太多了。况且,在原文失传的情况下,回译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尊敬,也是保护文献的一种办法。
瓦尔特·本雅明说:希望全部用看似没有关联的“引文”来完成一篇作品。如果说《心经》真的是从《大品般若》中抽取一些段落,由玄奘“创作”的话,那真是九转还丹、仙胎自孕,东渡中土而开花矣。玄奘代观自在菩萨立言,将600卷《大般若经》准确提炼为260字的《心经》,化机在掌,信手拈来,境界全出,妙谛自成,甚是浅易,甚是深处,无一个是闲字,无一句不警策,空古准今,无所不备,其功至伟哉!如此超入圣域之无上神品,非玄奘不能为也!可以说,《心经》是中国人“写”的影响世界的佛经,《心经》是中国人献给全人类的“安心经”。
王羲之抄过《心经》吗?
中國许多书法家抄写过《心经》。线装书局曾经出版《书法名品精选——心经大系》,将王羲之、张旭、欧阳询、苏轼、吴镇、赵孟頫、傅山、文徵明、八大山人、董其昌、吴昌硕、乾隆、刘墉、溥儒、于右任、弘一法师等16位大师抄写的《心经》会聚,以原作尺寸高清复制,蔚为大观。
我还买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制的启功抄录《心经》(经折装,每页四行,每行八字),出版社为印这本书,用朱砂调制了pantonr专用油墨,仅印三千册。
令我惊奇的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心经》抄本。
长安之南,天子峪口,有百塔寺。此寺始建于西晋,为中国佛教三阶宗祖庭。寺中有个介绍说,东晋王羲之在此写过石碑《心经》,石碑现存西安碑林内。
王羲之(303—361,一说321—379)在前,王去世几十年后才有罗什《心经》译本(约402年),去世三百年左右才有玄奘《心经》译本(649年)。王羲之可以穿越终南山,但不可能“穿越”到后世去抄写《心经》。
西安碑林里王羲之的《心经》(玄奘译本),是唐代弘福寺怀仁和尚集王羲之的字完成的。
让一位不在场的伟大书法家“抄写”一部伟大的经典,美美与共,更加其美,这是热爱《心经》者的美意——美得无有时间隔离,无有空间分别,无智亦无得。我们当心领神会,并为之心旷神怡。
王维读过《心经》吗?
王维被称为“诗佛”。有个朋友见我一边读《心经》,一边读王维的诗,问我一个问题:“诗佛”读过《心经》没有?
鸠摩罗什大约在402年翻译了《心经》,玄奘649年又翻译了一遍《心经》。信佛的王维(701—761)应该看过《心经》。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他读《心经》的记载。
作为“天下文宗”的王维,笃志奉教,精通佛学,他的名(维)与字(摩诘)就是从《维摩诘经》或维摩诘这个古印度著名的“在家菩萨”中化来的。《旧唐书·王维传》说:“维弟兄俱奉佛,……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对大乘经典比较熟悉,对《维摩诘经》应该是有所悟的。《心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心脏”,说他读过《心经》,也不是什么很不靠譜的事情。从他的诗词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先看王维的《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空山”不空,诸“色”纷呈。作者用明月、松树、清泉、石头、竹林、浣女、莲叶、渔舟等一个个具体而形象的“色相”,写出了“空山”不空跟“空山”之“空”。这正是《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心经》的中心教义是“空”,这个“空”,不是了无一物的顽空,而是色空不二、空色合一,是说形色性空——所有事物都以自己的形状色彩、以面貌存在于世界之中,但它们的本质是“空”的,是“空性”。虚空中有妙有,妙有即虚空。王维通过写山中缤纷的现象,道出了色相俱空的“空山”,也证悟了空性,达到了众缘和合、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空色圆融的大自在。
再看《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山中的这朵花,不求人知,不冀人赏,无负无累,一任自然,体现了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性妙体”。盛开的花朵,发于自然,自开自落,开也是落,落也是开,超越开落与生死。这正是《心经》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诸法空相”。四大五蕴的缘起和合,建立起人的幻相,只有悟出“五蕴皆空”,才能够生死圆融。这首“心无挂碍”之作,写花的开落自然,名言两忘,色相俱泯。诗人像尊者那样只是拈花微笑,“其意不欲著一字,渐可语禅”(刘辰翁《王孟诗评》)。所谓不用禅语,时得禅理;所谓诗之化境、禅之悟境,就是如此了。难怪它每每为禅宗所引,的确值得细参。
还有《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呀,真的是释仙杖履,无住无沾,超然物外,悠然自适。非深于佛法禅理,如何能达到这般境地。
其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尽是禅机、禅悦、禅趣,写出了他对“色”与“空”的独特理解。“行到水穷处”,是逆流而上,下游的洪流中游的浪花上游的细水到源头都是“无”是“空”,在追根溯源中将那形形色色的万象看破,这是“色即是空”的境界,是从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声香味触法”……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的境界。这里没有阮籍穷途末路时恸哭而返的痛苦,只有“去执”后返本归源、明心见性、得见本来面目的从容自在。“坐看云起时”,是立足于万物空性的立场,看那大千世界生生不息,这是“空即是色”的境界。水穷何碍?云起何干?关于这两句诗,清人徐增说:“行到水穷去不得处,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即坐而看云之起。……于佛法看来,总是个无我,行无所事。行到,是大死;坐看,是得活;偶然,是任运。此真好道人行履。谓之‘好道,不虚也。”(《说唐诗》)王维的这首诗,水穷云起,自在流出,无挂无牵,纤纤出尘,进入了安身立命、动静圆融的神境。
王维的组诗《辋川集》二十首,以及他晚年的许多诗歌,满是禅理。他存世的四百多首诗歌,用“空”字八十多回,“空”是他诗歌及生命的关键词,这是他的般若空观在诗歌里的投射。
可以说,王维读通了包括《心经》在内的大乘经典,沟通了佛教体验、生命体验与审美体验。众生难以形求的佛学义理,被他以诗歌的形式形象地显现和演示出来。他引禅入诗,以诗写禅,书写了他的“心经”——诗歌版的“心经”。他被大家公认为“诗佛”,名符其实。
《西游记》中的《心经》
中国古代名著中对《心经》着墨最多的是《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代表作,讲了三藏师徒去西天取经的艰辛历程,其实也是讲一个人的修心过程。《西游记》第十九回、二十回、三十二回、四十三回、四十五回、八十回、八十五回、九十五回等都出现有关《心经》的情节,其中第十九回还收录了《心经》全文。
《西游记》第十九回说,唐僧西行,经过浮屠山,遇到乌巢禅师。乌巢禅师知道西天取经之路遥远,且魔障甚多,于是口传唐僧《心经》以护身避邪。他说:“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障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按:270字是指玄奘法师翻译的《心经》正文260字,加上经名全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0字)
《心经》,“乃修真之总经,作佛之会门也”。唐僧耳闻一遍,即彻悟了《心经》,打开了门户。从此,“常念常存,一点灵光自透”。(第二十回)
《西游记》中,《心经》又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多心经》《蜜多心经》《般若心经》等,是《西游记》中着笔最多的佛经。
李卓吾曰:“游戏之中,暗传密谛。学者着意《心经》,方不枉读《西游》一记,孤负了作者婆心。不然宝山空手,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
唐僧读《心经》,曾做了一篇偈子:“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生灭尽由谁,请君自辨别。既然皆己心,何用别人说?只须下苦功,扭出铁中血。绒绳着鼻穿,挽定虚空结。拴在无为树,不使他颠劣。莫认贼为子,心法都忘绝。休教他瞒我,一拳先打倒。现心亦无心,现法法也辍。人牛不见时,碧天光皎洁。秋月一般圆,彼此难分别。”(第二十回)这个偈子,是唐僧读《心经》的感悟。
《西游记》毕竟是小说家言,在这部书的叙述中,《心经》对唐三藏的帮助好像没有乌巢禅师说的那么神奇,许多时候他正念《心经》,或者遇到魔怪时念诵《心经》,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像《西游记》中说的那样“空念空经,不能济事”,最终还需要孙悟空去战斗。一路上,唐僧基本上没有给他的徒弟讲授《心经》,也没有提醒徒弟们念诵《心经》,反倒是孙悟空不断地提醒唐僧不要忘记《心经》。孙悟空对《心经》,有自己的心得和解释。他曾经自夸说:“我解得,我解得。”
《西游记》第三十二回,唐僧西行见高山挡路,对徒弟们说道:“前遇山高,恐有虎狼阻挡。”孙行者说:“师父,出家人莫说在家话。你记得那乌巢和尚的《心经》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方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之言?但只是‘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你莫忧虑……”
第四十三回中,唐僧耳朵里忽然听到水声,产生幻觉,孙悟空批评师父说:“你把那《多心经》又忘了也?”唐僧说自己没有忘记。悟空说:“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嗅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这样的解说,还真是有所思悟,不是信口开河之语。这一席话,提醒了唐僧,原来是他思乡的念头作怪。
第八十五回中,唐三藏见到前面高山阻挡,内心惊惶,神思不安。孙悟空提醒师父说:“你把乌巢禅师的《密多心经》早已忘了。”三藏说:“我记得。”悟空说:“你虽记得,还有四句颂子,你却忘了哩。”三藏问:“哪四句?”行者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里修。”这四句不是《心经》里的话,却是对《心经》的解读。三藏说:“若依此四句,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行者说:“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你这般恐惧惊性,神思不安,大道远矣,雷音远矣。”这些话对三藏颇有启发,他一听,心神顿爽,万虑皆休。
第九十三回中,唐僧感叹取经之路遥远,悟空又提醒师父说:“师父,你好是又把乌巢禅师《心经》忘记了?”三藏说:“《般若心经》是我随身衣钵。自那乌巢禅师教后,那一日不念,那一时得忘?颠倒也念得来,怎会忘得!”悟空说:“师父只是念得,不曾求那师父解得。”三藏说:“猴头,怎又说我不曾解得!你解得么?”悟空说:“我解得,我解得。”唐僧表扬悟空说:“悟空解得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得到这样的评价,对悟空是合适的。通观《西游记》,孙悟空对《心经》的领悟比唐僧深刻许多。
唐僧和他的徒弟就是这样一路念诵着《心经》,食风宿雨,卧月眠霜,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来到西天,取回真经,修炼成佛的——唐僧是旃檀功德佛,悟空为斗战胜佛,八戒为净坛使者,沙僧为金身罗汉,白马为八部天龙。
《红楼梦》与《心经》
到八十八回,《红楼梦》中出现《心经》。说的是,明年是贾母八十一岁生日,老太太许下一场九昼夜的功德,发心要写三千六百五十一部《金刚经》。
贾母的丫头鸳鸯说:
俗说《金刚经》就像那道家的符咒,《心经》才算是符胆。故此,《金刚经》内必要插着《心经》,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经》是更要紧的,观自在又是女菩萨,所以要几个亲丁奶奶姑娘写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诚,又洁净。
鸳鸯请“几个亲丁奶奶姑娘”抄《心经》,她带来了香跟纸:“这素纸一札,是写《心经》用的。”又拿出藏香道:“这是写经时点着写的。”
八十八回的这段描写,透露出许多信息——
抄经文可以积功德。尤其是大户人家的老人过生日时,都是要抄经文的。当然也都不是自个儿亲自抄,而是自家出钱出物请人抄,抄出来后,再施舍于人。
抄经,抄哪部经文都好。在中土,《金刚经》比较盛行,篇幅不长不短,抄者比较多;《心经》正文只有260字,抄起来更容易一些,抄的人就更多了。
抄经时,是要点香净心的。
鸳鸯所说的“俗说”,虽然有些不太准确,但大致不错,道出了《金刚经》与《心经》的关系:“《金刚经》就像那道家的符咒,《心经》才算是符胆。”道家与佛家有些地方是相通的。《心经》虽篇幅短小,却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心脏。
如今,许多经书都是将《金刚经》跟《心经》合印在一起,这固然是两者的内容相通,都是大乘的经典,但民间的说法“《金刚经》内必要插着《心经》,更有功德”,亦可备一说。
《红楼梦》中,抄《心经》者有谁?
惜春抄了。八十八回中,鸳鸯给惜春送去了素纸跟藏香,惜春说:“别的我做不来,若要写经,我最信心的。”
黛玉不仅抄了,还讲对《心经》的理解。八十九回中,宝玉去看黛玉,笑问道:“妹妹做什么呢?”黛玉说:“我在这里抄经,只剩得两行了。等写完了,再说话儿。”黛玉的确是在净心抄《心经》。在九十一回中,几乎可以听到黛玉对《心经》的解读了。那天,宝玉发呆说:“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天地间没有了我,倒也干净!”黛玉说:“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恐怖颠倒梦想,更有许多缠碍。”这就是《心经》中说的,人有眼耳鼻舌身意,产生色声香味触法,心生挂碍,有了颠倒梦想啊。
贾母许愿抄三千六百五十一部《金刚经》和三百六十五部《心经》。其间,她的儿子被夺了封号,宝贝孙子宝玉几乎傻了,外孙女黛玉死了,宁国府荣国府被抄了,她最得力的王熙凤也蔫了,这个神奇的老太太大难不死,成为整个家族的支柱。
第一百一十回中,贾母病危,临终还问:“旧年叫人写了些《金刚经》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没有?”贾母享年八十三岁,笑着离开了人间。
一只会诵《心经》的鸟
会背诵与不会背诵《心经》是不一样的。以鸟为例——
先看一只不会诵《心经》的鸟。有一只海鸟飞到鲁国,鲁侯看见了很是喜欢,他命人把这只鸟捉拿过来,养在太庙中,每天给它演奏最美的音乐,给它送来最美味的食物。这只鸟,身为海鸟却过着不是海鸟的日子,身在太庙而心游大海,心在大海而身陷太庙……海鸟忧伤,愁眉不展,满目凄凉。面对音乐伴奏的美食,它没有吃一口,连一滴水也不喝。熬到第三天,海鳥死了。这是《庄子》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这只海鸟,它无法改变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也适应不了人类强加于它的生活方式——尽管鲁侯是爱它的,最终郁闷而死。
再看一只会背《心经》的鹦鹉。吴地有位姓段的巨商,从西北秦陇弄来一只鹦鹉。这只鹦鹉甚是聪慧,能诵《心经》,还会背李白的《宫词》等。每有客人来,它就呼叫上茶,问安寒暄。主人十分喜欢它,把它放在金贵的笼子里精心喂养。有一天,段商人出事入狱,半年后获释回家,他对鹦鹉说:“鹦哥你好吗,我在狱中半年,朝夕都在想你,这段时间家人喂饮你是否及时?”鹦哥说:“你在牢里被禁数月不堪忍受,这和我鹦哥一年到头被囚闭鸟笼中的感受是一样的。”段某听了鹦鹉的话,流着泪说:“我一定把你送回你的家乡。”他带着鹦鹉,乘着车马,不远千里来到秦陇之地,对鹦鹉说:“今送你回到了老家,你自由飞翔吧。”鹦哥整羽徘徊很久,才飞进山野。后来听说,这只鹦鹉遇到吴地来秦地做生意的人,就问:“你回去见我家段二郎了吗?他可安康?”并且吩咐说:“若见他时,告诉他鹦哥很是思念二郎。”这是宋代的文莹《玉壺清话》中记载的故事。《玉壶清话》是1078年前后作于荆州的一部野史笔记。
《玉壶清话》中并没有说鹦鹉如何背诵《心经》的,但会诵《心经》的鸟,它与一般的鸟是不一样的。人常说,“走来名利无双地,打出樊笼第一关”。那个不会诵《心经》的海鸟没能“打出樊笼第一关”,会诵《心经》的鹦鹉则可以打出樊笼,复得归自然。当我看到鹦鹉飞出笼子,飞向山野,立即就想到《红楼梦》中那个经历了大观园的繁华昌盛与悲欢离愁,走向大荒山青埂峰下的宝玉。宝玉最后作歌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毛泽东谈《心经》
毛泽东是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却从不以佛道为异端,他曾对班禅说:“《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第3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版)
毛泽东对佛教经典《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都比较熟悉。
毛泽东说:“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字太多,很难读完。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金刚经》的内容提要,只有几百字,比较好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1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内容提要”云云,语显粗些。《心经》不是《金刚经》的内容提要。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五千多字,不长,也容易读完。当然,毛泽东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毕竟《金刚经》与《心经》都是大乘经典。准确地说,《心经》单篇成经,与《大般若经》内涵一致,260字的《心经》足以洞见600卷《大般若经》之全体。
毛泽东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做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得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惠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把佛经分为“上层的佛经”与“劳动人民的佛经”,自古以来,只有毛泽东这样分析。
毛泽东对《金刚经》中“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即非般若波罗蜜多,是名般若波罗蜜多”这种表述句式和思维方式很熟悉。他曾问赵朴初:“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赵朴初说:“有。”毛泽东说:“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赵回答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
可见,毛泽东是认真研究过佛经包括《金刚经》《心经》的。
《心经》是老百姓随身携带的神秘中国
梁衡的《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说:中国从古至今,一篇文章而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和文化思想的文章共有十篇。这十篇政治美文是:(1)贾谊《过秦论》;(2)司马迁《报任安书》;(3)诸葛亮《出师表》;(4)陶渊明的《桃花源记》;(5)魏徵《谏太宗十思疏》;(6)范仲淹《岳阳楼记》;(7)文天祥《正气歌并序》;(8)梁启超《少年中国说》;(9)林觉民《与妻书》;(10)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好眼力!梁先生目光如炬。不过,笔者以为,梁先生如果不局限于“十篇”而再加一篇就更完美了——加上《心经》,这是世间一篇有数文章。
《心经》连题目268字(或者说270字),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经典之一,尽管它没被选入历代文选、收入大中小学教材,但是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拥有上亿人口的国度里,许多人背诵它,歌唱家吟唱它,书法家书写它,家庭里悬挂它,随身饰物上镌刻它;它成为婴儿的摇篮曲,它是生日及贺寿的平安符,它超度垂死者,它是佛教徒每天的功课,它印成各种版本的书卖给或布施民众,它影响且感化皇帝及目不识丁者;它使愚蠢者变得智慧,使残暴者变得慈悲,使生命变得空灵。哪篇文章有此殊胜殊荣?哪一本书具有如此影响力呢?
《心经》是中国人自救救人的心灵读本,是与中国人最为亲近的文字之一。它是中国老百姓随身携带的神秘中国。
《心经》照亮了中国人的心,改造着中国人的心灵。当之无愧,它是中华安心经。
《心经》正文260个字,宛然260尊菩萨化身。我等从中学会一个字,就是遇见一位菩萨。260个字覆盖自己的肉身,就是260位菩萨的护佑,够我们受用今世后世了……
(说明:《〈心经〉》故事这是《〈心经〉初见》的姊妹篇。《〈心经〉初见》见《美文》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