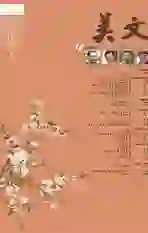汪曾祺,喜欢看云的导游实诚又任性
2017-12-13王国平
王国平
一

同学的儿子三四岁,有一天问:
妈妈,有白云博物馆吗?
孩子想的,跟白云一样美妙。
不过,假如真有个白云博物馆,汪曾祺是可以当“顾问”的,再不济也是个“明星讲解员”。
云,在他这儿是颇为受宠的。
《泰山片石·序》:
我从泰山归,
携归一片云。
开匣忽相视,
化作雨霖霖。
金实秋在《汪曾祺诗词选评》中感慨道,这像是一首禅诗,又似李商隐的无题,“也许会有多种诠释、不同揣测吧,似乎总令人看不清、摸不准、参不透”。
自己写的“咏云诗”月朦胧、鸟朦胧,但他最为中意的一首却明快、清丽。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
南朝齐梁隐士陶弘景的这首《诏问山中何所有》,汪曾祺是好生欢喜。
“这四句诗毫无齐梁诗的绮靡习气,实开初唐五言绝句的先河,一个人一生留下这样四句诗,也就可以不朽了。”他在《初识楠溪江·九级瀑》中不吝赞叹。
于是,行文屡次征引。
书赠友人时信手拈来。
还是朱文印章之印语。
“汪公好云”与“叶公好龙”不是一回事,这是真爱。
《觅我游踪五十年》,写在昆明的日子,“落拓到了极点,一贫如洗”,有时吃饭都是个问题,只好卧床不起。同学朱德熙见状,就夹着一本字典,喊他起来。卖了字典,把饭吃了,闲逛,或者到花园的草地上躺着,“看天上的云”。
给点阳光就灿烂,打着饱嗝忘了饥。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饭已吃下,什么为大?看云好了。
下一顿呢?管他个娘!
优哉游哉,云聚云散。
云聚云散,具体是个什么模样?21岁时,汪曾祺写下的《待车》试图描绘了一通:“云自东方来,自西方来,南方来,北方来,云自四方来。云要向四方散去。”
甲骨上有一段上古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一个云,一个雨,不知汪曾祺有没有借用?
方星霞评点道,汪曾祺这么写“很不好懂”,因为“意识如浮云流动”。
用“浮云”来评述这段“实在难以捉摸”之云片段,堪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么个逻辑关系,估计要让“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声气粗粗的”陈相公感到头晕。
这个《异秉》中的药店学徒,整天都过得“刻板枯燥”。只有趁着太阳,爬上梯子,到屋顶晒丸药,才是最快乐的时刻。特别是到了七月,傍晚时分,可以看巧云,“七月的云多变幻,当地叫作‘巧云。那是真好看呀:灰的,白的,黄的,橘红的,镶着金边,一会一个样,像狮子的,像老虎的,像马、像狗的”。
《大淖记事》,十一子的女人,唤名“巧云”。她恰好是七月出生的,“生下的时候满天都是五色云彩”。
十五岁的巧云,“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
大姑娘巧云跟陈相公看到的巧云各有各的“好看”,赏心悦目。
巧云和十一子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两只鸳鸯你情我愿,但各自家庭的缘故,让他们一时“弄不到一起”。只好“发乎情,止乎礼”,经常相约谈谈坐坐,各怀心事,自奏心曲,“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令读着的人干着急。
汪氏哲学是,再着急也要把云细细读。1945年的《老鲁》,他写道:当教员的干巴巴等着喝水,却迟迟不见挑水的,原来人家“正在软草浅沙之中躺着看天上的云呢”。
想必這些挑水工人心中的旋律正响起:不管春风怎样吹,让我先把云儿追。
没有投诉,也不开除。
汪曾祺的解释是:“没办法,这个学校上上下下全透着一种颇浓的老庄气味。”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是杜甫的句子。没想到,这个凭着沉郁和悲凉行世的汉子,也被流水、云彩收拾得这般服帖。
这么想来,几个挑水的,因为躺着看云而误工了,不仅可以原谅,而且值得赞赏。
当然,看云不要总想着只是一个姿势。
《沽源》,汪曾祺写:
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出去,走得很远。忽然变天了,天一下子黑了下来,云头在天上翻滚,堆着,挤着,绞着,拧着。闪电熠熠,不时把云层照透。雷声訇訇,接连不断,声音不大,不是劈雷,但是浑厚沉雄,威力无边。我仰天看看凶恶奇怪的云头,觉得这真是天神发怒了。我感觉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我一个人站在广漠无垠的大草原上,觉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点。
但是呢,转眼间,雨住了,又是一个很蓝很蓝的天。
刚才还“堆着,挤着,绞着,拧着”的云,又“故态复萌”,重新开始在天空作画,“灰的,白的,黄的,橘红的”。
人一辈子,就应该痛痛快快地看几次云。
二
说汪曾祺是个实诚的人,大体不差。
《自报家门》,他自白: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
这应该是事实。那么一个“恍恍惚惚”的年龄段,又生活在苏北小城镇,加上世事动荡,信息渠道不畅通,不说自己完全就是奔着沈从文而报考的,只是“想到过”,程度不是那么饱满,符合实际。
但如果他就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因为沈从文而报考了,不考上誓不罢休,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不留缝隙,不让喘息,别人也没啥可说的。反正查无对证,他可以趁机做个顺水人情,哄老头子开心,大树底下好乘凉,于自个儿的发展也有利。还能显出自己的眼光:打小就知道沈从文必成大器,矢志追随,成疯成魔,給文坛的一段佳话添油加醋。
生活中的汪曾祺似乎如他笔下的明海、小英子,心境纯净,不被这些世俗套路左右。事实是三分,就说三分。这或许有些绝对,有时还是稍微加码,说个四分。有时为了自谦,就往后退一退,说个二分。但绝对不可飙至八分。
人之境界高低,就在这点点滴滴。
《我的创作生涯》,汪曾祺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台湾一家杂志转载他的小说,前言中认定他是中国最早使用意识流的作家。他坦言“不是这样”,因为“在我以前,废名、林徽因都曾用过意识流方法写过小说”。
人家给足了面子,热心送来一顶帽子,他却不领情,害得人家吃了个闭门羹。
大帽子、高帽子,多少人梦寐以求。
反正是别人送上门的,又不是自己强行要来的,这么受用的评价,程序又“合理合法”,不可晾了人家的一片好意。完全可以收入囊中,玩他个一年半载。
话说有人还健在,老家要给他修建旧居,还计划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舆论哗然,这位“名家”颇为无奈地发声:家乡的人这么热情,我有什么办法呢?
潜台词是,人生在世,义盖云天,不可驳了人家的面子,何况还是父老乡亲。
也就是说,好不容易到手的帽子,得紧紧攥在手上,“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
有的人就无以消受这么好的运气,没人送帽子。那就为自己加冕。
逛书店,拿起一本小说,是一般人不太知道的当代“著名作家”酝酿八年、强势回归的力作,首次面世。封底的“上架建议”,写的是“文学经典”。我赶紧放下。
烫手!
友人说,有次参加一个文学评选,有一般人不太知道的当代“著名作家”,报送的图书名为《×××经典作品集》。这就好比裁缝师傅做了一身龙袍,自个儿穿上了。大家讨论时说,此风不可长,于是一票否决。
鼓掌!
到某地,看市情介绍,有一句说这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在全省非省会城市排名第一。其实也就是全省第二。但“银牌”哪有“金牌”优美动听?于是,不知是谁想出妙招,把外延缩小,限定范围,强行给这个城市新添了一枚勋章。
人才!
曾经遇见过一位教授,执教于京城某知名高校。初次相会,彼此没有“久仰”的“大名”,他操着深沉的男中音,耐心地介绍自己,是什么思想的“提出者”,是什么研究的“拓荒者”,是什么理论的“创立者”,还是什么学说的“开启者”。词汇都很怪异,艰涩,拗口,本来就是一个雾霾天,听他这么一介绍,雾霾的气息更浓了。
他说得认真,我也只好听得“认真”,眼瞅着他的嘴巴一张一翕,心在想:兜里的手机咋还不响呢?银行贷款的,卖保险的,卖房子的,卖茶叶的,那些整天喊我哥呀叔呀的,这个节骨眼上都干啥去了!
三
小说家这个行当,有点像导游,领着大家看风景。
彼此也是有合同的,故事渐次铺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处处设下伏笔,一步一步往上推,方向、节奏、目标大体是要满足读者期待的。
就像周杰伦歌曲《蜗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
最高点就在眼前了,你不能说别爬了,请回吧。
比如说,从外地来北京旅游,事先约定要登长城。但导游中途变卦,把这一站取消了,截断了游客“乘着叶片往前飞”的夙愿。这恐怕是要闹翻天的。
汪曾祺有时就是这么一个导游。
他的小说,正如王安忆所说,往往就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再“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得扑朔迷离”。故事淡淡的,但故事的痕迹和味道还是有的。只是有些篇章,故事往前走,走着走着,按常理说,眼瞅着就要到了A地,但汪曾祺偏偏自作主张,朝B地引了,这就扰乱了读者既定的情绪节奏,心理期待被搁置了,落空了。
举个例子。《大淖记事》,小锡匠十一子被保安队的刘号长和他的几个弟兄打了,“七八根棍子风一样、雨一样打在小锡匠的身子”,让他只存“一丝悠悠气”。
十一子和巧云属于自由恋爱,刘号长狗仗人势,破了巧云的身子,现在又大打出手,天理何在?
锡匠是一帮人,二十来个,平时就很讲义气,“扶持疾病,互通有无”。
赤条条的汉子,自家人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不得狠狠地干一仗!
而且,这帮锡匠的头领威信很盛,“说话没有人不听”。十一子恰是他的侄儿。于公于私,是要来那么一下狠的。
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这是民意。
刘号长和几个打手自行蔫了,不敢出来,保安队的门口竟然加了双岗,“这些好汉原来都是一窝‘草鸡!”对方怯了。
天时。
地利。
人和。
情绪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该动手了。
“波澜壮阔、大开大合、惊天动地”,王干在《论汪曾祺的和谐美学》一文中写道,如果是一个追求壮美的作家,肯定要这般处理锡匠抗议事件的。
但是呢,锡匠们经过开会商量,拿出的方案是上街,“这个游行队伍是很多人从未见过的。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
一走就是三天。
不见动静,就“顶香请愿”,只见“二十来个锡匠,在县政府照壁前坐着,每人头上用木盘顶着一炉炽旺的香”。
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
就像登长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你把干粮带了,水也备好了,手机的图片库也清空了,想着到时可以放肆地拍照了,新买了一双旅游鞋,担心新鞋磨脚,专门穿了几天,提前把鞋给驯服了。万事俱备,东风都不欠,正在路上。
可是,旅游大巴却驶入了北京植物园的门口。
这是怎么了?
什么!
啊!
不会吧!
我要投诉!
人家导游就是这么任性。
任性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他平缓缓地、乐悠悠地、笑呵呵地,领着你溜达,闲逛。
你看看这个菊花,颜色是很有味道的:
最初的菊大概只有黄色的。“鞠有黄华”“零落黄花满地金”,“黄华”和菊花是同义词。后来就发展到什么颜色都有了。黄色的、白色的、紫的、红的、粉的,都有。挪威的散文家别伦·别尔生说各种花里只有菊花有绿色的,也不尽然,牡丹、芍药、月季都有绿的,但像绿菊那样绿得像初新的嫩蚕豆那样,确乎是没有。
再看看这个葡萄,能耐大得很: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嗒嗒地往下滴水了。
这个树,很不错的,有年头。就在这树下,我给你朗读一段吧。也不知道我这个苏北口音,你是不是听得明白:
冬天的树,伸出细细的枝子,像一阵淡紫色的烟雾。
冬天的树,像一些铜板蚀刻。
冬天的树,简练,清楚。
冬天的树,现出了它的全身。
冬天的树,落尽了所有的叶子,为了不受风的摇撼。
冬天的树,轻轻地,轻轻地呼吸着,树梢隐隐地起伏。
他似乎有高超的催眠术,慢慢你也就平静下来了,投诉的想法也就给冲淡了,就像他笔下的云,“从远处来,过近处,又向远处去”。
你甚至可能已经“移情别恋”了:还别说,这个导游汪同志学问不浅,有股可爱的劲儿,挺有魅力的。再说这一路上的风景也不错,空气清新,绿意盎然,“情景交融”,蛮有意味,别有洞天。
既来之,则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