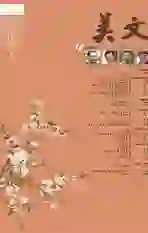茱萸:我的诗歌观
2017-12-13
茱萸,生于1987年。诗人,哲学博士,兼事批评与随笔写作。出版《花神引》《炉端谐律》《仪式的焦唇》《浆果与流转之诗》《千朵集》等作品、论著及编选约十种,发表诗学研究论文多篇。曾赴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访学。诗作被译为英、日、俄、法等多国语言,并取得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华语诗歌创作及翻译奖金。获全国青年作家年度表现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星星》年度诗人奖等文学奖项,参加《诗刊》社第三十一届“青春诗会”。现供职于苏州大学文学院,从事新诗史、当代诗及比较诗学诸领域的研究。
问:陕西有很多国内国际知名的作家,不知您对陕西诗歌界有什么印象?
茱萸:在我印象中,历史上的陕西诗歌界的国际知名作家似乎比现在更多,不是吗?哈哈,开个玩笑。贾平凹以及过世的陈忠实诸先生,当然都是很好、很知名的作家。至于陕西的诗人……大概十年前,我在同济念本科的时候,当时由文化批评研究所牵头,办过一场当代诗歌研讨会,其中的两位被研讨的诗人,就出自陕西,他们是阎安和宗霆锋。那年我二十岁,在诗歌之途上正是“初生牛犊”,并不知道自己的浅陋,跑去和他們交流过关于诗歌的不少话题。几年后,我在诗歌写作上遭遇了非常艰难的瓶颈时期,为了纾解焦虑,开始创作大量的诗学随笔。那时候阎安在《延安文学》做主编,数万字数万字地刊发我的这批随笔。就在两个月前,如今身为《延河》执行主编的他,又刊发了我三万多字的文章。我要感谢他,他不仅是优秀的诗人和编者,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是一名很好的批评家,无论是谈诗还是谈艺术,都极有见地。这次来西安之前,我和阎安只见过那一次。刚才我上去和他打招呼,他已经认不出我来了,因为十年前的我非常瘦,脸型和体型也没现在这样“圆润”。
除却诗人身份之外,宗霆锋还是一位画家和唱片收藏者,我很喜欢他的诗,在前几年还偶尔在微博互动,但后来就没有见过了。
我对陕西诗歌界的另一个印象是以伊沙为核心的口语诗人群,以及批评家沈奇。这几年,我跟他们两位也都见过。我觉得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批评上,陕西都挺多元的,有容乃大,这是好事情。昔日的长安,无论大到文化的繁荣,还是小到诗歌的热闹,其实也得益于这种对多元生态的接纳和营造。
问:诗歌创作一定有其暗含的脉络,我想了解您开始写诗的时候,哪些诗人或者作家对您影响最大?在您风格的转变期,又有哪些诗人做了您的引路人?
茱萸:我在初中时代意外地读到了波德莱尔、朗费罗和惠特曼。念高中的时候,又接触到当代汉语诗歌里的一些优异的作者,譬如王家新、孙文波、萧开愚、西川等等。后者主要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蓝星诗库”系列。要知道,在2002年前后的中国内地小城市的书店里,比这个更偏门的诗集就不容易遇到了。当然,还有海子、骆一禾和昌耀。后来在互联网上的各色诗歌论坛贴诗,认识了很多诗人朋友。念本科的时候来到上海,接触到了张枣和陈东东的诗。我在那篇长达数万字的随笔《陈东东:海神的导游图》(刊《收获》2016年第6期)里,详细回顾了当年与陈东东本人的初识,以及这十年来阅读他的作品的感受。张枣则无缘得见,不过近来阅读他的诗,愈发觉出其好。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之外,我的写作尚有另外的精神底色,即汉语古典诗歌及其美学传统。我童年时代习过几年旧诗,在阅读方面则偏爱六朝和晚唐(类似于日本近代诗僧大沼枕山所谓的“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那样),现代诗的写作,自然也不可能完全于此毫无沾染。在汉语的声、色、光、影几个方面,六朝和晚唐真是发挥到了极致。我将阅读它们的感觉带到现代诗的写作中来,并没有什么复古倾向,也不是评论界所谓的“新古典主义”,而只是就我的经验来说,那些古典时代的诗篇,至今依然能在我于当代的生活、阅读和思想中发生回响,产生新的生命力。
风格的转变期,大概是2007年前后,以及2012年前后两个阶段。促成前一次转变的因素相当复杂,带给我启发的诗人也非常之多,这种影响是综合的,很难拎出一个作者来说,是他/她造就了我的转变。所谓转益多师吧。不过在后一个阶段,我自己非常明确的是,对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阅读,为我自己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
问:目前正值汉语寻求世界认同之际,对传统的问题争论甚多,部分人认为有必要接续纯正的汉语传统,您在这方面持什么意见?有哪些方面的努力?
茱萸:我在2010年底写过一篇文章,叫《临渊照影:当代诗的可能》,后来发表在《当代诗》第二辑上。在这篇文章里头我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试图重估所谓的汉语(诗)的“传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老生常谈一点来说,我认可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头对“传统”的判断。我们汉语诗界的同行们,尤其是这些年以来,一直在说,要跟传统重新建立一种联系,或者就如你说的,要“续结纯正的汉语传统”。但实际上,就像我在《临渊照影:当代诗的可能》中谈到的,什么是传统,什么是古典诗歌的传统,我们都还没有足够的、真正的共识(有的只是似是而非、未加反思而人云亦云的“共识”),还没有足够地去理清思路。在这个时候,侈谈传统,侈谈与古典续接,我觉得有点胆大。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传统、谁的传统,它的内部风景是怎样的?你接续的是什么样的传统,你接续的是谁的传统,你接续的是这个传统中的哪个部分?你给它减少或增添了什么?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详加辨析的问题。
至于我自己的创作,在这个方向上或许也谈不上“努力”。对我来说,如果存在一个所谓的“汉语传统”的话,那我使用它,也是因为我对它比对其他资源和传统更加熟悉,用起来更顺手。像我弱冠时期写的《穆天子与他的山海经》系列也好,《夏秋手札》系列也好,甚至像《池上饮》这些在通常意义上偏所谓“古典色彩”的作品,对我而言,更多时候不是在接续传统,不是在接续古典资源,而是在征用古典资源。换句话说,我的思维、我借用的方式——戏谑或改造,是文学的某种“当代精神”——的属性还是“当代诗”的。我只是在写作中征用了这方面的一部分资源。至于这几年来致力于创作的长诗/系列诗《九枝灯》,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就更“努力”于“接续传统”了,但就我自己而言,它们依然是纯正的“当代诗”,回荡着古典时代人类声音的当代诗。
这些年我们的同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产生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效果,但是这个问题,我大概是觉得,是没有必要去问的。因为在每一个诗人的努力过程中,就可能重建或呈现出一种他个人、他所认为的传统,他的知识系统或认知系统中的传统,而不是一种普遍性的传统。每一个有志于处理古典汉语这份遗产的诗人,他们面临的问题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这头“大象”的不同部位,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盲人摸象”,我们都没有看到它的全貌;极端一点来说,它的全貌甚至是我们根本无法认知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在自己所能摸到的这块小领地上做到最好?
问:有人批评目前部分诗人技艺高于思想性,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在写诗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平衡这两方面的?
茱萸:我不太能理解“技艺高于思想性”这个判断。以我的偏见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流俗的观点。在诗歌中,存在一种脱离于技艺的“思想性”吗?文学作品的“思想性”都不是直接“说出”的,而需要通过技艺来实现。就算在一首诗中,技艺的痕迹超过了正常的限度,那么它所妨碍的应该也不是所谓的“思想性”——要“思想性”为什么不去写哲学著作或别的什么呢——而是作品的质地。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过重的“技艺”痕迹本身,也是创造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不存在什么“技艺高于思想性”的问题,只有诗的“技艺”是否足够高明或新鲜,能刷新人的审美或判断力。倘若用纯诗的观念来表述,说得更彻底一点,诗的“思想性”可能就是技艺本身。
问:作为旁观者,很想了解一名诗人的生活,您能谈一谈诗人生活与大众生活的普遍性和其自身的特殊性吗?
茱萸: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而言,他/她的生活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无比世俗,无比日常。我觉得这才是“诗人生活”的常态。但是这常态中又有一个隐秘的精神背景在起作用。诗人过的通常都是双重生活。在去年的初夏,我写过一首诗,即《诗人的隐秘生活》,其中的“隐秘”大概就是你说的,大众生活的普遍性中又有特殊性。关于这首诗其实还有一个背景。去年春天的时候,美国优秀的女诗人C.D.Wright去世,她的学生李栋,以其遗作《诗人的隐秘生活》出示,邀请不同国家的诗人分别用汉语、英语和德语创作同题诗,而我去年的那首《詩人的隐秘生活》即受邀而作。我写的是普遍属于诗人的“隐秘生活”,也是我自己的“隐秘生活”——
“诗人从云端跌落到了/具体的此时。/生活则不断召回它/派出去的使者:/在人间,你是否已赢得/收获的贫乏与丰盛?/咖啡,音乐,冗长午后/能给出的一切福利。/裁判者从不现身,他/注视着这平静的一切。/今夏凉爽,让人迷恋。/洒水车在不远处劳作。/窗外,风中摇摆的竹枝/投下了青翠的阴翳。/嘶哑的蝉鸣时断时续。/哦,我几乎快忘了/关于诗人的不幸消息。//穿过街衢,走进楼群,/在上海的旧工业区深入/厂房于新时代的改建。/如今改建早已完成,/人们委身于写字楼/枯燥的日常。而我在等待/又一天的过去,垂下窗帘,/昂着脖子劳作,屏幕/散发的微光/衬出脸部的轮廓。”
问:您觉得当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哪些影响?诗人如何在这样的时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茱萸:这个问题可以和上一个问题合并起来理解和回答。还是以《诗人的隐秘生活》为例吧。青年批评家王静怡在《具体的此时:茱萸诗中的时间和空间》这篇长文中重点谈到过这首诗,算是深得我心吧。干脆摘录在这里,作为对你这个话题的回应:
首句与波德莱尔那首著名的《信天翁》形成意义的相逢,诗人那曾经的云中王子却在尘埃中卑微而笨拙,这在文化浪潮退却的今天确实是诗人们无可抗拒的处境。茱萸把“隐秘”二字放在“生活”和“诗人”中间,并无意强调现实中诗人们和大众之间的疏离关系,而是从个人的生命经验中,发觉一些“隐秘”的面貌,换言之,是“隐于市”的自我判定而非“隐于林”的公众想象。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诗人群体活动空间的逼仄和话语权利的有限导致大众对诗人群体的偏见普遍带有“隐秘”的色彩。茱萸指出“具体的此时”才是诗人着陆的终点,也是自我审视的起点。茱萸……在将时间诗化的过程中,没有把关于“我”的存在结构化、抽象化,他只是平静地注视着外在世界也同样注视着自己内心。“裁判者从不现身”,诗人对于自我的存在更像是一个观察者,时间是诗人的镜头,诗人凭借镜头的伸缩可把流线状的日常生活显像在文字中。当然,从读者的一端望去,“具体的此时”亦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诗人内部情绪的“视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时间经验作为标尺,衡量诗人如何将生活延展或收缩。
问:80年代,诗人多以派别出现,集中出刊出书,本次的活动也邀约了众多的诗人,您觉得诗歌界的活动对诗歌发展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茱萸:相比于学术界或别的什么领域,诗歌圈子的一大特点是,尚存浓厚的江湖气息。我是在褒义的层面上来使用“江湖气息”这个词的。我在少年时期就在这个圈子里玩,颇有些“少侠行走江湖”的感觉,同时也获益良多。诗歌界的活动很多,几十年下来,各种花样的“聚啸山林”的场面也见过不少,很难说它们给诗歌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就行业生态而言,这个圈子并不算健康,但同时也因其丰富和驳杂,才显得我们又拥有着那么多的可能性。诗歌圈子是江湖,少年时期有一点江湖阅历总是好的,但我的态度包含在《庄子》里面:“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问:每个人对诗歌的评判有自己独特的标准,您对优秀诗歌的评判标准有哪些?什么样才是好诗?
茱萸:这个问题,是所有的关于诗歌的采访中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无法列出所谓的优秀诗歌的评判标准,不过已故的法国大诗人伊夫·博纳富瓦关于好诗的一种朦胧的论断和界定,我一直觉得堪称绝妙,就用它来作为回答吧:“诗和爱情一样必须对那些存在的存在加以抉择。诗应该忠实于黑格尔曾经自豪地以语言的名誉忆及的此时此地,应该将来自于事物的词语创造成一种向自身回归的深蕴和反常。”
问:您写诗,也做诗歌批评,您觉得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怎样才能使二者更良性地发展?
茱萸:进行诗的创作,而又从事诗的批评,在当代的汉语文化中,这种被讥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情况并不太能得到理解。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包括作家们)对“批评”这件事存在着普遍的误会,认为它是依附于创作的冗余之物,好一点的不过是锦上添花,不好的简直是满纸荒唐。但批评是和创作一样的独立行动,甚至在某些时候(比如这几年),我或许更为看重自己的批评从业者的身份,因为相比于优秀的诗人,此物种中的真正的优良品,在汉语里更为稀缺。用法国象征派大师保尔·瓦莱里的说法,“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因为诗人和批评家一样,都需要在一片混乱中找到那个提炼经验的“严肃的机会”。
问:当在诗歌创作中遇到障碍或者停顿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茱萸:我少年时代的写作,有着比较浓厚的青春写作痕迹,并因此一度使得自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自我厌恶感。带有这种痕迹的诗篇,有一些被收录在《仪式的焦唇》里,并不是“不悔少作”,而单纯是想“立此存照”。二十岁以后,我在写作上做得最努力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在清洗这种痕迹。这种清洗和转型很艰难,也带来你所说的“障碍”或“停顿”。譬如在2009年至2010年之间,诗的写作就完全停顿了一年多。不过正是在这段日子里,我写下了十多万字的诗学随笔,这也算是一种“代偿”吧?
问:您的诗习惯反复改、重复改吗?
茱萸:我比较不常修改自己的旧作。大多数时候,是在写的过程中“磨蹭”一点,一旦定稿,改的情况不多。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将作品结集时候,我会集中修改一批旧作,并落款注明“年月日初稿、年月日修订”。
问:您对您未来的诗歌创作想有哪些探索或者野心?
茱萸:和很多抒情性或即兴式的写作者不一样,我在诗歌写作中寄托了很多东西,譬如日常生活的轻与重、陈旧与新鲜、奇思和玄想,不停变换着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对阅读的索取和回馈等等。我在写作中有计划地安排和控制着这些内容,而不是采取一种触发的、即兴的或“行吟”的方式来处理这部分经验。如果说有所谓“野心”的话,大概就是这种非偶然式的书写里头,蕴含着心智的辛苦劳作,并且期望它有更深远的寄托。2013年以后,我考虑的问题是,怎样让诗在传达致密经验的同时,在表达上能够更舒展放松。至于前年开始尝试的“谐律”写作,我自嘲它是一个“怪胎”,是自己的一项极端试验。不过,长远来看,它可能会给当代诗的诗体建设带来某些启示。我很清楚自身的限度和问题,这种启示未必是正面的,很可能是负面的——但它在提示可能性失败之后,依然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崩溃的边界。
问:您是怎样看待诗歌中的借鉴与化用的?
茱萸:现下的社会风气是强调“创新”,体现在写作中,大家也都卯着劲想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想弄出新的东西。但事实上,就如《旧约·传道书》上的那句话所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的写作,说到底也是在重复前人所说,无一不是“借鉴与化用”。一个流行很广的说法叫“不是我写诗,是诗在写我”,其实也说明,人无不在既有的诗歌(语言)的“枷锁”之中,没有什么是凭空而来的。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剩下,怎么在无不是“借鉴与化用”的情形下,做得更高明、更特殊一些?
问:写诗的心,是自卑、孤独一点好?还是从容、温暖一点好?
茱萸:不怕你笑话,其实在“诗人”这个角色上,我一直是很自大又很自卑的。我对自己的写作和才能的评价经常游移不定,时而觉得很优秀,时而又觉得一无是处。其实在生活中我(至少试图)在扮演一个从容、温暖和宽阔的角色,但可能骨子里还是一个自卑又孤独的人。可能是因为从事批评以及在大学里教书,所以身上的社会性因素在这些年里多了起来,但是这些因素或许也无法消除性格中那种敏感的底色。
问:作为诗歌写作者,需要警惕什么?
茱萸:要警惕的东西应该有很多吧。不过,现在我的看法是,作为诗歌写作者,最警惕的或许是,总认为自己是个诗歌写作者。
问:诗人这个角色对您意味着什么?
茱萸:我记得前些年在沪上的一个诗歌活动里,有位听众向诗人萧开愚提问,问他是什么力量使他坚持诗歌写作三十多年。萧开愚的回答很有意思:“不坚持。”是的,对于“诗人”来说,写作虽然是艰难的,但它同时又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情,是本能,完全不需要什么“坚持”。诗,诗人角色,对于我来说,像一件随身携带的物品,甚至将要长成自己的一件额外的器官。虽然这些年下来,我每年的诗作产量也就十余首,但这不妨碍它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的生活几乎是围绕着它来展开的,除了创作,我每年还要写下大量的诗歌批评文章,如今的工作也是从事新詩史和当代诗的研究。
问:您认为诗歌写作的意义何在?是个体的的言说和宣泄,还是群体的代言,抑或是改变社会的工具?
茱萸:和一些同辈诗人不同的是,我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将诗歌视为“群体的代言”或“改变社会的工具”。因为能充当这两者的东西有很多,诗歌何必凑这个热闹?更何况,现代社会已经不是雪莱所说的“诗人是世上没有得到承认的立法者”的时代了。就算是雪莱的时代,这个“立法者”前头还缀着“没有得到承认”的限定不是么?
我再用一段写于二十岁时候的话来补充回答吧,这段话写得很幼稚,但多少能表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同时也是我当时的诗歌观念的体现:
“对如今的茱萸而言,诗歌成了他试图向这个世界传达某种特殊理念的小工具,是切割所有的柔软和坚硬的尖刀刃上不易觉察的光泽。时而明亮,时而黯淡。它们飞越现实和幻境的巨大分野,却注定失败。但这都无关紧要。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无所不在的焦虑感。冥冥中没有尽头的时间。它们像笑容一样,挂在嘴角,宛然呼啸着闪过的弧线:弯曲、犹豫不决、充满悬念。这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新的。全新的世界和纸张。镜子里的、幻觉里的、概念里的、来自遥远的神秘的声音里的、无限可能性的世界。”
问:在探索自我的过程中,难免会触碰到苦痛,您怎么面对这种苦痛?怎么面对自我?
茱萸:诗的写作是自我被呈现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挖掘和探索自我,也理解并消化苦痛。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有一句诗,“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有很重的佛教色彩,但它也意外地提示着我们,在这充满苦痛的人间,有诗的存在,就是一种疗救。
采访:孔吕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