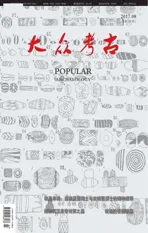后赵“建武四年”铭鎏金铜佛坐像结跏趺坐溯源
2017-12-12王趁意
文 图 / 王趁意
后赵“建武四年”铭鎏金铜佛坐像结跏趺坐溯源
文 图 / 王趁意

后赵“建武四年”铭鎏金铜佛坐像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铭造像(以下简称建武四年造像),被认为是目前发现中国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鎏金铜佛坐像。关于该造像的坐姿,一般被描述为“结跏趺坐”,例如有学者认为“建武四年造像高约四十厘米,结跏趺坐于方座上,身体微向前倾,双手持于胸前”。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并拟从源流上进行论证,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教。
“结跏趺坐”源自古印度耆那教等教派常用的修行姿势,后来成为佛教造像的基本坐姿之一,也被称为释迦坐。我们从古印度早期佛像上可以看到结跏趺坐的基本动作是:双脚裸露,左趾压在右脚股上,右趾压在左脚股上,脚掌交叉上下叠压,两脚掌心向上仰于二股之上,和地面平行,形成一种端庄、深沉的佛教仪轨和宗教艺术之美。
反观建武四年造像:呈正面端坐,身着通肩大衣,胸部衣纹为“U”字形六层衣褶,由上向下平行排列,衣纹断面呈浅阶梯状。双膝左右平伸,光素无纹饰,突兀外隆,宽度超越双肩。这种双脚不裸露、双膝光素无纹饰的坐姿,不经充分论证很难直接将其定性为“结跏趺坐”。

古印度早期佛像“结跏趺坐”
从字面看,“结跏趺坐”不是梵文的音译,而是汉语的意译。在东汉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中并无相关记述,可能直到东汉中晚期,在中国尚没有“结跏趺坐”的说法。汉代人习惯于席地而坐,按礼仪,坐姿又分为跽坐、跪坐、盘腿坐等数种。仅就我们可以看到的东汉神人画像而言,大多呈正面端坐,特别是作为最高神秩的西王母。正襟危坐是为了显示威严和地位。当然也有呈正面像而面颊稍倾的坐姿,但无论何种坐姿,都不会裸露神人的腿、膝、足部位,这与印度佛像双腿、双脚裸露的结跏趺坐有本质区别。
下面将以汉魏时期铜镜中的神人画像和铜摇钱树干佛像为例,分别与建武四年造像进行对比分析。

东汉“永元三年作”铭画像镜(浙江博物馆主编《古镜今照——中国铜镜研究会成员藏镜精粹》)
铜镜中的神人画像与建武四年造像坐姿
东汉“永元三年作”(公元91年)铭画像镜
此镜铸造于东汉和帝刘肇永元三年。画像镜中的主神为东王公、西王母,纹饰精致清晰。其中头戴冠的西王母,穿“V”形领交祍大衣,肩生上耸扫帚形双羽,一副眉目清秀的美女形象,头上虽没有插胜,但身前有“西王母”三字铭文可证其身份,右侧乳钉处有“永元三年作”铭文。西王母双手收于袖中,呈正面端坐状,仅面颊稍左倾,广袖遮膝,衣裾下摆堆于膝下,是典型的女性神像坐姿。头戴三山冠的是东王公,肩生上耸双羽,颌下有鬚,面目潇洒英俊,双手收于袖中,双腿收拢于臀下,呈正面端坐状。由于青铜材质、浮雕工艺相似,建武四年造像和此种铜镜人像坐姿相对比,具有较强的参照性。
东汉永元三年,即公元1世纪时,佛像在古印度正处于创始期,作为耆那教等常用的结跏趺坐式、禅定印手式,还没被佛教造像完全吸收过来。此时在古印度尚没有发现确凿纪年的结跏趺坐的佛像案例,更不用说结跏趺坐对中国的影响了。
永元三年铭画像镜作为东汉铜镜断代的标准器,主要特征包括神人身穿“V”形领交衽式博衣,尤其是不管端坐或侧坐,双腿收于臀下,双腿、双脚无裸露,这说明了在佛像传入中国之前,东汉已经有了一整套在铜镜上表现中国神像的成熟艺术仪轨,如神人的衣式、冠的类别、发髻的类型、羽人的形体、肩羽造型、侍女(郎)的妆扮等等都已成规范化的定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贯穿、规范着整个东汉至两晋神人造像的基本粉本,是该时期制铜匠师必须遵从的工艺规程。这些仪轨或为行业的自律,或为尚方官署颁发的律条,但它皆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权威性。
以此为参照,可知建武四年造像坐姿仍然是遵循此仪轨,而非受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自永元三年起的二百余年来,众多铜镜上的神人像,包括铜佛坐像,均按上述坐姿设计塑造。到了338年,以建武四年造像为代表,一大批神(佛)人造像群,虽然已经加入了很多印度佛像因素,但中国境内尚未发现一例真正的印度结跏趺坐的神人坐像,佛像的结跏趺坐姿,始终没有在这个造像群中展现过其风采,依然是以铜镜中这种神人坐姿为标准。不经科学论证非要把建武四年像的坐姿定性为“结跏趺坐”,是值得商榷的。
东汉同向式神兽镜
此镜纹饰精湛,铭文多至108字。可以清楚地看到镜钮两旁端坐的东王公、西王母。镜钮左旁的东王公神像栩栩如生、神采飞扬,肩两侧各生有四支羽翅,双手收于袖中,双腿收于臀下,双膝突出隆起,呈端坐姿态。这是一尊典型的同向式神兽镜的神仙造型,镜钮右侧的西王母神像的坐姿类同此例,不再赘述。东王公神像与建武四年金铜佛像除了衣服不同外,坐姿非常相似,比较有代表性。
东汉永康元年(167年)半圆方枚神兽镜
该镜镜钮上方为西王母,下方为东王公,二位神人均着“V”形领衣,肩生羽,双手呈袖手状,端坐于灵芝座上,其坐姿和建武四年造像坐姿相比,基本一致,永康元年距永元三年不足80年,似可说明这种神人坐姿,自永元三年始自东王公西王母画像镜后,一脉相承地在发展延续,未曾间断,最终出现在建武四年造像上是合乎情理的。
东汉建安六年(201年)铭重列神兽镜
该镜镜钮两旁的四尊神仙身穿V领衣,相貌端重,肩生双羽,头上梳高发髻,唇有长髭,老态龙钟,显示着尊贵的身份,应为镜铭中所说的“五帝天皇”。虽说因铜镜种类不同,在塑造神仙人物时的艺术手法也有不少区别,但是四神人端坐姿态,和前面列举的“端坐”像对比,更接近后赵建武四年金铜佛像的坐姿。

东汉同向式神兽镜(王趁意著《中原藏镜聚英》)
东吴太平元年(256年)半圆方枚神兽镜
该镜绘制四尊狮子,两两相拥护卫一尊神人,四尊神人均坐在基座上,身穿V领衣,肩生双羽,左右有凤鸟陪侍,双手收入袖中,双腿收拢,屈膝端坐,坐姿基本一致,和建武四年造像坐姿相似。
太平元年是三国吴会稽王孙亮的年号,此时离后赵建武四年仅几十年,二者的神像坐姿风格完全类同,存在相互重叠、影响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太平元年镜还没有出现佛饰要素。
从东汉永元三年西王母东王公画像镜,到永康元年东王公西王母神兽镜,再到东汉建安六年铭重列神兽镜,下延至太平元年半圆方枚神兽镜,直到建武四年金铜佛像止,神像的汉式传统坐姿是统一稳定的:袖手、双腿收于臀下,双脚无裸露,均按既定的模式端坐,流传有序,一脉相承。

东汉永康元年半圆方枚神兽镜(上海博物馆编《练形神冶 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

东汉建安六年铭重列神兽镜(《中国青铜器全集》)

三国东吴太平元年半圆方枚神兽镜(王趁意著《中原藏镜聚英》)
日本京都博物馆藏画纹带四佛四兽镜
这种佛兽镜以前均出土于日本,且尺寸都在22~23厘米以上,现存世不少于6面,日本专家将其定名“佛兽镜”(樋口隆康:《古镜》,日本新潮社,1979年)。据王仲殊先生考证,这种佛像镜,流行于西晋时期。故此,我们可知这是一个极难得的早期佛像镜群。另外,我在拙作《中原藏镜聚英》中收录的三国西晋半圆方枚佛兽镜,不但是国内仅存的画纹带佛兽镜,并且和日本京都博物馆的画纹带佛兽镜是同范镜。故此,我将两面铜镜放在一起考证,以达到博闻多见的效果。
该镜以乳钉为界,各有四组十尊佛饰神人,皆褒衣博带,或坐或立,神态各异。其中有一尊主坐佛,右手上举至胸部,左手执单柄莲。背有莲花背光,正面端坐于六瓣伏莲座上,双脚无裸露。另一尊主坐佛亦有莲花背光,右手伸于胸前,左手下垂抚摸于脚足部,呈正面端坐状,双脚无裸露。座下有双狮蹲伏。虽说两幅神人画像颈背后都有大莲花背光,坐下或有伏莲座或是双狮座,但他们的坐姿并没有裸露双脚、相互叠压掌心向上的所谓“结跏趺坐”关键特征,依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神人坐姿系统,不能因为有了伏莲、双狮等佛教因素,就把其强行定为“结跏趺坐”。这和虽然穿着“通肩大衣(袈裟)”,但不属“结跏趺坐”的建武四年造像是同一个道理。
在东汉至三国时期的铜镜上,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神人坐姿的案例不胜枚举。除了铜镜外,还有摇钱树干佛可以与建武四年造像相互参照对比。

日本京都博物馆藏画纹带四佛四兽镜
摇钱树干佛与建武四年造像坐姿
从20世纪40年代起,四川等地出土的大量摇钱树干佛像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被认为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汉魏佛像群。据何志国在《汉摇钱树佛像初步研究》中统计,目前己发现21件有佛像的摇钱树,共计67尊树干佛像。这些造像总体而言铸造不够精细,细节表达不够充分。但主要特征很明显:佛像有圆或椭圆形背光,均呈正面端坐,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或博带),头上无冠。额以上头发均向下梳成横宽形发髻,几乎没有上、下之分,其与印度佛像“肉髻”,更是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双腿盘于膝下,呈正面端坐。需要强调的是,摇钱树佛像分树干佛和树枝佛两大类,两者的造型有着极大的区别,当另作讨论。相关专家学者大多认为这些树干神像为“结跏趺坐”的佛像。我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是缜密、严谨,并实事求是的。在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不经论证就把这种坐姿简单判定为“结跏趺坐”,是有失偏颇的。通过参照前面列举的铜镜中的神人坐姿,可知这67尊树干佛像,没有一点古印度佛像结跏趺坐的特征,即没有裸露的腿脚,没有双脚的交叉叠加,没有脚掌心朝天与地面平行的物像表现。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这些树干佛像都是中国传统的神人汉式坐姿。从东汉中晚期到三国蜀汉灭亡,摇钱树干佛流行的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从陕西汉中到云南昭通上千公里的地域里,摇钱树干佛坐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若没有意识形态身份界定才能形成的戒律制约,这种现象很难理解,也值得深思。坦诚地讲,摇钱树干佛颈背后有横橢圆形项光,右手施无畏印,这确实是佛像典型的特征,但不能因为有了项光、无畏印,其他如发髻、坐姿等因素,也硬要贴上佛饰标签,归于佛教(像)因素,这就和建武四年造像“禅定印”陈旧的学术表述(见本刊2017年4月刊《后赵“建武四年”铭鎏金铜佛坐像禅定印考辨》)没有区别了,均值得商榷。

摇钱树干佛(① 重庆忠县出土

②四川安县出土

③四川绵阳何家山出土),何志国先生提供

北魏太安元年张永造石佛坐像
通过以上对建武四年造像与汉魏时期铜镜神人像、摇钱树干佛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推断建武四年造像的坐姿,是一种中国传统神人坐姿。这种神人端坐姿式的源头,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最晚可以上溯到东汉永元三年的东王公、西王母画像镜,在东汉至两晋时期都大量存世,和古印度佛像中的“结跏趺坐”是没有本质关联的两个独立文化体系的产物。在东汉永元三年到后赵建武四年的247年里,道、佛文化开始大量相互通融、渗透、杂糅,但国内还从来没有一件有确切纪年、真正意义结跏趺坐的神(佛)像面世,似乎已经说明了问题的本质。不能因为建武四年造像披了一件通肩大衣,摇钱树佛右手施了无畏印、头上有了背光,佛兽镜有了莲花背光和伏莲座,就不顾事实将他们的坐姿统统定性为结跏趺坐,这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金申的《中国纪年佛像图典》是国内现存纪年佛像的集大成者,其在书中推出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结跏趺坐佛像实物,是北魏太安元年(455年)张永造石佛坐像,具有结跏趺坐、禅定印、螺髻、裸肩袈裟等佛像规范标准。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应该从更深刻的角度去分析以建武四年造像为代表的一大批所谓的“佛像”,为什么都要披一件袈裟来妆扮自已,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其更深邃的文化内涵,而不是因为披了一件袈裟,其坐姿就一定是结跏趺坐。
(作者为中国铜镜研究会理事、河南省收藏家协会评估委员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