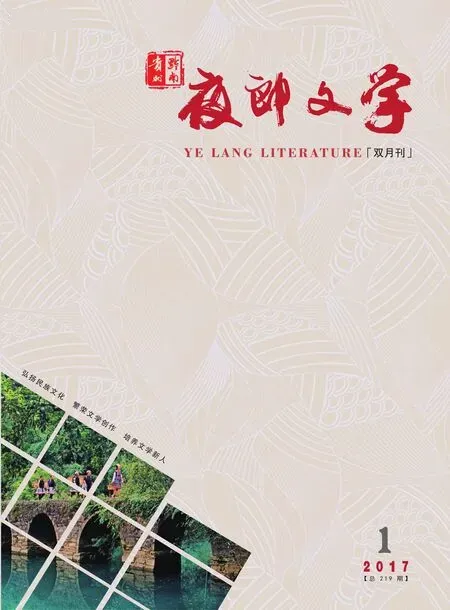只有宁静,能让风回到低处
——周雁翔诗歌阅读
2017-12-06伍亚霖
伍亚霖
一
所谓“宁静”,表现在诗歌里,应该是一种“慢”。在这个追求快速、追求变化的时代,对于诗歌写作来说,依然需要一颗心“不急不躁”的沉稳,在天地万物间漫步、思考、体察和感知的那种“慢”。
诗人周雁翔是我熟悉的诗友,见面我称他为“诗兄”,是纯粹因为诗歌而建立的友情,所以特别强调地在“兄”字前面加了诗歌的“诗”。都说文如其人,我自认为我对他有很多了解,当认真阅读他近期的诗歌,才发现其实并非如此,便也在内心自疑,或许要了解一个诗人真是太有难度,那其中的奥妙何在?或许奥秘就在诗歌里,因为,唯有在诗歌中,我们才能判识和认清一个诗人真正内在的本质。
而“低处”,在诗歌里,表现出的应该是一种无欲无求的生命状态或者对自身命运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一种抵达宁静后的内心安然与呈现,其间有大海的潮涌、有沟壑波涛、有飘摇不定的雨雪,但没有风暴、没有得失与宠辱,有的只是运用词语向内心深处挖掘的无限可能。
一张单程车票,承载无以分辨的幸运和悲伤
非此即彼,是孤独者的思维方式
掏出胸怀的水流,拴住白驹溜弯
不是每个人到了黄河,都听见白发的咆哮
星星伸出它的舌头,像时钟使用分秒
采撷奔腾的马群,锋利远不如速度重要
沿着这条线,只有宁静
能让风回到低处,回到细微的尘土
——《线性》
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孤独者的思维方式”真的是“线性”的吗?还是由“一张单程车票,无以分辨的幸运和悲伤”所能承载。尽管沿着诗人无意或者有意画出的路径标识,有许多次,我仿佛走到了诗歌的门前,只需要稍一抬脚,就能跨过阻碍的栅栏而入,不过最终,还是有什么阻挡了我,而且并不打算为带给我长时间的徘徊不定生出丝毫的歉意。
这就是“诗歌”的奇妙。当然,诗歌的奇妙得益于组成它的字和词,这其间也理当是有一条“线性”串接的结果。不过,那一条线是我们不能看见、不能听见、不能触摸,其间的喜悦涩苦,只能凭了感知去体味和品尝。
无可否认,因为诗人隐藏了太多,或者是诗人有意识的隐藏了自己,我并不能说出这首诗歌具体明确的指向。是孤独?是对过往的追忆?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还是因为,诗人刚刚经历了爱情的美好,而正在失去的路上。所有这些,都可能同时存在又单一和独立。每一个阅读者都可以对照自己的经历去解读它,去完成一次对诗歌的阅读,或许是顺畅的,也或许是坎坷的,总之,那都会是一次“危险”的行走。因为,“不是每个人到了黄河,都能毫无顾虑“掏出胸怀的水流,拴住白驹溜弯/都听见白发的咆哮”。也正如,词典中对“线性”一词本身定义的那样:抽象的、含义广泛的、边沿模糊或者规则以及无比光滑等等理由。
二
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无比沉默的人,一旦进入到诗歌里,或许会变得滔滔不绝、充满了奇思妙想和敏捷睿智;一个在现实中直言不讳、毫无心机、口不择言与至真之人,很可能在其写下的诗歌里,显露出曲折、迂回、隐蔽、尖锐等性格。
诗人周雁翔属于后者,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真诚率直之人,可以热情似火,可以冰冷如霜,所表现的应该属于日常标准所界定的不谙世事和作为诗人特有的单纯;而一旦进入到诗歌里,忠实于生命本元的特征便得以“水落石出”,其曲折、幽远、坚韧,我想那是诗歌赋予他的。由此,在阅读过程中,我也更多地领略到诗歌的奇妙和神秘。
是什么力量,让一棵老树结满白鹤
这与挂果,是截然不同的事实
如果这种力量,让我像叶子
有了超乎绿色的追求,像枝条
掏出梦境里的羽毛,像一个村民对着白鹤
默默祈福,像在默不作声的黄昏
旁听白鹤略微沙哑的歌唱,弥漫雍江河湾
我为什么,就不能找到一棵老树
来省去我的人生,所兜的大圈子
——《老树》
传统诗歌最显著的两个特征,无非言志和抒情;而今天的现代诗歌,除开了这两点显得会更加复杂一些,那就是在此基础上,更多地体现出所及的事物与生命所维系和发生的关系,这样的说法或许不太好理解,也就是说,在诗写过程中,在我们面对所书写的具体物象时,一个诗人会想象到更多,会延伸得更远。
在这首《老树》的诗歌里,诗人字词的指向和意蕴的根须与枝叶,一面是作向下深深的沉淀,有一种向内的力量;一方面又是向上或者枝叶披散的弥漫和伸延,是充满臆测和想象的。这之间,表现出诗歌追求的多意义和多指向,诗人一方面满怀了自省,另一方面又是怀着疑虑和肯定,他眼中看到的物象是具体的,真实的,而诗人感知和自省的一面,又充满了飘忽和不确定性。就像一棵结满白鹤的老树与挂果的事实,本身就存在悖论,是诗人对于所经历的一切相对峙的结果。
似乎一切都清晰明见了,而诗人依然有所隐藏。至于他隐藏了什么,我认为最为主要的,是诗人隐藏了自身宿命的痛感。他运用词句的巧妙组合,看似非常紧密的,无迹可寻的轻,其实是营造了一处开阔广大的场景。好了,过去的已经无可寻踪,让我们回到尘世间,那些令人追悔或者伤痛的往事,虽然已经发生和过去,却处处蕴含了无限“可以从头”的希望和新生的可能。
无一例外,既是一场风暴,也依然是沉静的。诗歌从不曾让我们一次一次对生活失望和放弃,让本来激烈的风,再次返回到低处,带给人思考和继续生活的勇气。
三
汉语诗歌发展到今天,走过许多曲折的路,或许不应该说“曲折”,那该是作为人类终极表达最高形式所需要经历的必经之途。总之,不管怎样变化,我赞同有一位诗评家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一眼能看到底的诗歌,根本就不是诗”,或许说得有些绝对,就我个人对诗歌的理解,最起码,“一眼就能看的底的诗歌”,不能算是一首好诗。
诗人周雁翔的诗歌,具备了“一眼看不到底”的特性,其多义性、多指向为一大特点。然而,在那一眼看不到底的背后,物象是清晰可见的,用词和意义也并非晦涩,就像涉足一面深不可测、意义模糊的池塘,清晰中有朦胧涌动的光影,朦胧中有历历可数的涟漪。作为阅读者需要不停的换一个点,再换一个角度,才能感受到其间的细雨飘飞或者雾岚烟霞、或者月光下的花开等等说不出、道不清的深邃抵达和旷远之意。
……
又是一场表演,补妆、灯光、场记……
各式角色,粉墨登场
旗风轻悄近身,它的吹拂是王者的抚爱
请不要惊扰这个姿态,也不要惊扰
其中的羽绒、泡沫、棉花,甚至玫瑰
更不敢去触碰,苍穹之下善意藏匿的旧伤
一朵睡莲,像一顶皇冠
不再被任何头颅催眠,它所涵盖的哲学
让黎明苏醒的瞬间,熟练于更为费解的雨露阳光
——《睡莲,不再被催眠》
这首诗歌让我想到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睡莲》。如果说莫奈是用色彩表现大自然的水中睡莲,用水中睡莲表现大自然的色彩,是抽象的,表现了一种光影浮动的朦胧和宁静。而周雁翔诗歌里的睡莲,则是动感十足、充满感性的思想和立体的姿态,能让人感受到每一支睡莲的翩纤和舞蹈,将一座隐匿的池塘,由远及近、或者由近及远中弹奏出“大珠小珠落玉盘”与“嘈嘈切切错杂弹”的清音和脆响。
这首名为写睡莲的诗歌,其实含涉广泛,其中曲折的布局、意境的深幽、意义的外延,比背后隐匿的一座池塘更为广大。作为阅读者,你可以就近停留,停留在字里行间,停留在表象的流水与亭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沿着字词铺就的深幽,一路走下去,领略和经历途中的潺潺流水、峰峦巉岩、村庄的恬静,甚至每一处雏菊盛开的庭院;当然,你还可以走得更远,一直走进这一生所追寻的幸福以及宠辱不惊的胸襟中。
在感性中呈现诗意,这也是诗人周雁翔的诗歌特点之一。在诗歌中,“感性”总是一支沸腾的箭矢,它将普通的字词经过诗人内心跌宕的情绪所带动而发生,这不是某一个词组或者语气、或者学识、或者文化可以完成的,感性是一个诗人天生具有的气质,拥有不可模仿的特质。
四
我极赞同诗人顾城说的:“诗歌不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正如台湾诗人洛夫所言:“诗歌并不止于语言,更有语言背后美妙深远的意涵”。这就意味着,诗人在写作的时候,或许会有少许约定的观念对自我进行约束,但是其精神是自由的。所以,我认为,对于诗歌写作来说,怎样表达、或者用什么方式表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歌中所表达的、在每一个普通字词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似乎深远和充满内涵。当然,我们都知道,其中所隐含的,更多的无非是生命体验,独特的或共有的,但要知道,我们在阅读一首诗歌的时候,并不是独特或者共有性就能打动你,打动你的其实是诗人与生具有的气质、品性、美学修养、胸怀等等元素,因为诗歌本身无可以言说、携带了太多的玄机和奥妙。
山成仙那年,看上去待嫁闺中
从没数过,修得多少月亮
才修得一顶花轿,一坐就一辈子
花轿抬过早晨,抬过与神定亲的礼盒
抬过幽暗的星空,因为一张闪烁的脸庞
让我相信一片浩淼的消失,无以抵销丝毫的孤寂
……
我不去比较一座山,与一顶花轿的遥远
一场婚礼,与一个传说的遥远
我只猜想散去的云影,走进共同的无尽岁月
——《仙侨山》
诗人周雁翔写过很多关于风景地名的诗歌,这类诗歌写作有一定的难度,这不是本身写作上的难度,一个娴熟的诗人,不管什么总可以在笔下成诗。而是在抒写一处风景地名时,只有恰到好处地融于自我的观照、驰骋古今的思考、或者奇妙之想象、或者心境、物象以及意象的移动转换等等复杂的过程,才能让其不流于俗套和显得庸常。这需要从诗人体内拿走很多东西,再注入很多,这之间,像是一个吸虹现象的容器,失去和得到变得相对。当然,这样的写作,必需要在诗人经历过长时期的诗歌写作和阅读的训练,才有能力达成。
在诗歌《仙侨山》中,诗人由此及彼,从实入虚,再原路返回。这很有趣,每一首诗歌都总有自己的奇妙之处,总有一条幽静和支流,静静的等待着阅读者的走近或者擦肩而过,这两者都会为诗歌的意义增添飞翔的翅膀。在诗人周雁翔更多的诗歌里,他对意象的把握运用得很娴熟,他在解说或描写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的同时,总是能及时抓住一些缥缈的东西,或者是“气”,或者是“场”。他用想象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有意蕴的心灵世界。
在写诗近二十年之久,我对诗歌突然生出一种不可以“逾近”之感,像面对一件奢渴与钟爱的“瓷器”,因为内心不够强大或者来自于一种模糊的缥缈。更因为一直以来,不管我经历什么,是虚妄的生活本身还是现实际遇的残酷,诗歌都是作为一种“风暴”的存在贯穿其间,而“风暴”的意识形态,无非“揭示”和“撕裂”;其“揭示”,是为了指出或阐明不易看清的世间万象,其实也是拨除诗人内心里一路走来所遭遇的疑虑层层的乌云;其“撕裂”,是一种精神与灵魂所伴随的生理痛感,是真相被揭示后的结果,也是当今众多以“我”为主观意识写作的诗人所追求的结果。
由于长期处于上述描述的两种形态之间,而结果又遥遥无期,我似乎走在一条并不光明的窄巷子。这样的心境下,阅读诗人周雁翔的诗歌,带给了我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诗歌不止是“风暴”,诗歌更多是诗人“内心”宁静的果实,是让风回到低处的轻曼姿势,是能带给人们对生命意义真正的抵达和理解,并感受其照耀的多色彩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