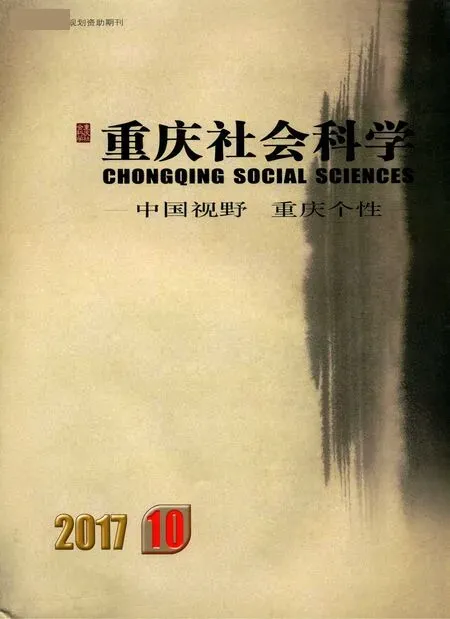《红楼梦》诗学与曹雪芹宗盛唐诗论偏差*
2017-12-05何蕾
何 蕾
《红楼梦》诗学与曹雪芹宗盛唐诗论偏差*
何 蕾
在家学渊源与诗坛风尚的影响下,曹雪芹论诗推尊盛唐,但在《红楼梦》中,主要通过林黛玉完成的诗歌创作实践却呈现出与中唐乃至晚唐诗相似的艺术风貌特征。这种论诗宗盛唐的观点与实际创作风格近于中、晚唐之间的偏差,并非曹雪芹刻意而为,是其身世遭遇、悲情气质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写情特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红楼梦》宗盛唐诗论 创作实践 偏差
关于《红楼梦》诗学理论与曹雪芹诗歌思想,相关论著已多,大多认为《红楼梦》诗歌创作所体现出的诗学思想受到明清诗论影响较深,并且与严羽《沧浪诗话》的诗论体系有相合之处。这些为数众多的论著与碰撞的观点为红楼诗学研究带来了生机与繁荣,对于清代诗学乃至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大有裨益。然而,当前的红学界却忽略了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红楼梦》诗歌创作与曹雪芹诗学思想之间是否完全一致,或者说《红楼梦》诗歌创作实践是否贯彻了曹雪芹的诗学主张。
一 《红楼梦》诗歌创作的理论环境
雍、乾诗坛是《红楼梦》诗学实践的文学背景,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诗论当属宗唐诗论。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十一章《传统诗学体系的再修正与总结:沈德潜的诗学》第一节《吴中诗风的转变与诗坛尊唐风气的再盛》,论述了晚年王士祯、叶燮、沈德潜等人扭转诗坛宗宋诗风的努力,其中尤以沈德潜传播宗唐诗说最为用力,影响也最大。至乾隆年间,宗唐诗论在诗坛已遍地开花。沈德潜之后,袁枚、赵翼、张问陶等人力倡“性灵”,其中尤以袁枚最为突出,袁枚“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1],以抒写真情为名在事实上承继宗唐诗论。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全唐诗》《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等唐诗总集和选集的出版,正是诗论界宗唐之风兴起的表现。而曹雪芹的红楼诗歌创作正基于这样一个大环境,不能不受影响。
除了诗坛大环境的影响,家学背景也不可忽视。从曹雪芹祖父曹寅的社会地位和诗坛交游情况来看,曹寅应当也是宗唐诗论的支持者、尤其推尊盛唐。影响曹寅诗论主张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人物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下令刊刻《全唐诗》,又曾说过“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2]足证其在诗歌审美取向上推尊唐诗的事实。曹寅与康熙过从甚密,又奉诏刊刻《全唐诗》,在诗学上不能不受康熙宗唐说的影响。曹寅又曾与朱彝尊交游,而朱彝尊论诗宗唐,与其交往的曹寅难免不受其影响。曹寅本人诗歌风格也被评为近盛唐,如姜宸英论曰“楝亭诸咏五言今古体,出入开、宝之间,尤以少陵为滥觞。”[3]简而言之,《红楼梦》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诗坛宗唐风气甚浓的情况下进行的,无论是从雍乾诗坛理论界还是从曹雪芹家学方面来看,宗唐、尤其推尊盛唐的风气都是曹雪芹诗歌创作的大背景。
二 《红楼梦》诗学实践与理论的偏差
在《红楼梦》涉及诗歌创作的情节中,曹雪芹宗盛唐的观点得到了鲜明体现,举凡评诗论诗之处,均以风格近盛唐为诗歌最高审美范式。然而最具诗人气质、也是最能体现曹雪芹诗论观点的人物——林黛玉的诗歌创作风格却入于中唐乃至晚唐,与其论诗宗盛唐的观点偏差明显,凸显了曹雪芹创作与理论之间的矛盾。
(一)诗学理论
从《红楼梦》里人物发表的各种评诗、论诗言论来看,曹雪芹论诗尊唐而尤以盛唐为宗。
首先,从评诗这一点来看,第三十八回、四十八回、四十九回、七十六回分别有相关论述。
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中:“李纨笑道:‘等我从公评来,通篇看来,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4]
李纨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5]
众人看毕,都说:“这是食蟹绝唱!这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6]
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词不雅;皆因你看的诗少,被他缚住了。’”[7]
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中:“众人看了,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8]
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妙玉)笑道:‘好诗,好诗! 果然太悲凉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这样去,反不显这两句了,倒弄得堆砌牵强。……只是方才听见这一首中,有几句虽好,只是过于颓败凄楚。 ’”[9]
以上是《红楼梦》中的评诗片段,撮要言之,曹雪芹评诗最重几点:一是新,题新、诗新、意新;二是诗境圆融而不露锤炼痕迹;三是温柔敦厚,讽刺批判不可太过尖锐;四是语言忌俗;五是不推崇境界凄冷悲凉的诗歌。
其次,看《红楼梦》中的论诗部分。第四十八回集香菱与黛玉论诗情节集中体现了曹雪芹诗论思想,也被无数红楼诗学研究者引述过。摘录如下:
“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10]
“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11]
“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的尽;念在嘴里,到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似的。……”[12]
第七十六回“妙玉道:‘如今收结,到底还归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检怪,一则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 ’”[13]
通过黛玉、香菱与妙玉之口,可知曹雪芹论诗大略有如下几点:一是重立意,认为“意”比词句重要;二是推尊盛唐诸人而尤重王维,认为学诗当以盛唐为门径;三是不重词藻雕琢而重意境圆融;四是重情讲真,反对险怪。
以上引述部分曾为很多红楼诗学研究者引述,但是鲜少有人将其与盛唐诗论联系起来。盛唐诗论最著名者当属殷璠与王昌龄两家。后世论盛唐诗者多非盛唐人,而殷璠与王昌龄以盛唐人的身份观照盛唐诗,往往别具眼光而得其真。殷璠诗论主要体现在其编纂的 《河岳英灵集·序》和对其中二十四位诗人的简短评论中。《序》曰:“至如曹、刘诗多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驾终成。然挈瓶庸受之流,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14]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勾勒出两个诗学主张:一是推崇自然本真;二是提倡声律风骨皆备。所谓声律风骨皆备,也就是声律和谐、情感饱满、气质刚健、境界阔大。而在对王维的评价中,殷璠说道“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15]突出“秀”“雅”“新”“惬”四字。 王昌龄则从自身创作经验和盛唐诗坛审美风尚出发,发出了与殷璠诗论相通的观点,认为诗歌语言应当本真而又不俗,诗歌创作最重立意,诗歌审美的最高境界是自然朴实与抒写真情。在已散佚的《诗格》中曾作出如下论述:
“语不用合帖,须直道天真,宛媚为上。”[16]
“格,意也。意高为之格高,意下为之下格。”[17]
“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18]
“是故诗者,书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 ”[19]
“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无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20]
有文章阐发曹雪芹诗学思想中“意趣”说与严羽《沧浪诗话》诗学体系的关系,事实上严羽论诗最主盛唐,以《沧浪诗话》这样一部体系分明的专著阐扬唐诗之美,推尊盛唐诗可谓不遗余力。而曹雪芹诗学思想与严羽诗学思想之间的相通处正是二人都推尊盛唐诗的表现。《沧浪诗话·诗评》中说“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与《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论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句与“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句所表达的看法完全一致,或者说曹雪芹完全认同盛唐诗以平常语而 “直道天真”的艺术风格。下面以简表的形式比较曹雪芹与殷璠、王昌龄、严羽诗论之间的关系。
从上表可以看出,曹雪芹诗论核心观点诸如重立意、倡真情、反对雕绘崇尚自然本真的诗境等观念与盛唐两位诗人兼诗论大家王昌龄、殷璠的诗歌审美核心观点基本相合,与严羽唯尊盛唐的诗论核心也相通。而作为曹雪芹宗盛唐诗学观的体现者林黛玉,不仅在观点的表达上与盛唐诗论相合,创作过程也与王昌龄诗论相合。第四十五回中黛玉创作《秋窗风雨夕》的“发兴”过程正体现了与王昌龄《论文意》中关于创作构思的观点。王昌龄说“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21]黛玉作《秋窗风雨夕》前“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知宝钗不能来,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22]由这段描写可知黛玉作《秋窗风雨夕》的缘由主要在于《乐府杂稿》中怨情诗的“发兴”作用,与王昌龄诗论“发兴”观完全一致。显然,曹雪芹论诗的核心是宗盛唐(见表1)。然而在诗学实践中,宗盛唐的诗学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在诗美的走向上偏向中、晚唐,尤其是大历诗风。

表1 曹雪芹宗盛唐的诗论诗评
(二)诗学实践
《红楼梦》中的诗学实践主要通过黛玉的创作完成。黛玉第一次展示诗才是在第十八回元春省亲时。黛玉作了两首“应制”诗,一是《世外仙源》,一是《杏帘在望》。这两首诗皆是奉元妃之命而作,近于应制,非“书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的真情之作,然而语言素朴、意境明媚、情感畅达,以清诗的创作环境而言,当算上品,尤其后一首《杏帘在望》颇具田园风味。然而与孟浩然《过故人庄》与王维《渭川田家》这些典型盛唐田园诗相比,《杏帘在望》则不够自然,在“意”与“真”这些盛唐诗家强调的诗歌要素上有明显的不足,有造境之嫌。前二诗中意象皆为田家常见之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与“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就是活脱脱乡野农家画面,是写实之境,即王国维所谓“写境”,完全符合盛唐诗歌本真的审美要求。而“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将春日与秋日之景并作诗中,则完全是造境,是诗人的想象之景,虽则对仗工整,语言清新质朴,但总觉意境不如盛唐田园诗自然、圆融,最后两句“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稍显突兀,与追摹晚唐贾岛等人的南宋四灵诗人较为接近。四灵之一翁卷的《乡村四月》语言朴素,清晰可喜,“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写乡村美景,但过于强调画面的唯美,却将真实农村风物过滤,只选择最符合诗人审美的一层加以表现,“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忽然插入繁忙的田家劳动场景,强调农家的繁忙与辛劳,与前面烟雨鸟啼的美景之间衔接有些突兀,有斧凿之痕和刻意之工。这一点,也是晚唐诗与盛唐诗的区别之一。从这一点来看,在以田园为题的诗歌创作上,曹雪芹的实践倾向于晚唐诗风。而在抒写性灵的诗歌方面,意境浑融、凄清,情感落寞、惆怅,倾向于中唐诗坛落寞清冷的诗美,尤近大历诗风。
第三十八回中黛玉作《咏菊》《问菊》《菊梦》三首诗,虽是应景、酬唱之作,但比起元妃省亲当晚“胡乱”作的两首诗而言,个人气质浓郁,个性标签鲜明。三首诗在情感的呈现上一首递进一层,以萧索惆怅的诗境将黛玉内心的寂寥落寞清晰呈现。第一首《咏菊》虽在结尾有意以陶潜典故来掩饰内心,但“满纸自怜题素怨”句的“素怨”暗示怨情非一时一日所起,又岂是一句故作淡然的“陶令平章”所能掩盖?第二首《问菊》“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正是黛玉品性气质的诗意表白,与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境界何其相似?整首诗意境浑融而清冷,与大历诗坛惆怅、失望、凄清的诗美特征接近。而第三首《菊梦》结尾“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则在凄清诗境的营造上更进一层,在前二诗“素怨”与“孤标傲世”的基础上深入到衰败、无望的境地。这种寂寥、凄寒的境界正是黛玉内心世界的写照。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小心谨慎的黛玉借助咏菊雅事,以超凡妙笔层层剥笋的展现自己的内心情怀与个人品性。菊花在盛唐诗中从来不是主角,而是以文人意象的形式衬托诗人雅趣与超然情怀,譬如“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 《过故人庄》);“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王维《偶然作六首》其四);“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李白《九月十日即事》);“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杜甫《九月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菊花成为诗歌的主角,在盛唐诗人中,当从杜甫开始。但以菊花为主角的杜甫,内心早已不再充满自信、昂扬的盛唐气概,而是经历了盛世后的萧索与零落不偶的失望。作于天宝十三载的《叹庭前甘菊花》是杜诗中唯一以菊为题的,但诗境萧索冷漠,充满失意的情怀。诗如下:
“庭前甘菊移时晚,青蕊重阳不堪摘。明日萧条醉尽醒,残花烂漫开何益。篱边野外多众芳,采撷细琐升中堂。念兹空长大枝叶,结根失所缠风霜。 ”[23]
其中“明日萧条尽醉醒,残花烂漫开何益”将酒醉的行为放在萧条的环境中来突出对社会、前途的失望与不满,以残花烂漫这繁华斗转残败的悲凉一幕来加深诗境的冷落之意。而黛玉所作《菊梦》尾联“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的境界与情怀与此何等相似,只是“衰草寒烟”不及“残花烂漫”惊心动魄而已。这样一种对比又令人更加确信曹雪芹宗盛唐、学盛唐的诗学主张。
黛玉一生诗歌创作,愈到晚期,诗意愈发清冷,以二十七回的《葬花吟》与四十五回的《秋窗风雨夕》相比而言,前者以落花自拟尚属自伤身世,后者诗境更为阔大,悲凉、伤感情绪也更加浓烈,并且上升至哲学高度,其中“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有模拟《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嫌,但诗句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差异之大形同两极。一是哲学发问,淡然中充满希望与生机,一是忧惧而疑问,伤感中充满无奈与悲凉。而这也正是盛唐诗与中、晚唐诗在精神境界上的区别。这两首诗一伤春一悲秋,悲凉氛围与季节尚有一些瓜葛,到后来第七十六回黛玉和湘云于中秋家宴之际在凹晶馆联诗时,不经意间吟出的诗句已经透骨清寒,一句“冷月葬诗魂”接“寒塘渡鹤影”而下,将清冷意境推到极致,读之凄神寒骨,在情绪上与前面伤感浓郁的歌行体长诗相比已近绝望之态。所以湘云叹道:“诗故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你现病着,不该作此过于凄清奇谲之语。”妙玉也说“果然太悲凉 ,不必再往下做。”事实上,从“寒塘渡鹤影”到“冷月葬诗魂”,在意境上有着鲜明的大历诗风和李贺鬼诗的影子。曹雪芹论诗宗盛唐与创作实践近于中唐风格之间的偏差在这短短两句诗里表现最为分明。历经盛唐的诗人刘长卿,晚期创作呈现出大历诗风的面貌,诗歌意境清冷,情感寂寥,形象孤独。例如《江中对月》:“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24]全诗弥漫着怅惘、孤寂的情绪,与孟浩然《夜归鹿门歌》诗意恰恰相反,“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体现的是超尘脱俗的隐逸之趣和隐士形象,而“月中孤渡水”呈现的却是寂寥情怀和孤独形象,与“寒塘渡鹤影”如出一辙,或者说后者的境界与情怀与前者一致。而“冷月葬诗魂”的境界愈加凄寒且诡异,正是李贺《秋来》“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的翻版,感情上却比李贺诗更为冷漠。李贺在诡异森然的诗境中张牙舞爪,拼尽生命冲撞着环境的镣铐,而黛玉作品中只有着心如死灰的绝望。
盛唐诗学本旨在于追求自然、本真、和谐、圆融的审美境界,展示的是昂扬向上的精神和壮健的生命力。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诗歌创作却展现出另一种面目:诗境清冷,情感寂寥,越到后来越发悲凉,这种创作与理论的偏差并非有意为之,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质和曹雪芹的身世遭遇有着必然的联系。
三 曹雪芹身世对其诗学实践的影响
关于诗歌创作的因由,陆机有 “缘情说”(《文赋》),白居易有“根情说”(《与元九书》),更早的儒家经典诗论《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25]中国古典诗歌以情为主,创作缘起情感,诗美追求真情,公认的经典全部是抒写真情的作品。而真正的诗人,即便是有意识地抑制情感,仍然会在诗中或多或少地表露性情。知名诗论家,诸如陆机、刘勰等人都说过在创作的时候,诗人往往置身于物外,完全忘却自身的存在,所谓“收视反听,耽思傍迅,精骛八极,心游万仞”[26],因此这个时候也是情感流动最真实的时刻。与激情忘我地创作相反,创作经验的总结、理论框架的搭建,需要理性思索、客观评述。因此,诗论家的观点往往是在理性、冷静的状态下发出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诗学主张的表达和创作实践的完成正基于这样两种心理状况,发表诗学观念,客观而又理性,进行诗歌创作,是在“书身心之行李”,理性只能成为抒发真情的障碍。进行诗歌创作时的曹雪芹,往往处于情感最真实的状态下,因此黛玉诗歌所呈现的冷落、寂寥与凄清、悲凉特征正是曹雪芹心态的诗意表达。这种心态,显然与曹雪芹的身世遭遇有着直接关联。曹雪芹少年纨绔而半生凋零,经历了繁华谢幕后的凄凉与落寞,人到中年“世事洞明”,对于当时的社会已不抱幻想,自知反抗无用而心如死灰,只是等待“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一天。这种凄凉与绝望在黛玉形象的塑造中时有显露。而黛玉“世外仙姝”的寂寞与清冷性情正是曹雪芹内心真实的一部分。第八十七回《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中黛玉的一段内心表白恰如在叙说曹雪芹人生遭遇。①第八十回虽为高鹗续作,但大旨所向未偏离曹雪芹的设定,且对黛玉命运的揭示遵照着曹雪芹原意,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人物个性与前八十回基本无异。因此,后四十回中的黛玉和前八十回中的黛玉是一个整体。此段黛玉内心表白虽是高鹗揣摩之作,但因延续前八十回风格,当与曹雪芹本意相差无多。
“因史湘云说起南边的话,便想着‘父母若在,南边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桥,六朝遗迹。不少下人服侍,诸事可以任意,言语亦可不避。香车画舫,红杏青帘,惟我独尊。今日寄人篱下,纵有许多照应,自己无处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么罪孽,今生这样孤凄。真是李后主说的“此间日中只以眼泪洗面”矣!’”[27]
这一段是全书中仅有的一次黛玉回忆往昔生活的较长描写,其所述如同曹雪芹感慨自身遭遇。林黛玉的前后两截人生,一繁华一凋零,一自由自在、诸事随意,一限于困厄、受制于人,恰似曹雪芹的人生遭遇翻版。曹雪芹的人生可分做两段,前段繁华后段凄凉,繁华处灯红酒绿、不知日之将暮,凄凉时白屋天寒、盼望漫天飞雪扫尽人间肮脏。这种人生的反差与其诗论和诗歌创作的偏差何其相似。诗歌创作缘情、根情,最重真实情感的表达,而身处凄凉之境的曹雪芹,如何能作出生机勃发、昂扬向上的诗歌?这与刘长卿等早期中唐诗人的心态甚为相似。历经盛唐时代的刘长卿、韦应物等人,早年看尽长安繁华,中年落魄而心境寂寥,后期创作被打上时代烙印,有着掩盖不住的惆怅、落寞,有时甚至充满悲凉之感和绝望之态。曹雪芹借小说写人生,以诗歌抒真情,创作时的处境与心态决定了诗歌必然写成清冷寂寥的面目。
除此之外,王维对曹雪芹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曹雪芹内心的悲凉与落寞主要通过林黛玉的言行表现。而林黛玉对王维的推尊和与王维相似的生活品味在书中时隐时现。其中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中黛玉和宝玉论琴的一段话将其“仙姝”气质和淡漠世事的情怀卓然显露。
“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所以古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琴。’”[28]
黛玉论琴之旨正是王维《辋川集》之《竹里馆》所呈现出的境界,“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想照”二十字被黛玉以论琴的方式演绎,这是曹雪芹推尊王维的表现,也是其内心淡漠、冷寂的表现。《辋川集》是王维于天宝三载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后至天宝十五载之间而作,所以从王维一生创作来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可纳入晚期创作范围内。《辋川集》弥漫着淡漠与空寂的情怀,“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与“惆怅情何极”(《华子岗》)的心态主导全篇,鲜少昂扬与生机之感,与其前期作品差异巨大。因此,在时间范围内虽属盛唐,但在情感气质上已经呈现出朝向大历诗过渡的迹象。黛玉论琴之说,表现的是王维生命后期的情怀,可以说这也正体现出曹雪芹内心的枯寂与淡漠。诗根情,枯冷之心创作出来的自然是冷寂、萧索之境,因此,曹雪芹论诗宗盛唐,然而创作却呈现出中唐诗、尤其是大历诗的清冷之貌。
综上,曹雪芹具有深厚的诗学素养和家学渊源,他“既想通过小说人物之口来申明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又欲借他们来展示自己的诗歌创作才能。”[29]其诗学理论倾向于盛唐,但诗学实践却滑向中唐以至晚唐,诗学理论和诗学实践未能保持一致,而是发生了微妙的偏离。这种偏差的产生并非有意为之,而与其身世遭遇、悲情气质及中国古典诗歌抒情写意特质有着直接联系。
[1](清)袁枚著:《随园诗话》,顾学颉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页
[2][24](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 5、1482 页
[3](清)曹寅:《楝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页
[4][5][6][7][8][9][10][11][12][13][22][27][28](清)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黄山书社,1994年,第242~243、243、244、313、314、526、311、311、312、527、291、601、599 页
[14][15]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巴蜀书社,2006年,第 1、66页
[16][17][18][19][20][21]胡问涛 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第267、267、290、299、304、300 页
[23](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 210~211页
[25]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26](梁)萧统:《文选》,(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63页
[29]陈才训:《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诗学素养》,《韵文学刊》2011年第 1期,第 22页
(责任编辑:张晓月)
The Deviation Between Poem in A Dream in Red Mansionsand Cao Xueqin’s Poetic Theory Praising Highly of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He Lei
Cao Xueqin praised highly of poetry in glorious age of Ta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ime’s fashion and the origin of family learning.But in A Dream in Red Mansion,the poetic practice mainly through Lin Daiyu’s creation appeared style that near middle Tang and late Tang.This contradiction was not result of Cao Xueqin’s intentional act,but the result of several factors working together,which include unfortunate life,sad temperament and the lyrical qual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A Dream in Red Mansion,the poetic theory praised highly of glorious age of Tang,creative practice,deviation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 安徽蚌埠 233030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 (批准号:gxyq ZD2016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