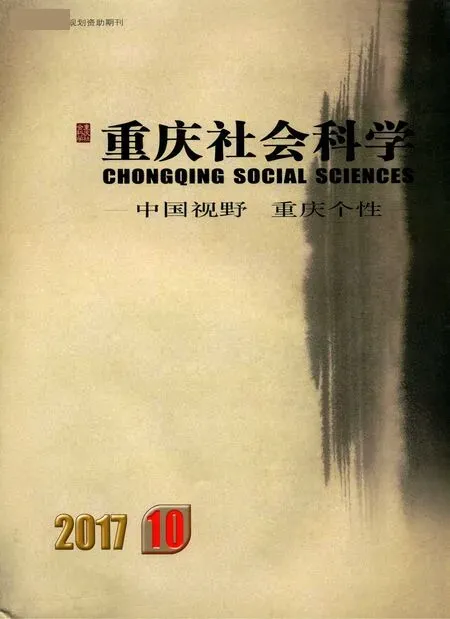宋初三先生到二程的《中庸》解析转变
2017-03-28王瀛昉
王瀛昉
宋初三先生到二程的《中庸》解析转变
王瀛昉
宋代理学的建构大体上可以看作依赖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理学家们之间联系导致的学统的形成,二是儒家经典中新标准四书地位的确立。而在四书当中,《中庸》为理学的本体论及修养论的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对宋初三先生到二程关于《中庸》的诠释的发展过程就诚明、执中与皇极三个向度进行探讨,从而阐明一些来自乐律、释道的因素以及在处理《中庸》文本细节困境时的策略与宋代理学的理论建构的关系。
《中庸》诚明 执中 皇极
宋代理学的一大拓新就是从十三经内整理出四书,且关乎四书的探讨在南宋闽学的理学系统内重视程度已不下于五经,甚至在某些方面较五经更甚。虽然在北宋还没有专门提出四书的说法,但对《大学》《中庸》的重视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尤其是《中庸》,自唐李翱开始着重于此篇之后,《中庸》在北宋初期重视程度得到了进一步、大幅度的加强。对这一时期涉及到中庸之道的研究,近年来也有一些尝试,但主要仍是一家一叙,类似学案体的形式,对各家关于细节的看法采用较平行的表达方式,没有具体到其联系与发展,且主要只集中在“性”与“中”的意义,涉及到的其他《中庸》原文内的细节问题不是太多。在此从胡瑗关于《中庸》的解释进行归纳,并将所得的向度作为全篇的框架,主要从学界涉及相对较少的层面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从某程度上对现有关于北宋前期及中期《中庸》解读的研究情况进行补充。
一、宋初三先生的《中庸》研究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一般被视作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奠基人。而按《宋史·艺文志》记载及夏长朴先生的说法,胡瑗对《中庸》的义解之书《胡先生中庸义》一卷也大约为北宋儒者最早的一部专门研究《中庸》的著作。[1][2]除此之外,朱长文《乐圃余稿》曾有诗云:“天意绍斯文,成书在圣孙。一篇穷妙理,万古诵微言……奥义谁钻仰,真儒善讨论。”下有小注“谓安定先生也。”又在其序内言“窃惟《中庸》之篇,自安定先生常以是诲人”。[3]
(一)胡瑗解读《中庸》的三个角度
从上可知胡瑗确治 《中庸》且对其十分重视。虽然最能直接了解胡瑗对《中庸》研究及体会的《胡先生中庸义》一书今已散佚,不过从《周易口义》及《洪范口义》中仍能找到部份其对《中庸》的认识与理解的内容。从这部份文献中找到的关于胡瑗论《中庸》之义的向度,大致可分列为三。
一是中庸的诚明之德。胡瑗注《文言》乾之九二“闲邪存其诚”时,引《中庸》“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与“惟天下至诚为能化”之语,并结合咸之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意解说至诚可以感动人心,从而化其本性。[4]若据此而诚明之德亦可视作圣人的德性标准,而胡瑗又言,“圣人积中正诚明之德。德既广,业既成,即人君之位,上合天心,下顺人情,以居至尊之地也。”[5]可见胡瑗所说的圣人与君王在某程度上出现了重合。
二是执中庸之道,关乎君子的个人修养方法。此为胡瑗在解释《文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一句时提出:“君子之人,禀天之全性,发见于世,而能执中庸之道者也”。而执中庸之道的办法,由于这里注经,则主要按学、问、宽、仁四项来解说。[6]而后文解释需之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时,则引《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一句并展开解说到:“言君子虽居贫贱而但守平易之心,不妄动,不躁进,俟时而已;小人则务险诐其行以徼恩幸,今初九能守常不变是君子所为也。”[7]这里又融入了居易守常作为君子之行,在解释否之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时也提到了这点。胡瑗引《中庸》“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及“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两句为据,认为“君子其时虽否,然能以道自处,以正自守,不与小人杂”[8]。亦即君子行止自有其义,从而能处而守之之意。
三是君教与皇极。此条与第一条诚明之德的不同之处在乎本条以 “君”的概念意义为主体,而第一条则是以为君王者自身的修养与德性为落脚处。《周易口义》中胡瑗以“夫君子之道积于内则为中庸之德,施于外则为皇极之化。”[9]而在《洪范口义》中胡瑗解释“五福六极”时则将其分为“君使然”与“天使然”,前者对应“教”,“以皇极而言则曰教”,引《中庸》解之则为“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后者对应“天”,“以向威而言则曰天”,引《易》解之则为“干道变化,各正性命”。而又“言乎命,一人之私也;言乎教,天下之公也。洪范九畴何尝以私言哉!”[10]胡瑗把教、公、君联系起来,既可诠释洪范九畴中皇极的概念,也可发挥《中庸》在政治上的意义。
(二)石介对“中”的解读
从以上三项来看,现存文献中胡瑗对 《中庸》解读的落脚点分别在德性、君子个人以及君主政教措施上。且总其意义还大约可用“化”与“处”来进行概括。前者主要就德性的作用和君教而言,后者主要就君子自身的修养而言。由于胡瑗对《中庸》的研究文献未能全面保留,胡瑗对“性”的解说及是否用“极”来建构儒学自身的本体论这两方面暂时无法了解,不过与其同受学于泰山的石介则对这些内容有过一定程度的论述。在《上颍州蔡侍郎书》中,石介认为物性不齐、人材不备,然而可藉天吏裁正物性、君宰长育人才的方法,分别令物与人“皆得其和”与“各得其中”。此处石介便将“和”与“中”解为各个个体在经历了“裁正”和“长育”后达到的状态,并归结到《洪范》篇论述皇极的“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从石介的说法来看,第二个“有极”与“中”或是第一个“有极”在概念之间似乎是总体与个别的关系,合言之即极,分言之即中。对于“中”石介继续进行了解释,以“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有所“几”动,而君子大约此时有所选择,即“合于中也则就之”与“不合于中也则去之”。这看上去应是说自己个人的修养,然石介又说到“天以刚方直烈之性授于介,不纳介于中”与“今阁下驱介,归之于中”。虽然其中可能有一些自谦与尊重对方的成份,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并不见得石介具有普遍性的人的本然之性都能自得其“中”的意思,石介在文章内容中只提到了人材不备,而达到“中”的状态似需经“君宰”的长育作用。[11]
在诚明与执中方面,从《徂徕集》来看,石介没有太多补充,《送龚鼎臣序》曾提到 “与性生者,诚也;与诚生者,识也。性厚则诚明矣,诚明则识粹矣”,从这里来看在性上所下的工夫在诚上也能反映出来,而后在识上能够达到“不思而得”。[12]不过就诚明的内涵而言,该篇没有再进行具体解释。至于泰山孙复,从其所存留的作品十二卷《春秋尊王发微》与一卷《孙明复小集》中并未发现直接涉及到《中庸》的内容。总体而言,由于存留文献不够充分,对三先生在《中庸》上的理论思想难以窥其全貌,不过仍可从中整理归纳出解析向度条目,且恰好这三条目在北宋前期及中期的 《中庸》研究中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因而,以此三条目为向度,从而能有系统地探讨《中庸》解读从宋初三先生到二程在理论上的扩充或变化。
二、诚明分合——从涉乎圣贤之别到专乎明诚之功
诚明为贯穿《中庸》全篇的一个重要概念,前文已述及胡瑗关于德性及感化的解读。
(一)北宋中前期对“自诚明”的解读困难与暂时搁置
不过由于《中庸》一篇中有“自诚明,谓之性”与“自明诚,谓之教”两句,因而北宋专门探讨《中庸》往往主要就诚和明的关系着手。但亦有合诚明以言君王德性者,其代表人物即古灵先生陈襄。
在泰山三先生活跃在太学的同期,以陈襄为首的古灵四先生亦在闽中讲学。按 《宋元学案》记载其门人亦过千人,且胡瑗门下孙觉、管师复等也尝兼事陈襄,其地位不可谓不重。[13]陈襄有专论《中庸》的篇章《中庸讲议》,然今所传本《古灵集》仅存“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以前各句之注。虽今本不全,然《古灵集》犹有《诚明说》及《至诚尽人物之性赋》二篇,可略补其说。此两篇皆以诚明为本,且与胡瑗类似,陈襄亦将诚明作为帝王的德性根基,即《诚明说》所谓“帝王之德莫大于务学,学莫大于根诚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然而陈襄的说法中把帝王之德再进行了一次推导,以务学作为帝王之德的最高标准。务学的意义在《中庸》内即“自明诚”,陈襄亦以此学为“明诚之学”。然又因陈襄在对“自诚明”和“自明诚”的差别阐释上,沿用郑玄以来的说法,将前者归为圣人,后者归为贤人。然而由于《诚明说》是上给宋神宗的文章,既规劝宋神宗务学,又不便表达宋神宗为贤人而非圣人的意思。因而在《进诚明说剳子》中称神宗“天资圣性”,从而调和两者,避免了对皇帝进行分类的问题。[14]
但即便对象不是当朝天子,对上古圣王也具有在思与不思、圣贤划分层面上的问题。因而较陈襄稍早的欧阳修在《问进士策》中虽然沿用“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的说法,但他又提到“孔子之圣”也是经历“学而后至,久而后成”来的。连孔子都需经过学习,使用自明诚的方法,欧阳修即因而感慨到:“《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欤!”而对于上古圣王,欧阳修提到了尧因为“思之不能无失”而“用四凶”,以及舜遇事都要“问于人而择执”,这些行为似亦对应自明诚的 “诚之者”。综上所述,欧阳修得出了《中庸》之诚明不可及的结论,甚至认为《中庸》内容有“则其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乃至怀疑《中庸》谬传。[15]虽然欧阳修甚至开始怀疑《中庸》内容的态度在北宋中前期不为普遍接受,但自其以来各家亦渐多避开以圣贤区别来解释诚、明的向度。若王令《师说》则不再分论诚、明差别,而是用自诚而明来总括自诚而明与自明而诚,即“夫人所以能自诚而明者,非生而知,则出于教导之明而修习之至也”[16],将教导与修习亦纳入自诚而明的范畴。不过自欧阳修以后对诚明问题处理相对较多的方式,还是以诚、明各合一德而论。若张方平在回答宋英宗的提问时,将《系辞》之易简与诚明进行对应,先以易简本于诚明,而后“诚则易,明则简。诚明者,君子之性也。诚则易知而有亲,明则易从而有功,故其德业可久、可大”[17]。再若张载《正蒙》专有《诚明》一章,将自诚明与自明诚对应到 《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句,以自明诚为“由穷理而尽性”,自诚明为“由尽性而穷理”。穷理与尽性皆为修养过程中的方法,张载从其入手,而不再详细解说修养者的区别。其后《正蒙》又云:“性其总,合两也;命其受,有则也;不极总之要,则不至受之分,尽性穷理而不可变,乃吾则也。”[18]因而怎样达到诚或是诚明的问题的讨论暂时被搁置,重点变成了关于性自身的修养而回到性命论了。
(二)两种对“自诚明”的重新解读
再到与二程同期的苏轼,则论诚明“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明合而道可见,虽有黄帝、孔丘,不能知其孰为诚、孰为明也”[19]。可见苏轼已认为诚、明的差别难以区分,而见道亦要兼合二者。不过苏轼在直接面对自诚明与自明诚在原文词句上的差别时,仍大致类似此前诚、明各合一德的方式进行处理。但苏轼较为别致的使用了“乐之”与“知之”,《中庸论上》云:“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谓也,知之则达,故曰明夫。”诚明与明诚也变成了一个谁更先入的问题,即“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与“若夫贤人乐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虽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之说,但是苏轼又言“君子之为学,慎乎其始,何则?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乐焉,则是不如不知之愈也”[20],从这里来看,苏轼虽然把自诚明与自明诚分别对应了圣人与贤人,但其内部推导逻辑大抵有差别,并非是从圣人与贤人出发推导其修养、为学的方法,而是用君子为学之始选择的不同方法来概括圣人与贤人,因而从意义上已不再强调圣贤之别,而是强调修养起始方法的选择。
程颐的说法则与欧阳修的说法又略相似了,“由明以至诚此句却是,由诚以至明则不然,诚即明也”。[21]但是程颐用“孔子之道发而为行,如乡党之所载者,自诚而明也”为自诚明进行了解释,以“道”作为自诚明的主体,从而打消了像欧阳修那样对《中庸》的疑虑。[22]但总体而言,二程关于诚明的学说以明诚之学为重,而就“自诚明”一句的论说则所言甚少。
三、从何以执中到何以至执中——修养方法的寄托
前文已述及关于诚明圣贤区分及自诚明与自明诚差别的问题,至二程以后明诚之学成为重点。
(一)中庸修养的主体——君子、小人的中庸
而本节所述胡瑗所言的 “执中庸之道”,按《中庸》原文大抵可对应到“择善固执”,亦是关乎“自明诚”或“诚之者”的个人的中庸修养。为使重点更为突出,本节主要就“执”的方法进行讨论。在探讨“执”之前先有一个问题,即是在明诚之学的主体上,按《中庸》原文有:“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这句既说小人反中庸,又有“小人之中庸”之辞,因而在北宋时期对其的解析出现了小人有无中庸之性的问题。
古灵先生陈襄对这个问题就“人性莫不善”而推出“君子、小人皆有中庸之性”,然而小人之所以反中庸是因为小人“性以情迁”,从而导致“蔽于情欲之自私,而不知戒忌畏难”,与李翱《复性书》“情既昏,性斯匿矣”的说法接近。[23]陈襄的说法大致因从《孟子》观点出发,而较重中庸的普适性,但这种说法相对来看似减弱了北宋一般认为的“无忌惮”对小人的贬义。而与其几乎同时的张方平则大抵以性三品之说为基础,将“小人”一词用“中人”的概念来进行解释,以“小人”为“中人与之下者”。其《中庸论》云:“中人之行,可与之上下者也。彼中人者,不得道之至正,是故刚者自伐,柔者自怠。故曰:‘小人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24]据此句,“小人之中庸也”与“小人而无忌惮也”被以并列的对比关系进行解析,似又与北宋一般学者所认为的这两句间的关系不类。到其后的苏轼,虽言“有小人之中庸”,但其诠释的入手处不再是小人或是中人自身,而改为从“时中”出发进行推导,“时中者,有所不中而归于中,吾见中庸之至于此而尤难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归于中,是道也。”苏轼以“时中”反推而得“有所不中”,从而表明“小人之中庸”一句的合理性,但其解析较陈襄与张方平则减弱了“小人之中庸”中“小人”其自身的主体性。而至于其“无忌惮”,苏轼则认为是“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窃其名”。不过苏轼又倒推上去,“小人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从而提到了“小人之中庸”可能还具有近似而窃“中庸”之名的含义。[25]不过这三人的说法大致皆与一般学者对《中庸》这句的解释有不相合之处,均未能为宋儒所广泛接受。
除上述几人之外,这个问题还有一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即依王肃本《礼记》改为“小人之反中庸也”。晁说之《中庸传》云:“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温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26]按晁说之的说法,胡瑗、司马光、程颢都认为应多一“反”字,然而现存文献已不见这几人的具体说法,惟《中庸辑略》有程颐“小人更有甚中庸,脱一反字。小人不主于义理则无忌惮,无忌惮所以反中庸也”一条。[27]这个说法在理学系统内一直到后来的朱熹也都接受,但不同于《大学》,《中庸》此句原文自二程以来并未受到改变,仅是出现在注解之中。因而就其具体程度而言,王肃本的“小人之反中庸”亦可能只是作为解释的一条径路,而不能就此对当时通行本所流传的原文之辞进行程度更深的否定。
(二)“固执”的具体方法
接下来即是“诚之者”最直接的问题“择善固执”,亦即怎样才能执中庸之道的方法。《中庸》原文中“择善固执”的下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似主要就“自明诚”的内容而言,并未直接提出“固执”的办法,因而北宋诸儒也对此进行了讨论。大致北宋中前期诸儒解“固执”有两条径路:一是就《中庸》原文的概念进行对应或融合,二是用另一经典之辞而为之详说。
用第一条径路者,若陈襄,在《诚明说》中他融慎独与固执于一方法:“精一以守之,中正以养之,持循戒惧于不睹不闻之际。”[28]“固执”的方法经慎独的“持循戒惧”之说显得相对而言明确了一些。而关于陈襄此句的前半部份,司马光则叙述得更为详细。不过司马光的说法以 “中和”为主,没有特别谈到慎独,即“治心养气,专以中为事,动静默语,未尝不在乎中,此正所谓择善而固执之诚之者也”。司马光以“治心养气”为“固执”的修养办法,并以“君子守中和之心,养中和之气”进一步阐释“治心养气”,用中和之说将“固执”的方法表达了出来。[29]但司马光的说法为韩琦所反对,韩琦在答复司马光的《中和论》时认为“治心养气”无法达到“择善固执”的地步,以“中”有“礼之所自生,政教之所自出”与“对外而为言”两种,而“治心养气”的“中和”属于对外而为言,并非《中庸》所谓“诚”的境界。①此篇《传家集》原作《景仁答中和论》,然《传家集》另有范镇《景仁答中和论》,文字不同,且与范镇来往书信未提到诚之者,而该篇又可见韩琦《南阳集》,应为韩琦所作。[30]这个境界差别的意义在范祖禹的《中庸论》中也有体现,范祖禹将中庸分为三部份,有“众人之所易行者”、“圣人之所难行者”、“圣人与众人之所同行者”,汇总起来即是“始于易,终于难,而不可以过乎中,是故谓之中庸”。而“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的只是众人之所易行者,[31]而关于怎样“固执”从一定程度上看是从易到难层面的问题,且大抵涉及到“严之以难,使天下不得而轻也”的中庸的问题,并非只是“固执”一境界或某一部份中庸的问题。但这又不能直接回到“自明诚”的方法,主要是因“明”已经是较深程度的修养了,而“众人之所易行者”相对而言大约较浅。不过由于范祖禹仅论“中庸之大略”,没有再具体谈到从易到难层面的方法,因而关于“固执”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思考。
而以第二条径路进行解释的情况,则首先可见于苏颂的《李惟几改字说》。按《中庸》原文有“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矣”一句,苏颂则以颜子为主,用《系辞》解复之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时所用的“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一句的“殆庶几”代“择善而固执”,从而推出“思之详”与“慎之至”,再以“事之未彰,横乎思虑”与“念之戒之,勤勤若是”为其方法。[32]到张载与二程也选用了从另一部经典进行寄托的办法。程颢在回答宋神宗的提问时,提到了“正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33]将《大学》内的“诚意正心”之说与《中庸》的“诚之者”联系起来,从而可在《大学》内寻找择善固执的阐释空间。张载《正蒙》则有“知德以大中为极,可谓知至矣。择中庸而固执之,乃至之之渐也”[34]一句,大约也将《大学》的内容与《中庸》联系起来,不过张载是用致知来解释择中庸而固执。但张载虽然联系二篇起来,却没有在《正蒙》中继续探讨怎样“至之之渐”,而程颐则更为详细具体地用致知回答了“执”的问题。程颐将择善固执融到致知过程所达到的地步或境界中,《中庸辑略》关乎“诚者”、“诚之者”一段录伊川先生所云:“知亦有深浅也,古人言乐循理之谓。君子若勉强,只是知循理,非是乐也。才到乐时,便是循理为乐,不循理为不乐,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须勉强也。若夫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35]这与前文苏轼解诚明差别时所用到的“乐之者”与“知之者”的方法类似,但程颐没有直接用它去解诚、明的字义,从某程度上更容易为人所接受。而在择善固执整体融入致知过程中的情形下,怎样“固执”的这个问题也因而被“知”的深浅问题替代掉了,而二程关于致知的论述则相对颇多,不再进行详细讨论了。
四、从皇极到极高明——本体论的倾向
北宋初期论及君德化民,多兼皇极、中庸而言,乃至贺表之中亦出现将此两词连用者,若田锡《贺正表》云:“伏惟尊号皇帝陛下,明融瑞日,德动玄穹,皇极中庸。”[36]
(一)乐律中“极”的观念
自汉以来,训“极”为中,就皇极而论大中之道,以之涉及《中庸》似亦是较为顺理成章之事。而宋初皇极一词即频繁出现,除宋结束了五代五十三年分裂的局面,思想上亦需明确君德以显一统之原因外,北宋频繁重修的乐律制度也是一大重要原因。按《宋史·乐志一》“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37],律管积黍之法中乃至黍排列的横纵,亦变动不止。①见陈旸《乐书》卷九十七所云:“李照以纵黍絫尺,黍细而尺长;胡瑗以横黍絫尺,黍大而尺短。”《四库全书》(第 211 册),390 页。自汉唐以来,乐章舞曲虽各朝不同,然音律度量之制却在多数时间内相对稳定,晋、宋、齐皆延汉制,而后梁武帝、西魏废帝、隋文帝曾欲改作,但分别因侯景之乱、北周代魏、炀帝即位而中止;唐代沿陈、隋旧法,至唐末昭宗时,殷盈孙变黄钟律管,然采用不久,二十年内而唐又为朱温所代。②可参见《隋书》中《律历志上》及《音乐志》上、中、下三篇及《新唐书·礼乐志十一》等相关内容。因而可谓北宋频改律制,为自汉以来前代之所无。
在律管之法中,黄钟为律之本,而《汉书》又有以太极元气为黄钟之说,北宋改正音律,多考前代乐律制度,因此各类论律文章中太极一词频出亦不奇怪,若宋祁 《十二管还相为宫赋》、《黄钟为律本赋》、陈襄《黄钟养九德赋》等皆以太极为音律之根本所在。而其中 《黄钟为律本赋》、《黄钟养九德赋》又发挥了黄钟在君主政治及主宰方面的意义,宋祁将其解为“其黄,君也,化得君而明;钟,种也,物待种而生”[38],而陈襄则以黄钟“群生重畜,我总其化;九德万事,我总其权”[39]。在“极”的意义联系到君主自身的话语要求下,《洪范》篇中表达君德主宰意义的 “皇极”一词的频繁使用便不难解释了。而再反推回来,北宋的一些以皇极比拟音律从而论政的说法亦属正常,若夏竦《政犹水火赋》即有“然则建皇极、合中庸,若惨舒之更用,类律吕之相从”[40]之言。
(二)释道中对“极”意义的使用
此外宋初的儒释道融合并用的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突出皇极的意义做出了贡献。道家《老子》之书自古以来即曾被用作帝王术的一大所据之书,宋以前亦有合皇极而言者,若唐陆希声《道德真经传序》即云:“夫老氏之术,道以为体,名以为用,无为无不为,而格于皇极者也。”[41]而宋初太宗、真宗皆崇道家,真宗以道家之说“本于自然,臻于至妙,用之为政,政协于大中”[42],可见道家之受重视及其能用于政事的向度。因而这期间将道家与皇极联系者亦不缺乏,若戚纶奏言 “参内景修行之要,资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极以御烝人”[43],扈蒙《宋东太乙宫碑铭》亦云:“建皇极,奉天统,稽茂典,崇明祀,斯圣人之能事也,惟我后得之。”[44]
同时释家亦多言皇极,且明确用之结合中庸而论其义,约宋真宗时期自号中庸子的智圆即以中庸即释家中道的含义,从而融合儒释。①见智圆《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传上》所云:“释之言中庸者,龙树所谓中道义也。”《卍续藏经》(第10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110页。现存文献中虽未有智圆专论《中庸》之篇,但从部份涉及《中庸》的篇目中亦可一窥,若《闲居编》中《叙继齐师字》一篇云:“夫大中之道,非圣人莫能至之,非君子莫能庶几行之,书曰:‘建用皇极。 ’语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 ’”[45]可见智圆已将皇极、中庸联系起来描述大中之道。
智圆之后,契嵩则对这方面又进行了相对更为详细的论述。今《镡津文集》中可见《皇极论》一篇及《中庸解》五篇,契嵩在此以皇极为大中之道外,也提出了中庸的“极”的意义,“夫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46]具体而言,契嵩对于皇极和中庸的解释基于儒释融合的意义要求下,以《洪范》五福六极为是否心合乎皇极所致,从而对应释家所说善恶之报;而《中庸》性情之言则与释家相同,兼用之则能广为道德,水深为河海,土积为山岳。此说亦似《中庸》“博厚而高明”之意。同时契嵩通过论述释家教义,使得皇极和中庸较为系统化的整合了,《中庸解》云:“皇极,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万物也入万物也,故以道为中也。”此外契嵩论皇极时也涉及了其君主治道上的意义,在其上给宋仁宗的万言书中,契嵩指出“夫王道者,皇极也。皇极者,中道之谓也”[47]。又在论及治道皇极之时,契嵩亦表达了一些关乎本体上的含义,《皇极论》云:“礼者,皇极之容也;乐者,皇极之声也;制度者,皇极之器也。”又云:“所以五福六极者,系一身之皇极也。休征咎征者,系一国一天下之皇极也。”[48]而中庸之道作为皇极教道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意义也有所体现,《中庸解》云:“夫中庸之为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无以过也,吾人非中庸则何以生也”[49]之说。除此之外,加之前文所提到的与契嵩大约同期的石介以《洪范》之语解《中庸》的“中和”之说,可见在皇极因导下,关于《中庸》本身的极致意义的解读,使得关于中庸的诠释逐渐出现了本体论的倾向。
(三)二程对“极”本体含义的发挥
在上述原因影响下,北宋出现了许多相关提出皇极的《洪范》篇的书或篇章,除前文提到的胡瑗的《洪范口义》外,还涌现了若苏洵《洪范图论》、曾巩《洪范传》、王安石《洪范传》等作品,对皇极、《洪范》之盛言可见一斑。而及至二程起初亦曾向神宗进言王道之“极”,若《近思录》有程颢曾进言宋神宗一条:“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50]但二程在熙丰变法期间因其作为反对新法的旧党而受排斥,在地方讲学而少皇极之说,不过却在涉及 《中庸》的“极”及本体的含义则多有发挥,并将中庸融入了其理气本体论系统中。首先是二程特别重视《中庸》原文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一句,并进行了大量论说,若“极高明道中庸,所以为民极,极之为物,中而能高者也”[51]“极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极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极”[52]等。此外除明确中庸的“极高明”的意义外,二程也着重于中庸的“尽致”,若“中之理至矣……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中庸”[53]及“中庸言尽已之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54]之句皆表达了这方面的意义。整体来看,结合“极”与“尽致”,使得中庸的本体论意义得到了更为明确的彰显。
五、总结
从上文可见,《中庸》在从胡瑗到二程的过程中,在具体字句的处理中曾出现了一些直接解释时的问题或争议,但二程通过主体改变、整体寄托等方式将这些问题逐渐化解掉,且在化解的同时又开启了新的研究主题。这些新主题在之后的洛学到闽学系统中,也逐渐代替了皇极、复性等洛学以前《中庸》解析的主要话语。从一方面来说,二程乃至从其开始之后形成的洛学,将关于《中庸》的研究从字句意义层面转向了具体实践修养及本体层面,形成了文本研究外的较为系统的修治方法论,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中古及近古哲学的研究课题;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二程对北宋中期及前期一些讨论的问题主要采取消解的办法,没有将其汇总以进行评价或议论,虽在学统上显得更为集中,但在某程度上使得后来关于《中庸》的哲学研究难以从中注意到这一部份问题,而亦较难系统地进行归纳关洛之学以前的北宋儒学对《中庸》的研究情况。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转变对于比较或探讨中古至近代中西哲学的差异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意义。譬如从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差别论到明诚之学的转变,与西方相对晚一些的洛克、巴克莱、莱布尼茨到前康德时期的认识论转向前期有所相似。不过中西在这方面研究的主体有所差异,宋明理学注重自身的修养工夫,而欧洲哲学则从原子、理性入手,逐渐发展起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新思潮,形成了康德批判以前哲学的主流。这些差异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中西哲学研究在范畴上的较大区别。
而关乎《中庸》的“极”及本体含义的发挥,乃至在北宋时期重新建立的形而上学架构,也较乎早期巴门尼德到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形而上学更相似于前康德时期笛卡尔及斯宾诺莎关于实体和属性的说法。但相比而言,我国传统更注重君主皇极之说,而斯宾诺萨及之前的哲学更偏向于使用相关宗教及上帝的词汇,因而“神性”与“神律”之类的字样成为了其主要的哲学用语。
[1]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5049页
[2]夏长朴:《北宋儒学与思想》,大安出版社,2015年,第 96~97页
[3]朱长文:《乐圃余藁》(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 7~8 页
[4][9]胡瑗:《周易口义》(卷一),《四库全书》(第 8 册),第 178、176 页
[5][6][7]胡瑗:《周易口义》(卷二),《四库全书》(第8 册),第 190~215 页
[8]胡瑗:《周易口义》(卷三),《四库全书》(第 8册),第 245~246 页
[10]胡瑗:《洪范口义》(卷上),《四库全书》(第54册),第 457~458页
[11]石介:《徂徕集》(卷十七),《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 307~308页
[12]石介:《徂徕集》(卷十八),《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 312页
[13]黄宗羲 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2年,第 225~228页
[14]陈襄:《古灵集》(卷五),《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 526页
[15]欧阳修:《文忠集》(卷四十八),《四库全书》第 1102册,第 367~368页
[16]王令:《广陵集》(卷十八),《四库全书》第1106册,第490页
[17]张方平:《乐全集》(附录),《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530页
[18]张载:《张载集》,章锡深 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第 21~22页
[19]苏轼:《苏轼文集》(卷十),孔凡礼 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325页
[20][25]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孔凡礼 点校,中华书局,1986 年,第 60~61、63 页
[21][22]程颢 程颐:《二程集》,王孝鱼 点校,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08、323~324 页
[23]陈襄:《古灵集》(卷十二),《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 601~602页
[24]张方平:《乐全集》(卷十七),《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 136页
[26]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二),《四库全书》(第 1118册),第 226页
[27]石塾 编:《中庸辑略》(卷上),《四库全书》(第198册),第 571页
[28]陈襄:《古灵集》(卷五),《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 526页
[29]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二),《四库全书》(第 1094册),第 570页
[30]韩琦:《南阳集》(卷三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 763~764页
[31]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十五),《四库全书》(第 1100 册),第 388 页
[32]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七十二),《四库全书》(第 1092 册),第 754 页
[33]杨时 编:《二程粹言》(卷下),《四库全书》(第 698册),第 420页
[34]张载:《张载集》,章锡深 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第27页
[35]石塾 编:《中庸辑略》(卷下),《四库全书》(第198册),第 601页
[36]田锡:《咸平集》(卷二十三),《四库全书》(第1085册),第 500页
[37]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2937页
[38]宋祁:《景文集》(卷四),《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 38页
[39]陈襄:《古灵集》(卷二十一),《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 672~673页
[40]夏竦:《文庄集》(卷二十三),《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 241页
[41]《道藏》(第 12 册),上海书店,1988年,第 115页
[42]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九),《道藏》(第 17册),上海书店,1988年,第878页
[4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90年,第1532页
[44]《道藏》(第 19 册),上海书店,1988年,第 687页
[45]智圆:《闲居编》(卷二十七),《卍续藏经》(第10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133页
[46][48][49]契嵩:《镡津文集》(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台北世桦印刷企业有限公司,1990 年,第 666、665、667 页
[47]契嵩:《镡津文集》(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台北世桦印刷企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687页
[50]朱熹 吕祖谦 编,张京华 辑校:《近思录集释》,岳麓书社,2010年,第644页
[51][52][53][54]程颢 程颐:《二程集》,王孝鱼 点校, 中华书局,1981 年, 第 246、367、122、182~183页
(责任编辑:张晓月)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ong Yong’s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ThreeMasters of Early Song Dynasty to Er Cheng
Wang Yingfang
Neo-Confucianism’s construction in Song Dynasty,in general,could be regarded relying on two aspects:the formation of bonds between Neo-Confucianists,namely the new scholastic tradition,and the rise of new standard on Confucian classics the Four Books (Si Shu)as well.Zhong Yong,one of the Four Books,gives a crucial foundation of ont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theory for Neo-Confucianism.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book’s interpretation from Three Masters of Early Song Dynasty to Er Cheng on three dimensions:sincerity and enlightenment,holding themean,and the supreme principles,clarifying how elements ofmusic and other religions,and strategies on addressing dilemma in textual details could be linked and devoted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Neo-Confucianism.
Zhong Yong,sincerity and enlightenment,holding themean,the supreme principles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香港九龙清水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