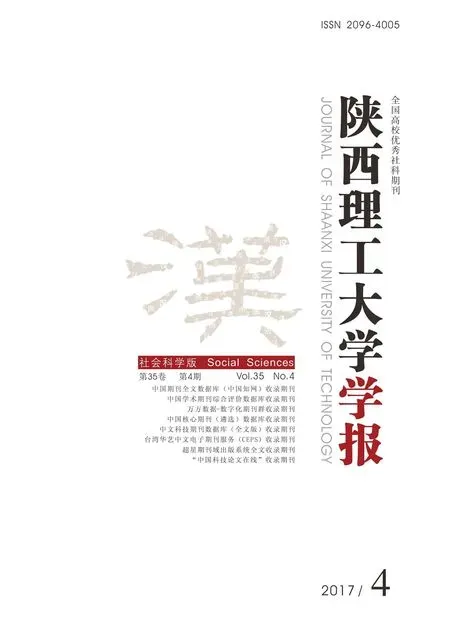地志、碑石所见清代汉中府县地方官的诉讼认识与实践(上)
2017-11-29胡瀚
胡 瀚
(陕西理工大学 经济与法学学院, 陕西 汉中723000)
地志、碑石所见清代汉中府县地方官的诉讼认识与实践(上)
胡 瀚
(陕西理工大学 经济与法学学院, 陕西 汉中723000)
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统治体制必然要求对地方进行有效管控和治理,因此府县地方官在统治体系和行政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诉讼这一法律现象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案件处理的进程、方法和结果。清代汉中地方志的相关记载显现,汉中府县地方官的诉讼认识均集中在好讼问题上,并对诉讼持否定性评价,这显然受到汉中当时的好讼风气以及自身知识背景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然而,与这种消极的、理想化的诉讼认识相对应的却是实用主义进路下的“能动司法”,表现为“革除弊病,减轻讼累”、“案结事了,息讼是求”等两个方面。这种极具张力的诉讼认识与实践之关系可以成为我们认识、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诉讼问题的出发点之一。
诉讼认识; 诉讼实践; 汉中; 清代
传统司法体制下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决定了府县地方官在传统诉讼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诉讼这一法律现象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案件处理的进程、方法和结果,因此,府县地方官是我们探究传统地方司法状况的关键之所在。本文拟以清代陕西汉中地方志为基本史料,以府县地方官为切入点,从诉讼认识与诉讼实践的双重维度审视清代汉中地区的司法状况,在勾勒清代汉中地区司法图景的同时,以期充实我们对清代司法制度与实态的理解与把握*前人针对地方官的诉讼认识和实践的研究早已有之,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张小也《儒者之刑名——清代地方官员与法律教育》(《法律史学研究》2004年版)、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中国的司法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日本学者山本英史《健讼的认识与实态——以清初江西吉安府为例》(析选于《日本学者中国法论著选译》: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汪雄涛《清代司法的中层影像:一个官员的知府与臬司经历》(《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等。。
一、 清代府县的地方官与司法职掌
(一)府县地方官
清代的地方政府体制较为复杂,《大清会典》载:“总督、巡抚分其治于布政司,于按察司,于分守分巡道。司道分其治于府,于直隶厅,于直隶州。府分其治于厅州县。直隶厅、直隶州复分其治于县。”[1]1由此可见,清代的地方政府分为五级。县、属州、属厅作为最基层的政府组织,虽然级别最低,但是其所系綦重,所谓“万事胚胎皆由州县”[2]772。“天下之治始乎县”[3]。“州县为国家之根本,动关国家之治乱”[4]1。“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5]1。府则“为承上接下要职”[6]3357,是连接行省与州县的中层政府组织。
按照清代的官制,职官分为正印官和佐贰官。以汉中为例,知府为府的正印官,佐贰官则包括同知、通判、推官、经历、照磨、府学教授、训导等。县的正印官为知县,佐贰官则有县丞、主簿、典史、巡检、教谕、训导等。属州的正印官称知州,其佐贰官则有州同、州判、吏目、州学正等。属厅的正印官称同知或通判,其佐贰官包括司狱、巡检、训导等。清代形成了“官非正印者,不得受民词”[7]2的审判原则。因此本文考察的主要对象是知府、知县、知州、厅同知等执掌审判全权、负审判全责的府县地方官。清代的法律不允许佐贰官和杂职官受理诉讼,州县官若允许他们受理诉讼或委派他们听审案件则要受惩处[8]25。佐贰官虽然经正印官的授权,可以调查取证、逮捕押解以及调解等,但不能正式审理案件,更不能对案件作出判决,因此此类人员在诉讼案件上的参与度是很低的,故而本文不作重点考察。除职官外,府县还存在一批佐助人员,包括胥吏、差役、幕友、长随等,此类人员虽然在府县衙门中具有较为特殊地位,亦参与各类政务的处理,但不是职官,因此也不属于本文考察的范围。
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统治体制必然要求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控和治理,故而府县地方官在统治体系和行政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且反复强调知府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性,所谓“外官莫要于知府”[9]。顺治皇帝就认为:“知府乃吏治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10]368雍正帝则从整肃吏治的角度指出“一府所属,其多者不过十余县,耳目易于周知,如能与督抚同心协力,则举核悉当,吏治自然肃清”[11]。知府的重要性乃是因为其是清代官僚体系和政治系统的中间环节,起到沟通上下,监督所属的作用,正如嘉庆间两广总督蒋攸铦概括的那样:“去民较近,察吏最亲,承上达下,以佐督抚耳目之不逮,则道府之任更专,而知府为尤要。”[9]州县官虽然在官僚体系中品秩较低,但基于州县政府在传统治理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其在地方政务中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真正的行“政”之官、“亲民之官”。正如汪辉祖所言:“自州县而上至督抚大吏,为国家布治者职孔庶矣。然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12]267
(二)府县地方官的司法职掌
清代知县“掌一县之治理,决狱断辟,亲理民务”[13]。《清通典》进一步解释为“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励风治,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14]2211。由此可见,司法审判是州县官的重要职掌,甚至有学者认为“处理狱讼是州县职掌中最为庞杂的事务”[15]43。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州县官在处理“狱”与“讼”时,权限是不同的。尽管清代在制度层面上还没有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严格区分,但是区别对待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已然存在。涉及户婚、田土、钱债等所谓雀角细故的诉讼称为“讼”或“词讼”,因这类案件由州县全权处理,故而亦称为“自理词讼”,且州县官在判决时“不必事事照例”[16]。此外,州县官亦可通过调处的方式了结此类案件。涉及谋反、叛逆、盗窃、人命等罪名的诉讼称为“狱”、“案件”或“重情”,对于这类案件州县官有权审理,但仅能对处笞杖刑的案件作出判决;徒刑以上案件则在审理后,根据律例提出处理意见后,将案件与案犯一并解赴上司复审。
清代知府的职掌是“掌一府之政,统辖属县,宣理风化,平其赋役,听其狱讼,以教养万民。凡阂属吏,皆总领而稽核”[11]。《清史稿》载:“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岁察属吏贤否,职事修废,刺举上达,地方要政白督、抚,允乃行。”[6]3356据此,知府亦职掌司法审判。知府的司法职掌主要有三:一是审理“自理词讼”的上诉案件;二是复审州县上报的徒刑以上及命盗等重案,根据律例拟定意见,上报按察司决定;三是负责审理督抚衙门、按察司交发审理的案件。
二、 清代汉中地方官的诉讼认识及其影响因素
(一)诉讼认识
由于府县地方官承担着重要的司法职掌,负责绝大部分刑事、民事案件的审理,长年处理诉讼问题,必然会在诉讼实践过程中形成相应的诉讼认识。汉中地区的清代地方志收录了部分任职于斯土的地方官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们的诉讼认识,本文将按照年代顺序对之加以梳理。
1.王廷桂的诉讼认识
王廷桂,顺天大兴人,监生,康熙五十二年任汉中府通判。《城固县志·艺文志》记载了王廷桂撰写的《上谕十六条约解》一文,该文反映了王氏对诉讼的认识。首先,王氏对诉讼持否定性评价。他在对“和乡党以息争讼”条的解释中写道:“稍有小忿,讦讼公庭,争讼不止,后来倾家荡产,两败俱伤,可见争讼不是好事。”[17]590而在“息诬告以全良善”条的解释中,他再次指出:“古人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可见告状是第一件不好之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王氏对于诉讼的认识是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思考。他之所以认定诉讼不是好事,乃是因为讼累繁重,所谓“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诉讼的结果往往是倾家荡产,两败俱伤。其次,王氏认为息讼是非常必要的。他极力赞成《上谕十六条》提出的“和乡党以息争讼”的观点。他认为息讼的关键环节就是“和乡党”,他指出:“若要息争讼,尤要和乡党,乡党既和,争讼自息矣。”[17]590按照他的理解,所谓“和乡党”就是:“年高之人要尊敬他,孤寡之人要怜惜他。我若富贵必须谦让,我若贫穷也须安分,平日和平谦逊,自然彼此无争。切不可倚势横行,欺良压善。”[17]590一言以蔽之,就是乡党之间要形成一种以儒家文化为指导的伦理秩序。再者,面对捏词诬告这种诉讼策略的问题,王氏认为诬告是害人害己的最差策略,得不到任何好处。他指出:“即有十分冤抑,不得已鸣官究治,只可据事直陈,官府自然伸理。乃有无赖棍徒,见良善之人便要欺侮诈骗,稍不遂意,即捏词诬告,害得良善之人见官见府,多少拖累,岂知官府审出真情,将诬告之人加等治罪,其意原要害人,谁知反害自己,仔细思量,有何益处?”[17]592
2.严如熤的诉讼认识
严如熤,字炳文,湖南溆浦人。嘉庆五年,举孝廉方正。六年,补洵阳知县。八年,补授定远厅(今汉中市镇巴县)同知。十三年,补潼关厅,寻擢汉中知府。严如熤任汉中知府十余年,得成南山镇抚之功。上述的经历使严氏对汉中的诉讼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考察了汉中的两个诉讼问题:一是好讼的原因问题,二是差役鱼肉百姓的问题。
在好讼的原因问题上,严氏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认识的。他首先写道:“川楚民情本自好事,加以讼师包揽刁讼,鼠牙雀角往往酿成大讼。”[18]741在严氏看来,山民好讼的原因,其一是居住在汉中秦岭巴山之中的山民多是川楚移民,本来就有好讼的习气;其二是讼师从中包揽刁讼,也就是讼师插手全部诉讼过程,甚至为达到诉讼目的,不择手段,将鼠牙雀角等琐事细故夸大其词,捏造成为能够引起官府重视的重大案情。
在差役鱼肉百姓问题上,严氏对差役鱼肉百姓的手法观察得细致入微。他写道:“差役奉票视为奇货,边境窎远,每将所唤之人羁留中途客店,伙同店主关说分肥,所欲既遂,则称未票先逃;索诈未遂,或更有株害,则云唤至中途,被某某等纠众抢回,禀请加票;至城,又羁之保户,屡月经旬,不得质讯。差役坐食两造,口岸费已不赀至;命案之邻证,盗案之开花,一案犹必破数十家。”[18]741而差役鱼肉百姓的后果并非仅仅是使百姓“破家荡产”,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是使“民苦莫诉,几何不胥民而盗也?”[18]741为此他再次从“人”的角度入手,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地方官严勒限期,相地远近,计日审结”[18]741,并相信只要这样就能达到“案无留牍,狱无系民,而盗自弥矣”[18]741的理想状态。
3.德亮的诉讼认识
德亮,江南满洲驻防正白旗人,乙卯科进士,咸丰三年由高陵令升任定远厅同知。《光绪定远厅志》载其“民有牒者,力为开导,务使两造心平”[19]233。德亮之所以在处理民事诉讼问题时,采取尽力开导而不是其他方式,使双方当事人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处理结果,与他对诉讼的认识是有很大关系的。德亮曾经写下的五言诗《听讼》,其全文如下:
太息山陬里,纷争遍士农。岂知谦叶吉,未解讼终凶。
多诈胸参甲,无情舌逞锋。陷人深掘井,射敌巧弯弓。
不畏悬明镜,应难醒曙钟。何当霑圣化,薄海返纯风。[19]334
这首诗可以说集中反映了他的诉讼观念。面对定远厅诉讼纷争繁多的局面,德亮对此不仅仅是叹息,而且引用《易经》中的《谦卦》《讼卦》表达了他对诉讼的反对态度。同时,他又从道德的角度对诉讼进行了价值评价。他认为诉讼是多诈、无情的,充斥着各种诡计,而当事人却对案件审判毫不畏惧,就是拂晓的钟声也难唤醒。从该诗的最后一句不难看出,德亮认为圣王的教化是解决诉讼问题的唯一方案。
4.余修凤的诉讼认识
余修凤,字云朴,湖南平江人,监生。光绪三年至光绪八年任定远厅第四十二任同知,期间纂修了《光绪定远厅志》。余氏在纂修该志时,非常重视风俗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他在《定远厅志·例言》中写道:“而末附以风俗、苗俗,则又验政治之得失也。”[19]4为此他特意附录了严如熤的《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在此之后的按语中,余氏首先将“好讼”定性为八种陋俗之一,应当通过教化加以改易。其次,他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了诉讼的动因,他认为诉讼“其始不过一念之不平,未必不可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乃因一朝之忿,一惭之不忍,遂启讼端”[19]100。进而,他又在分析当时诉讼的外部环境——“讼棍为之主唆,痞徒为之拨弄”、“丁差之伪诈,歇保干证之花销”[19]100的基础上,得出了诉讼的结果对当事人而言是极为不利的结论,所谓“耗财产,费日力,荒正业,结冤仇,生事变,坏心田,甚者丧身亡家”[19]100。基于上述认识,作为地方官的余修凤语重心长地劝谕其治下的民众应当学会忍耐,不要轻易诉讼。“平居济人利物之事,求一文之佽助,犹有难色,今乃以有用之财填无底之壑,事后追思,悔已无及,则何如忍之须臾之为得乎?至如骨肉相残,尤为奇变,其家亦必立败。”[19]100在余修凤看来,讼棍、痞徒、丁差、保户等人在诉讼中往往扮演着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对这些以诉讼为营生之人,余氏认为他们必遭天谴。他写道:“若夫踞城之保户、乡曲之地痞,利人之讼,以营己之生,未有不遭天谴者。”[19]100-101
5.张鹏翼的诉讼认识
张鹏翼,四川人,同治癸酉年拔贡,光绪二十二年署任洋县知县。光绪二十三年,《洋县志》在张鹏翼的主持下得以修纂。该志第七卷《风俗》的最后,张鹏翼就当时洋县的风俗发表了总结性的论述:“洋州风俗,男务耕耘,女勤织纺,洵称勤俭,然习于偷簿,至今日而浇漓极矣。奸贪险诈,诡谲无耻,其大要有三,曰:好赌,好讼,好货。”[20]554在上述总结之后,张氏并没有对好赌、好货进一步发表议论,而是集中阐述了他对好讼的看法。他这样写道:“不惟睚眦之忿,不讼不止,往往有同室操戈,自相鱼肉者,皆一利字误之也。”[20]554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张氏将好讼的原因归结为利益使然,这一认识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然而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念往往更强调“义”,以“利”为核心的诉讼显然有违伦理纲常,是对传统伦理秩序的严重破坏,故而张氏感叹道:“伦理纲常几于废坠,旧染污俗,谁与维新?”基于上述认识,张氏进一步提出了破解好讼的对策,即“革薄崇忠,移风易俗”[20]554。
通过以上梳理,笔者发现汉中地方官的诉讼认识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共同点:一是他们的诉讼认识均集中在好讼问题上;二是他们均对诉讼持否定性的评价。至于这种共同性是如何造成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究诉讼认识的影响因素,如此才能给予该问题一个合理的解释。
(二)影响因素
认识的形成往往受制于诸多的因素,但总体而言可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笔者认为,清代汉中地区的诉讼风气是影响本地地方官诉讼认识最重要的客观因素,而作为主观因素的地方官知识背景也在诉讼认识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影响作用。
1.诉讼风气
汉中因地处秦蜀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末清初,因战乱频仍,汉中人口锐减。为解决人口问题,清廷接受了时任川陕总督鄂海的建议,实施移民政策,招募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地客民到汉中定居。这一政策实施后,汉中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带来了社会转型,其中诉讼风气的变化尤其明显。时任南郑知县的王行俭描述了当时汉中地区的诉讼风气,“深山穷谷,垦荒辟土者多异地之人,睚眦启衅,狱讼滋多,此则阖郡皆然。”[21]19王行俭的这一概括可以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汉中地区的诉讼风气,汉中所属各厅州县的地方志大都有类似的记载,可参见“清代汉中地区诉讼风气表”。
据表,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除褒城县外,汉中其他厅州县的诉讼风气显然属于“好讼”、“刁讼”、“健讼”的类型。面对如此的诉讼风气,汉中地方官将关注点集中于好讼问题上,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角度而言,地方官的诉讼认识不过是当时诉讼风气这一客观存在在其头脑中的主观反映而已。

清代汉中地区诉讼风气表
2.知识背景
地方官给予诉讼以负面的、否定性的价值评价,则与他们的知识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清代选官的机制包括两种,一是通过科举考试进行选拔的“正途”,二是经由捐纳获得功名和官职的“异途”。但是无论是“正途”还是“异途”,官员的知识背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具有某种同质性。从本文业已考察的上述地方官的出身来看,王廷桂、余修凤为监生,严如熤则是以制科中的孝廉方正科授官,德亮为进士,张鹏翼乃拔贡,虽然他们取得官职的方式各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在当时教育体制下接受教育的士子。唐宋以降,科举考试是官员铨选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途径,因此科举考试对当时的教育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进而影响着传统士人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顺治二年颁行的《科场条例》规定了乡试和会试的考试内容,“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29]3148首场是直接考察士子对儒家经典的掌握,二三场虽然考察的是士子是否具备治理国家的行政技术和政治能力,但是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如果没有对儒家经典的领悟,所谓的治国技艺是无法通过考卷充分表现出来的。加之乾隆时期的科场改革又将论、表、制概行删省,儒家经典在科场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由此,我们可以说清代科举考试考察的重点仍然是儒家经典,故而传授儒家经典就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理解和研习儒家经典是士人学业的关键环节。一以贯之的儒家教育使得士人必然普遍接受儒家的价值观,而儒家在诉讼问题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周易·讼卦》就说,“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30]480。儒家创始人孔子也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30]28由此可以看出,“无讼”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而诉讼特别是“好讼”、“刁讼”、“唆讼”等现象显然是不符合儒家价值观念,作为长期接受儒家教育的地方官对诉讼给以负面的、否定性的评价是在情理之中的。
除了传统儒家经典的熏陶以外,清廷关于基本伦理规范和行为规范的相关规定也构成了地方官的知识背景,对他们的诉讼观念不无影响。康熙九年,清廷颁布“圣谕十六条”,其中有两条与诉讼有关,即“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雍正二年,清廷又发布《圣谕广训》,对“圣谕十六条”进行疏解,在对“和乡党以息争讼”的疏解中这样写道,“乡党中生齿日繁,比闾相接,睚眦小失,狎昵微嫌,一或不诫,凌竞以起,遂至屈辱公庭,委身法吏。负者自觉无颜,胜者人皆侧目。”这段疏解能够非常清晰地表明,清廷对诉讼持负面的评价。而在对“息诬告以全良善”的疏解的最后,则表达了无讼理想的强烈追求,所谓“庶几从风慕义,胥天下而归于无讼,岂不休哉”[31]。由此可见朝廷对诉讼的态度与儒家的观念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官对诉讼问题所秉持的立场。
[1]昆冈,等.大清会典:卷4[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
[2]王又槐.办案要略[M]//官箴书编撰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4卷.合肥:黄山书社,1997.
[3]张望.乡治[M]//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2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4]郑观应.盛世危言续编:卷2[M].清光绪丙申年巴蜀善承堂刊本.
[5]徐栋.牧令书·自序[M].清同治七年江苏书局刻本.
[6]赵尔巽.清史稿:卷116[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昆冈,等.大清会典:卷52[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
[8]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9]蒋攸铦.谢颁遇变谕旨陈言疏[M]//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246[M].清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
[12]汪辉祖.学治臆说[M]//官箴书编撰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5卷.合肥:黄山书社,1997.
[13]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卷85[M].四库全书本.
[14]嵇璜,刘墉,等.清通典:卷34[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5]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6]方大湜.本案用何律例须考究明白[M]//方大湜.平平言:卷2.清光绪十八年资州官廨刊本.
[17]王穆.康熙城固县志:卷10[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8]严如熤.嘉庆汉中府志[M].郭鹏,校勘.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19]余修凤.光绪定远厅志[M].胡瀚,张西虎,校补.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20]张鹏翼.光绪洋县志:卷7[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4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1]王行俭.乾隆南郑县志:卷2[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2]贺仲瑊.留坝厅志:卷4[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2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3]刘煐.光绪佛坪厅志:卷1[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3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4]卢坤.秦疆治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25]张廷槐.道光续修宁羌州志·吴特征跋[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2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6]王穆.康熙城固县志·胡瀛涛序[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1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7]孙铭钟,等.光绪沔县志:卷1[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2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8]朱子春.光绪凤县志·郭抄本序[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36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9]赵尔巽.清史稿:卷108[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0]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1]清实录·雍正朝:卷16[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曹 骥]
K290
A
2096-4005(2017)04-0040-06
2017-02-07
2017-05-12
胡瀚(1982-),男,安徽阜阳人,陕西理工大学经济与法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学理论、法律史。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4JK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