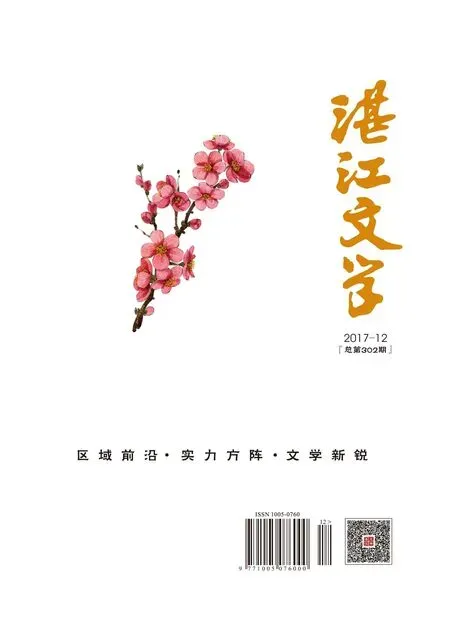出于史,呈于戏
——评《大吏陈瑸》
2017-11-29陈国威
※ 陈国威
出于史,呈于戏——评《大吏陈瑸》
※ 陈国威
陈吴森先生也许是一位创作精力十分旺盛的文人,其作品《雷州之旅》《商情情仇》《通背神拳》《白鹭湾》《月亮湾》《将军石敢当》(上述为剧本),《暖风》《见证》《县委书记李昌梧》(上述为报告文学),《守望》《我爱您,湛江》等等已为学界、社会所知、传诵。而其撰写的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大吏陈瑸》更是获得湛江市文学艺术精品创作资金扶持。从陈先生作品来看,他比较注重乡土特色,时常将家乡情怀诉之于笔下,令人阅读后,产生别有特色的感觉。其最近创作的历史剧《大吏陈瑸》除了乡土风情外,更是传承“借古鉴今”的史剧观念,突显剧本主题愈发鲜明,形象更加高大,与现实生活贴近的愈发紧密,展示出一种愈加成熟的态势,具有“出于史,呈于戏”之特点。
陈瑸,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清史稿》卷277有“陈瑸传”。其载曰:“陈瑸,字眉川,广东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授福建古田知县。古田多山,丁田淆错,赋役轻重不均,民逋逃迁徙,黠者去为盗。瑸请平赋役,民以苏息。调台湾,台湾初隶版图,民骁悍不驯。瑸兴学广教,在县五年,民知礼让。四十二年,行取,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四川提学道佥事。清介公慎,杜绝苞苴。上以四川官吏加派万民,诏戒饬,特称瑸廉。未几,用福建巡抚张伯行荐,调台湾夏门道。新学宫建朱子祠于学右,以正学万俗,镇以廉静,番、民帖然。在官应得公使钱,悉屏不取。……(康熙谕曰)‘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追授礼部尚书,荫一子入监读书,谥清端。” 除了《清史稿》外,《台湾通史》卷36“循吏列传”亦多处记述他的政绩,湖南、四川、福建、广东的省志,漳州、泉州、台湾、雷州、长沙的府志以及古田、台湾、湘潭、海康的县志,更是详细地记载了陈瑸在当地的活动。不难看出,陈瑸是历史一名清官,诚如清人李元度在《国朝先正事略》上册卷12评价陈瑸,“知谋国而不知营家,知恤民而不知爱身”。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陈清端公清操”中亦载曰:“居官能以清廉著闻者,观于公益信……圣祖目为苦行老僧,又曰:‘从古清官,计无逾瑸者。’”如此清官值得弘扬!
电视剧作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对正能量的传播具有其他媒介不可替代的功能。而从历史剧创作的角度来看,从史实出发,对故事情节作一些变动、改动,通过人物性格、关系的设定以及语言风格的呈现,往往更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促进价值观的传播。眼前的《大吏陈瑸》正是如此。英哲柯林武德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意人克罗齐亦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许剧作者正是想通过历史人物陈瑸的历史事迹为我们社会提供一份正能量的价值观的展现。
我们注意到,作者此处对剧本风格、基调的指示围绕陈瑸的清廉气质来展开的,所以开头就告诉人们陈瑸是出身在一个清贫的家庭。剧本第一集第3页:“一方栅门、一堵矮墙围着一个小院、三间小房。”其后剧本中仍然不断地强化这种家庭出身。“啥都不如蚶蛘好,空手挖来装满篓。也得卖钱得换米,也得配饭上酒桌。”“日头晒死老虎母,鬼捉蚶蛘做模样。躲回海中短命去,苦坏蒯人奈无何。”(第10页:雷州歌)“我家是有五亩之田,可是濒临南海,那里堤围失修,每年海潮作患,基本上种不了庄稼。”(第50页)如此史实、故事情节的展现,可以令人反思当今不少官员在落马时会含泪哭诉到自己是农民家庭出身,为其腐败找借口的原因:“出身贫困家庭”“农民的儿子”。前段时间火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开始的主角赵德汉正是如此。“几辈子的农民啊,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看着心里踏实,看着精神满足。看久了,钞票上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呢。”如此对比,无疑可以告诉人们,腐败与否、贪污与否并非与个人出身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关键还是是否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是否以人民利益为核心?是否从人民角度出发?诚如陈瑸所言的:“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剧本不断强化剧作者这种清廉史剧观:“对老百姓的财物,取之一厘,与贪千百万无异,都是对老百姓的犯罪。”(第七集第111页)“卢副使:别说这么大数额的银子,就是取之一毫一文,也与取之千百万无异,都是犯罪。”(第十二集第192页)“我为官以取民之一厘,与贪千百万无异为座右铭自勉,且以此来约束我身边的人,出门当官十多年来一直如此。”(第二十八集第471页)许慎的《说文解字》曰:“吏,治人者也。”故在传统社会中,往往是强调通过官吏的清廉来管理社会:“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唐文粹》卷十八姚崇《执秤诫》)“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陆游《春日杂兴》)陈瑸的清廉事迹是需要弘扬,我们可以通过弘扬历史上如此的正能量事物,以之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 年 4 月 19 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刘云山同志曾认为,宣传作品要“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长灵气”。他强调,日常宣传中要贯彻落细、落小、落实的要求,注重接地气、贴民心,找准与时代的对接点、与百姓的共鸣点,把核心价值观宣传渗透和体现到各领域宣传报道之中,努力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剧本《大吏陈瑸》正是具有如此之特点。这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剧本,除了用传统的叙事手法,还加入了许多雷州半岛本土文化的游艺、戏剧、歌谣、民俗等成分的的内容,在挖掘历史性和人性的同时,增加了许多娱乐性和趣味性,通过最短的时间使人物给观众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强化了剧作者史剧观的核心内容。
如雷州换鼓,虽言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之“乐小舍(扌+弃)生觅偶” 篇有载:“从来说道天下有四绝,却是:雷州换鼓,广德埋藏,登州海市,钱塘江潮。这三绝,一年止则一遍。惟有钱塘江潮,一日两番”。但由于文献、考古材料之欠缺,目前学术界对于其内容表述并不很清晰,但由于钱塘江潮等的存在,人们都相信雷州换鼓是存在的,只是到底是自然现象还是人文现象,目前仍需要探讨。但剧本中却采用多方收集到的有关雷州鼓文化内容,汇聚而成自己心目中“雷州换鼓”的内容,将把雷州粗旷的文化呈现出来。相信若处理得好,舞台效果势必会给观众带来一场艺术的享受的。马尔库塞所说,“一件艺术作品的真诚或真实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也不取决于它的纯粹的形式,而是取决于业已成为形式的内容。”((德)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三联书店,1989年,第212页。)除了“雷州换鼓”外,还有婚俗习俗也会给此部历史剧带来强烈的舞台效果。如第53页的“打扇头”、第186页的“哭嫁歌”、第203页的“打茶歌”等等都是比较“接地气”民俗文化,是普通老百姓日常耳闻目睹的文化。“打扇头”是雷州半岛婚俗文化的一种,起源何时?流行于何时?仍需挖掘。具体的内容是,当新娘的花轿到达新郎屋门时,新郎即向轿门行一个礼,然后亲手揭开轿门封条。此时,新娘在婶嫂的搀扶下姗姗下了轿,款款步行到门前。这时,新郎正站在大门一侧的高凳上,用摺好的纸扇敲打新娘的头顶三次,俗称“打扇头”。“打扇头”这一习俗含意是什么?众人说法不一,有的说图吉利,“一打多儿孙,二打孝高堂,三打兴六畜”;有的说,女人要讲三从四德,新娘入门,先要给她一个“出嫁从夫”的下马虎威,免得以后回过头来欺负丈夫。雷州有些地方还以为扇头打得越响,新郎日后会更听话。而“哭嫁歌”亦是雷州半岛婚俗文化一大内容。指的是女子出嫁前,同村的姐妹到其家陪哭一个余月,有说有唱,内容多是与亲人离情别意,唱到情深,痛哭不止。对于哭嫁习俗,目前流行于诸多地区及民族。但对于其之来源,众说纷纭。《战国策》卷二十一载,战国时期,赵国的公主嫁到燕国去作王后,其母赵太后在临别时,“持其踵,为之泣,祝曰,必勿使返。”故有人言,此大约就是后来长盛不衰的哭嫁风俗的滥觞了。“打茶歌”其实是雷州半岛人们称呼婚礼中闹洞房的叫法,也叫“打外茶”。传统婚礼中男女青年拥到新房,喝糖茶、吃花生糖果、嬉戏玩闹,出些难题让新婚夫妇演绎,甚至恶作剧,逗得新郎面红耳赤,新娘羞答答,借以取乐。这些传统民俗文化普遍存在社会,带有一定娱乐内容,亦是普通老百姓熟悉的内容。若在舞台中很好展示,对剧本所宣扬的价值观一定能够起作用。电视剧《血色湘西》就是通过“爬刀山”这一民间民俗内容,将剧中主角那种不畏危险、公平正直、敢于挑战的形象传扬下来。而“爬刀山”民俗技艺里面那份扣人心弦的紧张内容亦利于剧情展开。“群众注目于场上,每遇奸雄构陷之可恨也,则发为之指:豪杰被难之可悯也,则神为之伤;忠孝侠烈之可敬也,则容为之肃;才子佳人只可羡也,则情为之移。及渲者形容尽致,淋漓跌宕之时, 观者亦眉飞色舞,鼓掌称快。”(箸夫:《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一,中华书局1960年,第60页。)民俗文化在剧中表现,说明剧中人物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是具有人间社会柔情的一面,可惜的戏分似乎不多,略有意味未尽的感觉;加入这些感情戏可以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和需求,如果仅以历史说事,没有观众欣赏,那即使再好的剧也起不到想要宣传和表达的效果。另外,陈瑸在剧中这些戏分的表现还可以与他对待家乡海堤的问题的对比,强化他“清正廉明,勤躬政事,慈惠利民,解纾民困”人物性格,不愧“清端”之谥号!
在肯定剧本《大吏陈瑸》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指出,剧本个别地方也一些地方是值得商榷的。如把米庙之产生,若将其产生来源处理弃婴事件,是否弱化了陈瑸“清廉卓绝”的核心思想?在古代中国,民间往往是存在“有功德于国、民者祀之”民间习俗。《太平御览》卷二十五引许慎《五经异义》云:“王者所以郊祭日、月、星、辰、风伯、雨师、山川何?以为皆有功于民,故祭之也。”后来,慢慢地,民间社会产生了“有功加于民者,祭之以报焉”;“有功于民则祀之”;“有功德于国、民者祀之”的习俗。但剧本里面第十二集第202页是如此考虑“把米庙”的产生的:犷夫人:(举起女婴)姐妹们,为了感恩陈大老爷的救命大德,我提议,高凉寨的女人们从今天起,每天做饭都节省一把米,积攒起来,为陈大老爷建造祠堂,大家说好不好? 众人:好!好!好! 犷酋:我提议,祠堂的名字就叫“积米祠”吧!如此的情节,虽然有将陈瑸“好生之德”品性展示的功能,但一则不适合历史,二来也许弱化剧本为官要“清廉卓绝”的主题。还有一点就是官庄问题是否也可以考虑采用旁白方式说明一下?一方面李光地说:“台湾的官庄是复杂的,施氏、郑氏、陈氏、李氏、周氏……形形色色,统共87门”,(第460页)另一方面陈瑸又说:“对于那三处官庄的收入,我从心里认为,那不应当是我的囊中之物,它产于台湾,理应用之于台湾,我将其全部捐出,作为修建启圣祠、明伦堂、文昌阁的经费”。(第452页)在这里,观众也许不清楚官庄到底怎么回事?是合法还是非法的?也许采用旁白方式对官庄说明一下,更能显现出陈瑸那份清廉风格。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极其深厚的国家,史籍题材十分丰富,自然造成历史题材的创作一直是媒介传播至为重要的部分。宏观考察《大吏陈瑸》这部历史剧总体创作情况,可以发现其中的强烈现代意识、浓厚而鲜明时代感弥漫于整部剧本中。剧作者正是通过史剧形式来反思历史,借之架设连接古今社会的桥梁,创造“沟通历史与现实的审美场”,折射出独特、多元的戏剧特效追求。剧本通过讲述陈瑸一生的经历,以其个人之经历,弘扬清廉之风气,告诫人们要“在官惟明,立身惟清”,对廉洁奉公之士给予肯定,歌颂清官文化,反映社会对清廉社会风气的向往!
(作者系岭南师范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