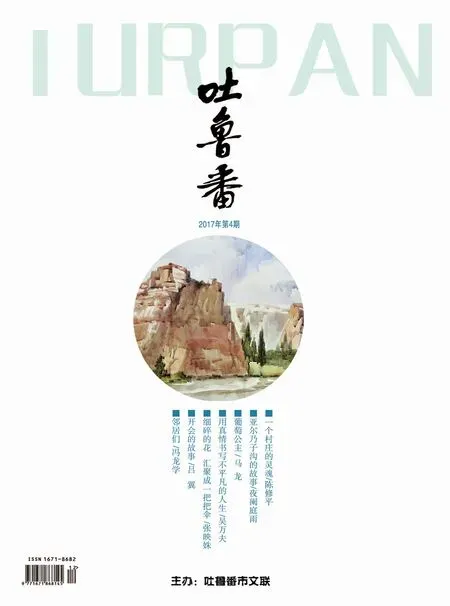一只顽强的疣
2017-11-25海南严敬
○海南 严敬
一只顽强的疣
○海南 严敬
一
一阵风刮过,龙生浑身皮肤收缩了一下。这股风马上无影无踪。可是它带来了隐藏的凉意。水里的鱼咬钩不再凶狠,带芒的狗尾巴草开始发黄。龙生身上莫名其妙地骚痒起来。骚痒困于皮肤之下,常常像蚂蚁那样蠕动。三天过去,龙生身上安静下来,蚁群似乎突围而去。疣,一只疣,如同污点一般突然出现在龙生光洁的下巴上。这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多少还是有点碍事,只要龙生一抬手,他的手指就奔向这只疣。他拈着它,轻轻地抚摸,不知怎样对待它更好。
暑假结束得匆忙,秋风一起,新学期就开始了。龙生模模糊糊记得,这只疣好像就是伴着秋风到来的。他的下巴本来十分光滑,虽然谈不上精致,但没有明显缺憾,现在,孤突突地长出了一只疣,显得很扎眼。龙生开学上的是高一,他同班的同学,有的考上了地区中学,有的考上了县中,有的考上了农场中学,也有没考上的。他考的是农场中学。接到通知那天,他郑重其事地考虑,要不要继续把书念下去。直到开学前几天,他还是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好拿着入学通知去报名。
教室前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衰败,时时往下飘落。全部是陌生的面孔,没一个熟人。龙生感到压抑,想起初三的同学,那些熟悉的面孔正各奔东西。他找到自己的教室,在靠墙的一个座位上坐下。班主任还没有来,同学们各自想着心事,谁也不主动搭理谁,极力保守着距离。龙生的头扭向窗外,一片枯黄的梧桐树叶脱离枝头,发出隐隐的碎裂声,在他的注视下,左摇右摆,缓缓下落。他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片落叶。他抬起手,那只疣,迅急地投入他的手中。
过了两天,分了座位,坐在他前两排的是两个女生。左边的女生扎两支长辫,面庞方正,笑容温柔。右边的女生,剪短发,双耳掩藏,皮肤白皙,两眼漆黑。若是经过她身旁,可以闻到一股香味。这种味道与龙生闻惯的气味不一样。不是雪肤膏,也不是青草,有点刺鼻,像一线柔软的刀锋,直入鼻腔,沉游肺腑。又过一天,物理老师点名,得知左边的女生叫张小萌,右边的女生,叫周倩云。物理老师姓慕容,这是一个少有的姓,覆满了灰尘,似乎只有历史老师姓这个姓最恰当。因为这样一个姓,往往叫人在最初相识时对他多看一眼。慕容老师五十开外,肥头大耳,满面红光,只有一只眼睛。点到周倩云时,他独眼看过来,目光浓酽,闪闪发亮。以后每每上课,慕容老师的独眼都要多看周倩云一眼,那是一股耀目的光束,也是一根直通通的棍子。几乎每节课慕容老师都要向周倩云提问,都是简单的课堂内容,周倩云有时回答得对,有时答非所问。即使答不上来,也没关系,慕容老师始终和颜悦色,从不批评。
但慕容老师仍然是一个严厉的老师。龙生有一次被叫到黑板上做一道物理题,结果他做错了,在同学们面前丢脸。可是,他的不幸没有就此结束。自他写下第一个字,慕容老师的独眼就在他身上扫来扫去,慕容老师嗅觉极其灵敏,早意识到猎物到手。随着他的错误成为定局,慕容老师甚至露出欣喜。龙生将手中剩下的半支粉笔放入讲台上的粉笔盒,准备回到座位。慕容老师一声断喝:“往哪里走,站住!做不来题目,还想回去?站到那里去。”慕容老师手指黑板旁边的墙角。龙生犹豫一下,慢慢走到墙角。他面对墙壁,只让同学们看到他瘦弱的脊背。“转过来。”慕容老师命令。龙生没有马上转过身,瞬间,他头脑一片空白,身上某处出现短路,他想遵从老师的命令,但身体却不听使唤。
“怎么?耳朵聋了?”
慕容老师走过去,用双手扳过他的肩膀。全班同学的目光都泼向他,他感到自己赤身裸体,骨头发冷,筋肉颤抖。他的手指有点痉挛,像时钟的指针那样,企图旋转。他的右手,慢慢抬起,越过肚腹和胸膛,来到下巴,立即同那只疣在一起。他摸到它尖细的样子,有点潮湿,还有些微的暖意。而他本来极想旋转的手,渐渐安静下来。龙生抬头,在剑戟中寻找。其实不用找,他知道那双映着波光的眼睛在哪里。周倩云也盯着他,他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他的目光瞬息闪开,溜到脚前。
“站好!脚比齐。”老慕容喝道。他的手,顺从地垂下。
“谁会这道题?请举手!”老慕容满脸堆笑。
有人举手。老慕容视而不见。
“请周倩云同学到台上来,给严龙生同学当一回老师。”
周倩云犹豫了一下,站起身离开座位,到黑板上演算龙生做错的题目。
“做对了吗,大家说。”
“对了。”异口同声。周倩云回座位的步伐异常轻快。
龙生的目光往右,流向窗外。教室外面,远处的天空蔚蓝,下面是一望无际的棉花地,棉花的叶子被染成褐色,露出衰败的样子。老慕容又开始讲课,直到下课铃声响起,龙生都伫立在角落里示众。在半个小时里,龙生内心变得孤寂而麻木,不就是罚站么,罚站就罚站,无所谓。老慕容的课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你可以罚我的站,我可以用不听你的课回敬你。只是此前并不知,站着不动会如此累人,简直比干体力活还要累。为了保持平衡,他暗暗将身体的重心左右移动。期间,他数次悄悄抬手,抚弄下巴上的疣。疣还在,疣没有鄙弃他。他也曾担心过,他的动作,会牵引同学们的视线。幸好,同学们的目光都盯着老慕容。他的两指拈着疣,竟有点恋恋不舍。假如老慕容杀个回马枪,他肯定又一问三不知。值得庆幸的是,老慕容对他已无兴趣。
二
地上的树叶越来越多,叶子干脆,怕碰,一碰就碎。早先地上的那些灰尘也逐渐不知去向,土路和操场变得光洁、坚硬。
在班上,龙生很少出声,有的同学喜欢说话,用声音显示自己的存在。众人的声音组成了一片树林或者一丛荆棘,他就掩藏在其下。老慕容的目光即使犀利无比,但穿过层层枝叶,也要受阻变钝。
龙生的耳朵极其灵敏,能扑捉到教室里每个角落发出的细微响声。一天,老慕容上课,大家正在认真听讲,突然,一股异臭像墙壁一样堵住了所有人的鼻孔。这臭味辛辣尖锐,似乎击昏了所有的人。首先,老慕容愣住了,他很吃惊,瞬间失语,接着,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嫌恶和迷茫的神情。同学们面面相觑,有的拼命忍住笑,有的伸手在鼻前轻轻扇动。大约过了五六秒,微笑回到老慕容的脸上。他欲盖弥彰地说:“哦,没有什么,真的没什么。”课堂差点就要爆发出一阵大笑,但老慕容瞬间绷紧脸,刹住了车闸。
几个女同学的脸微微发红。龙生知道这股异臭是谁创造的,他听到了它在酝酿的时候撞击空气的极其细微的声音。龙生看了一眼周倩云。他坐在她的左后侧,能清晰地观察到她脸上的表情。她的左脸颊漫上了一朵红云,一直红到耳根。那片红没有马上褪去,而是向周围洇开,攀上了主人的耳轮,使主人的整个耳朵显得艳丽。尤其是,那耳垂,像一片花瓣,生有茸毛,洁净,圆润,红得透明,小小的血管,像根须一样清晰可见。它柔软娇嫩,似乎还发出一股莫名的香气。
“严龙生。”有人叫他。他有点惊慌,急忙收回自己的目光。他记得他有所掩饰,目光是迂回接近目标的,捕获目标后也并没有粘在上面,而是若即若离。“严龙生。”第二声又来了,老慕容点他的名。他慢慢站起来,垂着头,等待老慕容提问。自然,他又要答错什么。老慕容并没有发难,直到下课铃声响起,也没有向他提问。但也没叫他坐下,老慕容的独眼也不多看他一眼,仿佛他变成了一团空气。老慕容夹着课本走了,在就要跨出教室的时,又回头望了一眼。既像检查龙生是否没有经过允许就擅自坐下来,又像对学生们充满留恋。
等老慕容走远了,龙生才坐下。他觉得有点累,又十分丧气,手托下巴,瘫倒在座位上。他思绪一片混乱,这个老慕容,可能盯住自己了。为什么呢,为什么?龙生几乎想吼叫,但他没有叫出来,他非常清楚,他没有道理。
这时,有人唱歌。原来是周倩云。
我站在龟蛇山上/两眼平视前方/沸腾的扬子江啊/后浪推前浪/一直奔向远方。
离上课还有几分钟,教室异常安静。大家都在听。周倩云又唱了一遍。龙生屏声静息,手指微微颤抖,习惯地抬手,摸自己的下巴。
三
龙生新交的朋友——李小南,对他说:“那个姑娘,知道吗,她是武汉人。”
“哪个?”龙生问。
“就是坐在你前面的那个。”
龙生的心颤抖了一下。李小南又说,她的父母是下放到农场的武汉知青,她出生在农场,长在武汉。现在,又回到农场中学上高中。
这些情况,李小南不说,龙生也已猜到,周倩云满口武汉话,还有她唱的那首歌,都清楚地表明了她的身份。此前,龙生认为,天下最难听的就是武汉话。因为,在农场,到处都是武汉人的脏话,尤其是,农场人争相效仿,骂得比那些武汉学生还要出色。这些难听的脏话像狗屎一样撒满农场。可是,听周倩云说话,他却感到陶醉。原来,武汉话也可以像音乐般动听。
“他们都说,她很漂亮。”李小南又说。边说边盯着龙生,似乎是在询问他的想法。龙生低下头,躲过他的目光。“哎,她来了。”
龙生抬头,看见周倩云正往座位上走。她的双眼幽黑,正望着他。他没有丝毫的畏怯,而是张眼迎上去。一秒,也许是两秒,他们相互对视。他捉住了她的目光,或者说他被她捉住。这个过程太漫长,龙生使出的是浑身的力气,终于筋疲力尽,垂下头来,气息奄奄。
“哎,说话呀。”李小南说,他推了龙生一把。这一把仍然没有把龙生从梦中摇醒。“没味道,我走了。”
李小南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课铃响过,老师站到了讲台。龙生还在回味刚才的一瞬,自己神情的痴呆,还有身体的僵硬,如同遭到梦魇。老师的课,他一句也没有听明白,却明白了这个姑娘,她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魔力,可以对他施行定身法。她的眼睛,足以杀生。
杀是杀不了,那只是龙生的一种渴望。龙生活得好好的,并没有少胳膊少腿。就是一根头发,也不曾少。他渴望周倩云看他一眼,再多看一眼,重复体会那种被靥的感觉。天还没有亮,他就起床,跑到教室,因为在教室,他能看到周倩云,而且最有机会扑捉到那一双媚眼。他呆在教室的时间最长,一般都是最迟离开的一个。做学生的都把教室看成牢笼,但对龙生来说,教室给了他隐秘的希望,教室像一片树林,他隐身树下,等待他喜欢的鸟儿鸣唱。
教室有时很静,有时很吵闹,龙生的耳朵很尖,可是,再也没有扑捉到那股听来既优美又忧伤的旋律。“沸腾的扬子江啊,后浪推前浪,一直奔向前方”。这歌好听,一遍,他就全记住了。但这歌与他有什么关系?没有,也有啊。为它陶醉,可以说出很多理由。其实,也不用说出理由,因为它是周倩云唱的。歌声袅袅,消逝在扬子江江面。还有呢?龙生固执得很,想听到下一曲。
教室热闹时,大家不免放声谈笑,身子晃动。可是,这个星期,龙生发现即使在安静的课堂,有人也悄悄地晃动身子。眼睛是看不出来,因为晃动幅度极小。龙生是用耳朵听出来的。晃动的身躯只是微微颤动,没有视觉上的位移。但这身躯使劲地摩擦空气,发出了响声。晃动带有传染性,龙生听出了许多人都在悄悄晃动。龙生偶尔抬眼,看到那些晃动的人的脸,有一种隐秘而快意的神情。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正在享受的人们也不让他知道那是什么。从被老慕容示众开始,龙生就感到他游离在这个班集体之外。
老慕容说,别让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羹。老慕容把他看成了一粒老鼠屎,他想,我就这么臭吗?他很难受。他总是躲避着老慕容,身量极力缩小,目光也尽量不和他对接。他只在老慕容的独眼的余光之中。龙生越来越有体会,只要他沁头听课,目光低垂,整个身子似乎要缩到课桌下,老慕容就对他视而不见。他一不存在,当然,他就不臭了。他打定主意,让大家忘记。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发出声音。大家都关注喜欢发言的同学,关注被老师提问的同学,关注被老师表扬的同学。他都不在其中,一两个星期过去,大家渐渐忘记了他的存在。
教室越热闹越好,教室一热闹,好像树长得枝繁叶茂,于是,龙生感到躲藏得越紧。任何一声喧哗,都像一片厚重的树叶,覆盖在他身上。然而,有时,教室突然戛然无声,树枝瞬间光秃,他失去了遮蔽物,如同被脱光衣衫,将被众人目光凌迟。他听说有一种隐身术,渴望学会,能在安静的教室隐而不见。课堂上,他的比一般同学高大的身躯总有下坠的欲望和趋势,说老实话,他把课桌当成了树叶。但他又不甘心彻底溜到桌下,因为那样,就看不到周倩云。
到了中秋节,学校要放假,班主任让几个走读生晚上来校看护寝室,这几个走读生晚上必须睡在寝室。龙生也是走读生,有幸加入了看护寝室的行列中。他和几个伙伴在那个凌乱肮脏的寝室睡了一晚上。这一睡,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却使游离班级之外的他,回到集体的怀抱。
四
在学校寝室睡过一晚之后,仅仅两天,龙生身子就出现奇痒。痒处首先是发生在屁股,过后是大腿根,之后四处蔓延,连手指缝都像生出了一群不停噬咬的虫子。没人处,他会畅快淋漓地抓挠一阵,暂时把虫子治服。可是,那些虫子是赶不走的,只要有机会又跑回来袭击他。人群里,或在操场上,他不好意思挠痒,他只能装着自己的手好像是无意间拂过身上某一处,可是这一拂,不仅没有吓跑虫子,反而招惹了它们,让它们变本加厉地反攻。
最难堪的是在教室,屁股一挨上板凳,便奇痒无比。痒,有时比痛还难受,痒得钻心,就是这种最难受的痒法。龙生火烧火燎,但又不能让别的同学看出来,更不能伸手挠痒。他坐在位置上,对于那些虫子一轮又一轮的反攻,束手无策。一堂课,他听的少,很多时候都在想对付那些虫子的办法。他把自己的屁股紧紧抵在凳子上,双手扳住板凳,暗暗用力挤压屁股。好了,这个法子很管用,虫子打跑了。同时,如果晃晃身子,增加屁股的摩擦,取得的效果将更好。他自己这一晃不要紧,瞬间发现大家都在晃,他听见大家都在悄悄地摩擦屁股。原来,所有的同学都在接受一场传染病的洗礼。此前,老慕容把他说成是一粒老鼠屎,只有他身上有臭味,但现在,大家共患一种病,都是平等的。
龙生回家找来《现代汉语词典》,七翻八找,找到一个词——疥疮,由疥虫引起的传染性皮肤病,对照症状,他知道大家都得了疥疮。深秋时节,疥疮席卷了农场中学,没人幸免。龙生又成了班上一员。
上课时候,周倩云也悄悄晃动身子。大家共同的感受,在她身上也有体现。只不过,她晃动的幅度极小,似乎只是微微的颤动,很难看出来。周倩云那么白净娇嫩,为什么也要遭受疥虫的侵扰?龙生心里因此十分难过,假如可以的话,他愿意疥虫咬他,而放过周倩云。他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好,可是太一厢情愿,不说人家周倩云是否愿意让他代为受苦,就是那些虫子是不是愿意专门咬他,也是极大的疑问。道理很明显,一尺绸缎,一块麻布,你想从谁先下手?龙生像很多孩子那样,喜欢自虐,仿佛自己就是一块麻布,经咬,耐咬,还不怕咬,所以,他想牺牲自己,拯救他人。
龙生从总场街头走过,恰好看到一根电杆上贴着治疗皮肤病的广告,他被这张广告引到一家旅社的二楼。一个戴着毡帽、满脸胡须、自称医生的中年人,拿起他的手端详,啧啧几声后,给他一白一黄两种药。药价很贵,中年人两手的食指交叉成十字,10元。龙生大吃一惊,他一个学期的学费也就18元而已。他荷包里只有5元,他问中年人,5元可以吗?我只有5元。中年人叹口气,5元就5元,谁叫你是一个学生。回到家,他照中年人说的做,过了两天,他身上的刺痒居然消失。他本来将药物分成了两份,另一份是给周倩云准备的。他迫不及待地想把药物送给周倩云,让她尽早摆脱那些虫子的噬咬。可是,怎样把药物给她呢?
龙生想了又想,一定不能当着大家的面给,如果那样,会叫周倩云难堪,说不定她要生气,她一生气,可能会拒绝。他开始寻找单独和周倩云见面的机会,一般地,从寝室到教室,再从教室回寝室,到食堂打饭,上厕所,这些路途上都可能有机会,可是,总有女同学陪伴在周倩云身边,她的同桌张小萌,与她如影随形,亦步亦趋,似乎存心不给他一点希望。龙生心里犯愁,恨不能一声大吼,吓跑她身边的人,然后把药物送给她。机会还是来了,一天早晨,朝读,下课铃响过,同学们很快离开教室,龙生自然是最后一个离开。正当他从座位上起身时,周倩云跑回教室,走到座位上拿起一个小物件要走。龙生毫不犹豫地叫:“周倩云!”
周倩云停住了,她很吃惊,犹疑地问:“我?”
龙生掏出一直携带在身上的纸包,走近她:“给你的。”
“什么?”周倩云神情露出恐惧,仿佛见到一条蛇正在靠近。
“药。”龙生说,“治疥疮的药,特效药。”
“我要药干什么?”周倩云问。
“治疥疮啊。”
“你以为我有疥疮?”
“难道没有?”
“神经病!”周倩云愤怒了。尽管她在生气,但她的眼睛却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好像往相反的方向去,里面有隐秘的笑意,是湿润柔和的。
“给。”龙生又说,他很顽强,一点也不害怕挫折。周倩云的目光转向他的手,说,真的是药?龙生说,真的。她打量他手中的东西,充满了疑问。她的疑问还不只这个,她的目光又慢慢上移,像一股潮水涌了上来。
“那么,这个,是?”她的目光钉在他脸上的某一处,好奇、猎奇、奇怪、调笑、关切等等,如同箭镞一齐向他射来。
“是?”她又问,嘴角朝两边舒展。
龙生懂得她的意思,他另一只手抬起来,迅速接近自己的下巴,食指和拇指马上掩住了那只孤立无助的疣。
“是什么?”周倩云毫不松懈。无疑,它成了她攻击的目标。“难看死了。”接着,她发出一串锋利的笑声。
五
元旦要来了,学校在元旦前一天举办了一个简陋无比的迎新演唱会。各班排队聚于操场,同学们就在队伍前面表演他们的节目。龙生班上也出了节目,周倩云的独唱《外婆的澎湖湾》。这是龙生第一次听这首歌。这没有伴奏、没经修饰、质朴而流畅的歌声打动了他,歌声里有海浪和外婆,有寂寞孤单的少年,充满了莫名的甜美和超凡脱俗的梦幻。龙生看着周倩云,她十分投入,往日迷雾般的双眼,异常清澈,她对着所有人舒展歌喉,然而又好像只为他唱。“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声音圆润利落,娇美甜蜜,弥漫青春魅人的气息。龙生想哭,眼眶里蓄满了液体,只要一动眼皮,这些液体就会坠落。他又抬起手,先抚摸一下那只也着了迷的疣,然后,食指和拇指张开,八字形地上移,不着痕迹地拂去了两边眼角的泪水。他不知道,此后他也将变成沙滩,时时被澎湖湾的海浪淹没和浸泡。
周倩云那天将短发扎成一个马尾,使她更与众不同,差不多所有的女生都是两条长辫,要么是驮在背上,要么是摆在胸前,了无生气,而周倩云扎着马尾,左右晃动,上下飞扬。而且,所有人都看见,周倩云的耳垂上,别着红色的饰物,像珍珠,也像一枚鲜艳的扣子。没有女孩子这样打扮自己,一是不会,做梦也想不到;二是不敢,这样要招人大骂。但周倩云这样打扮了自己,有点离经叛道,有点心照不宣的媚惑,仅用一首歌,短暂的两三分钟,打开了许多人的眼界。龙生闻到了一种味道,像花香,也像药香,让人沉迷陶醉,也让人头晕目眩。
演唱会结束,学校开始放假。龙生好半天都不知道干什么,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它们散发出强烈的气息,在他心里弥漫。他晃悠悠地进了教室,坐在位子上,似乎等待老师上课。可是,教室空荡荡的,除了他没有别人,这才想起放假了。他突然想到,周倩云家在分场,此刻,她正在回家的路上。龙生马上起身,跑着回家,他从家里推出自行车,纵身跨上去,向分场的方向急驰而去。他想的是,追上周倩云,或者,与她相遇。天色晦暗,飘起微雨,他的发丛凝着雾霭,他被火烧灼的目光四处搜寻,行完了整个路程,最终还是没有寻到他要看到的身影。他离小镇已经不远,他心里想不妨到小镇走一趟。小镇有一家书店,他买了一本杂志,这样,他没有空手而归。
元旦本来只有一天假,但连着星期天,一下放了两天假。这两天,龙生觉得十分漫长,好像踽踽独行在沙漠上,望不到边际。上学的头天晚上,他先是睡不着,躺在床上,一会儿盯着黑暗中的楼板看,一会儿看昏黄的小窗。他甚至起身打开小窗,将目光伸向窗外,试图寻找冬夜里像他一样失眠的人。月光浑浊,沉重,冰冷,但月光深处,传来隐隐的鼾声。天快亮时,他才沉沉睡去。等他醒来,抱着书包往学校跑,同学们已下了早读。教室空无一人,课桌哑然无语,龙生越过一排排桌凳,坐到自己位子上。他慢慢拿出语文课本,一目十行地看起来。他像一只先入林的鸟儿,等待另一只鸟儿的到来。
忽然,他身边出现一个身影,是李小南,他是不声不响从后门进来的。李小南对他嘿嘿一笑,脸上皮肤皱成一团,没有再松开,好像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负担。龙生很觉奇怪,但李小南不再理他,继续往前走,停在周倩云的位子旁边。他伸手从屉肚里掏出周倩云的笔盒,迅速打开,将一张纸条搁进去,再咔嚓一声关上,把笔盒放回屉肚,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教室。
龙生胸脯噗噗乱跳,面红耳赤,似乎是他刚刚做了一桩勇敢的事情。接着,他感觉浑身抽紧,如同有人挤压他的身体,他拼命与这人抵抗,但他始终处于下风,渐渐地,他被挤扁,挤干血肉,变得轻飘飘的,像一团浑浊的空气。还有,他胸口位置,很清楚地悸动了一下,如同刀锋从那里划过。
快上课时周倩云才进教室,龙生一抬头,便捉到了她的目光。“只是一片海蓝蓝,海蓝蓝。”那首歌,又萦绕在龙生的耳边。她唱的是海,她的眼睛也变成了海,一片,海蓝蓝。她嘴微张,舌尖轻弹两下,海——蓝——蓝。放假的两天里,龙生也学会这样在口腔里弹跳自己的舌头。
周倩云坐下后,便从屉肚往外拿书和笔盒,她打开笔盒,那张纸条出现在她的眼前,她把它抓在手心,然后那只手若无其事地垂下,躲入了裤荷包。
龙生设想不是这样的,他原先的设想是,周倩云发现了纸条,很气愤,要么把它撕得粉碎,要么把它交给老师。可是,周倩云的表现恰恰相反,她镇定自若,好像早有预料,以同谋者的默契接受了那张纸条。周倩云的手好半天都没有露面,龙生觉得她的手在裤荷包里紧紧攥着那张纸条,手指轻轻蠕动,她靠手指就能读懂纸条上的内容。龙生的心上,又有一丝刀锋划过。
这节是老慕容的课。本来龙生对他早有提防,他经常装出目不斜视、认真听课的样子,让老慕容高兴。但今天不行,他的舌头颤颤的,时时在微张的嘴里弹跳,海——蓝——蓝,海——蓝——蓝,一片海——蓝——蓝。
“严龙生,”老慕容大叫,“你在自言自语什么?”
“海——蓝——蓝。”
全班同学都惊诧地看着龙生。周倩云也扭头看他,他又捉住了她的眼睛,一片海——蓝——蓝。
“莫名其妙。”老慕容说,“你说梦话吧,我真要打断你的骨头。”他扬起手臂,做出要打的样子,但独眼竟充满了慈祥。
下课,周倩云急急走出教室,龙生想,她一定是急着看那张纸条。龙生眼睁睁的,看着周倩云跨过门槛,身影越过两个大窗户,消失不见了。他扭头看后面的李小南,他也不见,教室的后门是敞开的。龙生的心抽紧,抽紧,身子怕冷似的颤栗起来,他抱紧胳膊,极力想镇静一下,但不行,他又抬手,摸到下巴,撞到那只疣,他忽然很生气,他揪紧它,一使劲,立即取消了它的寄居权。他的下巴开始滴血,一滴,两滴,滴的很慢。这样的鲁莽带来了一点疼痛,可是,这痛实在不如刚才他心中的另一种痛。
六
那年冬天注定有雪要下,连着半个月,天空都挤满了烂棉絮似的云朵,这云散发出浓稠的黄光,落到人的脸上脖子上,竟冰冷似刀。乌鸦来了,成天在空中盘旋,呀呀叫唤,有人说,它们这样吵闹,是在造声势,等着下雪。天很冷,早晨穿衣,衣服变成了铁衣铁裤。龙生天天上学回家,有条不紊。天不亮他就到校,下晚自习,同学们都走尽了他才回家。看外表,他算得上一个用功的学生。一天晚上下自习,他摸黑回家,走到村口,一种坚硬的东西撞到他的脸上,起初他没在意,接着,坚硬的东西又撞了他的脸。他用手摸,凉凉的,他把那东西凑近眼前细看,原来是雪花。下雪啦!下雪啦!雪花纷纷下落,发出模糊细微的亮光,但它们相互摩擦的声音却清晰可闻。龙生心里欢喜,他转身往回跑,一直跑到学校,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同学们,最主要的是要告诉周倩云。但校园里已是一片静寂,教室和寝室不见灯光。他本想喊:“周倩云,下雪啦!”但他觉得这样不妥。他只好这样喊了:“下雪啦!”他的声音不大,没有底气,漫无目标。大家都裹身在温暖的被窝里,听不到他的声音,似乎也不愿受到他的打扰。他又喊了一遍,依然没有得到回应。突然,他改变主意,他大喊:“李小南!李小南!李小南!”自从发现李小南的诡秘举动之后,龙生不再主动和他说话了,李小南来找他,他总是躲避。他的三声喊之后,男生寝室的灯光亮了,李小南走到窗户来,问:“龙生,是你,什么事?”
他说:“下雪啦!”
李小南脸压在玻璃上,说:“真的,下雪啦!”李小南马上回到床边,龙生以为他怕冷,回到床上去,不想他穿好衣服跑出来,两个人喊起来:“下雪啦!”
路西边的女生寝室的灯也亮起来,她们好像更兴奋,有人打开窗户,几个女生聚在窗前,不停地赞叹,还伸手到外面接雪。龙生看见几人中有一个就是周倩云。她的脸绯红,还对着他们望过来。那扇窗户关上之后,他俩还站了很久。地上已铺满了一层雪。李小南说:“别回家了,我们挤一床。”龙生说:“家里还留着门,我得回去。”他往回慢慢走,踩得雪吱吱响。
七
别的同学只看课本,李小南却在读一些课外的书,他手上有一本《中国现代爱情诗选》,有一天,他把这本书塞到龙生手里。龙生迫不急待地把里面的诗都读了一遍。不读还好,读了之后,他的心事变得更为沉重。开始时,他很兴奋,但越读越绝望,刀切肺腑的疼痛,时时划过心头。其中《雨巷》《蕙的风》《教我如何不想她》这些诗,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字里行间到处是周倩云的身影。他很是吃惊,这些诗句好像都是他写的,写给周倩云的。
这本书在他和李小南之间传来传去,他知道他喜欢的,李小南一定也喜欢。像那首《雨巷》,李小南不喜欢,没道理的。
被他揪掉的疣,不知不觉又回来了,还是落脚在先前的地方,无论是手感,还是通过镜子会面,龙生发现,它依然是原来的样子,同以前的那个,如同孪生兄弟,一模一样。它是不速之客,龙生感到惊讶。他摸着它,不断地表示出自己的抚慰、歉意和无奈。
俯首看书时,龙生也拈着它,这样,龙生的样貌显得奇异而高深。别人以为他开始长胡须,因为绝大部分男生都希望自己长出胡须,而胡须据说是越拔长得越快,龙生可能就是时刻惦记着自己的胡须。如果是胡须,当然美不可言,可是,它是一只疣。龙生图谋再一次除掉它,然而,事情总是很奇怪,龙生时时抚摸它,纵然有时不怀好意,但很多时候,它给了他安慰。他寻找周倩云的时候,他的手总是搭在下巴上,他在掩饰它,同时,它变成了他的兄弟。
八
李小南说:“周倩云说,你很可笑!”
“我很可笑,周倩云说的?”一股刺骨的寒风刮来,龙生又抬手捂着下巴。“她说的,说我很可笑?”
“是的。她说你动不动就手抓下巴,怪得很。你下巴有什么毛病?”
这次聊天龙生得知,李小南和周倩云说过话,而且说到了他,还谈起他的下巴。龙生推测,他们约会了,在有一次约会,他们议论了他的下巴。他的无辜的下巴,最少一次,成了他们约会时的话题。
“你们约会了?”龙生直勾勾地盯着李小南。
“约过了。”
“约过几次?”龙生想咽一口唾沫,但他嘴里发干,巨大的喉结夸张地上下滚动。
“好几次吧,我想一下,四五次了。”
“都在哪里?”龙生听见自己发出一点点呻吟。
“学校,校外的麦地,还有总场。”
龙生头皮发紧,身子好像从高处往下坠落,一团黑雾淹没了他,他溺水了,水堵住他的鼻腔和喉咙,让他无法呼吸,他伸出双手,去抓一根救命草。
“干嘛,又来了。”李小南边说边移开龙生搭在下巴上的手,“让我瞧瞧,是什么玩意。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哦,是有个小东西,小小的,像痣,可以忽略不计嘛。”
李小南也许是幸灾乐祸,也许真的认为那只疣可以忽视,说完他张口唱道:“没有椰林缀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
龙生不得不承认李小南唱得非常好。他一直等待机会,想听周倩云再唱一次,可是,周倩云再也没有唱过。现在李小南唱了,唱得和周倩云一样好,特别是“海蓝蓝”三个字,一样地轻快,舌头的弹跳也一模一样。龙生又一次感到头晕目眩。
过了三天,李小南跑来和龙生咬耳朵,说出一番让龙生脸红耳热的话。他说:“别看班上这些女孩那么清爽漂亮,其实,她们比我们脏。”
“什么意思?”
“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告诉你,她们月月身上来血。”
李小南鬼鬼祟祟的,又塞给他一本书,说:“要想弄明白,看看这本书。”
这是一本《新婚必读》,李小南神秘的样子影响了龙生,他好奇地打开了书,顿感周身发冷,他心虚地抬头观望一下,然后,身不由已地迈上了一种冒险的旅程。
再见李小南,李小南朝他诡秘地一笑,他知道李小南笑什么,他慌张了一下,好像心里不良的念头被人识破。惶乱地望着李小南,脸上微微颤动,似笑非笑。李小南盯着他,似乎不打算轻易放过他,最后,李小南又笑起来,笑得坦然而又充满诚意。他松弛下来,脸上也出现了笑容,起码对一件事,他们开始有所领悟,他们仿佛一起干了一件坏事。
可是,龙生没有料到的是,事情后来变得不可收拾。
首先,他按捺不住,总想问李小南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也是一件他非常想弄清楚的事情。这个问题像子弹一样在他的舌头上弹跳,时刻都想发射出去。终于,一个晚上,下自习了,他把李小南拉到暗处,他问:“你说女生比我们脏,她们每月身上都要流血,是吗?”“是的,我说的,书上也这样说。”龙生犹豫了一下,继续问:“那么,周倩云身上每月也有血?”
李小南愣了一下,点点头:“是的。”
龙生兴奋起来,追问:“你见过?”
龙生的莽撞和无理让李小南措手不及,几乎把他打蒙,他睁大眼睛看着龙生,半天答不上话。他摔开龙生的手,往寝室走去。
龙生的子弹射出去,伤不了别人,却伤到了自己。周倩云那么白皙干净,他想象不出,在她身体的某处会汩汩地流出血污。第二天,龙生坐在位子上,看到周倩云进了教室,她脸上白里透红,耳垂上又别上了红艳的耳钉,龙生的思绪变得飘渺起来,也许,她身上正流淌着另一片红?
九
李小南要龙生将那本书归还给他,龙生估计他要把书借给别的同学。这另外一个将要和他们分享同一个秘密的人是谁呢?龙生禁不住问李小南,李小南说很多人想看,但不一定谁想看就能看,至于给谁看,李小南又是神秘的一笑,说你别管。上学时,龙生把书带来了,教室里闹腾腾的,他没敢立即把书还给李小南,而是藏在抽屉的深处。第一节是数学课,下课铃响了,数学老师讲得正起劲,延迟了五分钟下课。龙生朝李小南使眼色,意思叫他到教室外去,但李小南没会意,坐在位子上发呆。这样,第二节课上课铃声响了。龙生看见老慕容夹着课本向教室走来。
龙生对老慕容总是心有余悸,老慕容的独眼常像灯泡一样照着他,让他感到无从逃避。上老慕容的课,龙生双眼牢牢盯住黑板,不敢有半点杂念。但有一次上电流正负极的内容时,老慕容忍不住说这玩意就像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一样,有意思得很。这是一个容易发生联想的话题,龙生盯着黑板的眼睛出现了一片彩虹,的确,他心里想到了周倩云,嘴里又悄悄地弹跳着“海——蓝——蓝”三个字。老慕容真是火眼金睛,立即识破了龙生心中的念头,他往讲台上扔掉课本,厉声大叫:“严龙生,你又走神了,你说说,正负两极是怎么回事?你站起来!”龙生摇摇摆摆站起来,每回站起来老慕容都不准他再坐下,老慕容继续讲课,像忘记了龙生的存在。龙生在课桌底下的双腿,时而绷直,时而打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龙生的经验是,上物理课只要脑子不飘过周倩云的影子,老慕容就能和他相安无事,这时候,老慕容的独眼会像冬天的太阳。
第二节课,龙生又做到了心如止水,的确,老慕容的脸上荡漾着春天的光芒。他讲到了物体的惯性,他说物体在外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匀速运动,外力突然停止后,物体仍然会沿着此前的方向继续运动,这就是惯性,比如——这时,校长王小驴出现在教室门口,他招手把老慕容叫出去,对着他耳语。老慕容走回讲台,长脸变成冬天。他清了一下喉咙,说:“就在上课前,二班的一个同学搁在抽屉里的手表被人偷走了,现在每一个人都是怀疑对象,如果是我们班同学偷的,我给他一个机会,最好是坦白交待,现在就坦白交待。”老慕容的独眼目光如炬,在大家身上扫来扫去,教室里鸦雀无声。“好,都是好样的。为了证明各位的清白,现在,请大家到教室外面排队,我要搜查每个人的书包和课桌。到外面排队,不许携带任何东西出教室。请班干部监督。”龙生走到教室外,看到其他班的同学也在外面排队,大家都在议论,有这样的人吗,真有这样的小偷吗?起初,龙生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不幸的迫近,教室里老慕容挨个翻查同学们的课桌,快到他的课桌时,他突然想到那本书,顿时手脚冰凉。
自然没有搜查到手表,但老慕容的脸越拉越长,挂满了凌冰。他又咳嗽了一声,才说道:“通过检查,证明同学们都是清白的,但是,咕——咕——但是,也发现了严重的问题,比偷窃更严重更见不得人的问题。咕——”大家知道,老慕容身体好得很,从不感冒,但他喜欢咳嗽,尤其喜欢在课堂上咳嗽,一咳嗽他就感到威严无比,雷霆万钧。说起来,他的咳嗽很有渊源,校长王小驴就喜欢咳嗽,他的咳嗽十分独特,像驴叫,他只咳嗽一声,“哼——”,像一只大兽对小兽们发出的警告,于是同学们便噤若寒蝉。老慕容受到启发,创造了自己的咳嗽方法。
“大家看这是什么书?”老慕容向同学们展示了那本红色封面的书,他擎书的手臂还摇晃了几下,那书页散开,将要露出里面繁花异草的影子。“这是你们能看的书吗?只有思想极其肮脏、极其下流的人,才看这样的书。总场派出所前不久不是抓到了一个流氓吗,这个流氓经常到女厕偷看,我要说,看这种书的人比那个流氓还要可耻!咕——”
老慕容将书砸在讲台上,“咕——说,这书是谁的?”他将目光射向教室的屋梁,仿佛那可耻的人正藏身在屋顶上。“谁的?”
“谁的?要我点名吗?”老慕容的声音突然低下来,而且变得温和。“我知道是谁的,我希望他能自己承认。”
教室里既冰冷刺骨,又暗暗飘荡着期待的春风。龙生一时还不明白老师在说什么,起码老师的话暂时与他无关,他抬手掩住那只疣,这个家伙昨天差点又被揪掉,龙生有点怕痛,才没有动它,这会儿,它湿润,还传递出一片米粒般的温暖。
“严龙生,站起来。”恍惚中,他听到老慕容点他的名。他站起,抬头,与老慕容的独眼相遇,老慕容像俯冲的鹞鹰,目光中浸透了凄厉的风声。
但他的长脸刻出了笑容,他说:“严龙生,说说刚才物理课上的什么内容?”
龙生犹豫了一下,说:“物体的惯性。”
“没错。你的记性真好。那么,你不会说,这本《新婚必读》不是你的吧?”
龙生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所有的同学的脸都转向了他。
“是你的?”
“是。”
“哪来的?”
龙生沉默。
“再问一遍,哪来的?”
“捡的。”
“捡的?你运气好啊,捡的,为什么我捡不到,大家都捡不到,唯独你捡得到?”
龙生只能沉默。
“你肯定看过,别说没看过。”老慕容和蔼地说。
“看过。”
同学们的脸像一堵墙,围住了他。在密不透风的阵势中,龙生还是挣扎地抬起头,劈开一条缝隙,朝周倩云看去。周倩云也正望着他,但她瞬息逃开了。
“你记性好,和大家讲讲,你看到了什么?”老慕容笑容可掬,始终像鹞鹰在盘旋。
龙生再次选择沉默。他摸疣,疣也是沉默的。
老慕容终于爆发了:“你敢讲吗,敢说你到女厕所去偷看过了吗,你比那个流氓更下流更可耻!同学们,这事非常严重,关系到思想品质问题,严龙生的道德品质十分败坏,我要向王小驴校长汇报,一定作出严肃处理。”
龙生的头垂得更低,他的颈项与胸脯成了一个标准的直角。
按照惯例,王小驴校长要找龙生谈话,还要在全校大会上公开和批评他的劣迹。但过了一个星期,王小驴校长也没来找他。这不是王小驴校长的作风。
李小南说:“这奇怪啊,是不是要开除你或者干脆放过你?”
龙生说:“开除也罢,既往不咎也罢,我的脸已丢到家了,无所谓。就像这样,”他搭在下巴上的手,食指和拇指瞬间挤拢,揪下那只无辜的疣,一举荡平下巴,“这个东西,我已把他摘除了好几次,每次除掉它,它都马上长出来,其实,有它没它,都一样。”龙生下巴上很快结了一个血珠,到了绿豆般大小,便滴落下来。第二个血珠还没结成,龙生用手擦了一下下巴,血迹很夸张地铺到他的脸颊上。
“别往心里去,”李小南安慰龙生,“要说流氓的话,大家个个都是流氓,因为好多人都想看。”
“还有谁看过?”
李小南望着龙生,说:“有很多人想看。”
十
放寒假了,二十多天的假期,对于龙生是刑期。他渴望回到教室,又惧怕进教室。过了元宵,开学的那一天,他第一个到教室,打开一本书,看了几页,同学们才陆续到来。但周倩云的位子是空的。又过了两天,周倩云还没有来。龙生忽然想起周倩云唱的另一首歌,“我站在龟蛇山上,两眼平视前方”,他也喜欢这首歌,这是当初作为武汉知青的她的父母唱过的歌,被她传唱后,显得宁静而动人。因此,龙生推测,周倩云一定是回武汉过年还没有回到农场。
龙生继续和那只疣斗争。李小南说过,周倩云说他很可笑,当然指的就是他下巴上的疣。
龙生曾经仔细研究过这疣,也曾采取种种手段对付它,像手揪、指掐、刀切等等,他甚至采用了村里一个年长的女人传授的方法,用一根长头发,从根部勒住疣,断绝营养供应,使疣饥饿或者窒息而亡,但每回,这疣都会无声无息生长出来,傲然而立。最近,龙生又创造了一个新方法,取一粒文火,灼烤这只疣,直接把它烤熟,炭化,然后轻轻抹掉它。它确实被抹干净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然而,仅仅几天,龙生的下巴又显不平,在一天清晨,它,又回来了。龙生无奈,只好轻轻地抚慰它。
令龙生无奈的还有,他指望再看到周倩云,但她再没有在教室出现。这种渴望时时涌起,像水里的葫芦,按下去,又冒出来。“没有椰林缀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这句歌词总是悄悄地从他的舌面滑过,在他的双唇间弹跳。他有一个隐秘而巨大的奢望,就是能再听一听周倩云唱这首歌。那时,王洁实和谢莉斯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已常在校园里播放,每次听这首歌,龙生都想哭,眼眶涌满液体,头脑一片空白,身体像遭无数人践踏。
教室的东边开满了油菜花,香气扑鼻,随着夕阳将落,暮霭升起,油菜花的香气更加浓郁。这是晚自习前一段美好的时光,龙生和李小南一起在小道上漫步,他第一次告诉李小南他要退学。
李小南说,你知道为什么王小驴校长会放过你吗?因为老慕容根本没有把那本书上交给王小驴,他自己把那本书截留了。他自己当然也会看那本书,最主要的是他想把那本书送给别人看。
李小南说,你知道老慕容要把书送给谁看吗?告诉你,别吃惊,他送给了周倩云。本来我让你还给我,就是想送给周倩云看,没料到竟会出现意外。老慕容经常给周倩云补习物理,而且也补数学,他保证帮助周倩云考上大学。有一天,周倩云去补习,老慕容就把那本书给了周倩云。老慕容对周倩云说,这也是知识,只要是知识,我们就应该学习。周倩云跑来和我说,慕容老师为什么要这样?我很生气,我说慕容老师为什么不能这样!周倩云要我承诺不把和我说过的话告诉任何人。她还同我约会,也照样到老慕容那儿去补习。
李小南说,现在,周倩云离开了农场,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了,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一切。
龙生心里涌上一股邪劲,他有许多问题要问李小南,和周倩云经常幽会吗?幽会时干些什么?她会让他干什么?见过她的每月一次的流血?他的手和眼睛到达过她身上的哪些地方?
但龙生只是极其简单地问:“她为什么离开农场?”
李小南说:“我也不知道。”
花香浮动的校园,暮霭重重,又有人唱歌,这歌声像血液,许多年一直在龙生心上流淌。
严敬,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作家协会理事,1964年12月生于湖北省国营龙感湖农场,现居海口。2005年获海南青年文学奖,获2010—2011年、2012—2013年、2014—2015年三届海南文学双年奖。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五月初夏的晚风》《宛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