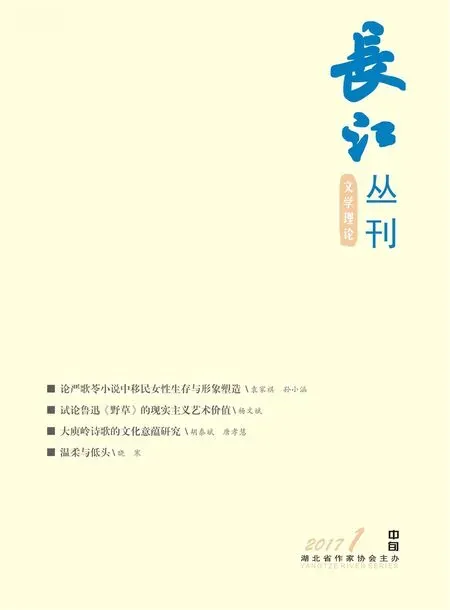崇高美的审美形态位置及与时代的紊和性
——郭沫若新诗中的崇高美探究
2017-11-25刘娟
刘 娟
崇高美的审美形态位置及与时代的紊和性
——郭沫若新诗中的崇高美探究
刘 娟
从古及今、从西方到中国的美学家们在对崇高美的阐释中,多从纵向注意了对崇高美产生根源的求溯,而忽视了崇高在横向审美形态中的位置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往往暗合着某种相同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关系。郭沫若的《女神》所体现出来的崇高美在审美形态上承上启下的位置是与五四这个恢宏的时代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相紊和的。以《女神》为范导进行崇高美地位与历史形态之间关系的探究,不但在美学史上有建立于审美形态上的历时性与具时性时空观的探究意义,对于历史上对郭沫若新诗《女神》的美学价值偏见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纠正作用的。
崇高美 五四运动 郭沫若 五四新诗
任何社会的文艺思潮和审美形态都应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和评判。“崇高”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形态,自古及今都不乏对其阐释的哲学家。古希腊的朗吉努斯认为,崇高最重要的精神来源是奇特的思想和激情,语言的美与伟大思想的结合;英国理论家博克将生理学引入对崇高的阐释中:“崇高者的情感基于自保的冲动,基于畏惧,亦即一种痛苦,这种痛苦由于并不一直达到对肉体各部分的现实伤害,所以就引起一些激动,当这些激动使更细的或者更粗的血管清除了危险的和麻烦的堵塞时,就能够激起适宜的感觉,尽管不是愉快,而是一种惬意的颤栗,是某种掺有惊恐的平静。”[1]康德将崇高划分为“数学的崇高者”与“力学的崇高者”,“崇高不是包含在任何自然事物中,而是包含在我们的心灵中,只要我们意识到对我们里面的自然,并由此对我们外面的自然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凡事在我们心中激起这种情感的东西,就叫作崇高的。”[2]“每一种具有英勇性质的激情,都在审美上是崇高的。”[3]前苏联的鲍列夫将崇高定义为“宇宙的无限大和永恒性,自然和人巨大的内在力量,在征服自然中,在使其人化中,展现出的无限远景。”[4]在对崇高的阐释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向度是由内而外、由主观朝向客观的态势。从阐释向度的转变过程中,哲学家逐渐将视野从自我投向宇宙,重视现象界对于审美意识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国内生态美学的代表陈望衡教授将审美形态分为:美、丑、崇高、悲剧、喜剧五种形态;陈炎教授则以“和谐”为标尺,将审美类型划分为:优美、壮美、滑稽、崇高、荒诞、丑陋。在两种划分中,“崇高”均居于五大审美形态(类型)之中间环节,不难发现,审美形态与其所处的时代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因此——与“崇高美”对应的时代在历史发展中也往往处于承前启后的关节点,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
一、客观事物中原生的崇高感与历史形态中蕴蓄的崇高感
作为崇高感产生的自然力学的源头,险峻高耸的山崖、无边的被激怒的海洋、高悬的瀑布等诸如此类的自然景观,因为我们与之阻抗的能力与它们的威力相比成为无足轻重的小事而被视为崇高的——原因在于“它们把灵魂的力量提高到其日常的中庸之上,并让我们心中的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阻抗能力显露出来,这种能力使我们鼓起勇气,能够与自然表面上的万能相较量。”[5]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首先体现在面对几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封建陈旧意识形态之顽疾时所展现出来的劲健的义无反顾的反抗精神和革新力量上。这既体现在五四先驱与学衡派的持久论战中,也体现于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胜利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捍卫共和,与当时的执政党段祺瑞政府相一致,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因此作为权力关系再现形态的新文化运动得以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五四先驱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主张全盘西化,采用共和制,力图用先进的西方文化进行思想启蒙,从而拯救国民,实现国家的富强。文化革新均是对已经废除科举制的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大洗礼,当时的思想真空状态也允许知识分子建立一种个体与现实环境之间的想象性关系,让人们在四顾茫然的历史文化断崖上有所依。五四新诗作为崭新的文学形态,摆脱了几千年来格律诗、古体诗对诗歌的限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新文学的先锋呐喊前行,具有先天的革命性品格,为现代诗的发声争夺了话语权。创造社的郭沫若在新诗上的创作尤其体现出与其时代相吻合的崇高美,现以其代表作《女神》分析之。
二、郭沫若《女神》中的崇高美阐释
《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有独创性、影响很大的一部诗集,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这部诗集,充满了大胆的反抗精神和对于祖国前途新生的渴望;作者以火一般的热情,唱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洪亮歌声,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战斗精神和英勇姿态,表现了企图创造“未来”的信心与力量。”[6]诗人以独立的个体与整个黑暗的旧时代进行反抗时所展现出来的英勇性质的激情,正是康德笔的崇高美。《凤凰涅槃》既是对被打破的旧世界的哀歌,又是在澎湃的悲壮所激越起的崇高美里对新世界的一曲赞歌!全诗从《序曲》凤凰集香木准备自焚写起,为全诗升腾起一股耶稣受难般的神圣悲壮之情。在《凤歌》和《凰歌》中,以屈原天问似的“问天”、“问地”、“问海”、“问宇宙”将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以及“前不见灯台,后不见海岸”的陈子昂似的源自生命本源的孤独意识和困顿处境淋漓尽现。最终在《凤凰更生歌》中,诗人反复吟唱“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喻示着只有用革命打破旧世界,才能换来新鲜、芬芳的你和我,才能实现自由和雄浑,达到“悠久”的永恒之美。《凤凰涅槃》以狂飙突进式的气势、澎湃的激情和近乎粗粝的浅近的语言展现出与中国古诗被冠以的含蓄纤穠、绮丽典雅美学风格截然不同的“雄浑悲壮”的新诗品格,让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颤栗!这种由于外在社会变革的阻滞所在诗歌中表现出的惊恐的颤栗,便是崇高感——而这一审美品格的形成正是投射于“五四”这个波澜壮阔的对中国新文学起变革作用的特殊时代之上的。正如胡兰成所言:“五四时代是中华民国要发生无数大事之前,酿花天气风风雨雨的豪华。”[7]崇高感成为凤凰由尘世通往永生的桥梁——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是促成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天狗》用“天狗”作比,以近乎疯狂的一咏三叹的反复的修辞手法、气吞宇宙的豪迈气概将五四时期呼唤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时代精神予以展示;《炉中煤》以“煤”自比,以“炉火”暗喻五四这个天风海雨的伟大时代,抒发了个人急切地要实现个人价值,改变陈腐落后的旧世界的满腔豪情;《晨安》则将时代赋予的澎湃激情抒发到了极致:全诗三十八句诗行中,有二十七句用了相同的咏叹句。《地球,我的母亲!》以“海洋”为意象起篇(以及在多首诗中反复出现的“海洋”意象,不能不说这绝非偶合,而是与“崇高”感所源起的自然物象相紊和的),赞颂田地里的农人、炭坑里的工人、植物、动物,分别赋予他们神圣、高尚、自由、新鲜的品质,将五四时期的平等、民主意识渗透到诗歌的每一处角落,最后决定在劳动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自我的价值……
郭沫若的《女神》成为五四时期新诗的优秀代表和崇高美的典范,原因有四:其一,诗集里的新诗意象多以“大海、太阳、宇宙”贯穿于诗文字里行间,这些客观物象本身就给人一种气势上的压迫感,这种气势越宏大诗歌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崇高美就越强烈;其二,诗人关注的以及诗文抒发的都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核心相印的“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等诸问题,诗歌的主题与时代精神实现了高度契合,这与《尝试集》的主题大多源出生活琐碎大异其趣,亦是《女神》形成崇高美的关键所在;其三,语言平易而不过于浅白,求得与白话文写文章的“文垅”,避免失去了诗歌之韵味;最后,诗人在诗文中流淌出的“真”是足以动人的根本,也正是这种“真”激发起了崇高美。诚然,五四时期也出现了与崇高美并行的美学形态: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和闻一多为代表的“象征派”新诗。“新月派”以“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为逻辑起点的对优美的追求和“象征派”对丑怪的描摹所呈现出的悲剧形态都丰富了五四新诗的领域,但由于郭沫若的新诗所体现出的“崇高美”追求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跃动,始终占据着新诗的主流并对五四以后的诗歌创作的美学形态起着引领作用,继文革失去文学本身的价值追求而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后,在八十年代重新焕发出活力,形成至今影响深远的“朦胧诗派”。
三、崇高美是一种源自生命本真原始体验
郭沫若的《女神》的崇高美体现与诗人对作品审慎的甄别挑选不无关系。在这样的 挑选过程中 , 我们能够感 受到诗人对 于自己的诗歌理想的营造与摸索—— “以宇宙全体为对象, 以透视万 事万物底核心为天职”的郭沫若努力走出一己的私情与狭隘 的思维, 将最充实最开阔的景象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种景象就是对崇高美的追求,这也便是他与同时代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在诗学境界上大异其趣的原因之一。郭沫若在新诗美学形态上开创出的崇高美新诗境也突破了以往在诗歌鉴赏中囿于遣词造句、修辞的弊端。
正是这样一个郭沫若, 才最终以他的富有创造力的 《女神》让闻一多击节赞叹:“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 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 最要紧的是他 的精神完全是 时代的精神 —— 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 。”创造社不乏浪漫主义的诗作,同一部《女神》郭沫若第三辑的诗歌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浪漫主义诗风,如《雷锋塔下》对锄地老农外貌的过度摹写所展示出来的对个体生命的热爱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 我的爹!’/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但这并不妨碍整部诗集崇高美的展现,反而为这种崇高在诗行的延伸中积蓄了更加劲健的力量,使之充满向时间纵深处伸展的无限张力。这种延伸的张力一直贯穿到四十年代《棠棣之花》的创作中。由于这种崇高美是原发性的生命本真的原始喷涌,它紊和于人类本真的生命体验,因此同那种与意识形态的刻意贴合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便可以解释为何五四新诗的美学价值远远高于文革诗歌的美学价值了。自《女神》起,新诗的境界大开,展现出与五四精神在中国文化精神发展中重要引领作用高度一致的在诗歌发展方向上的重要坐标作用。
[1][德]康德,李秋零译注.判断力批判(第一 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103.
[2][德]康德,李秋零译注.判断力批判(第一 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91.
[3][德]康德李秋零译注.判断力批判(第 一 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99.
[4][苏]鲍列夫,乔修业,常谢枫译.美学(第 一 版)[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2):86.
[5][德]康德,李秋零译注.判断力批判(第 一 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88.
[6]郭沫若.女神(第一版《出版说明》)[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4月,胡兰成〈山河岁月〉.
[7][美]克林斯.布鲁克斯,郭艺瑶等译.精致的瓮[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22.
刘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美学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