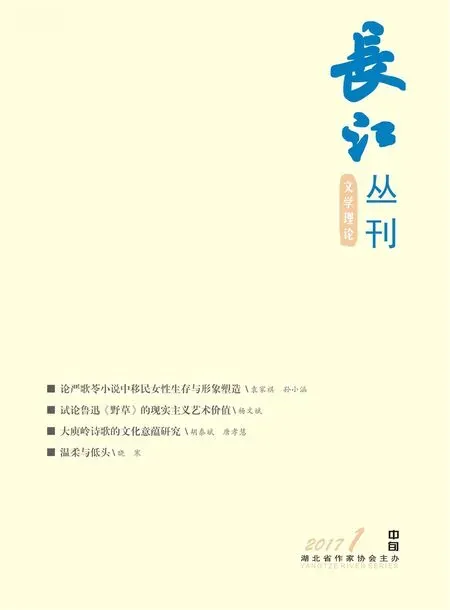论严歌苓小说中移民女性生存与形象塑造
2017-11-25袁家祺孙小涵
袁家祺 孙小涵
论严歌苓小说中移民女性生存与形象塑造
袁家祺 孙小涵
严歌苓作为出生于中国,拥有中美两国生活经历的华语作家,是当下最为著名的移民文学写作者之一。其写作生涯创作多部女性移民题材小说,以移民女性的生存现实、形象转变构造出一个独特的女性世界,影射跨文化交流的方式与实质。在此之中移民女性艰难顽强求生、受制度与文化的排挤、与现代城市疏离陌生,即便如此,弱者凭借无私的、包容一切的爱联合社会边缘人,依然能够感化、战胜强者,获得心灵自由,传达出奇妙的古老东方母性魅力。
严歌苓 女权 母性 文化异同
随着女性运动开展,文学文本中的女性角色数量渐增,相比男作家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女性观,女性作者因在社会生活中的切身体会,其笔下展现出的女性形象更为立体、全面,小说中创设的人物命运更是现当代女性社会遭遇与社会地位的现实体现。严歌苓从自身中美两国的生活经历中,体会女性的生存现状、归纳移民女性形象异同点,展现“女性文学从反抗述说过渡到性别书写的过程”和“异文化语境对女性书写的影响”①,以女性话语体系的构建及隐喻的文化差异入手带给读者广泛的思考。
一、移民女性在西方社会的生存写照
严歌苓擅写女性,从早年部队题材作品《雌性的草地》,到新近出版的《床畔》,小说中主人公大多为女性,而作者的旅美经历又造就其移民作品书写上的独树一帜。当笔者将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看,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女性,背负着“东方”、“弱者”等标签,个人在异域背景下的人物命运与生活轨迹,折射出整个东西方文化认知的差异。
《波希米亚楼》是严歌苓关于自身移民经历的散文,“波希米亚人”这个词特指那些希望过着非传统生活风格的艺术家、作家与任何对传统不保持幻想的人。在这个概念中,笔者试图对严歌苓移民题材小说中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包括《扶桑》、《栗色头发》、《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少女小渔》等,女主角均带有“波希米亚人”的特征。中国女性移民至美国后,不仅受到东方与西方这一固有矛盾带来的生活习俗、语言沟通等方面的冲击,更有身为女性天生背负的父权、男权压迫。来自东方的移民女性,在异域社会挣扎求生,如“波希米亚人”般拥有原种族的特质,却在西方主流社会中遭受到多重维度的放逐,勉强在社会底层维生。
对于移民女性自我处境的深刻认识,反映在了严歌苓的多部小说之中。《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伊娃在窘困的生活中不得已选择替同性恋男子亚当孕育后代,出租子宫换取移民后的生活资本。而在《少女小渔》中,这样的交换体现得更为明显:移民女性想在城市中获得赖以生存的金钱与社会资源,不得不嫁给当地男子。遗憾的是,摆脱了原来压抑困厄的生活空间,以放弃自由权利换来的主流阶级生活,实质上却不属于自己,仍易受到原有阶级与种族思维方式的排斥。
移民女性在新的环境中遭受的不仅是父权体制、西方文化的排挤,更有后现代都市社会带来的困扰。《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女主角,只身一人移民美国,后与美国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相爱,因此受到了国家安全局雇员的侦查。对比严歌苓的自身经历,小说亦有着自传的色彩,然而纠缠着女主角的并不是审讯或羁押,却是不定时的电话调查:国家安全局的理查·福茨如幽灵一般隐秘,通过有线电话“控制”着弱势的新移民。密密麻麻的电话线路,成为了束缚女主角的网络,“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打开台灯,看到小闹钟显示器上的数字——7:00,显然是一个预先计划要打电话的人。我赤脚跳下床,一把抓起话筒,怕它继续响下去把牧师夫妇吵醒。”②本为现代科技文明成果的有线电话,在作者小说中被刻画成了新移民生活的侵略者,颇有黑色幽默的色彩。
严歌苓确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一见钟情,步入婚姻的殿堂,但笔者无从得知面对电话追查的焦虑是切身感受还是人为构设的隐喻,相对于传统的文化反差、霸权政治压迫,在后现代的城市中如此异质化的沟通引发潜在控制,加剧了女主角在陌生环境里的恐怖与不安。
身处上述空间的移民女性在时空交错中苦苦寻找自己的位置,都市社会带给了她们太多超越以往认知的新鲜事物,这使得人作为一个个体,在城市生活经验中的主体性逐渐消失,移民女性无家可归、无所适从,只能做短暂停留,与抽象的城市权力话语形成矛盾统一:移民者真实地生活在城市之中,两者关系却又疏离陌生,于是仍然“无出路”。
二、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形象
西蒙娜·波伏娃著有对当今学界影响深远的《第二性》一书,两卷书从各个角度来分析现实中女性的处境及探讨女性独立可能的出路。波伏娃一方面强调经济的独立才可能使得女性在社会地位上有所提高,另一维度则指明,女性“温柔”、“乖巧”、“文静”等阴性化特质,并不是天生的,只是受到社会群体意识的影响,是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因此,性别平等的最终实现,更需要女性对发挥自身特质进行深刻思考。
纵观严歌苓作品中的移民女性,如扶桑、伊娃、阿绵等,处于被高压父权政治控制的状态之下,她们面临的是被男性随意操控的恐惧——性交、怀孕、生产、流产均受管控,无法遵循女性的本能。而从赴美初期的《少女小渔》,到小说《扶桑》出版,严歌苓创作出的女性形象均具有强烈的象征性。
作为较早关注女性与女性权益的一批作家,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不是激愤、刚烈的打破不平等权力关系,而是以东方女性所拥有的母性特质,在平权过程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小渔作为弱势的东方女性,展现出东方文化中的宽容与无私,借此小渔成功感化了代表男权和父权的江伟,亦将自身特性输出从而与房东意大利老头走向和谐,完成跨文化交际。《扶桑》一书中的少女扶桑,藏污纳垢、包容一切的东方古国“地母”形象体现的更为突出。小说中扶桑的身材、胸部被具体描摹出来,代表着东方原始的雌性,“阿妈从扶桑交上拔下一只鞋,托在掌心上从人跟前游走,说真正的三寸金莲是二寸八!”③女性身体中生理性的现象——月经、流产、怀孕,也多次被有意识的重点刻画,构成严歌苓小说中原始的女性群像。
作者想表达的,是东方女性以柔克刚的气质,扶桑遭到毒打、轮奸、转卖乃至生存的威胁,仍然活了下来。她始终“保持着微笑”,任人蹂躏毫不抵抗,虽弱小但顽强,这样一个卑顺的女性形象,以强大的生命力、无差别的爱与包容,吸引了异族的十二岁男孩克里斯。她与克里斯的爱情有着丰富的象征意蕴,克里斯爱上的是陌生的东方魅力,这与扶桑“弱者”形象有紧密的联系,扶桑虽弱,她拥有的是心灵与精神上的自由,接纳万物、悲天悯人的母性情怀是东方雌性特有的,在西方的异域文化之下,破土重生,感化一切。
三、移民女性与社会边缘人的友情
《梁书》列传四十八中记载,齐永元元年(公元499年),沙门慧深宣布在大汉国遥远的东方,茫茫大海中发现了一块陆地,其上遍布扶桑木,慧深遂决定以“扶桑”二字命名这块土地。严歌苓将小说中的东方名妓取名为“扶桑”,有意无意将如今妓女扶桑被定义被拍卖的现状与千余年前发现命名土地的传说对比,展示出作者呼应历史神话、在虚实切换中建构人物、重塑话语权的写作意图。
与慧深发现新大陆不同,现当代移民女性踏入异国的领土带有弱者向强者“朝圣”之心态,而西方则多有“欣赏”的目的。《无出路咖啡馆》中女主角立足未稳便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审问,特工福茨的调查充斥了窥探色彩,背后是东西方文化相遇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移民者居高临下的审视与控制。扶桑的形象在全新政治文化背景中作为东方女性与传统文化的象征,结识克里斯早已不是单纯的男女恋爱,代表了强大年轻的西方文明遇到成熟美丽却处于被控制环境下东方弱者的碰撞历程,陈思和教授曾说:“克里斯和大勇,这两个男人是扶桑的对照与视角,尤其是克里斯,他对扶桑充满善意的误解正表明了文化的沟通有多么困难。”④
弱势移民的社会地方普遍较低,不被主流阶层接纳理解,在这样的生存现状下,文化背景各异而同处边缘地位的民族自然结合在一起,共同面对强势西方文化的压力。《少女小渔》故事环境设定在意大利老头出租的公寓,其间小渔亲眼目睹老头与相好瑞塔的生活状况:“摊着一桌子碟子,一地纸牌,酒瓶,垃圾桶臭得瘟一样。”⑤作者以小渔之眼揭示出西方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形象,然而小渔何尝又不是如此呢?“粗拙,凶悍,平底鞋,一身短打,并且复杂的过盛的体臭涨人脑子。”⑥除去现实生活的窘迫,为了在美国立足,小渔不得不与意大利老头假结婚,凭借绿卡获得永久居留权同男友江伟合法在美国长期定居,属于移民史上的“曲线救国”。意大利老头虽有相好瑞塔扶持生活,靠的却是平日在街头巷尾卖艺求生,或与新移民假结婚挣钱,拥有美国居住资格的老头在政治经济地位上被分离出主流阶级,与小渔一起为生存艰难打拼。
《少女小渔》中小渔与意大利老头同为异域文化背景的移民经历使其建立超越年龄、种族的友谊,社会边缘人间的“同病相怜”是他们相互理解支持的基础,小渔交还老头被风吹散的钞票,老头给小渔以居住的方便和关怀。美国社会向来以开放包容自称,却不能给第三世界的移民提供一席立足之地,同为弱者的移民者,跨越种族与肤色,建立起联系共同应对强大西方文明的排他性显得不难理解。
严歌苓塑造出的女性形象,以东方地母魅力、女性特有气质,宽容父权社会主流阶级的压迫,感化同处社会边缘的异族群体,完成跨文化跨民族交际。个性勃发的东方移民女性,无声无息中彰显了女性生命的特质,严歌苓笔下女性群体构成的生存范式,对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可借鉴样本,也促使读者重新思考移民者生存与命运背后的东西方政治隔阂、文化差异。
注释
①肖薇. 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 ——海外华人女性写作比较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2002.
②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③严歌苓.扶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④陈思和.关于〈扶桑〉改编电影的一封信[J].文艺报,1998(5).
⑤严歌苓.少女小渔[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7).
⑥严歌苓.少女小渔[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7).
[1]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8.
[2]庄园.严歌苓访谈[J].华文文学, 2006(2).
[3]沈红芳.在苦难中升腾——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当代文坛,2008(9).
[4]林翠微.百年良妓的凄美绝唱——严歌苓《扶桑》女主人公形象的文化意蕴[J].华文文学,2004(6).
[5]陈思和.关于《扶桑》改编电影的一封信[J].文艺报,1998(5):14.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
本文系秦惠莙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项目编号:21315003。
袁家祺(1995-),男,汉族,江苏昆山人,本科,苏州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