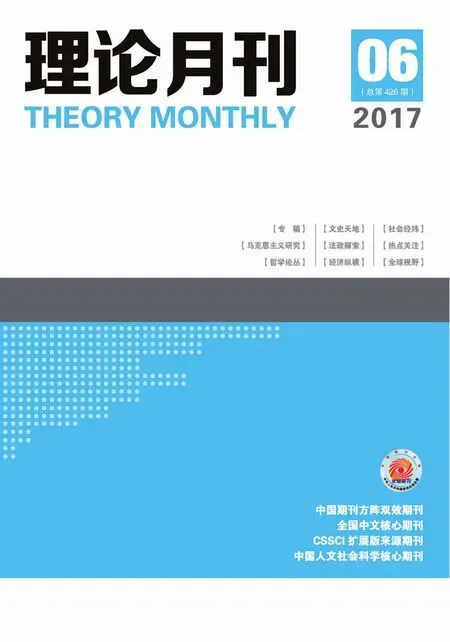美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
2017-11-23朱碧波
朱碧波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美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
朱碧波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在国家建构与成长的过程中,美国多民族社会始终存在多元民族带来的文化紧张、利益博弈和民族分层等问题。面对多民族社会内生的多重张力,美国在不同时期分别择取盎格鲁遵从理论、熔炉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积极推进族际政治整合,试图把各民族整合成一个巩固的国家共同体和国族共同体。纵观美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手法,存在民族界线模糊化、民族属性文化化、民族权利公民化、民族政策社会化等诸多特点。探讨和反思美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得失,对于当代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和民族事务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美国族际政治整合;民族政策;民族权利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民族构成多元和国家政治一体的基本特征。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的非重合性导致多民族国家内部无可避免地存在难以化解的多重张力。为了化解这种多重张力,多民族国家往往通过族际政治整合,不断模铸国家共同体的巩固和型构国族共同体的认同。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多种族、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各个移民群体在移居美国之时依然挟带着自我的民族认同、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这使得美国难免存在着移民群体与移民群体、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面对多元移民群体带来的族性多元和文化多样,美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极具美国特色的族际政治整合,为美利坚民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美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得失对于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事务治理不无镜鉴之意。
1 美国民族问题的流变与梳理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不同国家的民众向美国内聚式移民使得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简直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观[1]。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来自英伦三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成为北美大陆最早的殖民者。在随后的年代里,世界各地一些民众为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现代的政治制度和完善的福利体系所吸引,不断移民美国。其中,在1820-1860年间,美国发生该国历史学家称之为“伟大人类迁徙运动”的第一次移民高潮,大量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移民潮水一样涌入美国。而随着1965年移民法案的颁布,美国随之出现历史上第二次移民浪潮,入境人员主要来自拉丁美洲以及亚洲。这股移民潮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久、种族与族群之多以及低技能工人在其中所占比例之高,使得多元民族的相互调适与和谐共生成为美国族际政治整合必须直面的一个重大问题[2]。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外来移民前往美国的热度依然不见衰减,仅在2000-2006年,合法移民就高达702.73万人,与此同时,非法移民也与日俱增,其数量平均每年为20-30万之间[3]。
移民潮的持续不断使得美国成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美利坚民族也成为一个由许多民族复合而成的民族。然而,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却也使得美利坚民族的构成不免多元复杂而异质纷呈,也产生了各种民族歧视、隔离与纷争等问题。具体而言:
其一,文化异质与利益紧张问题。美国是一个通过移民构成的多元民族国家,各类移民在向美国流动的过程中,虽然他们按照既定程序要放弃对母国的忠城,宣誓效忠美国,但是他们即便在美国获得合法的公民身份之后,也无法摆脱母国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集体记忆和生活习俗。而多元民族身上的文化印记和民族特性使得他们与美国既有的民族存在很大差异,双方在价值理念、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之间理所当然地存在各种异质性,并诱发文化张力的产生。美国社会不绝如缕的反移民情绪、白人至上主义等等事实上都是美国既有民族面对不断汹涌的移民潮产生的文化排斥和文化傲慢。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针对移民群体产生的文化排斥更加凸显。一些民众甚至认为,正是因为大量移民人口的存在,才导致美国民众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受到威胁”[4]。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美国民众看来,当代不断汹涌的移民潮不但带来了文化张力的问题,而且还意味着美国各民族之间的利益碰撞与权利博弈:外来民族要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要求政府捍卫每个人都平等享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而美国本土民族又要求维护自己的既有权益,担心移民抢占就业机会和分享社会资源。一些白人更担心多元而异质的民族使得美利坚民族成为一种百纳衣式的民族,认为多元而异质的移民文化将解构美利坚民族的主流文化,影响美利坚民族的国家认同,因而发出“我们是谁”的疑问。
其二,种族歧视问题。种族歧视是美国民族问题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由于移民群体本身与生俱来的文化异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受到美国主流社会(所谓来自西北欧洲老移民)的歧视。美国主流社会经常性地给新移民群体以侮辱性称呼,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裔移民、东南欧移民、斯拉夫人在移民潮中占了很大比重,但在老移民、本土出身的人看来,这些新移民并不是“像盎格鲁-撒克逊那样的完全白人”,只不过是一种非黑非白的中间人,是一群“黑狗”“黑手党”和“天生的罪犯”[5]。至于早期移民的亚裔多从事洗衣店或者苦力一类的行业,一些新闻媒体也常常对其加以丑化。亚裔(尤其是华裔)往往被视为“危险的章鱼”“异教徒和滑头”,是“瞪着杏眼,梳着辫子”的老鼠,是“天生的小偷”[6]。一些联邦地方更是出台各种歧视性法律,如《排华法案》(1882)和以《凯布尔法》(1922)为代表的反异族通婚法。虽然随着时代发展,美国逐渐废除反异族通婚法,亚裔也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但美国文化中隐形的种族歧视却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种族形象定性和红线歧视问题依然时有所见,以致就业领域中少数民族仍然遭遇诸多歧视性待遇。
其三,民族分层的问题。民族分层是从社会分层转借过来的一个概念,主要研究的是“不同民族集团之间由于其结构性差异所引起的不平等”[7]问题。由于美国各移民群体之间、各移民群体与世居民族之间的教育背景、文化程度和发展机会并不相同,他们之间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民族分层和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在美国民族分层研究中,研究者常常从各民族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教育水平、就业状况、职业结构、收入结构等方面展开探讨。其基本的研究结论为:从美国各民族人口的产业结构来看,在历史上非洲黑人和墨西哥人成为美国农业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印第安人作为美国的土著居民主要在政府为他们选定的保留地内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亚洲人后裔、南美洲人则大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寻找就业机会;从教育程度来看,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大多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就读,而白人贫民孩子和黑人孩子则在条件相对较差的公立学校就读;从就业率来看,印第安人、黑人男性就业率较低,印第安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妇女就业率较低;此外,在职业和收入等方面,美国黑人总体上从事低工资职业,其平均收入与白人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8]。美国各民族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成为民族问题滋生的重要渊薮。不管是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推演来考量,还是从美国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的实践走向来审视,族际结构性不平等对各种移民群体的团结与和谐都会造成深层次妨害。
2 美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考释
面对各国移民向美国内聚式迁徙,美国民族构成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移民不断推动着“彩虹式底层阶级”的形成,导致美国民主制度下滋生着各种或隐或现的民族纷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面对美国多元民族问题的滋生,民族理论界相继产生了盎格鲁遵从、熔炉和文化多元等理论模式,深远地影响到美国的族际政治整合。
2.1 盎格鲁遵从理论
盎格鲁遵从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由于具有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背景的新教徒先人一步地移居北美殖民地,在文化自傲的心态之下,他们产生了要求非英裔移民学习英国的制度、语言和以英国文化作为导向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想法[9]。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达尔文进化理论传入美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盎格鲁遵从理论逐渐系统化,并成为当时美国族际政治整合的主要指导思想。盎格鲁遵从的理论假定主要为:在人类社会进化中,必然有一个优秀的民族在激烈的民族角逐中脱颖而出,这个民族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作为最为优秀的民族,是人类社会在优胜劣汰的进化历史中上天选定的,是“天定的民族”。由于盎格鲁-撒克逊群体的人口数量占据国家人口的多数,他们的文化又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东道主”国中的新移民及其母国的文化只能算作是亚民族和亚文化[10]。
盎格鲁遵从理论的基本主张为:在美国的移民群体中应该根据人种的不同而划分为优秀民族和次等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优势,决定了他们必然是美国的核心民族。其他民族必须完全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政治理想、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11]。换而言之,凡是美国的移民群体,不管来自何方,拥有何种文化背景和种族特性,都必须接受盎格鲁文化,并以此作为自己在美国安身立命的基本规范。盎格鲁遵从理论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也反映了他们试图以盎格鲁文化作为整个国家文化共识的努力。
盎格鲁遵从理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也曾经对美国的形成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美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正是以盎格鲁文化为核心,对其他各种民族文化和政治亚文化进行凝聚、整合和同化,才实现了以盎格鲁民族为主体的社会体系,才实现了国家的制度化和秩序化。不过,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化和各类移民群体的增长,盎格鲁遵从理论致命性漏洞逐渐凸显,其合法性也遭遇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质疑。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诟病和批判其内蕴的种族优越、强权理念和强制同化思想,并直接导致另一种相对温和的“大熔炉”民族理论的流传。
2.2 熔炉理论
熔炉理论是与盎格鲁遵从理论大相径庭的一种民族理论。盎格鲁遵从理论的核心在于主流政治文化对各种亚文化的强制性同化,而熔炉理论的核心在于各种亚文化与民族文化融而为一,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即美国文化。这种熔炉理论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美国作家克雷夫科尔早在《一个美国农场主的来信》(1782年)中就设想了作为一种新的“美国人”,他“丢弃了古老的偏见和方式,接受了所处新环境中的生活模式,包括新政府和新身份”,他是“所有民族的人融化为新的人种”[12]。克雷夫科尔在这里就已经萌生民族熔炉的思想,认为美国独特的政治文明和社会环境将会把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异族移民熔制成具有相同品质和共同理想的人。不过,真正使得民族熔炉理念广泛传播的还是1908年犹太移民作家赞格威尔的剧作《熔炉》在纽约百老汇的上演成功。赞格威尔在《熔炉》之中,借助主人公之口,形象而深刻地阐明民族熔炉理念的精髓:“美国是上帝的熔炉,在这个熔炉之中,所有欧洲的种族在这里融合和重构。……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或是英国人,犹太人或俄国人都将一同进入熔炉之中。上帝正在铸造美国人”。美国“正在净化着各种外来民族,他们在这里众志成诚,以建立理想的共和之国”[13]。《熔炉》的发表和上演受到了美国社会的热烈欢迎,熔炉理念自此不胫而走,不管是醉心国事的政界精英,还是久居美国的老移民,都真切地认为外来异族移民必须在美国熔炉中进行美利坚民族特性的煅造。
熔炉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祛除了盎格鲁遵从理论中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又具有“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所不具备的相对温和的品质,因此在美利坚民族的煅造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民族熔炉理论的驱动下,美国通过一体化的教育体系和政治文化的训导不断在外来异族移民群体的心目中种下盎格鲁-撒克逊人“关于公正、法律和秩序以及民众政府的观念”,同时唤醒他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利坚民族生活中“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的崇敬”[14]。不过,熔炉理论提出来之后也受到了很多批评。一些批评者认为,美国熔炉理论是将外来异族移民熔合成一个统一的无差别的同质性民族,本身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民族大熔炉是由国家占主流地位的文化群体建构的,占主流地位的文化群体决定着熔炉的文化内核和预期产品的生产程式。由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文化势差”的影响,各种民族文化不可能在美利坚民族精神的产出中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熔炉理论也依然逃脱不了强制同化的嫌疑。也正是由于“熔炉论”并未臻于完善,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移民群体对维持民族特质需求的觉醒,文化多元主义逐渐从后台走上前台,并成为一种影响日甚的民族理论。
2.3 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对熔炉理论的反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15年,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在《民主对熔炉》一文中开始发表系列文章批评熔炉论。他认为,那种带有同化主义色彩的“美国化”和“熔炉化”存在将非盎格鲁-撒克逊的欧洲移民看成是低等民族的嫌疑,认为他们不配享有同等的权利。这种做法违背了《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平等精神。真正的美国精神应该是“所有民族间的民主”,而不是某一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绝对统治[15]。1924年,霍勒斯·卡伦在《美国的文化与民主》一书中正式提出“文化多元论”,认为不断扩大的移民群体溶解了早先的美利坚民族,使美国变成了一个多民族的联邦、一个多民族的民主国家[16]。多元文化主义提出来之后,在美国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由于20世纪上半期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能够挑战熔炉论在美国族际政治整合中的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女权主义、黑人政治、后现代主义思潮、权力话语批判的兴起,“弱势”“少数”“身份”“特殊性”等话语逐渐成为解构普遍主义模式中同一性支配下的霸权话语和主流体制的“另类之声”[17]。日益庞大的移民群体使得多元文化主义具备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多元文化主义对弱势、少数、身份和特殊性的关注,迎合了各移民群体在长期一致性社会压抑下产生的自我关切和寻根渴望,并为各种亚文化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因此,多元文化理论迅速成为学术界和大众媒介解释美国社会架构和文化态势的经典理论,并对美国历史著作的写作产生了近乎革命性的影响[18]。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美国族际政治整合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它与盎格鲁遵从理论和熔炉论存在迥然不同的理论面向。盎格鲁遵从理论和熔炉论是一种明确的“合众为一”的思路走向,更加强调各个异族移民同化或熔铸为一个同质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或美利坚民族,而多元文化主义的思路走向更近于一种“和众为一”,强调各民族之间包容差异、宽容异质、和谐共处,最终在相互尊重和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多元并存而又混为一体的美利坚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差异构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起点。在多元文化主义看来,各民族之间存在与生俱来而又难以磨灭的差异,“人们可以在较大或较小程度上改变他们的衣服,他们的政治思想,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处世哲学,但他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祖父”[19],将人们连接成一个民族群体的“祖先和家庭纽带”[20]是一种命运,而不是一种选择。各民族之间命定的差异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在族际政治整合之中必须尊重差异,尊重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旨趣的不同。那种无视民族差异而试图将各个民族特性予以消磨的同化主义,不但耗资巨大而且注定徒劳无功。在多元文化主义看来,民族差异构成人类昌盛的必要条件,它不仅向个人提供各种选择权,使他们的自主权更有意义”[21],而且这种民族多元和道德差异也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和丰富多姿。
多元文化主义提出来之后,激赏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在多元文化主义回应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社群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保守的多元文化主义等各种理论分支。这些理论分支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是他们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诉求还是存在最为基本的共识。在多元文化主义看来,多元文化是当今多民族国家一个普遍而不可逆转的客观现实,多元文化之间存在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只是不同,不是优劣。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这就决定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必须倡导文化平等、尊重文化差异和包容民族异质。当然,多元文化主义却并不满足于此,它要求给予少数群体一种“差异化权利”,即不仅承认少数群体的身份与多数文化具有相同的意义和地位,而且还要根据差异原则和少数群体的特点进行差异化授权,“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同时也能发展和享用自己的文化传统”[22]。不过,差异化授权是局限于文化领域、经济领域抑或是政治领域,多元文化主义内部却存在很大的分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强调“文化差异”“尊重差异”,甚至“维护差异”,但他们并不反对整个国家建构一种基本的文化共识,“多元文化主义在承认一种政治生活中永远都会存在着若干文化群体的同时,也要求确立一种共同的文化……所有文化群体将不得不接受一种共同体的政治语言和公约,因为它们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们参与资源竞争,参与保护集体和个体的政治利益”[23]。
3 美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手法与特点
在美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历史上,虽然出现了盎格鲁遵从、熔炉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但这些价值旨趣迥异的民族理论却有着殊途同归的目标导向,即完成美利坚民族的建构与巩固。这种清晰而一以贯之的目标导向使得美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虽然一直在发生变迁,但却并没有发生历史性断裂。而作为族际政治整合外在表征的整合手法从总体上也存在诸多一脉相承的做法。概而论之,美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手法与特点主要有:
其一,民族界线模糊化。美国是一个移民众多而民族问题十分繁复的多民族国家,但是美国与前苏联在族际政治整合上却存在本质性区别。前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是通过民族识别,将少数民族一一识别出来,然后再推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这是一种先分后合的思想。而美国族际政治整合不管是盎格鲁遵从理论和熔炉论的合众为一,抑或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和众为一,其重点都在于各民族的“求同”和“合一”。美国族际政治整合对民族之间的界线并不作十分严格的辨识和区分,只是简单地将国内各民族划分为5大类,白人、非洲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亚洲裔美国人、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岛民。其划分标准要么是依据种族血统,如白人,要么是依据某个大陆板块或海洋板块,比如非洲、美洲、亚洲或太平洋等[24]。总之,美国在国内民族(种族)的划分和认定上大致采取的是一种宜粗不宜细的模糊化处理方式。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更进一步允许民众选择一个以上的种族归属,更加明确地凸显美国将民族边界模糊化和刺激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努力。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其内在价值在于,一方面它使得美国各民族之间并不存在十分明显的、泾渭分明的民族界线,便利了各民族的跨界交流和相互涵化;另一方面民族界线模糊化客观上也弱化了民族主义的动员能力,而赋予民众以多重的种族归属,则进一步刺激民众对多元种族身份的认同,避免民众认同过于聚焦于单一的种族身份。这无形中扫清了各民族对美利坚民族认同的障碍。
其二,民族属性文化化。在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之中,将国内各民族看作是文化群体还是政治实体,直接决定着族际政治整合的根本走向。美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推进,向来是将少数民族的属性界定为文化群体而不是政治实体。美国对于少数民族属性的文化定位直接导致政府将民族群体与政治实体相剥离、将民族群体与居住区域相剥离。美国政府担心,如果将少数民族看作是一个民族(nation)实体并赋予他们以“自治权”的话,不但会刺激少数民族关于国家和主权的想象,而且客观上也难免会刺激其他移民群体提起类似诉求[25],这就将导致各个民族都追求自治的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与此同时,美国族际政治整合也十分注重民族群体与固有疆域的剥离。美国政府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担心,当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时,可能就会出现暴力、自治或分离运动”。更何况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民族群体与既定疆域之间的强关联往往会导致一些少数民族将自己所处的国家行政区域视为本民族古已有之的民族领地。这种民族领地意识的形成显然又是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刺激因素。因此,从美国宪法到一般性的地方政策,都反对将民族聚落模式地域化,美国不允许各民族集团在美国的土地上独居一地以实行民族自治。联邦单位的权力不是以民族为单位,而是以地域(行政区划)为单位的;联邦单位的自治权也不是建立在民族聚居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之上的[26]。这就从根本上拒绝了美国由区域性联合变成民族性联合的可能。
其三,民族权利公民化。在美国的文化体系中,自我是一切价值的轴心,也是衡量价值的根本尺度。美国文化渊远流长的个人本位使得国家十分重视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独立宣言》中的政治昭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深刻地反映出美国对公民权利的极力推崇。美国对公民权利的推崇也使得他们在族际政治整合之中形成了重视公民个人权利,而不太看重民族集体权利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美国信条构想的是一个由自己选择并对自己负责的个人组成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以不可侵犯的民族社团为基础的国家。宪法保障的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群体的权利。”[27]随着当代人权理论中少数民族集体人权的凸显,美国少数民族对集体权利的诉求也开始高涨,但美国在看待少数民族集体权利之时,依然从公民角度来看待民族集体权利保障,依然习惯于将各少数民族民众都视为无差别的国家公民,依然致力于将民族权利保障置于公民权利框架之下,试图通过公民保障来实现民族权利保障,通过公民权利平等来实现民族权利平等。因此,即便在少数民族集体权利诉求日益走高之时,美国通常也拒绝单纯地以“民族”为标准进行差异化授权,而以“少数人”(包括妇女、身障者、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为标准赋予“差异化公民权”。这在本质上依然是力图避免反复刺激民族意识而致力于型构各民族的公民意识和保障各民族都能享有事实上平等的公民权利。
其四,民族政策社会化。各民族结构性不平等是美国族际政治整合必须直面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发展起点和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单纯地从权利平等的角度对各民族公民权利进行无差别保障事实上并不能改变少数民族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边缘化困境。这也就是说各民族发展起点的不平等,并不能保障发展机会的均等,更无法保障民族发展结果的正义。正因如此,美国在族际政治整合中也十分重视通过一些特别的政策和行动对少数民族进行补偿,但美国族际政治整合中追求的补偿性正义和实质性正义,并不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扶助,而是以“弱势群体”为标准进行的特殊性照顾。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肯定性行动是针对那些在历史上或实际生活中因为各种因素而被剥夺发展机会、实际上是完全有能力的人却没有得到发展机会。肯定性行动扶助的对象包括少数民族而又不局限于少数民族,而是囊括了性别差异和阶层差别等,注重保障最少受惠群体的最大利益。这就使民族扶助政策更近于一种社会扶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不谈民族帮扶而推进民族帮扶之目的。
参看文献:
[1]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M].沈宗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1.
[2]郝令昕.美国的财富分层研究:种族、移民与财富[M].谢桂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
[3]欧阳贞诚.美国当代外来移民的成因及特征分析[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1).
[4]DAVID A.HARRIS.Brief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J].2001(12).
[5]姬虹.美国新移民族研究(1965年至今)[M].北京:世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51.
[6]BEVERLY ANN DEEPE KEEVER,CAROLYN MARTINDALE&MARY ANN WESTON,eds. U.S.News Coverage of Racial Minorities:A Sourcebook,1934-1996[M].NewYork:Greenwood Press,1997:192-195.
[7]马戎.美国的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1997(1).
[8]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34-253.
[9][25]威尔·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M].马莉,张昌耀,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88-89,97.
[10][11][18]钱皓.美国民族理论考释[J].世界民族,2003(2).
[12]MILTON M.GORD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and National Origin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1964:116.
[13]ISRAEL ZANGWILL.The Melting Pot:Drama in Four Acts[M].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 1994:33,185.
[14]MACEDO.S.Diversity and Distrust:Civic Education in a Multicultural Socity[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91.
[15]BRIMELOW,PETER.“Time to Rethink Immigration?”[J].National Review,June 22,1992:34.
[16][22]常士訚.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
[17]王敏.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内在逻辑、论争与回应[J].民族研究,2011(1).
[19]HORACE M.KALLEN.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pot:A Study of American Nationality[J]. The Nation,Feb25,1915.
[20]HORACE M.KALLEN.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Studies in the Groups Psychology of the American People[M].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198.
[21]迈克尔·沃尔泽.论宽容[M].袁建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
[23]J.Raz.Multiculturalism:A Liberal Perspective[J]. Dissent,1994(41).
[24]任一鸣.美国和前苏联民族政策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观察,2013(2).
[26]杨恕,李捷.当代美国民族政策述评[J].世界民族, 2008(1).
[27]Alain.G.Gagnon,James Tully.Multinational Democrac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9.
责任编辑 朱文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6.031
D73.62(712)
A
1004-0544(2017)06-0171-0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Z010)。
朱碧波(1981-),男,湖北潜江人,法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