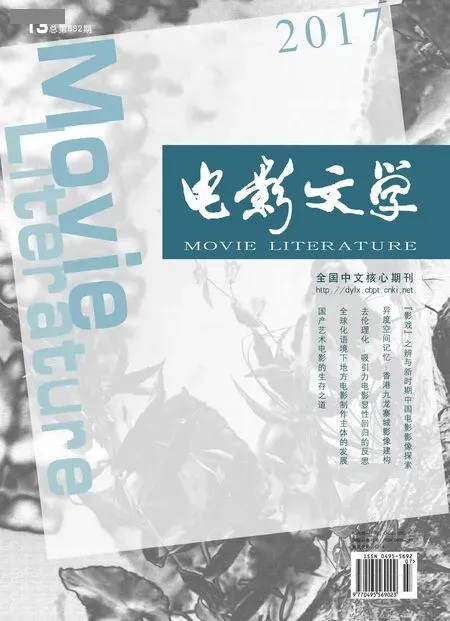从后经典叙事学角度分析《现代启示录》
2017-11-16郑敏
郑 敏
(通化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2)
20世纪70年代是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最好的时代,也是他人生中最坏的时代。1971年,因为巴顿将军的剧本在好莱坞声名鹊起的科波拉,临危受命接手执导《教父》系列影片,获得广泛赞誉、名声一时无两;却也在1979年遭遇了人生滑铁卢。花费巨资、耗费科波拉数十年心力的《现代启示录》非但没有赢得票房战场的胜利,在评论界同样遭到冷遇。站在38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现代启示录》,可以发现《现代启示录》的票房失败似乎是可以预见的。虽然该片拍摄手法、声光效果、演员阵容在当时都属于顶级,但影片的文化内核、叙事手段、影像的叙事内容都和当时流行的好莱坞工业电影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启示录》中鲜有波澜起伏的线性叙事高潮,也没有刻意设置悬念与伏线,更没有复杂缠绵的情感表达,这些非娱乐化的因素也进一步造成了《现代启示录》在大众接受上的局限。本质上《现代启示录》是一部被时代误读的影片。
1997年,戴维·赫尔曼正式提出“后经典叙事学”后,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现代启示录》的思考视角。后经典叙事学者习惯将叙事作品看作文化语境的产物。经典叙事为后经典叙事理解叙事文本的手段,着重关注作品的读者接受与历史语境在叙事作品产生时的再创造。在后经典叙事的理论框架分析下,《现代启示录》成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文化的反射。本研究也基于此展开。
一、失落的西方与失落的世界——影片的非理性叙事
《现代启示录》的开场,镜头描绘的是一片热带的蕉林椰雨。在晚霞中,热带树林显得野性又静谧,紧接着一架直升机飞过,投弹,引起的爆炸火焰比开始画面中的天边晚霞更为耀眼。此时The Doors乐队的Theend(结束)响起。构成了叙事上潜在的巧妙回环,预示着威拉德上尉的刺杀之旅从开始就陷入了一种焦灼的虚无,开始也就意味着一种失败的结束。影片开场的十分钟既是对主角威拉德的状态的引出,也是对整个电影故事主线的描述:一位美军的高级军官库兹陷入了精神失常,逃离了军队后,在柬埔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自己的军队,专门反对美军。因此需要威拉德杀死这位已经疯了的上校。然而威拉德自己却对录音中库兹的“刀锋与蜗牛”的言论感到了困惑和一定程度上的共鸣——在参加越战之后,威拉德已经和越南产生了一种难以言明的联系,一边厌倦和恐惧杀戮和战场,一边又难以逃脱战争对其投下的阴影。威拉德在等待任务中的失控恰好从一种角度说明了威拉德人生意义的主题偏离,和妻子的团聚没有意义;在美国的享乐没有意义;在西贡的等待让人焦灼;参与战场则让他渴望。影片中,在旅馆等待任务的威拉德一觉醒来,看到的是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电风扇,然而在他耳边听到的却是嗡嗡作响的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直到威拉德拉开窗帘,才确认他虽然已经回到了越南,却并没有深入战场。
随后影片则更具体地阐明了这种非理性和无意义的叙事。威拉德和没有战争经验的四人组成的船队溯流而上,首先遇到的是已经接近发疯的空中第九小队的指挥官比尔·基尔高。他对战场不了解,对轰炸没有定位和规划,却在听到兰斯来自加州,擅长冲浪的时候来了兴趣。第二天就带着空中小队轰炸一处北越村庄,只是为了赶冲浪的浪头。他给每一个杀死的敌人都发一张“死亡扑克”,却给垂死的敌人喂水;上一个画面里,他的手下被敌人的手榴弹炸死,他愤而大骂:“野蛮人!畜生!”驾着直升机追踪扫射两位越共农妇;下一秒,他又让人开着他的专架送一个受伤的越南小孩去红十字会。更为疯狂的是,他在尚未结束的战场上,就要求上滑板冲浪,仿佛丝毫不畏惧战场双方的投弹可能会杀死他。在兰斯和威拉德偷走了他的冲浪板后,他派空中小队四处广播“还板不咎”。
在比尔·基尔高身上就已经体现出了文明的两面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杀死敌人是光荣的;可是另一方面,尊重敌人和拯救妇孺同样是人道主义的,可是在战事胶着的战场上,这种人性的意义和光辉应该怎样取舍呢?是否要出于人道主义拯救一个可能已经杀死你的同胞,也许在未来还要杀死你的敌人呢?比尔·基尔高的失控恰好可以看成是西方文明中难以调和的产物,文明在暴力和野蛮面前不堪一击,荣誉、人道主义在无意义的死亡面前不值一提。深入东方丛林的美军在越战中束手束脚,补给精良但毫无战斗力。每个人都想回家,每个人都渴望啤酒、冲浪和摇滚乐,但是从美国再度动身返回战场的威拉德本身却已经证明了文明对蛮荒去魅的无解。东方的丛林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危险。在前殖民主义的文本叙事中,东方的丛林总是蒙昧的、蛮荒的、神秘的,但本质上对西方人却是致命的。
在威拉德的上游之旅中,这种情绪不断被放大。荒谬的酬军晚会,军人们群体性的对性感女郎的渴望和失控。一直认为越南人不过是一帮野蛮人的“大厨”,在一次上岸后偶遇老虎,仓皇逃命后,发誓永不上岸。航行中在河边例行的巡查最终却引发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大屠杀。收音机一边播放着克林家人对他的期待:“一定要安全回来。”一边是被流弹击中,无声无息倒在血泊里的克林。荒诞虚无的叙事本身所暗藏的是对西方脆弱的文明的嘲讽。美军可以看成是相对越南而言的文明者,当文明进入野蛮后,理应改造野蛮的文明却脆弱得不堪一击。在深入丛林的过程中,文明逐渐被未开化的蒙昧感染,开始失控。文明者对文明和蛮荒意义的思考则导致了他们的彻底疯狂。在叙事上,两者互为表里,互成一体,向人们展示了失落的文明西方,同样也展示了一个文明失落的人类世界。
二、历史语境的先破后立——“丛林恐惧”与“黑暗的心”
在《现代启示录》的影片纪录片《黑暗的心》中,导演科波拉自陈:“我不是想拍反战电影,《现代启示录》并不是反战主题。”而影片则相对忠实于康拉德的原作小说《黑暗的心》。只是从西方殖民探险背景转移到了正当时的越战背景。在事实层面上,这种转变也隐含了一定程度上的文明与蛮荒的批判性思考。1979年上映的《现代启示录》是153分钟的版本,而在2001年科波拉推出的导演剪辑版时长足有202分钟。两个版本之间的差距体现在克林死后在航程中遇见的法国庄园桥段。这一段相比较威拉德的河上之旅之外,说教意味更为浓郁,也更具有导演的思辨眼光,同样对影片主题的展示也更为深刻和全面。
威拉德一行人偶遇的法国人,曾经是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殖民者的后代,百年前一穷二白的祖先来到越南,开辟了种植园。此后这些法国人就留在了越南,虽然他们依旧会说英语、法语,依然姿态优雅,吃西餐,听钢琴乐曲,但是他们本质上已经成为衰落和迟暮的贵族。在越南他们通过文明的教化,让家中的越南仆人和管家都有了良好的教养、说法语、做西餐,恭敬有礼。但是本质上却没有办法抹杀他们外来者的可悲局面。当威拉德问到为什么他们不回法国的“家”时,法国人义愤填膺地说:“回家?这里就是我们的家,除了这里我们已经没有家了。”然而西方的文明在越南丛林里,又一次失效了。这些法国人在越南孤立无援,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是外来者。在文化上,他们的改造与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威拉德一行人中的“大厨”对西餐赞不绝口,要求认识一下厨师,结果被告知厨师是一个越南人,不会英语。这一桥段的讽刺性十足——即便法国人自认为他们教会了越南人“正确”“文明”的方式,这些越南人本质上依旧是这片蛮荒雨林的子孙,尝试获得文化上的理解和沟通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威拉德和丧偶的法国女子之间,也接近于鸡同鸭讲。尽管两人对越战都抱有失望的情绪,但从根本上,两人所面临的处境完全相反。本质上只是两个“外来者”的惺惺相惜。
法国庄园一段是科波拉对威拉德见库兹的伏笔。百年前的法国文明在与丛林的碰撞中以失意收场,而现代的美国人又将如何呢?在影片的陈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库兹对威拉德的影响。库兹出身军人世家、战功赫赫,却在来过越南一次之后坚决要求调职特种部队。当时库兹四十多岁,在特种部队里升职空间有限。在二次返回越南后,库兹屡立战功,但是嗜杀和随意性已经在他的身上有所显现。直到最终他只身一人逃到柬埔寨的丛林里,成为一支柬埔寨武装力量的头目。库兹的疯狂有理有据,并且科波拉也尝试以船上一行人的经历阐释这种疯狂。溯流而上的过程也是深入丛林的过程。最先开始发疯的是见到老虎的“大厨”,他的“绝不下船”的誓言,事实上是对丛林与蒙昧东方主义的一种被动抗拒。紧接着开始失常的是兰斯,他吸食大麻从而忘却战场,以为在脸上抹上颜料,就可以隐蔽在丛林里,这种“精神逃避法”也不能让他逃离死亡。一直理性的“酋长”死于他认为只是“乱射的树枝”的弓箭。克林依靠和家人的通信联系保持理智,最终却无声无息地死在家人祝福的录音带背景下。深入丛林后,每个人都失去了把握和掌控命运的能力,成为相对可笑的无意义战争的一分子。在康拉德原作《黑暗的心》中,主角威拉德醒悟,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所谓的探险只是一场打着文明旗号的掠夺。在《现代启示录》中,导演尝试隐瞒了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从历史立场上更为隐秘地吐露了文明对人的异化。正如罗杰·伊伯特所言:“与其说它(指《现代启示录》)描绘的是战争,不如说是战争揭露了我们永远也不愿发现的真相。”
三、语言镜头之外的叙事——音乐的叙事立场
《现代启示录》的叙事成就并非简单地局限于镜头和剪辑,同样还蕴含在音乐中。《现代启示录》展示了一个失去了理智的战争世界,这种叙事语言和一般的好莱坞相比,是夸张的、失控的、超现实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其叙述的蛮荒东方的形体特征却是具体的、可靠的。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就是音乐对气氛的烘托。
虽然《现代启示录》使用音乐的场景不多,但是每一段音乐都具有其具体的叙事主题。例如,开场时的TheEnd展现的是西方文明的隐秘预言。正如这一段迷幻的、缥缈的、散乱的音乐所言:“一切都结束了,我美丽的朋友。我们费尽心机,我们代表的一切,最终都结束了,我唯一的朋友……”影片基调中对现代文明的失落、对战争的意义都解构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结束”。而空中第九小队的空袭中交响乐《女武神的骑行》则展现出一种超现实的荒谬。空中飞行的数架直升机,对海滩的平民村庄开始轰炸,其背景却是描写九位女武神四处寻找勇士,拱卫神殿的音乐。负向的随意轰炸和正向的歌颂勇武的音乐形成了微妙的反差,隐喻了战争的不义性。
音乐使用的高潮则安排在威拉德刺杀库兹一段。此时的背景音乐同样还是TheEnd,但是画面却发生了变化,这里出现了一段剪辑的蒙太奇。一边是柬埔寨人的祭祀杀牛,手持砍刀砍向牛头;另一边是威拉德手持砍刀,砍杀库兹。两边的手法、情绪、状态如出一辙。原始的杀牛和威拉德的“受命刺杀”表现得毫无区别,既反映了人类文化的伪善性,又在一定层面上展示了现代文明的脆弱。这一段音乐的使用代替了杀牛时人群的叫声,也淹没了威拉德杀死库兹时搏斗的声音。音乐代替了台词,也代替了环境叙事,成为这一阶段的叙事主体。在库兹倒地后,音乐减弱,威拉德走出山洞,发现原来库兹的子民在向他朝拜——“旧王已死,新王当立。”然而威拉德没有被这森林的原始诱惑吸引,最终开着汽艇,消失于茫茫的黑夜中。开头和结尾的TheEnd的应用,仿佛印证了一个轮回——文明的象征者来了又去,但是他们从没有征服过这片原始蒙昧的热带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