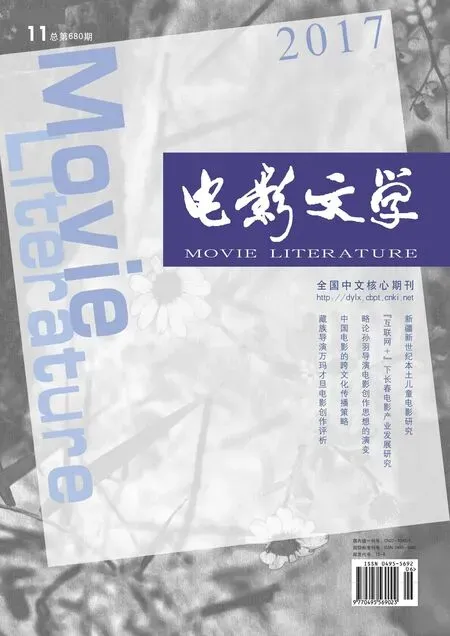小说《宠儿》改编电影的文化隐喻
2017-11-16房丽颖河北传媒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00
房丽颖 (河北传媒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1998年由乔纳森·戴姆执导的好莱坞影片《宠儿》用影像的方式为现代观众讲述了美国蓄奴制时期,黑人女奴赛丝为保护女儿不再遭受奴隶主的玷污和摧残,被迫残忍地杀死亲生女儿后,在痛苦深渊中日复一日忍受着回忆和鬼魂的折磨,最终在小女儿丹芙与黑人社区的帮助下走出生活阴影的故事。作为由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同名小说的改编电影,影片《宠儿》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同时还采用隐喻性表述,以抽象的叙事为这部哥特式故事增加了更多的负重感,同时也为现代观众认识美国血腥的历史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因此,本文通过对影片中奴隶制、女性意识及民族文化等内容的隐喻性表述的分析,探究影片《宠儿》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
一、跳跃时空隐喻奴隶制的黑暗残酷
作为后现代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宠儿》打破了传统叙事时空线性规律,而是让贩奴船、蓝石街124号等不同时空跳跃穿插于故事情节中,不仅有助于观众全面了解故事情节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赋予了时空情景更多的隐喻作用,让观众认识到美国奴隶制度的阴魂不散及黑人生活状况的悲惨,对于揭示影片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例如,影片中不断跳跃出现的非洲贩奴船,既让读者了解主人公等黑人的身世,也成为黑人集体惨痛记忆的空间隐喻。影片《宠儿》作为一部饱含沉重历史的电影,导演乔纳森·戴姆将镜头延伸至遥远残忍的奴隶贸易和黑人作为奴隶制度牺牲品的历史事实,让赛丝等主人公成为六千万死去黑奴的代表。影片中黑人主人公赛丝作为贩奴船幸存的黑奴,见证了黑奴在大西洋的悲惨经历。贩奴船狭窄肮脏的夹板、船舱、死尸堆等空间意象在电影中时不时出现在赛丝和宠儿的记忆中,不仅让主人公不断遭受创伤记忆的侵蚀,引发观众对黑人的同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以影像化的方式揭开了美国奴隶制度血腥的面纱,为现代观众更为清晰地认识奴隶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可以说贩奴船这一跳跃的空间已经成为黑奴集体记忆重要的空间表征。
除此之外,电影中“甜蜜之家”的空间影像作为赛丝个体的创伤记忆空间也以跳跃的方式在影片中不断闪现,成为揭露奴隶制度残酷的重要意象。影片中“甜蜜之家”作为奴隶主安排给主人公赛丝的家,虽然号称“甜蜜”,但无论赛丝、黑尔、萨格斯还是保罗、西克索,在这个所谓的“甜蜜之家”生活得都不幸福,甚至在日后,很多主人公回忆起此地的生活时仍然心有余悸。导演在影片中采用极具后现代风格的重复空间叙事,巧妙地让这一场景呈现在赛丝等人物的脑海中,尤其是赛丝出逃之前在学校被白人抢去奶水并遭遇毒打的情节,在电影中前后跳跃出现十余次。电影用这种违背叙事习惯的空间跳跃凸显了美国奴隶制度违背人伦等残忍行为,同时为奴隶制的社会环境冠以“甜蜜之家”的讽刺性名称,隐喻了美国奴隶制的虚伪,也增加了影片的反讽效果,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作品的内涵深度和批判意识。
除了贩奴船和“甜蜜之家”外,导演在影片中还经常将“蓝石街124号”这一主要的场景跳跃地浮现在赛丝的回忆中,隐喻奴隶制的阴魂不散和弑婴案发生的必然性,对美国奴隶制度的批判达到最高潮。电影中赛丝出逃后和萨格斯租住在蓝石街124号,但是她们仅在此地过了28天的自由幸福生活。为防止女儿继续沦为奴隶制的牺牲品,赛丝在蓝石街用极端手段将女儿杀死。电影在构建这个悲剧故事时,让观众随着空间的不断跳跃参与到故事建构中,用不同的时空记忆隐喻奴隶制度的顽固和危害性,同时唤起观众对黑奴的同情。同时在影片中,因为蓝石街124号空间不断浮现在诸多人物的脑海中,让主人公赛丝不仅受到白人的歧视,更受到黑人同胞及爱人的嫌弃,此时124号成为赛丝的心魔,同时也影响到赛丝女儿丹芙的成长,让她和母亲一样封闭在恐惧和自卑中,成为创伤记忆的囚徒,更成为美国奴隶制度的牺牲品。总之,《宠儿》一片中,跳跃的空间意象既承担了回忆叙事的功能,同时也具有隐喻作用,导演通过贩奴船、“甜蜜之家”及蓝石街124号的空间切换,既让影片呈现出后现代空间化叙事效果,同时将空间和黑奴生活、对奴隶制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以空间变化凸显黑奴的悲惨,让观众对黑人的命运产生更多的忧患意识。
二、不同命运隐喻黑人女性意识觉醒过程的艰辛
电影《宠儿》中导演将拍摄视角集中在祖母、赛丝和孙女三代美国黑人女性人生命运和悲惨经历上,以三代人不同的命运渐进式地隐喻奴隶制度下黑人女性意识觉醒虽然艰辛,但是一直在成长的历程。
首先,作为第一代黑人女奴,萨格斯在影片中虽然有关为奴数十年的经历,但是导演却没有赋予她丝毫主体意识,乃至于萨格斯也认为自己走起路来像三条腿的狗。萨格斯为奴60年虽然生下了8个子女,但是当她的子女被卖掉或继续当奴隶时,萨格斯没有表现出愤怒,而是默默地接受了白人主人的安排。导演在萨格斯生活中穿插入非常多的痛苦回忆,如被贩卖、毒打,这种重复性的创伤记忆让萨格斯不敢,甚至不想去反抗,成为缺乏价值感和归属感女性的典型代表。当萨格斯在儿子的帮助下重获自由之后,已经习惯被奴役的萨格斯居然被眼前自由的生活震惊了,甚至不习惯自由地呼吸和说话。然而此时电影却没有让其自我意识得到发展,反而让她再一次见证了黑人奴隶制逼迫赛丝将孙女杀死的悲剧及周围男性的冷漠,而这种残酷的情节则再一次将她打入被奴役的深渊,刚萌芽的自我意识及价值观被彻底摧毁。可以说,导演乔纳森·戴姆用萨格斯无法逃避的命运,既隐喻了奴隶制对黑人女性生理和精神的摧残,同时也隐喻了黑人女性意识的完全丧失。相较于萨格斯主体意识的丧失,主人公赛丝在电影中显然具有更为强烈的反抗意识。但是由于对奴隶制过于恐惧,赛丝身上的女性意识及女性反抗精神仍然是无意识和被动的,同时也是极端的。相较于原著,主人公赛丝无论在形象上还是性格上都更接近现代女性。为避免孩子受到奴役,她宁可不依靠男性只身逃走,母爱和对自由的渴望让其女性意识超越了萨格斯。但是电影仍然遵循原著,让赛丝无奈之下选择杀死女儿,用极端的方式为女儿争取自由。电影用赛丝这种极端的反抗,隐喻第二代黑人女性的觉醒,赛丝也成为一心保护家庭及寻求自由身份女性的典型代表,然而极端的弑婴行为同时也隐喻其女性意识是被动的,她所追求的不过是自己的独立,这种女性意识仍然较为朴素,具有局限性。最终赛丝也只能挣扎在痛苦的深渊中,并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与萨格斯丧失自我意识、赛丝被动无意识追求主体身份相比,电影则赋予第三代黑奴丹芙更为现代的女性主体意识。电影中,丹芙主要通过主动的自我追寻,成功地摆脱种族歧视的历史阴霾,甚至成为当代自强独立女性中的一员。导演乔纳森·戴姆没有让丹芙遭受奴役压迫,但是却采用哥特式情节改编,让丹芙与鬼魂宠儿形成跨时空交流,并逐渐形成对奴隶制度的批判意识,在思想上走向成熟。导演在丹芙身上注入了更多现代女性的思想元素,让其更加独立,不再像其祖母和妈妈一样依赖男性。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具备了更多的独立意识。电影用丹芙隐喻女性完全可以寻求属于自己的身份,实现性别、种族、家庭的平等。同时,电影中丹芙也逐渐认识到黑人身份和黑人社区的关系,并充分利用黑人社区帮助母亲摆脱宠儿鬼魂的纠缠,和母亲一起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导演在电影中由三代女性的不同命运及选择隐喻女性意识觉醒过程的艰辛,同时这种递进式的女性意识构建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观众带来不同的心理冲击,引导观众对不同时代的女性及女性遭遇形成客观的认识,有助于观众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
三、非洲意象元素隐喻对黑人民族文化的寻根之旅
《宠儿》受到原著作者非洲文化的影响,在故事中存在大量具有典型的非洲文化的影子,导演乔纳森·戴姆在影片中没有将这些非洲元素予以完全删除,而是将好莱坞电影元素与非洲意象结合在一起,以大量非洲元素引导观众展开民族文化的寻根之旅。
电影《宠儿》虽然是好莱坞电影,但是借鉴了非洲文化中朴素的自然观,赋予某些自然元素强大而神秘的力量,与黑人民族文化形成了天然的契合,象征着电影导演及黑人对民族文化的憧憬。例如,非洲神话中“水”这一令人崇敬的自然元素,在影片中被赋予一定的神秘力量,尤其在鬼魂宠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中鬼魂宠儿无论是首次出现还是最后消失,都与一条神秘的河流相关,而这种生于水、归于水的故事情节,让电影极具隐喻意味,象征着源于非洲民族文化的黑人,最终也必将寻回民族文化之根。电影还赋予俄亥俄河神秘的力量,只要奴隶越过该河就能获得自由,这种哥特式的故事既让电影充满神秘色彩,同时也与非洲民族文化强烈的自然观形成联系,让观众形成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影片中丹芙生在俄亥俄河中,因此也具有非洲黑人传统文化河水的神秘力量,可感知鬼神并与之交流。除了河流意象之外,电影还对非洲文化中代表神秘力量的植物进行了充分的利用,让树木、花朵等自然元素成为象征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引发观众对黑人民族文化的希冀。电影中导演让植物成为黑人心灵慰藉及忍辱负重生存的力量来源,植物在很多情节中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引导主人公由毁灭实现再生。如保罗出逃时,询问当地的土著居民怎么才能到达自由的北方,土著居民告诉保罗沿着花朵走就能到达其理想的终点。结果在花朵的指引下,保罗成功地逃脱奴隶制的统治,与赛丝团聚。同样,赛丝背后树形伤疤、丹芙的树屋都与非洲文化传统形成了天然的联系,并让主人公从这些非洲文化元素中获得力量和安慰。电影采用这些非洲意象一定程度上让观众不再局限在白人文化思维中,而是主动地对民族文化根源进行探索追寻。
除此之外,电影《宠儿》将原著故事进行了一定的精简,但是仍然集中讲述了宠儿借尸还魂回到人间的故事,这种极具非洲传统神话色彩的故事内容与白人崇拜理性科学的主流文化形成了强烈的撞击。电影打破了生和死、人和鬼的时空界限,采用碎片化的叙事将死者和生者置于同一叙事情节中,尤其是祖母萨格斯虽然1873年就已经去世,但是在影片中却和主人公赛丝经常进行语言和感情交流,这种哥特式的表现手法也具有典型的非洲文化特点,与非洲文化传统形成了直接的联系。总之,电影《宠儿》通过对非洲文化元素的大量运用,不仅满足了现代观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而且隐喻了黑人民族文化的存在及黑人民族文化对黑人主体意识、文化身份的作用。
四、结 语
总之,1998年版电影《宠儿》因为受到原作者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民族属性的影响,蕴含强烈的反种族压迫意识、女性主体意识及黑人民族文化意识。但是,在艺术表现上导演乔纳森·戴姆并没有对美国奴隶制度进行直接性批判,而是采用隐喻性创作手段对故事主体进行深化。影片通过文化隐喻体系,对影片主题进行了多层次的阐述,为观众提供了更大的想象和思考空间,对于提升影片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