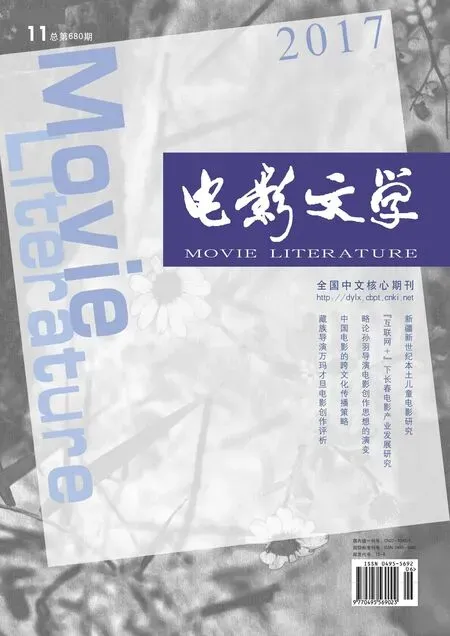论导演乔·怀特电影的视觉空间建构
2017-11-16郑君玲河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河北石家庄056000
张 莉 郑君玲 (河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6000)
视觉空间作为影视艺术美学表现的重要元素,直接影响着影片故事的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深谙此道的英国新锐导演乔·怀特,以唯美的视觉空间画面为观众创造出与众不同的视觉盛宴,激发观众对影片的想象和思考,被誉为电影视觉空间美学大师。基于此,本文以乔·怀特电影视觉空间特点为切入点,探究其视觉空间的构建策略和作用。
一、乔·怀特电影视觉空间的特点
(一)文学改编电影视觉空间:精致唯美
乔·怀特在文学改编电影中经常使用唯美的视觉元素将观众带入视觉艺术的世界中,其电影影像仿佛一幅幅精美的油画作品,与故事人物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让观众随着景观空间变换感悟情感的发展。例如,在文学改编电影《傲慢与偏见》中,怀特将影片内容与自然景观距离明显拉近,对英国中世纪的乡村风光和生活进行了详尽的呈现和描写,让影片摆脱了原著的贵族格调,焕发着泥土自然清新的芬芳。影片中自然风光几乎贯穿了主人公经历的全过程,当主人公伊丽莎白只身前往庄园时,自然与人物完美契合,呈现出一幅开阔大气的视觉空间;当伊丽莎白与达西争吵时,电影对急风骤雨、摇摇欲坠的建筑、草木构建起一个风云变幻的室外自然空间,凸显人物愤怒的内心世界;伊丽莎白最终面临人生选择时,为凸显其内心的悸动和复杂,电影将镜头聚焦于山崖的险峻和平原的广袤,用自然景物的外形与人物共同营造了一幅深沉壮阔的视觉意境。除此之外,在《赎罪》中,怀特也将溪水、树林、桥洞、喷泉、庄园、长滩等自然景观贯穿于主人公塞西莉亚姐妹的情感发展中,为观众展示了一幅幅精致同时又蕴含深意的唯美画面。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乔·怀特更是充分利用了舞台剧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段,在故事人物形象、镜头画面上讲究明亮华丽,极具绘画和舞台艺术的唯美特性。例如,在电影空间上,影片大量借鉴剧场空间安排,人物服装精致华丽、空间布景和谐统一,灯光变化莫测,将俄国19世纪宫廷的奢华之美与电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观众如痴如醉。
(二)现代题材电影视觉空间:破败混乱
在《汉娜》《独奏者》这两部现代题材影片中,导演乔·怀特在视觉空间的构建上不再追求精致唯美,而是出于故事主题的考虑,集中展示都市空间景观的破败无序,以陌生化的城市视觉空间展示现代人的心理状态。以2005年的《独奏者》为例,故事虽然发生于大都市洛杉矶,但影片中靓丽光鲜的地标符号几乎没有出现,视觉空间中画面都呈现出普通都市的共性景观,导演通过对城市身份的陌生化和模糊化处理,凸显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一方面,电影用大量镜头聚焦洛杉矶贫民区的破败简陋,尤其是收容主人公的社区被完全定义为城市边缘,但这种破败的视觉空间让影片呈现出强烈的人性关怀意味。另一方面,电影《独奏者》采用航拍镜头俯瞰城市地貌,用模糊的城市景观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认识洛杉矶这个大都会,让观众摆脱了对大都市的习惯印记,将注意力关注到主人公的生活现实,增加了视觉空间的人文深度和批判意识。同样在影片《汉娜》中,乔·怀特通过14岁少女杀手汉娜的复仇和逃亡之旅,将摩洛哥、芬兰、西班牙等国家的视觉空间予以艺术化的颠覆,视觉空间元素不再是唯美的,而是粗糙的、危险的。例如,电影中当汉娜逃到柏林后,进入了一个废弃已久的儿童乐园,本该如童话般美丽的公园却破败不堪,甚至童话中常见的小木屋也阴郁恐怖,充满凶险,导演用错综复杂的场景、阴暗的光线、颤抖的画面将视觉空间营造出一种诡异风格,让观众也随着视觉空间的推进而紧张。总之,导演乔·怀特在其现代题材的电影中,最大限度地将视觉空间形象予以异化处理,都市不再喧闹华丽,而是变得阴郁破败。这种视觉空间凸显了影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及乔·怀特的人文精神。
二、乔·怀特电影视觉空间的构建手法
乔·怀特在电影创作中,将个人风格和主流拍摄手法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结合,让电影空间美学在宏大空间和微观视觉元素上形成了复杂的、动态的平衡,让观众在影片有限的时间内感受电影艺术的视觉冲击力和主题意蕴的感染力。
(一)以长镜头手法保证视觉空间的整体性与连贯性
为凸显电影的空间之美,乔·怀特经常在电影中采用动态的长镜头对画面进行调度,以单独的长镜头手法为观众带来通畅和连贯的视觉空间审美感受。例如,在《傲慢与偏见》中,乔·怀特交代伊丽莎白的性格和其空间环境就用了长达88秒的镜头,而酒会跟拍镜头甚至达到170多秒;在电影《赎罪》中,敦刻尔克撤退的场景中,全景长镜头长达300多秒,完整地构建起敦刻尔克惨烈混乱的视觉空间。乔·怀通过长镜头将画面聚焦在死亡的战马、燃烧的物资、浑身是血的伤兵的地狱景象,同时又将镜头瞄准象征天堂的海边儿童游乐场,通过惨烈的战争长镜头描写形成了天堂、地狱强烈的视觉对比,让电影呈现出强烈的史诗感。同时,为了表现视觉空间的变化,怀特电影中的长镜头以运动镜头为主,用蒙太奇式动态拍摄思维代替传统定点机位拍摄,让影片的视觉空间本身具有运动节奏,这也成为其视觉艺术的重要标志。乔·怀特电影经常让镜头和主人公之间保持动态的关系,主要以主人公的行踪为线索,以自由拍摄视角跟随,游移展示影片的空间位置和空间情态,同时改变电影画面构图和取景,这样既能保证人物和空间结构的强化,也能保证视觉空间的整体性与连贯性。
(二)以道具、模型等元素作为视觉空间转场媒介
乔·怀特电影中的视觉空间不仅细致真实,而且空间转换较为灵动利落,让电影的视觉空间呈现出较强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为实现空间转换的合理顺畅,乔·怀特将道具、光线等视觉细节元素作为视觉空间转场的媒介,让空间变化显得非常自然。电影中乔·怀特利用同一事物的细节相似性,例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一片中,当安娜的小儿子的火车玩具由玩具假山隧道开出后,视觉空间马上跳转成真正的火车。乔·怀特采用了文学中“明喻”这一修辞手法,让场景转变毫无违和感。同时,乔·怀特还利用了不同事物某一层面的相似属性,为观众造成视觉上的连贯。例如,在《傲慢与偏见》一片中,当伊丽莎白在卧室梳妆台前向手中的羽毛吹气时,气流声、羽毛波动与舞会火焰燃烧的声音和火苗联系在一起,将视觉空间转移至舞会上,电影的空间变化的美感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如《独奏者》一片中,纳撒尼在卧室中拉小提琴时,镜头逐渐上移对准了屋顶的星球模型,而慢慢地电影视觉空间就由室内转换至黑暗宇宙,球形模型也变为卫星视点中的地球。通过这一特殊的视觉空间转换可以发现,怀特充分利用模型等细节将不同的视觉空间联系起来,让影片具有科幻片式的美感和纪录片式的震撼,既完成故事叙事任务,又让影片具有一定的诗意美感与人文情怀。
(三)以人物心理、情绪为线索连接视觉空间
乔·怀特经常以人物心理为线索,让故事人物的情绪连接视觉空间,这样既能实现电影的传情达意,同时也让观众发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倾向与波动。例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一片中,故事结尾万念俱灰的安娜身着华服独自漫步在寓所内,她突然腹痛难忍跌落在沙发上,但她抬起手拉开布帘时,却赫然出现了列车的窗外景象,电影瞬间由室内空间变为火车的车厢。安娜在绝望中走出了车厢,穿梭于乘客恶意的眼光中,最终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安娜在站台边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电影在该过程中,以安娜的焦灼与绝望心理为动力,以突然的、大幅度的空间变化预示人物的精神状态,形成了心理节奏与时空变换的同步,也让整个故事视觉空间联系得自然顺畅。
三、乔·怀特电影视觉空间建构的意义
乔·怀特通过镜头语言将电影中的道具、人物、场景等视觉元素与故事内容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增加了的影片的美学价值,而且也让视觉空间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对观众理解影片内涵起到重要作用。
(一)电影美学层面意义
乔·怀特在影片创作中通过对视觉空间个性化的设计,使其影片在故事内容和视觉画面上均衡和谐,同时让商业影片呈现出更多文艺气质。通过对自然景观、城市景观个性化的表达、动态长镜头的大量运用及视觉空间的无缝连接,乔·怀特电影在视觉画面完整度和视觉空间承接连贯性方面实现了空间美学的艺术创新。同时,乔·怀特通过唯美的庄园景观让电影呈现出浓郁的英伦风格,与好莱坞电影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也让电影视觉艺术具有古典文化情境,符合现代都市观众对审美的心理需求。尤其在《傲慢与偏见》《赎罪》《安娜·卡列尼娜》这三部文学改编电影中,通过城堡、树林、溪水、庄园等画面的集中展示让现代观众形成对古典文学及空间美学的直观认识,让观众不再将观影重点完全聚焦于故事本身,也注重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可以说,乔·怀特通过对电影视觉空间的个性化设计,在好莱坞奇观电影、技术电影发展的背景下,形成了较为独特的美学意识形态,为理解电影的技术之美与意境之美提供了成功的范本和有益的启示,对电影视觉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二)电影表现层面意义
乔·怀特电影的视觉空间对电影本身来说,首先将故事角色的内心世界直观地展示给观众,实现对现实的解构。电影人物内心世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乔·怀特通过外在空间景观和事物与人物内心形成密切联系,让视觉元素的变化、排列组合形成对故事人物内心的彰显。尤其是乔·怀特对于人物心理与现实时空背离式的表述,成功地展示和挖掘了人物心理动因和精神历程。如《独奏者》一片中,乔·怀特对主人公纳撒尼求学的心理通过其在空荡荡的剧场、密闭的电话亭、黑暗的后台等空间予以表现,将其紧张和敏感的心理状态完整地展示给观众,这些视觉空间成为纳撒尼心理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写照。其次,视觉空间的构建推动了影片的叙事进程。乔·怀特影片对大量现实空间的长镜头和动态镜头运用,增加了观众对场景、人物的认知程度,从而能主动建立视觉元素、氛围与情节发展的逻辑关系,对情节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例如,在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一片中,主人公安娜的爱情历程总是伴随着火车车头、火车车轮等意象,可以说,火车等元素构建的视觉空间成为其爱情的载体,同时也暗示了安娜毁灭的最终方式。同样,在《汉娜》一片中,导演乔·怀特通过科幻元素、惊悚元素、公路镜头、城市景观等视觉元素的糅杂,借助慢镜头、高光和滤镜等拍摄方式营造出一系列视觉空间,通过空间的连续性展示将主人公汉娜的寻父、复仇情节联系在一起。
四、结 语
英国新锐导演乔·怀特并不多产,其作品在影视艺术审美层面上,达到了影像艺术和美学价值之间的平衡,实现了视觉空间和电影主题的和谐同一。乔·怀特电影艺术别具一格的视觉空间构建方式,既是其对电影表现力、影像之美的个性化尝试,同时也为当前商业影片审美空间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因此,乔·怀特在电影视觉空间美学价值上的探索无疑值得全世界电影艺术者广泛关注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