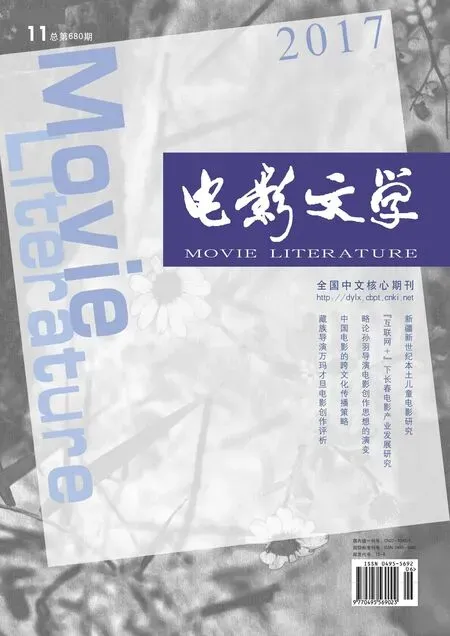新疆新世纪本土儿童电影研究
2017-11-16熊建军石河子大学新疆石河子832000
熊建军 高 雅 (石河子大学,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新疆本土儿童电影是中国儿童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其定义为:以新疆文化为背景,以新疆各民族儿童为主要表达对象,反映新疆儿童在多民族区域、多元文化环境中生活、学习、成长的电影类型。在创作主体上满足主创、拍摄、主要演员都出自新疆本土。在叙事中,它记录新疆各民族少年儿童的成长经历,展示新疆各民族多元的文化,表现新疆各民族儿童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主要文化影响因素。也就是说,新疆题材儿童电影作为电影艺术的一个种类,具有体现新疆元素、儿童元素、传统元素和新媒体元素的共同特点。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够被归入新疆本土儿童电影中的影片并不多,而进入新世纪,新疆本土儿童电影更是屈指可数,能够归入这一范畴的仅有《至爱》《买买提的2008》《爱在旅途》《幸福的向日葵》《伊宁的不眠夜》五部电影。本文以内容分析、符号分析的方法,研究上述文本在主题呈现、符号表达等方面所体现的价值倾向,同时分析在“新疆表达”方面对于受众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梳理重构新疆本土儿童电影的可能性。
《至爱》拍摄于2005年,是天山电影制片厂以2003年新疆巴楚地震为背景制作的影片。电影讲述了曾经遭受两次地震、失去五位亲人的阿布拉大爷收养在地震中失去双亲的小艾利并帮助他走出心理恐惧、回到美好生活的故事。《买买提的2008》则以北京奥运会作为背景,讲述了“沙尾村”一群孩子们追求足球梦想的故事,影片由天山电影制片厂出品,2008年上映。《幸福的向日葵》由天山电影制片厂出品,2011年上映。故事讲述小姑娘阿曼古丽在失去母亲后与外婆寻找外出打工的爸爸的故事。《爱在旅途》拍摄于2013年,拍摄背景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解救被拐卖儿童专项行动。影片以小主人公木拉提的行为、思想、心理发展和转换为线索,展现木拉提在警察的帮助下寻找“家”的故事。《伊宁不眠夜》讲述8岁小男孩玉米提在老爷爷阿里木的帮助下寻找“风火轮”,如愿参加轮滑比赛并获得冠军实现梦想的曲折故事。①
一、凸显——价值观念的追寻
新世纪新疆本土儿童电影,几乎不约而同地凸显同一个主题——寻找。《至爱》是寻找没有梦魇的生活与曾经的欢乐时光;《幸福的向日葵》是寻找一种父亲的足迹;《爱在旅途》则是寻找肉体与精神的归宿;《买买提的2008》和《伊宁不眠夜》则是孩子们对梦想的追逐。在寻找中,影片中的主人公虽然遭际不同、人生经历不同,但是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失去。表面上看是失去了亲人、家园、故乡、机会;从深层次看,则表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博弈、恶与善的较量、绝望与希望的转化,最终则是关于身份与心灵的重新定位。
在《幸福的向日葵》里,所有人都在寻找:阿曼古丽在找爸爸,奶奶在寻找40年前的初恋不回来的原因,阿米娜在寻找没有了消息的情人,乐器艾合买提在寻找同道,兽医艾合买提在寻找自己的恩人。而《爱在旅途》中,木拉提不断地寻找,不断地失望。丢失成为一个符号,丢失的不仅仅是梦中的家,还有自身的善与幸福。在小木拉提那里,家只存在于他精心保存的图画中:金秋的胡杨和波光粼粼的湖水。除此之外,任何对于家的概念都是模糊的,连同自身的幸福。在《买买提的2008》中,买买提渴望回到县城工作,他在寻找解决“回去”的途径,孩子们在沙地上追逐梦想,卡德尔村长则渴望那条消失了五年的“阿拉干河”重新出现。《伊宁不眠夜》里,小玉米提和阿里木爷爷在寻找“风火轮”——对梦想的追逐,大玉米提在寻找邮包——一种职责担当,阿依古丽老师、艾山和许多不相识的人在寻找小玉米提和阿里木爷爷——人性深处善的流露。
电影《至爱》中,地震后,当人们送走了遇难者,艾利回到废墟寻找墨镜。墨镜既是现代文化的隐喻,来自于城市,也是爱的隐喻,因为是妈妈买给他的。显然,现代文化、城市文化对于年轻一代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种影响给老一代带来了焦虑。影片《幸福的向日葵》中,奶奶和阿曼古丽到了乐器艾合买提家,阿曼古丽被悠扬的巴拉曼声音吸引了。乐器艾合买提诧异于孩子热爱这样一种传统的音乐。奶奶说:“要静下来听,都会喜欢的。”乐器艾合买提回答:“谁又愿意静下来听呢?”这是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老人希望皈依传统,至少是希望弘扬传统里面优秀的文化。但是乐器艾合买提认为年轻人已经抛弃了传统,他们热衷于吉他、电子琴,而且“爱往外跑”,从老人的叹息中也可以看到他们面对强大的新文化的冲击时的那种无奈。作为传统的守护者,“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1]。这是老人的视角与思路,而阿曼古丽第一次听到巴拉曼的声音就喜欢上了这个传统的乐器让老人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个希望也恰恰是乐器艾合买提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与理解。在《至爱》中,我们看到农村的孩子在沙地里立一根树干,上用毛驴车轮胎和绳子制作的转轮成为南疆孩子嬉戏娱乐的工具,这是城市意象的乡土化,表达了大家对城市文化的一种不自觉追求。老人看到了孩子的孤独,于是要陪孩子玩“转轮”,这既是一种爱,也是固守传统的老人对现代游戏的接受。但是与生俱来的排斥让我们看到了在老人的意识深处,传统观念牢不可破,最后这种接受(玩新鲜游戏)以老人的失败告终。老人对城市文化、现代文化的接受在失败中被延宕。老人虽然力不从心,但是想要打破传统的努力在他身上萌芽了。最后他选择了让“下一代”这个群体共同推动“转轮”。这是两代人观念与生活方式的碰撞,也是老一代人内心禁忌的松动。《至爱》结尾设置了一个南疆结婚场景,这是一种别有意味的表达,开在前面的是一辆汽车,后面跟着几辆毛驴车。从生活层面来说,这是一种改变,传统向现代生活的转变;从文化层面来说,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交接,是一种期望。对于老一代人来说,他们希望年轻人回归传统,因为“一切组织和一切协调行为都是传统的绵续性的结果,并且在每个文化中,都有其不同形式”[2]。改变对于老一代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更愿意以新鲜的事物作为未来的依靠,这时,身份与心灵都在不自觉地转换。事实上,《伊宁不眠夜》中小玉米提常常提到的霸天虎、擎天柱,带着阿里木爷爷到网吧通过QQ和表弟联系,无形之中代表了一种新观念的转换。
除了现代与传统的博弈,在新疆本土儿童电影中,还存在对善的自觉表达。近年来,随着社会变化,社会风气、道德水平在走下坡路,而现实对下一代的价值观念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如何通过电影这种传播载体影响少年儿童,让他们回到善的自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通过电影不难发现,编剧与导演都在尽力设置一种看上去与生俱来的善,这种善有来自阿布拉爷爷、阿里木爷爷身上的自觉,也有来自阿曼古丽、玉米提身上的坚持,还有来自亚力坤警官、阿依古丽老师身上的职责。而这些人身上的善又是通过不同的角度和事物表现出来的。
《伊宁不眠夜》中的阿里木爷爷则是典型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坚持要把玉米提这个倔强的孩子送回她的父母身边,但同时又能够不厌其烦地帮助玉米提,帮助他实现参加轮滑比赛的梦想。现实中,我们见到了太多的回报,见到了太多的善恶报应。但是在这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在《幸福的向日葵》里,奶奶认为“帮了别人,不是等着要别人回报”。在她们寻找的过程中,遇到了兽医艾合买提,这是一个曾经接受过她的女婿艾合买提帮助的年轻人。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兽医,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又恐惧于生命的逝去。他害怕因为自己,那些牛、羊失去生命,他在惊惧中感到无助。这时候,奶奶站了出来,她教兽医艾合买提如何接生小羊羔。在奶奶看来,这是对生命的拯救,也是对兽医艾合买提的拯救。正是奶奶这一举动,让兽医艾合买提找到了引导生命的勇气。影片在这里一方面告诉我们万物生命相同的道理,同时也告诉大家,只要有善良的愿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恐惧。不管是兽医艾合买提时时想着还钱,还是奶奶帮助别人克服恐惧心理,或者奶奶面对自己最需要的钱时的拒绝,无不体现了内心深处最自然的道德情操。而电影《爱的旅途》里,也自然地在表现这样一种善的观念。小木拉提在偷人钱包时看到对方被车撞倒,在老爷爷因为自己失误跌倒在地时的内心斗争,都是这样的体现。实际上,受到环境影响,小木拉提已经成为一个小偷,沾染上了一些恶习,但是人性深处的善并未消失。在这部电影中,关于善,在爷爷和木拉提身上有一种自然的转换:最初,二人互不相让,到后来老人为孩子着想,最后孩子帮助爷爷。而这种转换还体现在木拉提的行为上:从偷阿依古丽的钱去玩游戏,到捡到钱包准备拿走、经过思想挣扎后又还给失主,到最后给阿依古丽还没出生的孩子买婴儿车。这种转换实际上也是一种皈依,皈依到人性最初的善。而《买买提的2008》中,买买提最初的谎言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是当他看到一群纯真无邪的孩子对于梦想的追求时,这种“谎言”变成了一种动力——一种渴望成就孩子梦想的动力。
对于幸福的追寻,是每一个个体内心最强烈的冲动,新疆本土儿童电影也不例外地表现出大家渴望幸福、追求幸福的内心愿望。对于阿布拉大爷来说,他的幸福生活就是希望艾利生活得快乐一些。他说:“爷爷希望你生活得快乐一些。”他还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要往前看。”显然,快乐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阿布拉的话不仅仅是对一个孩子的期望,也代表了他对幸福的态度。木拉提想要的幸福是在记忆中的,记忆中金色的胡杨,波光粼粼的湖水,自己坐在树下,父母在湖里摇着小船……在《幸福的向日葵》中,阿曼古丽眼里先后三次幻化出向日葵。第一次是奶奶帮助兽医艾合买提给小羊接生,她看到奶奶、兽医艾合买提、羊的主人变成了美丽的向日葵。在阿曼古丽看来,奶奶帮助别人是幸福的,兽医艾合买提战胜恐惧是幸福的,羊的主人和家人的希望没有破灭也是幸福的。第二次阿曼古丽眼前幻化出一丛向日葵,是在阿米娜和她们分别时,在阿米娜离开的方向,阿曼古丽又看到了向日葵,对于和自己相同目的的阿米娜来说,向日葵是一种祝福,也仿佛是一种期许,她希望自己和这位大姐姐的寻找都有结果。第三次是热依汗和阿曼古丽告别时,阿曼古丽眼中又出现了一丛向日葵,她轻轻地说道:“再见,葵花。”这时,葵花是什么?在笔者看来,葵花不仅仅是对热依汗洁净人格的赞美,也寄托了一种希望。阿曼古丽希望这位阿姨早日找到自己心仪的男子汉。影片结束时,我们看到了满屏幕的向日葵,这是一种对幸福满满的希望。而《伊宁不眠夜中》阿里木爷爷告诫玉米提的那句:“想要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行”在片末成为玉米提最后的人生追求,表达了获取幸福需要我们自身努力不懈地追求的价值观念。
新疆本土儿童电影基本上都存在着一种教人向善、追求梦想、寻找幸福的价值取向。创作者通过故事、情节、对话、音乐、色彩、人物行为等一系列电影符号,自觉地表现出一种教化功能,教儿童行为向善、心灵纯洁,鼓励他们实现梦想。这样一种价值追求对各族儿童的成长无疑有着正确的引导作用。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从新疆元素的表现来看,新疆本土儿童电影又稍显单调,存在加强新疆刻板化认知的可能。也就是说,从人物行为上来看,它对于引导儿童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正向作用,但是从文化符号角度来说,它可能会对受众造成潜意识影响,加深受众对于新疆的固有认识。
二、缺席——多元文化的失语
作为新疆本土儿童电影,除了具有“儿童性”的特点之外,当然还应该具有“新疆性”。就目前来看,新疆本土儿童电影普遍存在弱化“新疆特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创作者对于新疆由来已久的多元文化明显表现不足,甚至存在弱化多元化或者失语的倾向。在符号元素使用上,又明显地存在强化刻板认知的可能。在人物塑造上,过分强调单一民族的身份特征。
首先是多元文化的弱化或者失语。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区,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会的地方。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3]显然,多元化、包容性、开放性是新疆特色之重要部分,让不同文化通过电影语言进行交流应该成为常态,也应该是新疆本土儿童电影的应有之意,影片中渗透跨文化的理念也成为必然。但是,从电影表现来看,创作者并没有展现出多元性、开放性,更多的是单调抑或单一。从文化元素看,《幸福的向日葵》的维吾尔色彩至为浓烈,或者说,整部影片都是在浓郁的维吾尔风情中展开的。音乐、道具使用上存在明显的维吾尔特色。在影片中,服饰、建筑、饮食都有着明显的维吾尔风格。而阿曼古丽奶奶、乐器艾合买提对于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执着坚守,大概是形成这种单一性的主要原因。奶奶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走出去,守住家园,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她说:“一个馕,一碗茶,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那就是好日子。”奶奶的观点代表了老一辈维吾尔族人在世俗生活中对家园的固守和对幸福的要求,虽然简单明了,但也多少让人觉得一种单一性对于民族的影响是明显的。奶奶对走出去的反感可以从对女婿的态度上看出来,在她心里,阿曼古丽的爸爸就是一个“贼娃子”,一个偷走了人自己女儿的心的“贼娃子”。而这个“贼娃子”没有安于生活,他走出了老一辈固守家乡的观念,走向了外面的世界。所以,对于奶奶而言,“走出去”就是一种叛逆。下一代人在努力改变这种单一性,他们渴望外来的文化,希望走出去,甚至逼迫老人接受他们的观念,但是这种改变总是微弱的,甚至有时候戛然而止。在《幸福的向日葵》中,奶奶向阿曼古丽妥协,走上了寻找父亲的路,这条路既是一条寻找父亲的路,也是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路,更是一条内心渴望走出去的路。在阿曼古丽的父亲身上,在阿米娜男朋友的身上,他们都已经迈开了第一步。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阿米娜的男朋友因车祸死了,阿曼古丽终于找到了父亲艾合买提,但是他们又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走出去或者改变,对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守护者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木拉提和爷爷,一个拿着收音机收听传统的维吾尔音乐,一个打开电视看动画片《猫和老鼠》,两人为了争夺“观看——收听”的权利展开了“战斗”,相互拉锯,几个回合后,结果以木拉提拿走遥控器、爷爷离开而告终。遥控器的掌控权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的掌控权。后来,当爷爷看到不开心的木拉提,主动给他打开了《猫和老鼠》,这种妥协一方面是一种老人对孩子的妥协,又是单一化控制对多元化的妥协,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接受与理解的转化,但是这种理解与转化在影片中太少。即便是现代文化占据上风的《伊宁不眠夜》,最终也给了日渐没落的传统一点颜面:作为“都塔尔歌王”的阿里木爷爷,最终沦落为一个“守门人”,他希望有人跟着他学习都塔尔,最终大玉米提的应允算是给了传统文化些许安慰。我们需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面对日渐强大的现代优秀文化,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大概都要做好退让的准备,如此多元文化的生命力才会持久。
其次,在新疆符号的使用上,立足于对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表达造成刻板化加强。五部电影,视角基本上立足于新疆农村和偏远小镇。就连伊宁市市委、市政府筹划拍摄的《伊宁不眠夜》这部推介伊宁市的影片也不例外。镜头更多地停留在乡村,而伊宁市的城市风貌并没有得到足够表现。电影《至爱》开始,艾利回家的路上,镜头依次闪过的是:葡萄架长廊、小羊、驴车、路边的床,然后是妈妈使用的老织布机,紧接着是赶着毛驴车去巴扎。整部电影都围绕毛驴车、摩托车、涝坝、土路、土房等展开,看上去,新疆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图景中……新疆是这样的吗?曾经是,现在的南疆偏远的一些地方也依然是。但是从整体来看,经过发展,新疆面貌有了很大改变,我们如果刻意渲染一种落后的观感,只会加强刻板印象。
新疆刻板印象的形成是一个历时的过程,远可追溯到中原与西域最初的交流,在当时,由于两者的自然环境、文化因素、生活习惯不同,传播者在通过口头传播和文字记录时,以传“异”为主,在哪儿看到的都是不同点,这种“异”表达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偏见。“偏见的产生是在人们对某些群体保持刻板印象,并将其加诸个人身上时,怀有偏见的人们会依据这个刻板印象,假定这个群体成员的所作所为,将如‘他们想象的行为’那样行事,并将许多个人行为作为这个刻板印象的证据。”[4]从历史的角度如此,从媒体的角度来看,过度单调的“优势”传播和“特色”传播导致了新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形象的刻板化。政治上我们由于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宣传不够,尤其是对新疆之外的公众宣传不够,导致大家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理解,从而导致非自治区域的公众出现误解,以为什么民族自制,那么这个区域就是哪个民族的错误观念的出现,其他民族往往被大家抛诸脑后;社会方面,过分强调民族性、特殊性,反而会导致社会撕裂;自然方面,倾向于“大景观”传播,于是大沙漠、大戈壁、大草原成为一种定式,无论是文字、图片还是视频,总是围绕“大”做文章,最终给予受众的心理定格就是“沙漠、戈壁、草原”形象;文化方面,缺乏对多元文化信息的深度挖掘,无论是外部公众还是内部公众,都有“多元文化”的概念,但是对“多元文化”的“多”不了解、不清楚、不传播,从而存在多元向二元转化的可能,甚至出现一元倾向。这与历史上的异化传播相关,也与今天新闻媒体报道框架有联系,同时还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文化模式息息相关。
再次,从形象塑造上来说,存在角色身份单一的情形。新疆有13个世居民族,其中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在人口比重、文化影响等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整体来看,新疆本土儿童电影在角色塑造上基本上都立足于表现某一个民族,其他民族成为“路人甲”“路人乙”。这种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的表现方式,实际上是弱化新疆特色——多民族特色。《至爱》《买买提的2008》《幸福的向日葵》《爱在旅途》和《伊宁不眠夜》等,基本上都是从某一个民族的视角出发,表现这个民族的个体行为与群体文化,表现他们的追求与梦想。可以说,多民族视角的缺席从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观众的误读。电影《至爱》《爱在旅途》《买买提的2008》在人物安排、音乐音响、装饰建筑、饮食文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单一文化倾向。《爱在旅途》中,在内地生活了7年的木拉提在警官亚力坤家吃饭的时候,吃的是“手抓饭”,看似是强调细节,却明显地具有身份强化的作用。这种单一角色安排和文化强化实际上从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新疆的刻板印象,对于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传播新疆多元文化形象、增进域外受众对新疆社会的了解都是不利的。
当然,影视符号无论是文化、特色元素还是人物形象都是由个体而群体,因此我们不能反对单个影视文本表现某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表现民族文化的特色,而且单部电影的“特殊性”表达也并无不妥。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所有的文本都不约而同地进行这样的表现,那么我们需要警惕它对于集体无意识的强化,从而导致误读的可能性。而且这种集体无意识容易形成民族主义,从而不利于多元社会的建构。事实上,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疆题材的儿童电影存在着明显的身份混同、文化共享的情形,比如1987年上映的《小客人》、1994年上映的《广州来了新疆娃》、1998年上映的《会唱歌的土豆》都是文化杂糅、多民族形象共同出镜的典型,但近年来却出现了明显的文化收缩的倾向。或者可以这样表述:对于新疆本土儿童电影来说,在主题上,创作者力求凸显不同民族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但是在符号选择上,我们又存在求异驱同的倾向。如果这是一个问题,那么重建就成为当务之急。
三、再造——未来生成的可能
电影是认知教育、跨文化交流、区域形象建构的重要形式。一部《泰囧》让泰国清迈的旅游人数大增,《非诚勿扰》中的三亚海景房也成了为三亚宣传的最好注脚。这实际上就是通过电影这种载体让大家了解、认识对象,让观众产生认同,从而提升对象的知名度、美誉度及亲和力。但是我们通过对新疆本土儿童电影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关于价值观念,尤其是关于善恶、幸福与不幸等人生价值的认识上,新疆本土儿童电影能够以正确的观念影响人、教育人、改变人。但在表现多元文化、改变新疆刻板印象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加深刻板印象和表现单一文化的倾向。要想改变目前这种情形,新疆本土儿童电影制作应该改变思路。从顶层设计来看,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民族地区儿童电影的多元文化表达而非特殊文化表达;从制作人来讲,要抛开身份限制,进入多元世界;从电影语言表现上,需要多层次、多元素建构。如此,方能建构一个生命力更为顽强、影响力更大的新疆儿童电影平台。
首先是顶层设计上鼓励新疆多元文化在儿童题材电影中的交流、融合、展示。我们要通过“儿童形象、新疆镜像、现代文化、中国表达”的建构策略,把儿童和新疆的特色融于中国文化之中,融入相互影响与改造的现代优秀文化之中,这样才能建构一个多元的新疆镜像。就电影市场前景看,观众对民族地区原生态艺术的好奇决定了民族地区艺术发展的大方向,“特色表达”“民族性表达”成为主要价值元素。但是面对未来、面对下一代,我们需要努力建构共性而非特殊性,建构国家性而非民族性。基于这样的要求,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有意识的单一性表达,要鼓励作为共性的东西出现在银幕上,建构一个所有新疆儿童认可的世界,而不是站在“我们(外来的表达者)”的视角上建构“他们”,或者站在“我们(具有民族身份的表达者)”的视角上建构“我们”。基于这样的发展思路,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创作激励基金,采取申报激励政策、票房激励政策和公益制作政策,鼓励更多的创作者进入新疆题材儿童电影这块园地,建设新疆儿童影视基地,通过对新疆历史、现实、自然、社会风貌综合反映来表达新疆。与此同时,政府构建以电影电视网络为载体的儿童影视传播教育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影像世界了解真实的新疆。
其次是制作人的文化思路需要发生变化。目前来看,新疆本土儿童电影的制作人、导演、摄影、演员无论其身份如何,在创作思路和表现上基本都是围绕特定民族的文化与身份展开的,这种惯例渗透在编、导、摄以及音乐音响各个层面。“九十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则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贴近异族文化……尤其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一批少数民族导演,更是开始力图从自我族群内部出发思考本族文化的生存和走向。”[5]可以说,身处多元世界,缺乏多元视角成为一种思维惯性。当然,如果主创人员是少数民族,因为文化身份的原因所造成的对自我文化的张扬与坚守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表现的单一化容易造成“我们”和“他们”的话语表达区分。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制作人需要有一个更为开放的心态,用现代的视角、多元的视野去审视我们的创作思路。所谓开放心态就是要有接纳新疆多元文化的勇气。无论谁是导演、制作人、编剧,都绕不开新疆的“多元”这一特征,在表现“新疆特色”时要关注多元性,需要讲述更多的多民族一起生活、工作、娱乐的故事,我们需要表现多民族儿童共处同乐的场景,需要选择“碰撞——融合”的叙事方式。诚然,“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应当在不断走向一体化的时代文化潮流中,在多元整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格局中,在文化平等对话交流的过程中,深刻表现和揭示某种民族文化内涵、文化底蕴,包括民族风情、历史人物、社会生产和生活、思想感情”[6]。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体多元”的现实,热衷表达某个民族的原生态而忽略多元性的做法,实际上容易导致文化猎奇和刻板印象,从而导致新疆本土儿童电影文化盲点的出现,最终结果就是因为文化盲点遮蔽现实,造成成见。所以,要改变创作者的思路,尤其是要改变定格在创作者脑海的固化思维,尝试在一开始就通过特色反映多元,而不是局限于反映多元中的特殊对象。
最后是从电影语言表现上,需要表达与建构多元文化观念。“电影拥有一种极其复杂多彩的语言,它不仅能够灵活而准确地重现事件,而且还能够同样灵活和准确地重现感情和思想。”[7]观众的认知是通过电影语言实现的,虽然每一个观众在面对电影语言的时候相对自由,但是如果符号呈现过于狭窄或者单一,那么就会降低观众认知的自由度。因为造型、角色也好,音乐、画面也罢,甚至戏剧冲突、情节展示最终都指向观众的想法——思想。这种隐藏在电影语言内部的意义最终是由观众进行发掘与创造的。因此文化特征越明显,电影语言越单调,越容易造成简单认知和刻板印象。虽然因为儿童电影表达对象和观看对象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使用电影语言相对简单,以便于儿童理解。但是简单不是单调和单一。我们前面分析的电影,无论是从画面,还是音乐或者音响,甚至角色与文化,都强调特殊性,忽略共性,这种结果直接导致了单调文化的出现。这对于非新疆儿童观众来说,他们接受到的新疆的“与众不同”,加深了其对于新疆的陌生印象。对于新疆儿童来说,单一的民族文化,实际上加深了民族特征,而这不利于建构国家认同。因此,我们在进行电影语言的设计时,要从新疆实际出发,从多元文化的现实出发,直观地表达色彩绚丽的新疆而不是单一的新疆。
概之,目前的新疆本土儿童电影,从主题上来说,作为一种“儿童性”话语表达,追求归属感、心灵的皈依和善的自觉的编码方式明显地呈现在叙事结构中,但是作为一种“新疆性”叙事,在符号表现上,又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文化的单一性和对刻板印象的加强表达。这种局限显然会限制新疆本土儿童电影的发展。要建构新疆与儿童双向观照的电影,更为开阔的视野是在加强儿童认知的同时,进一步展示新疆多元文化,积极表现各族人民交流与包容的现实图景。
注释:
① 《伊宁不眠夜》虽然并不是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但是由于影片是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委、市政府筹划拍摄,创作主体和主要演员均来自新疆本土,因此,我们依然将其置于新疆本土儿童电影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