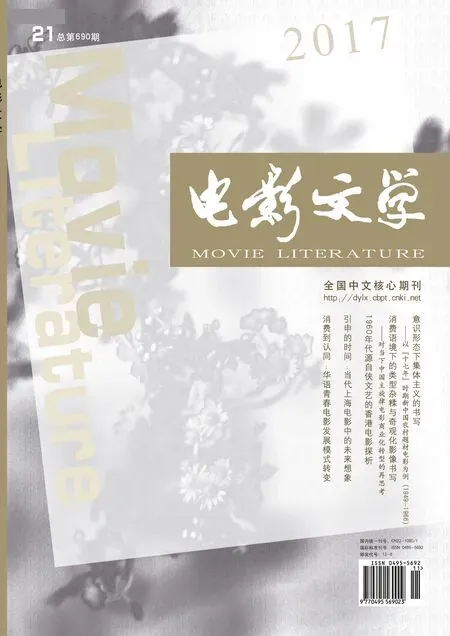中国电影中“疯子形象”的隐喻意义
2017-11-16罗婧婷长江师范学院重庆408100
范 虹 罗婧婷(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100)
中国电影中的“疯子形象”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所指,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它出现在中国电影的不同历史时期,附和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左右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隐喻意义,“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1]。他可以是封建文化的反叛者,拥抱尊重人性的现代文化;也可以是传统文明的守望者,控诉城市文明浮华背后的迷茫和虚无;甚至是社会秩序的迷失者,在多元的道德标准中踌躇彷徨,折射出从礼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中存在的扭曲现象以及这些现象背后,人们扭曲变形的价值观念。“疯子形象”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肆意妄为的载体,具有天生的符号优势,承载着创作者们别出心裁的隐喻意义,传递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主题。
一、封建文化的叛逆者
“疯癫”成为文明的副产品以后,变成了一种主动或被动的非理性代言。在艺术文本中,“疯子形象”一般出现在新旧文化更替、社会思潮碰撞或政治环境改变的时期。在中国电影中,“疯子形象”第一次成批出现并成为一个文化现象是在新时期电影中。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后,中国掀起了一股空前的文化反思热潮,而反思是一场重新表述、重新构筑的再认识过程,这一时期反思的核心问题主要(仍然)集中在西方文化的涌进与中国文化的摩擦,以及现代文化建构与传统封建文化之间的矛盾。
在新时期电影中,《老井》《大红灯笼高高挂》《洗澡》《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等作品中都出现了“疯子形象”。在电影《老井》(吴天明)中,人力挖井代表着传统的农耕文明,大学生们代表着现代的工业文明,在两种文明的交替下,放羊的疯二爷是愚昧挖井的受害者,他在电影中完成了由盲从到反叛的转换,他对挖井行为的对抗,实际上就是对封建文化的一种唾弃和反叛。例如,在电影中,疯二爷会在无人察觉的时候,把村民历经千辛万苦从地下凿出来的石块又丢回井里,以此来对抗“理智”的人们愚昧挖井的行为。他的反叛直指那个历史悠久、古老而落后的封建文化根基,但反讽的是,他反叛的理由却是“偷泥偷到土地爷手里来了”,“人们似乎可以用愚昧的方式来反抗愚昧,对愚昧的宣战成了本质上对愚昧的屈服”[2],展示出封建文化对人的奴役是浸入骨髓的,是无可救药的,是既无奈又无力挣脱的。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中女大学生颂莲是现代文化的典型代表,当现代文化被锁在高墙深巷的封建大宅中,本该是风华正茂的颂莲被活活逼成了怨妇疯子。影片里自始至终都没有露脸的老爷和人人口里提到的“老规矩”不断给颂莲制造压迫和惩罚,自进大院到最后发疯,既是颂莲反抗的过程,也是颂莲屈服的过程。影片一开始颂莲没有等花轿来接她,而是自己徒步来到了府门外,这是她反抗封建文化的第一次行动。颂莲和迎亲队伍被框在同一个镜头里,嘲弄、讥讽的意味显露无遗,这次“坏规矩”是成功的。而在影片尾声部分,颂莲在雪地里目睹谋杀的场景时,她走近房间的过程运用了一组主观镜头按全景、中景、近景的顺序交替切换,营造出足够的悬念,但在最后目睹死者的时候,影片却用了一个大远景,规避了触目惊心的画面,削减了事件本身的冲击力,也表达出声嘶力竭的哭喊仅仅是远处微弱的声音,不能产生什么力量,所以这里的挣扎和反抗是苍白无力的。影片通过视听语言微妙的形式呈现出“反叛”在开端和结局的两种结果,展示了颂莲从反叛到无能为力的过程,最后只得沦为无理性的疯癫,这里的“疯癫”有力地控诉了封建文化的落后野蛮对人的迫害。
这一时期文化反思的主题大致相同,所以这些影片中的“疯子形象”能够成为一种文化产物,构筑出一个共同的隐喻意义——封建文化的叛逆者。并不是因为疯子才具有这种反叛的意识,而是在一种社会文化氛围中,离经叛道的异己者注定会被定义为疯子。在文化反思的新时期中国电影中,古老中国的封建文化成为书写的主题,“疯子形象”则成为创作者的传声筒,成为批判和控诉封建文化的叛逆者。
二、传统文明的守望者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蒸蒸日上,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拔地而起,在喧嚣的城市里普通小人物的精神世界却是一片废墟,他们困惑、迷茫、无所适从。这一时期的创作者们以深刻的社会反思取代了文化反思中的民族寓言,他们探讨日新月异的城市中存在着的社会问题,在传统文明恬静的生活方式向城市文化躁动的快节奏生活过渡中,两种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也在进行着碰撞和磨合。
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创作者最爱引入一种对比模式,在人物命运的对照中去认识两种文明。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古伦木和马小军对比;《洗澡》里大明和二明的对比;《孔雀》中姐姐和傻大哥之间的对比,在对比之中更加突出了“疯子”们对传统文明的守望。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片尾,黑白色的沉寂与落寞与那个阳光灿烂的青春时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马小军与古伦木之间的对比更是意味深长,马小军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成功典范,开着豪车、喝着洋酒;而古伦木则守望着绚烂优雅的传统文明,他依然执着地骑着棍子蹒跚前行,只有他还停留在已经消逝的时代,在他眼里现代文明的一切都显得苍白乏味。在小说、电影中,“疯子形象”通常是标记时空的“道具”,以不变应万变,姜文正是借用古伦木这一特性,表达出对那个传统文明里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深深的留恋,古伦木也因为被钉在过去的时间坐标里,成为传统文明的守望者。
影片《洗澡》(张扬)中的二明深深地眷念着传统澡堂里的一切,大明却渴望在高效、快捷的现代商海里打拼,守望着澡堂的二明被设定为傻子,衣着体面的大明被塑造成了新时代的探索者。两种思想在影片中碰撞、摩擦、针锋相对,但是时代滚滚向前,最后父亲没了、澡堂拆了,二明一句“父亲牺牲了”令观众潸然泪下,在傻子的世界里澡堂的事业是值得守护的,父亲的死不是普通的死而是牺牲,二明的挣扎述说着创作者们对传统文明守望的深深无奈和无力。
《孔雀》里姐姐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崇尚自我意愿的表达和追求,这是所谓新时代的、进步的思想,傻大哥是安分的平凡庸碌者,对于命运和环境伤害采取忍受的姿态,是传统文化中“克己复礼”的中庸之道。创作者借姐姐命运的悲剧在质问这种“新时代的进步思想”是否真的可取,表达出一种对传统的深情守望。
相较于新时期电影,这一时期社会反思的电影作品中,更多着墨于表述现代城市的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这一时期电影作品中的“疯子形象”隐喻着一个悲剧性的角色——传统文明的守望者。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传统文明注定会被现代文化、商业文明取代,而“疯子”还始终停留在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里,这是他们自身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注定的悲剧,他们在当下不合时宜的言行举止被认定为疯言疯语,他们是现代城市里传统文明的最后一声叹息。
三、社会秩序的迷失者
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在对金钱、名利、效率、发展等观念的犬儒中,社会上涌现出千奇百怪的新现象,而在这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背后实际上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迷失,尤其是在城市以外的边远农村。“在法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依法而治。而在中国农村的乡土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是一个法治结构,而是一个‘人治’和‘礼治’社会。”[3]当传统中国礼治社会的价值体系慢慢地土崩瓦解,而法治的社会结构还没能完善的时候,边远农村的人们身处这种社会形态下,就会出现价值体系迷失的困境。
电影《一个勺子》(陈建斌)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傻子”(勺子),拉条子夫妇好心收留傻子、照顾傻子、帮傻子寻亲却反被敲诈得倾家荡产,拉条子夫妇是“傻子”;李大头信奉金钱万能的生存法则,面对拉条子三番五次地逼迫,他气急败坏最后掏钱了结此事,李大头也在混乱的道德标准中变成了“傻子”。在中国汉语中,“疯、癫、狂、愚等诸多概念在历史上曾经是相同或相近的意思,并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4]。所以本文将影片中的拉条子夫妇和李大头的形象界定为“疯子形象”。
“不识时务”或“自我矛盾”的疯子、傻子,实际上是迷失在礼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期间,价值体系模糊混乱的人,所以,“疯子形象”便衍生出了新的隐喻意义——社会秩序的迷失者。在一元的社会秩序标准中,“另类”会被定义为疯子,而在多元价值体系的社会形态下,“他者”即是傻子、疯子。而作为一个社会秩序的迷失者,始终游离于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自我矛盾与否定注定使他们成为所有道德标准之外的“他者”,成为匪夷所思、不识时务的“疯子形象”。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表述道,现在的农村“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所以这必定是社会秩序迷失的中间地带,生活于其间的人便成为多重秩序标准下的“勺子”。
而在电影《烈日灼心》(曹保平)中的陈比觉,也属于一个社会道德秩序的迷失者,他被困于善恶之间模糊的标准之中。不仅仅是陈比觉,片中三位主人公都是属于迷失在伦理道德里的“疯子形象”。小丰抓犯人拼命,救坠楼的人也拼命,阿道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也愿挨刀子拼命,他们都被罪恶感逼到了一种癫狂的状态,陈比觉聪明,他选择了装疯。很难片面地断定这三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善还是恶,因为连他们自己都迷失在了善恶之间。对于陈比觉来讲,如果他一直遵循着利己原则,彻底地“恶”下去,他能逃走,他的确也逃脱了;如果他能“恪守本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地一直“善”下去,也就不会酿成大错,背负烈日灼心的罪恶了,要命的就是他在这善恶之间徘徊、摇摆、迷失,最后只能走向自我毁灭(跳海)。这些拧巴的人根源在于社会道德秩序的混乱,既受着传统伦理“人之初,性本善”的社会教化;又深陷当今资本社会“利己主义”的病态伦理之中,这些自我矛盾的“疯子形象”也是典型的社会秩序迷失者。
四、结 语
纵观“疯子形象”隐喻意义的演变和发展,我们会发现,“疯子形象”始终诞生于新旧文化、思想、秩序等的矛盾之间。在新文化运动中,“疯子形象”第一次成批地涌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在对封建儒家思想的控诉和批判中确立自己的意义所在。“疯子形象”进入电影银幕是在文化反思的新时期中国电影里,在第五代导演们抒写的民族寓言里,将矛头指向那个遥远古老的中国,反思封建的、旧有的文化传统。但是,当整个社会扛着“发展”的大旗快速、高效地向前挺进,城市化、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时候,快餐式的生活必定带来人们的精神空虚,人们便开始怀念旧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明。在新的法治秩序建立的过程中,旧有的礼治社会和人治社会的思想观念还根深蒂固,尤其是在边远的农村地区,生活在这种多元价值体系下的人就会陷入一种社会秩序迷失的困惑中。在以上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电影中的“疯子形象”从未缺席,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倾注着创作者们不同的隐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