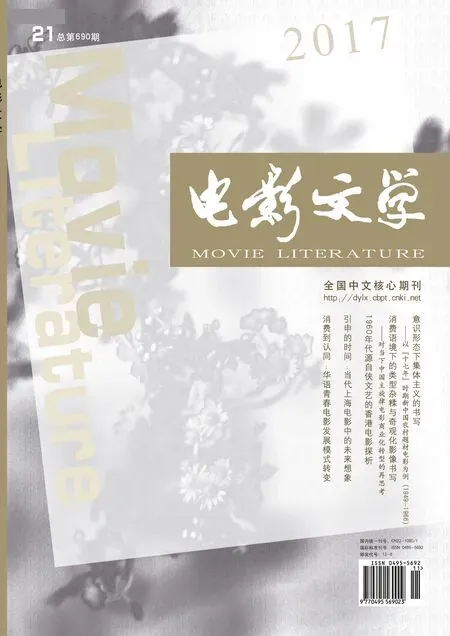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电影的价值取向
2017-11-16孔小彬九江学院江西九江332005
孔小彬(九江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当下的中国电影对于知识分子已经不大感兴趣了,知识分子不具有多少票房的号召力。20世纪80年代却有相当多的电影以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以写实的精神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人到中年》《人生》《巴山夜雨》《芙蓉镇》《庐山恋》《牧马人》《老井》等,都是80年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电影。这些电影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可以称作知识分子电影。今昔鲜明的比照,除了反映了知识分子地位的失落,也大致反映了时代精神面貌的转换。
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电影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苦难叙事。谢晋电影《芙蓉镇》中的秦书田是右派分子,长期遭受政治上的歧视,是“牛鬼蛇神”,失去做人的资格。他个人的爱情、他的人格尊严也公然地被极“左”专制力量所践踏。吴永刚、吴贻弓电影《巴山夜雨》中的诗人秋石被拘押失去人身自由,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已经是妻离子散,境况极为凄惨。《牧马人》中的许灵均因为资产阶级父亲的缘故而被定为右派,剥夺了政治的权利,到贫苦的大草原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改造,以放牧为生,连睡都在马厩里。许灵均感觉先是被父亲所抛弃,现在又被人民所抛弃了。这种内心的苦难对于他来说比肉体上的苦难还要难以忍受。《天云山传奇》是一部催人泪下的电影。电影中的主人公罗群受到极“左”政治力量的打击,陷入重病之中,是冯晴岚这位知识女性用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历史的重担。影片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幕是冯晴岚在漫山白雪当中拉着躺倒在板车上的罗群一步一步向前走去,此时音乐响起:“山路弯弯,风雪漫漫,莫道路途多艰难,知己相逢心相连。”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电影渲染了这样的一幕:在“山路弯弯”的板车歌声中,冯的遗像旁蜡烛燃尽腾起青烟,晾在室内的破背心,切了一半的咸菜,缀有补丁的布窗帘……《人生》《老井》中苦难的原因并非来自政治,而更多的是农村经济的贫困。《老井》就像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一贫如洗的家族,交换婚姻,因水而起的械斗。旺泉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空间当中,同《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他的自我被压抑在这样的空间当中。不同的是,高加林选择逃离,而旺泉选择接受。高加林的选择并没有获得成功,他还是回到了现实的苦难中来。《人到中年》中陆文婷等知识分子的苦难与政治历史的关联在影片中一闪而过,它更多涉及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中年知识分子是事业上的骨干,承载着超负荷的工作,生活条件却极为困苦。陆文婷一家两个知识分子,四口人挤在一间房里,根本谈不上办公、学习的地方。生活的艰难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马列主义老太太”对陆文婷的态度就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她既需要陆文婷,又处处对她不放心。因为苦难叙事,80年代的知识分子电影很多都是很沉重的。即使像《庐山恋》《女大学生宿舍》这样青春浪漫、具有蓬勃朝气的影片,也以历史的悲剧作为底色。《庐山恋》中耿华的父亲就受到政治的冲击,成了靠边站的老干部,影响耿华的自由恋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主人公也因右派父亲的早逝而要独立承担生活的重担,读大学期间拉板车养活自己。
大凡经受过苦难的挫折,人都会有这样的几种反应:一种是不堪忍受苦难的折磨,精神上失望,从此走向颓废,自暴自弃,一蹶不振;一种是深感这种不公平与非正义,激起反抗的意志,做不妥协的斗争;还有一种是默默忍受,不悲观,不失望,相信希望就在前方,并在转机来临之时重新振作、奉献自己。80年代的知识分子电影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与颓废无缘,也拒绝对不公开的历史做反抗的战斗,而是相信未来,承受苦难,并献身于充满希望的伟大事业之中。这大概可以说是中国80年代知识分子叙事同苏联小说所表现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可以从《日瓦戈医生》《第二圈》等苏联小说中读到知识分子在苦难中的怀疑、不合作乃至反抗,但80年代电影中的知识分子从未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他们在默默承受巨大的苦难,但相信苦难只是暂时的,是别有用心的小部分人造成的,因此一定会过去。
在80年代的电影中,苦难因此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底色,苦难让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英雄挺立起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可视为8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象征。《庐山恋》中的耿华因为家庭悲剧性的历史而对异性具有独特的吸引力,是苦难赋予他这个高干子弟人格魅力;《巴山夜雨》中的秋石既是苦难的承担者,又是国家、民族命运自觉的思考者,还是知识分子良善的代表,因其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感化力。《芙蓉镇》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他以疯癫为自我保全的方式,以阿Q式的自轻自贱来躲避阶级斗争的风暴,但内在的气质却绝不软弱,他不过是在忍辱负重式地等待时机,“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①是相信终有一天会乾坤颠倒的自我勉励,也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承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苦难。《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与罗群不是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有爱情的是宋薇和罗群,在这里爱情的力量远远小于苦难的力量、信念的力量。是苦难使得二人结合,是对正确道理的信念使得冯晴岚把承受苦难当作人生的幸福。在冯晴岚身上体现的是知识分子高贵的精神信仰和不屈的意志。从苦难中升腾起坚强不屈的意志,表现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是80年代知识分子电影共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价值取向与五四以来鲁迅战斗性的反抗叙事无关,而更多地指向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中国儒家思想有轻物质而重精神的传统,孔子讲“忧道不忧贫”,强调在贫苦之中仍可保持乐观的精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认为苦难是可以锻造人的,孟子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②凡是合格的士大夫是没有人畏惧苦难的,反倒认为苦难可以成全读书人。因为士大夫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没有坚强的意志何以完成这重大的使命?应该说,80年代电影中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价值取向上都回归了士大夫的传统,是地道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的延续。
80年代知识分子电影价值取向的另一个维度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这既是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体现,也是新中国“十七年”精神倡导的重现。80年代的知识分子电影大都改编自80年代的反思文学。作为比文学更敏感的领域,电影在处理反思题材上,更多地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旗帜。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反思只有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旗帜下才获得了表达的合法性。
电影《人到中年》原本是反映知识分子苦难的历史遭际与困苦的现实处境的,具有深刻的反思意味与高度的现实概括性。电影有意识地将陆文婷、傅家杰夫妇同姜亚芬、刘学尧夫妇对比加以表现。姜亚芬夫妇在经受磨砺之后选择远赴美国,这无疑是作为否定的线索加以处理的,以此来烘托陆文婷夫妇高贵的爱国主义情操。实际上刘学尧在出国前就曾痛苦地表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谢晋电影《牧马人》典型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反思与爱国主义的关系问题。许灵均因为政治的原因而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做人最基本的权利包括得到温饱的权利、爱的权利等都丧失了,处于一种半奴役的状态。新时代来临,许灵均远在美国的父亲要接他赴美,电影以此作为考验许灵均灵魂的重要一笔。在80年代的电影叙事中,是否爱国仿佛是真假知识分子的试金石。如果许灵均去了美国,似乎就是一种可耻的叛逃。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许灵均到美国去管理父亲的资产,再回国投资发展祖国的经济,可能比他仍在草原当个普通的牧民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更是爱国的表现。许灵均选择了与祖国在一起,与爱护他的人民在一起,他做出这个决定并没有经过多少犹豫。史蜀君的《女大学生宿舍》以青年女大学生为表现对象,与当下众多青春题材电影不同,这部电影没有把爱情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在风格上不是轻松的喜剧,而是沉重的正剧。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是没有年代差异的,但影片所呈现的80年代青年身上那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在今天的电影中似乎消失了。这群年轻人以天下为己任,在校园中讨论的话题往往是“大学生与当代中国”这样的宏大命题,她们崇拜的对象是那些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青年,是一些胸怀大志的学长。这样的年轻大学生已经带有思想者的气质了。影片中唯一一处涉及爱情的部分还是辛甘对学长一厢情愿的崇敬,事后证实这不过是一个误会。学化学的大学生看到农民挑着粪便给作物施肥,这一农村中常见的现象为外国访问者所嘲笑,当这位同学沉痛地讲述这一细节时,在场参与讨论的所有师生都沉默了。这一段镜语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知识分子所讨论的话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他们为科技的不发达、生产的落后、人民的贫苦、国家的没有尊严而痛苦,更能体会到作为国家培养的知识精英肩上承担的责任。
崇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80年代电影,在对知识分子个性要求的处理上往往采用压抑的方式。80年代的知识分子电影不承认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价值,往往将个人利益设置为群体利益的反面,因而对知识分子个人的要求并不打算满足。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牧马人》《人到中年》中看得很清楚了,爱国主义同个人利益不可得兼。《老井》中的旺泉为了家族的利益,选择放弃自己的爱情,为了族群世世代代的利益而克服各种困难,一定要打出水来。这是新时代一个忍辱负重的知识分子,只有在深不见人的井下、在确信没有未来的时候,才能从苦苦的压抑中释放个体的爱欲。以启蒙精神为主调的现代性,强调个人的自由、个性的伸张,主张个人主义的正面价值。这种思想影响到中国,鲁迅先生讲“任个人而排众数”,只有真正做到尊重每个个体的价值,才能“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③。在现代性思想中,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并不矛盾,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基础。但在中国80年代的启蒙语境中,所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排斥,要维护集体就得牺牲个体。旺泉因为个体的牺牲得到了族群的认同,也得到观众的认可。而《人生》中的高加林,因为追求个人的利益,而成了一个有道德污点的知识分子。高加林是有能力的,他凭借个人的奋斗完全胜任县城里的记者工作,他本也可以同爱他的黄亚萍到南方的大城市去幸福地生活。电影要让他承受良心的谴责,批判他自私自利的行为。从现代性的价值观来说,高加林追求个人的发展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80年代电影的价值取向以传统观念为是,高加林就是现代版的陈世美了。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电影,这些电影中的知识分子既是苦难的承担者,又是未来风气的引领者。“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其价值观在全社会具有示范作用。知识分子电影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知识分子在苦难中不抱怨、不颓废,而是默默承受,自强不息又无私奉献;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崇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都是80年代知识分子电影所肯定的价值立场。这些电影的价值取向与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思想有所不同,更多的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延续。
注释:
① 古华:《芙蓉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② 杨伯峻译注:《告子章句下》,《孟子译注》(典藏版),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30页。
③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