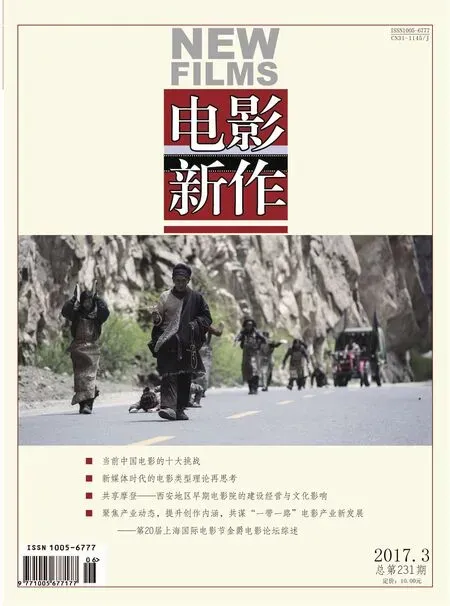传统伦理、爱国情感与主旋律创作:成龙电影的价值转向与重构
2017-11-16翟莉滢
翟莉滢
传统伦理、爱国情感与主旋律创作:成龙电影的价值转向与重构
翟莉滢
从成龙自出道以来的创作历程来看,影片中所蕴含的主题思想和价值内涵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注重对传统伦理表达转向对朴素爱国情感抒发,第二次则是近期向主旋律价值观的阐释与输出努力转变。文章通过对成龙的影片中的情感表达、精神母题与价值取向进行梳理与探询,以管窥香港电影与内地从离岸到融合的过程中,在伦理体验、身份塑造、国族认同等多立面上发生的变幻与发展。
功夫喜剧 国族认同 主流价值观
成龙的电影作品一直是华语电影圈内的热点与“爆款”,他在影片中颇具个人特征的表演风格、简洁明快的动作剪辑与主题思想,使他早年在圈内获得了“大哥”这一尊称。事实上,之所以成龙被称作“大哥”,是因为在他的角色往往在片中传递古道热肠、惩恶扬善、侠肝义胆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以及易于被观众接受的朴素爱国情感,从而令这些个性鲜明的角色被人所尊敬。不过,从成龙自出道以来的创作历程来看,虽然他的电影中的功夫元素与喜剧特征一直以来是最大的票房卖点,但其所蕴含的主题思想和价值内涵却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从他早年在香港的出道之作、蜚声国际后的大制作以及后来在内地与香港合拍框架下的一系列新作中,能够管窥并梳理出成龙影片价值转向的主线与内涵重塑的系谱。如今,香港回归已然20周年,通过对成龙的影片中的情感表达、精神母题与价值取向进行梳理、探询与研究,有利于我们管窥香港电影与内地从“离岸”到融合的过程中,在伦理体验、身份塑造、国族认同等多立面上发生的变幻与发展。本文以成龙新作《功夫瑜伽》及其他近期的作品为切入点,逆向溯源,试图将这一转变与重塑的脉络在成龙自出道以来作品中贯穿。
2017年春节档上映的《功夫瑜伽》,一共取得了17亿的票房成绩。从该片的市场表现上来看,作为春节档期的开画之作,上映之初中规中矩,后期依靠超高上座率逆袭《西游·伏妖篇》,成为登顶春节档票房榜首的影片。这意味着,影片依靠环游世界、嬉笑打闹、考古寻宝等观众所熟知的“成龙元素”,验证了成龙的创作习惯在当下市场仍然旺盛的生命力和接受度。该片由唐季礼导演,成龙领衔主演。《功夫瑜伽》中,成龙饰演的考古学教授杰克致力于文物的发掘与保护。他与一名自称埃什米塔教授的印度女子一起去找寻“摩揭陀国”失落的宝藏,因为这既能解开千年前印度遣唐将军失踪的谜团,而且聚焦“一带一路”经济带。于是杰克团队一同踏上了寻宝之路,在经历磨难后,终于发现了古代“摩揭陀国”的宝藏。然而,真正等待着他们的并非取之不尽的黄金,而是大量保存完好的宗教、医学等古代文献。最后,连影片极力塑造的反派角色兰德尔也与主人公们冰释前嫌、共护文化瑰宝,将古代中印友好的佳话加以传承。
可以看出,从内容和题材上来看,近年来的成龙电影正在不断向主旋律靠拢。包括《功夫瑜伽》在内,最近的《铁道飞虎》《天将雄师》《十二生肖》《辛亥革命》等影片皆是如此,其主人公要么保家国以御外侮,要么惩盗窃以正视听,甚至滑动至与一般的主旋律影片并轨的叙事模式来复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例如说,在《铁道飞虎》里,由成龙扮演的抗日游击队队长马原带领着几名铁路工人,白天在枣庄火车站工作,晚上化身为游击队与日军周旋,阻击日寇。《天将雄师》中,成龙则饰演被人陷害后发配到雁门关修城的西域大都护霍安,与保护罗马帝国小王子的护卫卢魁斯结为好友,以对抗野心勃勃的大王子提比斯所率领十万压境大军,最后霍安在各民族的帮助下战胜了提比斯。《十二生肖》则顺应了中国追回海外国宝的政策与法律要求,成龙在影片里饰演了一名国际大盗,在与一批文物贩子夺宝的过程中,他的爱国之心逐渐被唤醒,最终冒着生命危险为祖国追回文物。另外,由成龙联合导演的《辛亥革命》,则将视线投向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着重大历史变革的时刻,他在片中扮演了英勇善战的革命前辈黄兴。
成龙电影不论是哪位导演执导,也无论什么题材,成龙主演的标签就已足以确立这部影片的商业卖点与风格基础,使观众获得确定的观影预期。虽然成龙在电影创制中常常肩负导演、主演、编剧、监制、武术指导等多个职务,但就“成龙电影”最为显著的呈现特征及其精神内核来看,就是它们贯彻了“功夫喜剧”的动作表演风格,以及承载了一定的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等等。因此,本文所谓的“成龙电影”,主要是将由成龙主演的影片作为考察对象。不过,成龙电影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当代华语乃至世界影坛仍然保持较高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创作早期形成的“功夫喜剧”所具有的鲜明表演动作风格。
“功夫喜剧”是传统武侠电影和喜剧电影结合的特有类型,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香港影坛。20世纪70年末期,成龙、袁和平、洪金宝等人,经过大胆地尝试,将武术、杂技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功夫喜剧”成为那一时期最受观众喜爱的电影类型①。在贾磊磊看来,他的“喜剧+动作”的谐趣武打片作品在中国武侠电影中独树一帜,是传统武侠动作电影与现代喜剧电影相互结合的成功典范②。陈墨认为:“功夫喜剧将李小龙式的真打硬斗还原成妙趣横生、令人眼花缭乱的杂耍功夫,将李小龙式的英雄传奇还原成世俗故事;将充满意识形态的教训和道德宣传的武侠电影还原成纯粹的娱乐形式;将喜剧表演引入传统的功夫电影之中,让剧中人物有了更多的艺术表演的余地。”③
70年代末,“功夫喜剧”成为成龙电影乃至香港电影最显著标签之一。其特点是借助道具将武打动作夸张化,通过诙谐滑稽的动作设计来弱化殊死决斗时的紧张感,并以此突显主人公轻松幽默的人物个性。凭借这一具有程式化、类型化的创作套路,成龙奠定了“成氏喜剧”的风格与基调。不过,这时他的影片通过以功夫喜剧挟带传统伦理的创作思路获得成功,并没有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价值承载功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些影片是对传统武侠片中的兄弟情义、帮派恩仇、杀富济贫等精神思想的继承。比如《蛇形刁手》《醉拳》,宣扬的就是扶危济困、欺强不凌弱等传统价值观。在《蛇形刁手》中,成龙饰演的简福只不过是一介在武馆中打杂的伙计,当他目睹隐姓埋名的蛇形门长老白长天被市井无赖欺负时,却路见不平、出手相助。又如,他在《醉拳》里饰演的黄飞鸿,虽然是一个惹是生非、嬉皮笑脸的青年,后来折服于苏乞儿的武艺拜其为师,最后救家族于危难时刻,成长为一位见义勇为的青年。从精神承载、伦理宣扬的功能性乃至叙事模式上来说,它们与历史上大部分功夫片、武侠片是一致的。不过,在“功夫喜剧”的包装之下,成龙的英雄形象塑造往往带有更接近市井小民的性格特征,他们偶尔偷奸耍滑、妙语连珠,从而使影片在人物性格塑造上更加丰满,亦更接近观众日常生活的体验与经验。因之,这种“接地气”的故事与角色处理方法,使这些影片所挟带的传统“侠义”观念与观众之间在传播接受的过程中更为顺畅。另外,不管是《笑拳怪招》的复仇故事,还是《师弟出马》的惩奸除叛,都是这一时期成龙在“功夫喜剧”与传统伦理价值相结合的代表之作。
经过成龙等人的努力,“功夫喜剧”已然成为动作片与喜剧片相互交叉渗透的亚类型之一。此后,成龙开始尝试在“功夫喜剧”的外衣下,包裹不同的精神内核。从《蛇形刁手》《醉拳》等奠定他影坛地位的代表作来看,它们遵循的依旧是在传统武侠片所“规定”的价值框架下的拔刀相助、惩罚奸佞、除暴安良等元素垒砌,而有所区别的正是在于成龙利用“功夫喜剧”的外壳赋予了它们与传统武侠片截然不同的呈现形态。万众瞩目的“功夫喜剧”已然被研究者反复吟味,而成龙电影中扁平、质素的价值宣教与伦理灌输功能及内容却往往遭到忽视。虽然“功夫喜剧”是成龙电影获得商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管是何种电影类型也会有审美惊奇、审美接受与审美疲劳的不同时期。所以,恰恰是成龙电影中饱满而富有支撑力的价值内涵才是其长久不衰的保障。
但是,成龙电影中承载的价值内涵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稳定的,在成龙在香港影坛正式出道的四十余年间至少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与前述《蛇形刁手》《醉拳》等更为靠近传统伦理的影片有所不同,在80年代的《龙少爷》《A计划》与此后的《A计划续集》等一系列影片中,成龙开始在影片中注意表达更为宏大的朴素爱国情感,这成为他创作生涯中在影片思想主题的第一次转向。也就是说,影片的思想内核从以往的传统伦理表达向爱国情感逐渐转移。《龙少爷》是成龙第一次执导影片,背景设定在清朝覆亡之时,讲述了偷运国宝并与洋人交换利益的大内总管被代表正义的成龙一伙所铲除,从而确保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的故事。《A计划》系列则讲述成龙饰演的马如龙与港英政府在废除水警问题上产生争执,最后他与他的朋友们纠弹邪恶、打击贪腐,保护了香港的安宁,压制了贪婪的外国人。如果说,《龙少爷》依然部分在惩奸除恶的传统伦理框架下进行表达,那么《A计划》则对他的朴素爱国情感的呈现已然相当明显。例如,在《A计划》中,有一段长达4分钟的他怒斥港英政府高级官员的场景,并且把英国人与海盗互相勾结的恶行斥为“卑鄙无耻”。
需要注意,之所以将这一爱国情感称之为“朴素”,是因为它一旦与香港的本土主义嫁接就在视野与思想上表现出了狭隘与局限。将时代背景设置于20世纪初年香港的《A计划》,提供了爱国情感与本土情结相互对冲的博弈场。例如,片中英国高级官员同意马如龙重建水警队时,马如龙立刻表现出了合作与媾和的态度。又如在《A计划续集》里,革命党人要求马如龙加入革命团体,“一起挽救中华民族”。马如龙的回答却是否定的,因为他要“保障香港的每一个人都安居乐业”。这说明,此时成龙电影的朴素爱国情感表达,依然被限制在香港本土情结的范围内。当爱国情感与本土情结在片中“合理冲撞”时,后者成为两者之间的优先选项,本应崇高的爱国情感瞬间显示出了它的“朴素性”。
即便到了1995年的《红番区》中,影片也试图通过叙述一名美国华人青年由于钻石抢劫案被迫与流氓联手对付黑帮的故事,来彰显这种爱国情感与域外地理空间嫁接时所体现的适应性。此前,他的《快餐车》《龙兄虎弟》等影片也立足于表现正义善良的华侨华人在国外扬眉吐气的旨趣。如果把成龙电影比喻成一辆能够装载不同价值观念的“卡车”,那么从这一时期之后,它开始满载着爱国主义思想、本土主义情结与传统伦理观念在华语影坛里昂然奔驰。其创作模式就是,利用功夫喜剧的外衣与易于理解的情感逻辑来支撑影片的精神内核,并且尝试将这一理念向外国输出。例如,在中美合拍的《功夫梦》中,美国小孩德瑞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功夫,发现中国与国外宣传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这名美国小孩在向成龙学习中国功夫的过程中,领悟了中国武术的魅力和高深的处世哲学。这部影片无论从电影工业合作或文化竞合输出的角度来看,都可算是成龙电影中较早的“标准件”。可以说,这部影片在产业上伫立于中美合拍的前哨之位,同时也是理解此时成龙电影创作模式的绝佳范例。
接着,以他执导并主演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献礼影片《辛亥革命》所构建的宏大历史叙事为显著转折,从《十二生肖》开始,他在影片中通过主人公保护文物的经历来揭露民族的惨痛创伤历史,阐释并输出主旋律价值观。由于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导致中国大批珍贵的文物流落海外,该片围绕四尊十二生肖兽首的海外公开拍卖展开剧情,最终成龙使文物全部回归中国并上交给中国政府。在后来的《天将雄师》中,已经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成龙则开始在影片中聚焦“一带一路”概念并为之进行宣传,虚拟了一场古代中西文明相互摩擦冲突的大战。但是,片中“中西对立”的矛盾在影片开始不久,就通过成龙的角色与代表善良正义的西方人联手而转换为“正邪对立”,并且“邪不压正”,正义的汉人、少数民族以及罗马人以生命的代价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和平与安宁。
如果说成龙在他的早期影片如《A计划》中试图通过爱国情感的宣泄来激发观众的民族主义情感,那么很显然他在近期的影片中对这一操作逻辑已有所保留。因为在“正邪对立”的叙述框架下,如果以国别为阵营来分配正邪属性,则势必使影片的价值观愈显得狭隘,不能适应他近期电影充分体现政府所提倡的主旋律意识形态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但这一“爱国主义”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主旋律乃至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要求下,也不应将中国与西方作为截然对立的两个立面进行塑造,形成过于尖刻的文化与民族对立。成龙显然能够在影片中妥善处理这一“二元对立”。如《功夫瑜伽》中反派角色印度“王子”兰德尔虽然最初一心只想要夺取宝藏,不惜以杀人、抢劫来达到目的,但是兰德尔最后却通过与杰克的一番谐趣打斗,认同了杰克倡导的“历史是属于全人类的”价值理念,皈依向善并与大家和谐共舞。另外,《铁道飞虎》虽然将影片故事置于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却以“功夫喜剧”的方式适当软化了对立与仇恨情绪。一言以蔽之,在成龙电影的主旋律创作中,那些十恶不赦、面目狰狞、凶暴残忍的敌人形象几乎是缺席的。成龙似乎不需要用霍元甲、陈真或者叶问这样“战意昂扬”的元素就能框定在主旋律创作中的“安全区域”,并且也无意在片中体现某种令人亢奋的种族主义图谱。这意味着,在香港与大陆电影合拍的趋势之下,成龙以创作来摸索尝试,找到了用他所擅长的“功夫喜剧”与当下意识形态宣传进行融合的方法与路径。
从另一方面来看,从《神话》开始,成龙的影片里就不断出现考古、盗墓以及保护文物等元素,成龙几番在片中塑造了爱国的考古学家与良心发现的“古墓大盗”。《天将雄师》通过一场跨国古代遗迹的考古活动展开叙事,《十二生肖》保卫十二铜兽首的故事自毋庸赘言,《功夫瑜伽》的主要线索亦是寻找作为古代中印两国友好见证的失落宝藏。更重要的是,成龙通过在电影中对盗墓行为和文物保护之间价值观念冲突的讲述,找到了一条不必制造战争冲突等尖锐对立就能使观众对“爱国”与主旋律价值观进行认知的便捷途径。
成龙电影是从香港走向内地与世界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香港电影的文化精髓在成龙作品中得到了绝佳体现,“功夫喜剧”的生命力即是明证。回顾历史,香港经历了英国一百年的殖民历史,导致香港的本土文化形成了大众化、通俗性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聚集形态④。其中,中国文化在香港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香港回归前由于港英政府意识形态宣传的偏差,使香港人对内地在一定程度上抱有成见,他们也随着地方经济建立起了本土意识。1984年,经过中英谈判解决了持续百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使香港人的族群身份体认得以明确。1997年回归之后,即便“杂音”偶尔喧嚣,但香港人却从法律上拥有了更为确切的国籍和身份归属。我们可以从此发现成龙电影与历史相互照合的理路:成龙在《A计划》中塑造了对英国人贪污腐败恨之入骨的马如龙以及《快餐车》里勇救外国美女的正义华侨的爱国形象,虽然在1998年的《我是谁》中经历了暂时的身份迷惘与“失忆”,但最近成龙却以《警察故事2013》中的内地公安干警以及《神话》《功夫瑜伽》里的爱国考古学家等承载着厚重却焕然一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份再度登场。成龙电影中的主人公身份转换,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人身份认同变幻的微缩景观。香港人文化身份归属的变化脉络,同时也成为成龙电影中价值转型与意识形态重构的深层文化动因。
可见,自成龙以《蛇形刁手》《醉拳》等片蜚声影坛以来,他的影片中所承载的价值内涵与主题思想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以20世纪80年代的《龙少爷》《A计划》与《A计划续集》为代表,影片的核心内涵从以往所侧重的传统侠义观念转变为朴素爱国情感。第二次转变则是在他执导并主演《辛亥革命》之后,成龙电影开始注重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倡导主旋律,《十二生肖》《天将雄师》《铁道飞虎》《功夫瑜伽》等影片尽皆如是。需要指出,影片在核心价值上的转变并非骤然转向,而是有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同时,转变也并非意味着对前者颠覆,因为这些能够相互协调、包容的价值观念之间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成龙电影主要是以获取票房利益而制作的商业电影,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各种产业运作的手段来实现盈利,它的功能并非专注于宣传某种思想主题、提倡某种价值体系,不可能无休止地在每部影片中都充斥着关于意识形态的辩护与言说。但是,如果将所有成龙电影作品看做是一幅可供延展观赏的卷轴画,那么各个作品所蕴含的不同主题内涵正如散点透视般布局于画中,它们之间所构成的景深差异,形成了能够联动、定位、辐射其他作品的“价值生态”。
从更大意义上而言,成龙电影中价值转向与重构的系谱,与香港人在本土意识、地域身份、家国体认
[ ][ ]等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构性。20世纪80年代后,成龙电影开始在香港、内地与世界获得极高的声誉,几乎同时,香港社会上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逐渐向“分离主义”靠拢与演化。此后,成龙电影中所表达的基于本土情结的朴素爱国情感,也恰是在香港本土意识中埋藏至深的对祖国的向往的精神底流。近来,成龙的主旋律创作,正是对弥漫在香港社会上的“失败主义”与“分离主义”思想上的有力驳斥,代表了涵盖“建制派”“温和民主派”以及内地移民在内的更广大香港人的价值取向与思想观念。大而言之,对成龙电影中主旋律价值观的形成路径进行研究,是导正香港本土意识,并将之与“分离主义”思想剥离的通途之一。
不过,从成龙电影在主旋律创作中的局限性来说,“功夫喜剧”或是“考古题材”都不一定是价值宣贯的最优选项。例如,《功夫瑜伽》中本来恶贯满盈的印度“王子”兰德尔跟随众人在一曲《神话》之下弃恶向善、翩翩起舞,使这一突如其来的善恶转向诚如“神话”般不可思议。又如,《天将雄师》中的古城考古行动,却因两名队员因霍安事迹所感动而决意不令古城“受到文明的污染”,使古城再次尘封,用来为虚构的故事披上历史真实的外衣。需要指出,影片应使用更为圆滑并且符合逻辑的影像风格和叙事手法来对这些情节进行处理,才能使得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艺术上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注释】
①Paul S.N. Lee. The absorption and indigenization of foreign media cultures a study on a cultural meeting point of the east and west: Hong Kong[J].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1(1):56.
②贾磊磊.成龙:用动作改变世界[J].当代电影,2014(3):38-42.
③陈墨.功夫成龙:从港岛走向世界──成龙电影创作历程述要[J].当代电影,2000(1):72-78.
④周毅之.从香港文化的发展历程看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的关系[J].广东社会科学,1997,(02):20-24.
本文系中国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电影的国家理论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5BC037)阶段性成果。
翟莉滢,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