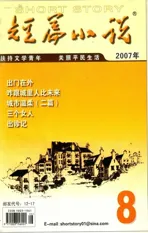锦瑟华年
2017-11-15毛胜英
◎毛胜英
锦瑟华年
◎毛胜英

那天吃晚饭时我一直在惦记一件事,吃好饭叫老高来帮忙修电脑。我的生活离不开电脑,因为每天我都要在博客上记载大事小情。也曾试过用手机备忘录来记事,可我根本不习惯使用它。老婆见我心不在焉,问我怎么啦。我说我要叫老高来修电脑,我还说我记得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来着,可没电脑,我记不起来。老婆剜了我一眼,瞧你那可怜的记性。
我今年四十岁,在一家海产公司上班,像芸芸众生一般有一个爱发臭脾气的老板;当然,我有妻子女儿。岁月裹挟着我朝前狂奔,沿途,我也丢三落四,这无可厚非。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并不是说我有多高尚,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闲钱来伺候这些玩意儿,但体内过剩的荷尔蒙还是让我拥有了另一个爱好——上网。五年前,我拥有第一个博客。慢慢地,我发现,博客竟然是最好的存储记忆的地方。
打小,我的记忆就有缺陷。母亲说我三岁时从家里移动的木梯子上摔下来,从此,我的脑子就出了点问题。母亲还说当时表姐寄住在我们家,家里狭小,没有多余的床,表姐就同我睡一张床。表姐温柔漂亮,喜欢猫,当时家里就养着一只黑猫。黑猫特别喜欢表姐,经常与我们挤同一张床。日子一天天过去,表姐总是翻来复去地讲着同一个睡前故事。她讲得津津有味,我听得有滋有味。
慢慢长大,记忆开始好起来,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在记事本的帮助下,在父母担忧的目光下,我的记忆发芽开花。虽说,相比于其他孩子,我的记忆力还是令人堪忧,这反应在我那可怜的学习成绩上。但有一点却让父母感到欣慰,我写作能力比同龄孩子好,我的想象力超级强大,它几乎弥补了我记忆上的缺陷。但是,严重偏科的我最终没能考上普通高中,我理所当然地上了职业高中,职高一毕业我就进入社会。干过许多份工作,每一份工作都不与人打交道。如今在海产公司上班的我是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上万次机械的运作,我根本不要担心我的记忆力,因为,机器会帮我记下一切。
家里买第一台电脑是因为当时上初中的女儿。女儿上初中,学习压力蛮大。她被我们宠坏了,打小她就习惯唤她老妈“小伙伴”,唤我为“大叔”。虽说她学习不咋地,但她快乐而自由,她买电脑是为了上网查作业的答案,她的志向是初中毕业后像我与老婆一样上职高,她在我面前特别强调她上职高是为了学做淘宝生意,她在我们面前保证将来她会闯出一片天地。妻子总是乐呵呵地听着女儿描述她的未来。妻子在科技园工作,各位别会错意,她干的是保洁工作,她十九岁开始工作,一晃这工作就重复了二十年。
是女儿教会我使用博客。刚开始时,我只是把这个平台当成我老婆,平时,我总是让老婆帮我记下每天要做的重要事件,对此,老婆总有微辞。自从有博客后,我就让它充当另一种形式的记事本。慢慢地,我还学会了在博客上存储照片以及写私密博客。
“今天,看到那么多银杏叶飘落下来,像一个个文字,我开始构思一篇文章的布局。”这是我博客上一篇日志的开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在博客上记录心情。如今,心情也成了我的“大事小情”。同时,上网写博客成了我每天回家必做的头等重要之事,我的每一篇博客形式几乎千篇一律:第一段记录当天的心情,第二段记下我第二天要做的重要事情。只是很奇怪,自从有了这个博客后,我发现我的生活中根本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之事。
“12月1日老妈来城里看牙齿,我要陪她去找商医生。”这算是我的“人生大事”了。只不过,这一件事,这两句话,可以重复出现在我博客上达两个星期之久,也就是说,那两个星期,我的“人生大事”只有这么一件。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当我再次温习博客上的内容时,这两句话像两个张牙舞爪的恶魔,在电脑上得意地望着我,我当场就把晚饭吃的馄饨给吐了出来。老婆喜欢在馄饨馅里掺些肥厚的五花肉,而我却喜欢纯瘦肉馅的,但自己不动手做吃的,我就不好意思特别去干预她。只是,每一次吃到馄饨馅里的五花肉,我就会想到老婆那肥厚的像丑陋伤疤的私处,然后会有一种叫做伤感的东西涌上心头。这也是博客给我带来的坏处,以前,我对老婆私处的记忆不会超过两个小时,而今,我却在那些“只有自己可见”的博客文章里一次又一次地读到这一句——“老婆的私处像肥厚的五花肉,更像一道丑陋的疤痕,与生俱来的疤痕。”
12月1日,老妈最终在我姐的陪伴下去找了商医生。我一不小心还是把这一件大事给忘得个一干二净。老妈打我手机的时候,我正跟老高在离家五十里地钓鱼。
本来,我是想在老妈面前表现一下的,结果还是被搞砸了。这事给我的打击非同一般,它甚至给我带来一个类似强迫症的后遗症——凡遇到自认为重要的“人生大事”,我会在博客上日复一日地记录,无休无止,即使那件事早已发生过。
秋末的一天,下班回家,发现老婆饭也不烧,灯也不开。平时不常回家的女儿也在家里,一双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
怎么啦?我问,有些不安。
我就知道打电话没用,女儿抢着说话,老爸,大叔来电话说,外婆病重。我们早上电话通知过你,你还说会早点回来然后同我们一道去乡下外婆家。
外婆病重?打电话?我说着就在电脑前坐了下来,这会儿,我有点后悔早上接到电话时没能第一时间在厂办公室的电脑上把这事给记录下来。
你想干吗?老婆平常不大发脾气,这一回却怒火冲天。
写博客。我打开电脑,准备记下这一件“人生大事”。
你,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写你那破玩意,快准备一下,大哥马上开车来接我们。老婆像天兵天将一般杵在我面前,双目怒睁。
写博客用不了几分钟,不误事。我边说边焦急地等待电脑开机,平时,电脑都挺配合的,在这关键时刻,它偏偏闹情绪。还没等到电脑开机,两双手架住了我的左右胳膊,老婆女儿合力把我架出家门。出门时,脑子里唯一记得一件事,我刚刚要写一件“人生大事”来着,一件值得我一遍遍重复记录的 “人生大事”,而今被老婆与女儿这一搅和,我竟然忘得个一干二净。
大哥木讷而不苟言笑。我根深蒂固地认为,这一类人是没有想象力的。对于这类人,这个世界是友好的?还是充满恶意?当我还在努力回忆我的“人生大事”时,岳母家所在的城乡结合村柳村就到了。去岳母家的路不是很好,我们只得把车停在村口,走路去岳母家。一下车,老婆就嚎开了,老婆肥厚的哭声使我清醒过来,我要记在博客上的是“岳母今日病重”。我不禁有些兴奋,像一个装有两万块的钱包失而复得一般令人兴奋,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兴奋的感觉了。
岳母床边围着许多亲人。老婆是岳母唯一的女儿,她扑上去抱住老人家的身子嚎啕大哭。她的声音肥厚而有质感。我有些不安,今天我的博客还没写呢,呆会儿我肯定会把这件人生大事给忘掉的。这可是难得的能让我兴奋与激动的人生大事。女儿也在一旁哭。我站在一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双手几乎没有搁置的地方。我得找一台电脑,当然,要可以上网,而在岳母家,我的这个愿望只可能是奢望。
岳母头发花白,眼睛紧闭,牙关紧咬,喉咙里发出粗重的呼噜声。有痰,排不出。很庆幸虽然我的记忆有问题,但我还是能记住亲人的容貌,我的大脑只是在记忆事情的时候才出现短路和故障。
大嫂与岳母的关系不好。她一脸冷漠地站在一旁,被她搂在怀中的孩子长着一张酷似岳母的脸。如果没记错,这个孩子叫李瑾。
老婆还在哀哀痛哭,我在一旁手足无措,大脑在这个时刻却异常活跃,我要找机会向李瑾要一张纸和一支笔,把盘旋在脑子里的大事记录下来。
我会写下:岳母病重,亲人团团围在她身边,老婆哭得很伤心,已经很多年没看到她掉眼泪了,这会儿看见,令我有些手足无措。岳母得了什么病,曾否住过院,我这会竟然都忘了。如果出门前温习一下博客文章就好了。
我走向大嫂身边的孩子,孩子红着眼,泪水却盈满眼眶,她努力不让它们掉下来。看来大嫂是强势的。
李瑾有些木然地望着我,她的眼神与岳母的一模一样。
李瑾,给姑父一张纸和一支笔。我说。
大嫂错愕地看了我一眼,遂让孩子去里间拿纸笔。老婆肥厚的哭声渐渐地哑了下去,我有一刹那间觉得眼前这一幕很不真实。李瑾拿来的纸与笔放在面前,脑子里却一片空白。这时候,老婆一声悲切地呼喊:“娘哎,你怎么可以就这么抛下我去了!”点醒了我。
我于是在纸上写下一行字:岳母去世。2016年某月某日。然后,我小心地把这张纸条折叠好装进口袋。
岳母火葬与出殡隆重而有序,老婆当然要在葬礼上充当孝子贤孙的角色。我也忙前忙后,一脸凝重。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慌了好几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电脑,同时,我还担心放在衬衣口袋里的那张纸条会不小心弄丢。因此,一有机会,我就会偷偷掏出纸条来读一读,要不,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在人多的地方,我好紧张,一紧张,我的记忆更加堪忧。
哭成泪人儿的老婆好几次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她的言外之意我当然懂:我怎么可以如此凉薄。岳母在世时相厚于我,如今她走了,我不落泪也罢了,至少老婆没能在我脸上找到一丝悲哀的表情。老婆当然不知道此时的我在想什么。不过,从公墓回来的路上,我注意到老婆偷偷地把一大把红辣椒从口袋里掏出来扔在路上。
农村办丧事较繁琐。等我从乡下回到城里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后了。很不幸,我弄丢了那张记着“重要人生大事”的纸条。不过,幸好,老婆在送我到车站时提到了这件事,老谭,我还得与大哥商量妈身后事,你与女儿先回城吧。老婆双眼红肿,布满血丝,我有些担忧她眼睛会不会发炎,红辣椒的威力不可小觑。老婆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又把她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这会儿,我总算明白了她的意思,那一瞬间我非常激动,要知道,我已经为丢了纸条一事烦恼了整整两天。在回城的车上,我一直在心里默念着四个字:岳母去世。一个半小时后,我最终在博客上写下这四个字,那一刻,我浑身舒坦,千百条血脉按部就班在体内安分守已地工作,那天晚上我也睡得特别香。在乡下奔丧期间,我几乎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
老婆从乡下回来对我说的头一句话就是,老谭,这么多年,我才知道,你是铁石心肠的。对于老婆的评价,我不以为然。老婆换了一个话题,老谭,你帮我在你那博客上记一点东西。什么事件,老婆大人尽管吩咐。我尽量掩饰自己不合时宜的高昂的兴致。
大哥欠我十万元。老婆闪烁其辞。虽然我很有兴趣知道大哥为什么会欠她十万元钱,但我还是闭紧了嘴巴,老婆心里存不住话,总有一天,她会一五一十同我讲。
日子一天天过去,博客内容一天天增多,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老婆的事情,我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查看以前的内容。而且令我可悲的是,写博后我那本来就软塌的记忆力有很明显的退步迹象。
刚开始写博的日子,睡前我总要做一件事:把记在博客上的所有事件从头到尾温习一遍,那时东西少,温习不会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可是现在,我根本不可能把所有博客内容都温习一遍。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活在一种深深的恐惧当中。虽然如此,我还是一下班回家就坐在电脑前写博客,同时,我尝试着把一些博客文章公开。
公开文章后第二天,博客上就有十几个陌生网友留言与评论,其中一个网名叫海的女儿的评论让我眼睛一亮,她说,不错,还挺文艺范的。文艺范。这三个字瞬间点亮了我的眼睛。于是,我回访了她的博客。出人意料的是,她博客上一点内容都没有。她在线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许是为了排遣那无边无际无时不在的恐慌,我同她打了个招呼。

你好,我是失忆人。失忆人是我的网名。
你好,失忆人。海的女儿回应。
海的女儿好,我有些激动,为什么你的博客上没有一点内容?
我很懒,海的女儿道。
哦,我从她的回话当中发觉她对我不感兴趣。
于是,我回到自己博客上,开始温习以前的内容,无论如何,这是我睡前必定要做的功课,即使成效非常微小,我还是要一次次浸淫其中,很多时候,博客更像是我的情人,它让我欲罢不能。这一次,我把我以前的很多条博客都设置成公开。随着那么多篇看着僵死的博客文章被设成公开,陆续的,一条条新消息渐次冒上来,像一条条深海的鱼,游到水面上来冒泡。我把那些消息逐一点开,发现全是海的女儿的评论与点赞。
谢谢你。我同在线的她打招呼。
不用谢,你的想象力让人着迷。海的女儿说。
受到她的表扬,竟然有些激动,我主动加她为好友。
谢谢你加我为好友。她反应很快。我继续看博客,知道有一个网友陪着我看文章,心情大好。
大哥,海的女儿跟我打招呼。
你说。我飞快地打字,习惯了被女儿唤为“大叔”,这会儿听到这声“大哥”,觉得特别亲切。
我想忘掉一个人,但我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能把他给忘掉。海的女儿说。
一个女人,一开口就对陌生男人说这种话,我不禁觉得这个女人有些不正常。我决定不理睬她。
海的女儿倒也识趣,见我不回应就下线了。
那天睡前我写下一篇博客文章:今天我加了第一个博友——海的女儿。
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在网上遇到海的女儿。也陆续有人在我的博客上点评点赞,对那些恭维的不着边际的点评,我提不起一点兴趣,我开始有点牵挂海的女儿。
有哦。主丧诵一句颂词,我们一干人就唱和一声。躺在大厅正中门板上的是我父亲,他走得突然。
接到乡下姐姐报丧电话时我正在上班,安排好手头工作后,我第一时间冲到了厂长办公室,因为他桌上有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
我要上会儿电脑,有很重要的事。我一脸凝重地对一脸愕然的厂长说道。令人意外的事,厂长没有啰嗦一句话就让我上网了。我在博客上写上一句话:今天八点四十一分,接到姐姐电话,家父去世。然后我仔细地搜索了一遍近一个月来写的博客,没有一条有关父亲病重的消息。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来,家父是猝死。我于是在刚刚写的博客上添上一句,系猝死。我起身,表情轻松,脸色红润。我说,钱厂长,家父去世,我要请假一周回乡下奔丧。钱厂长一张嘴巴张得大大的,他肥厚的下巴几乎要掉下来。他的下巴让我想起了老婆的下巴。
有哦——主丧颂了一大段逝者的丰功伟绩后结尾总要添上一句类似于反问,又类似赞叹的“有哦”,我木然地应了一句。脑子里却在极力搜索有关父亲的印象。父亲生前对我如何,他有没有打过我,我有没有跟他顶过嘴,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他对我有什么样期待?
年迈的老妈轻轻拉了拉我的手,姐红红的眼睛落在我身上,我连忙喊了一句:有哦——
喊完我才发现,一屋子披麻带孝的人只有我一人喊了这一句,突兀而可笑。这个时候我真的想笑,目之所及是飘飞的纸灰与一灵堂的乌烟瘴气。最终,我把目光投在那只刚刚被宰杀的公鸡上。这时候,我注意到身后传来一个不友善的目光,它来自老婆。莫名其妙一阵心慌,这时候绝对不能笑,我应该痛哭。可是,我却怎么也哭不出来,相反的,这时候的我只想笑。而且,我还很想在电脑上写博客,我有很重要的东西要记下来。
整个葬礼下来,我强压着想笑的冲动,并且在老婆不解的目光下感到一阵阵惭愧,继而又在老妈与老姐宽容的眼光下释放着惭愧。大冷天,衬衫却被汗水湿透了。
一切停当后,我又一次与老婆拥有二人世界,我相当累,只想睡觉,睡上个三天三夜。有一个意识很强烈,去他妈的人生大事,去他娘的虚弱记忆,老子不想记了,天老爷还能怎么着我。有时我也想过,记忆力不强也有它好的一面。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那么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崭新的一天。比如,当他看到一树金黄,二裂银杏,浪漫棕色的法国梧桐叶,红色的枫叶,他会惊呼,哇,深秋了,真美。第二天,当他又一次看到一树金黄,二裂银杏,法国梧桐叶,红色枫叶,他会再次惊喜,哇,深秋了,真美,你看那树金黄,你看那些被歌德赞美过的银杏叶,真美。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迷恋过歌德。
老婆忙了一天,当然也累,但她却认认真真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不笑,现在你可以笑了啊。我抬头看了眼老婆,累得不想说一个字。失忆是痛苦的,但记忆同样累人。这时候,我想起海的女儿说过的话,失忆人,我想忘掉一个人,你能告诉我方法吗?这一刻,我深刻地理解她的痛苦。那一份记忆应该重达一吨、两吨、三吨,终有一天,她会被那段记忆压垮。
老婆边脱衣服边说道,我就说,你是铁石心肠的。这话一点不假。
奔丧回来后,生活回归机械的重复,没有“人生大事”要我记录,我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像我的记忆力一般慢慢枯萎。
有空也看看书,看同一本书,就如小时候听表姐每天讲同一个睡前故事。有一天,我在博客上抄录歌德的《二裂银杏叶》,并把这篇博文设为“公开”。
生着这种叶子的树木/从东方移进我的园庭/它给你一个秘密启示/耐人寻味,令识者振奋/它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在自己体内一分为二?/还是两个生命合在一起/被我们看成了一体?/也许我已找到正确答案/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难道不感觉在我诗中/我既是我,又是你和我?
我把歌德的诗上传到博客的当天晚上,海的女儿第一时间在我博客上点赞。我竟然有些激动,因为她说她也喜欢这首诗。于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她在网上聊天,夜深了,道别前,海的女儿又一次问我,失忆人,我还是想问你怎样才可以忘掉一个人。
怎样的一个人?我问。
一个我喜欢的男人。海的女儿说。
你喜欢的男人为什么不去追,还要选择遗忘?我不禁对造物主的捉弄感到一丝伤感。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为了保住记忆而千方百计,而有的人却为了不能遗忘而痛苦万分。
因为我未婚,他却已婚。海的女儿说,我以后会有自己的生活,因此,我准备把那段记忆遗忘。
那很简单,你把你与他的事写成文章传到博客上,每天都上传,一段时间后,我相信你会彻底地忘记他。我说。
博客的存在最终是为了忘记,而不是记忆。就像人的生存最终是为了死亡,而不是永生。我对海的女儿说道。
那以后有三天我没有上网写博客,我觉得没意思。三天之后,我终于还是忍不住上了博客。海的女儿不在,但我的博客上有她私信:大哥的忠告很有用,我把他的事记在了博客上,我每写一点,内心的痛苦就减轻一点,谢谢大哥。
无聊透顶,别人的事关我屁事。我只想在这一刻关了电脑,去他妈的记忆。
大哥在?海的女儿同我招呼。她上线了。
在。我迟疑了一刻,然后回了一个在字。
大哥不开心?
忙。我懒洋洋地回了一个字。
可是,我还是忘不了他。今天我右眼皮一直跳,想起他的善良、他的坚持、他的多情,我流泪了。海的女儿说。
你流泪了?我的心触动了一下,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流泪了。
流泪是什么滋味?我像一个傻子一样问。
海的女儿传过来十个红色的问号。我看着这些鲜红色的问号发呆,却不知道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老婆在岳母葬礼上用红辣椒催泪的事突然在脑子里跳出来,对于这一件事,我竟然轻而易举地记住了。
出去参加同学聚会的老婆回来的时候我还没睡着,老婆在我面前大大咧咧地脱衣服,满身的赘肉,她在我面前说同学聚会上发生的趣事与在聚会上得知的某个老同学的不幸之事。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注意力很难集中,既然很快就会把这些事忘记,我又何必劳神费心地倾听。
老谭你耳朵聋了!我同你说话你一点反应没有!老婆忽然用力地甩了一件毛衣在我身上。
老婆的动作吓了我一大跳。
我就说你是铁石心肠的。老婆拿着一根牙签剔牙。我瞪着一双眼睛,大脑一片空白。
老婆,你刚刚讲了什么?我问。
老婆瞪大双眼,却不再吭声。房间里充斥着紧张的呼吸。她的呼吸与我的呼吸,紧张而充满了火药味。
你真是不可理喻。老婆甩给我一句话后气匆匆地进了卫生间。不一会儿,卫生间里传来抽水马桶的排水声,巨大的悲伤涌上心头,我用双手擦了擦眼睛,没有泪水。
深冬的一天,我头脑一热,答应了海的女儿的邀约。海的女儿与我同城,她说她会在民联路锦瑟华年咖啡屋等我。
民联路离家不远,我决定步行去见她。
二十分钟后,我站在了灯红酒绿的锦瑟华年咖啡屋前。从口袋里掏出纸条,纸条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二楼靠窗第二个桌子。
我徘徊在一楼,不敢上楼。年轻的服务生N次对我友好地微笑,他的记忆一定完好如玉吧。我忽然有了一个主意,招手叫服务生过来,附在他耳边吩咐了几句,他接过我手中的一张毛爷爷后喜笑颜开地拿着我的手机上楼。
在等待服务生下楼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开始后悔,后悔给的小费太多了。
有着完美记忆的服务生下楼来,他微笑着把我的手机还给我。手机上拍到的是一个瘦弱的男人,留长发,有着一双忧郁的眼睛,他正出神地望着窗外。对于这一张照片,我并没有感到意外。我刚刚叫服务生上楼帮我把“海的女儿”拍下来。
我向服务生道谢后头也不回地走出角落咖啡屋。我对自己说,明天我就会把这件荒唐事给忘记的。
令人可悲的是,第二天醒来,我根本没能把这件事给忘记。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接下去的日日夜夜,我都没能把这件事给忘记。似乎约定好的,那天失约后,我与海的女儿在好友一栏里删了彼此。这之后,我还是会忘记很多事,但我却记住了一件事:海的女儿是男人。同时,我心中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关于海的女儿的眼泪,既然海的女儿是男人身,那么她同我说的一切事情应该都是虚假的。
有一天半夜,老婆忽然把我推醒,我大哥是不是已经去世了?
这个问题很严肃,也很重大,我连忙上博客查找,找了许久未果,我博客上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大哥应该没有去世,他还欠我二十万元钱没还呢,妈死后,我们把乡下的房子卖了,大哥做生意急需钱,我就把我那一份钱还有存银行的一些钱借给他了。老婆只穿着内衣,在卧室里转来转去。
大哥他前段时间生病过吗?我问。
我记不起来了,应该没有。老婆鼻子上亮晶晶的,汗珠一个劲儿往外冒。看她急的,我不禁也有些着急。二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这时候,一篇内容简短的博客文章中的一句话吸引了我的注意:
大哥欠老婆十万元。
老婆,大哥只欠你十万元,不是二十万。我郑重宣布。
怎么可能,肯定是你记错了。老婆扑到我身边看电脑。
你自己看。我给她看博客上的文章。
这怎么可能。我明明记得大哥欠我们二十万。女儿眼见着毕业了,她想创业,正当用钱时候。老婆絮絮叨叨。
博客一般不会弄错。我一再强调。
这世上什么都会出错。老婆一脸认真。
同一时间,锦瑟华年咖啡屋服务生A正对服务生B说,那天,有个秃顶中年男人让我上二楼给坐在靠窗第三个桌子的客人偷偷拍张照,他当场就给了我一百块小费。这钱来得真容易,期盼老天爷再给我多一些这样的机会。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