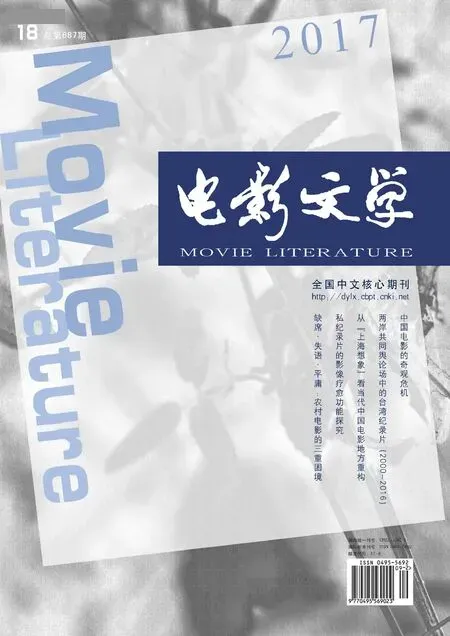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大明劫》的隐喻性叙事
2017-11-15魏改霞
魏改霞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1150)
隐喻代表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它渗透于人们的语言行为中,也直接体现在人们的艺术创造里。在电影中,隐喻性叙事也是广泛存在的:“隐喻不但存在于语言之中,还存在于非语言领域,如美术、电影和模式中。它们的‘文本’(text)就是一幅画、一组蒙太奇意象、一个具体模型。它们都可潜在地成为隐喻。我们将这些称为‘象征符号集合’。”王竞执导的独立电影《大明劫》(2013)便可以视作一部导演有意识运用隐喻的范例。讲述崇祯十五年明军爆发瘟疫的《大明劫》在上映之后尽管收获了几乎一边倒的褒扬评论,但其票房成绩并不理想。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大明劫》在市场上的受挫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被诟病为“电视电影”的制作特色,而电影就剧本而言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在视觉画面以及人物的简要对话中,导演隐藏了深层意涵和价值观念,电影剧情看似简单,冲突感不强,但正因隐喻的存在,使得电影的厚度得到增强,拥有一种触动观众心灵的强大力量。
一、隐喻性叙事机制与《大明劫》的艺术特色
隐喻从古至今的研究领域从修辞学发展到语义学,并最终进入了多学科研究的阶段。人们普遍接受,隐喻关系着人类的基本思维认知。这也就导致了在以叙事为主要艺术形态的电影中,隐喻也是一门常见的修辞或与观众的互动方式,帕索里尼甚至在他的《诗的电影》中认为电影的生存就是靠隐喻来实现的。除帕索里尼外,达德利·安德鲁、克里斯蒂安·麦茨等电影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也都将电影中的隐喻作为一个独立而重要的研究对象。
在电影中,隐喻性叙事机制首先来源于电影的记录性,电影的技术使其能够逼真地制造幻境,这种真实感构成了隐喻中由此及彼的“此”、由表及里的“表”,它们的存在是触发观众联想的关键;其次,电影又具有梦幻性,被认为是“白日梦幻”的一种,这也就意味着电影拥有和人的意识同构的表意机制,导演的表达、观众的理解都在银幕上完成,电影的画面引导着人们的意识流;最后,电影在给观众创造了一个幻觉化的视觉世界后,观众对具体问题的认知实现了重构,这也就是观众对电影主题意旨理解的完成。
电影《大明劫》讲述的是明末潼关一带爆发瘟疫,吴又可前去孙传庭军中医治病患,并最终写出《瘟疫论》的故事。电影的重点并不在表现孙传庭与闯军的交战等方面,加之观众基本都熟悉“传庭死而明亡”的结局,因此电影在戏剧冲突和悬念感的制造上是有欠缺的。
而《大明劫》的另一特色则是对史实的充分尊重,孙传庭与吴又可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又如从细节上来说,士兵的盔甲、三眼铳、子母铳和孙传庭的官服等都极为考究。甚至为了尽可能地贴合历史,电影也为这种对真实感的追求付出了在市场回报上的代价。整部电影的背景定位于明末这一乱世背景下,在满清虎视眈眈之下,国内又有天灾人祸,一是闯军造反,一是瘟疫横行。《大明劫》的制片及编剧谢晓东曾经表示,他们曾考据过明末时瘟疫的严重情况,如苏州原本的23万户人口在瘟疫的侵袭之下锐减为五万户,可见这是一场人力难以控制的劫难。主创们认为,有必要真实地再现这种惨烈的景象,迅速将观众带入到叙事语境中来,因此不惜动用大量演员来表现了焚烧尸体等情景。还有一些刻画死亡的镜头被删去。
在立场上,《大明劫》也持有一个相对中立客观的立场,尽管李自成本人并没有在电影中出现,而只是剧中人口中的“闯贼”“闯王”等,但电影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给予了必要的理解。电影拥有一个值得肯定的高度,即主创们并不忌讳以后来者的身份,静静地俯视明朝末年的悲剧一幕,而抛弃了非此即彼的,阶级斗争语境下的立场选择。由此可见,《大明劫》缺乏冲突,以至于缺乏娱乐性,但思想性深厚以及依托历史的艺术特征使得其有必要采取隐喻性叙事的方式,增强电影解读的余地,使影片散发人文历史的光芒。
二、《大明劫》具体隐喻性叙事管窥
(一)人物隐喻
《大明劫》中的两条叙事线索,即孙传庭的剿匪和吴又可的治病是相互照应的,两者一文一武,所带动的戏也一张一弛。甚至可以认为,就身份和终极使命来说,吴又可就是另一位孙传庭,而他“救人”这一行为对应的则是孙的“救大明”。吴又可是在军医赵提领染病身亡后明军不得不起用的并不被信任的医生。而孙传庭的出场则是被从天牢中释放,他也是崇祯皇帝在失去了熊廷弼、洪承畴等一干大将之后的无奈之选,崇祯对于孙传庭也是毫不信任,处处掣肘。而他们疗救的对象,那些已经七窍流血的人和大明朝,都已经是病入膏肓,医者回天无力了,孙传庭所在的军队只是大明朝无数崩坏的细胞之一。所谓兴衰,在电影中人看来不过是气数而已,而他们所做的也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隐喻并不意味着完全相同,孙传庭和吴又可两个人的个性与命运是迥异的。但是他们又是具有共同点的,那就是他们是无法用大善或者大恶来形容的,在秉承正直的人格之下,他们面对着无奈的世道又不得不忍受许多事情。吴又可为人谨小慎微,在面对瘟疫时破天荒地敢于打破成规,抛弃被视为经典的《伤寒论》,探索新的治疗方案;孙传庭看似冷酷好杀,在电影中从粮官开始不断杀人,但是他始终是一个试图力挽狂澜,将大明朝从风雨飘摇的境地中拯救过来的人。
(二)情节隐喻
在电影中,除了主干“医治”有所隐喻外,具体的叙事情节也有所指。如关于《黄帝内经》中“猛药”的一部分。吴又可对孙传庭解释说,人病到了这个地步就只能用猛药,反正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的就是后悔药。在听了吴又可的解释后,孙传庭面对朝廷不给补给,当地富豪吞并土地的景象,选择了用铁血手段掠杀当地富户(而之前孙传庭登记造册的方案却因火灾宣告失败,这里对应的是赵提领根据传统/章程治病失败的情节)。孙传庭痛心疾首地说:“你们四十三家都是害国之贼!斩首示众,家产充公。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在掠夺了富户的财资后,孙传庭又杀死了患病未愈的留守士兵,甚至连对吴又可本人的控制,也是孙传庭的“猛药”组成部分,然而受过吴又可医治的士兵却故意放吴逃跑。最终,孙的“猛药”还是没能换来形势的逆转。正如吴又可所看出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三)细节隐喻
在电影中还存在着一些由道具、服装等细节构成的隐喻。孙传庭和吴又可分别承担着救国和救人的职责,在电影中,孙传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身穿甲胄,电影中也专门交代了这副盔甲与他的渊源。当年孙传庭将李自成打得只剩一十八骑时,就是身着这身甲胄。而孙传庭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甲胄和自己都安享太平了。当妻子冯氏说孙传庭瘦了,甲胄需要改改时,孙传庭则表示不用改了,他坚信他解甲归田的日子不远了;而吴又可作为一个平民游医则是一袭布衣。在吴又可奉命前去给士卒看病后,他提出了用绒布来包裹面孔的预防方式,命令军中健康士卒全部戴上绒布,以免疠气通过空气传播进人们的口鼻。一时之间几乎所有的官兵们都以绒布蒙脸。如果说这仅仅是主创为了追求历史感而如实打造的话,那么从一个细节便可以发现,这一“盔甲”与“绒布”的对立是有深意的。那便是孙传庭去视察生病士卒时,手下让他也蒙脸,被孙传庭一把推开,因为孙传庭认为自己是主帅,“挂个破布成何体统”。而从孙传庭穿甲胄时说的话不难看出,甲胄被紧密地与“主帅”、与战争联系在了一起。两种穿着暗喻着两种身份的人对自己的不同保护方式,孙传庭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式便是杀敌建功,而吴又可则选择了流落江湖,以柔克刚。
三、以《大明劫》看隐喻性叙事与市场
如前所述,《大明劫》缺乏当下观众所热衷的视觉奇观,在电影中,称得上较能刺激观众眼球的乃是一些血腥镜头,王竞以一种几近残忍的方式展现了战乱和瘟疫盛行时期尸横遍野的景象,而这些镜头又被大量删剪,因而《大明劫》并不为院线看好,低迷的排片量直接导致了票房的不尽如人意。而因为剧本本身的扎实,电影依然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可以说,隐喻性叙事本身并不是市场失败的罪魁祸首,甚至通过对一些华人导演取得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作品的总结,如李安、张艺谋、姜文等人的作品,我们可以认为,隐喻性叙事恰恰有助于中国导演(或者是有东方文化这一背景的导演们)巩固和开拓市场。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强调稳重内敛的为人准则,也推崇含蓄收敛,意在言外这一传统美学观,在中国文学、美术经典作品中,这种含蓄精髓比比皆是。即使在当下,西方文化和西方电影处于强势入侵状态时,东方美学准则、东方美学表现形式依然能给电影人们提供养料。当中国电影人们对生命或人性等普适性问题进行思考时,将含蓄、厚重的表达方式带入电影中,将有可能更能触及观众内心,并引发人们长于电影院线放映时间的思考与热议。《大明劫》无疑便是使用了隐喻性叙事,将一种属于主创的史观乃至现实观点委婉地传达给了观众。
无论是电影抑或文学,其接受进入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引起接受者的共鸣。对于电影观众来说,他们拥有不同的思想情感、文化基础与人生经历。导演在故事情节中以隐喻来将原本复杂、暧昧、隐晦的历史问题,情感流动以及社会现实以极为直观的视觉听觉体验传达给观众,观众很容易在心理感应上被统一,产生一种与电影中角色相似的情绪体验。这正是隐喻的感染力所在。
除此之外,隐喻作为一座桥梁,它的表意实际上是双向的,人们既可以在这座桥梁上从喻体走向本体,同时也可以从本体走向喻体。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大明劫》是一部紧扣史实的电影,主创们并没有为了“借古讽今”,或突出某种艺术效果就牺牲了历史的真实,也没有简单地对史书上的记载生搬硬套,而是吃透、消化了历史,合理地将个人理念融入其中。对于原本并不了解明史的观众来说,也完全可以毫无窒碍地欣赏叙事,并因为这部电影而得到靠近史实的内容,并去了解更多与之相关的信息。这也正是隐喻对于开拓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的意义所在。对于并不在东方文化圈的观众来说,电影中的中医或明末官逼民反、崇祯君臣关系等都是并不好理解的,但当多重文本进行交互性阐释,叙事的段落与段落之间互为隐喻的时候,其中相通或者相同的关系、情感等便易于为这一类观众接受。使得电影在全球化这一经济背景之下站稳市场。
《大明劫》尽管票房成绩不佳,但是其在业界和普通观众中却得到了较大范围的认可,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隐喻性叙事带来的。在电影中,人物的角色设定、关系乃至情节之间都存在隐喻,它们在激发了解故事背景观众的深层次认同的同时,又为对这一背景陌生的观众起到了辅助理解、丰富其观影感受的作用。隐喻叙事为《大明劫》的观众带来了在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上的震撼感。可以预见到的是,在未来,这种以严肃态度和灵活艺术手法打造的历史题材电影,将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打开其在国内外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