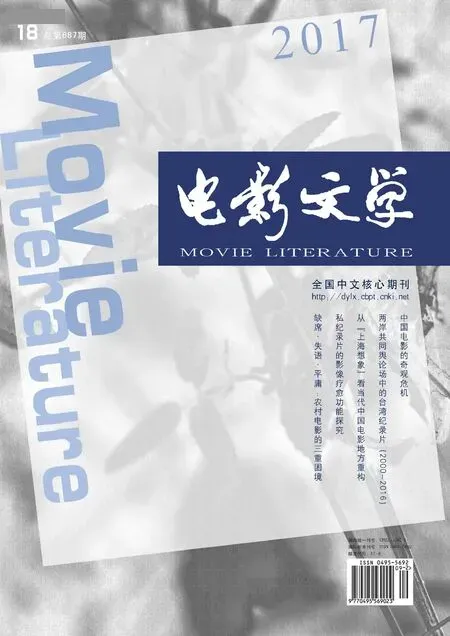浅析“单一空间电影”的典型叙事策略
2017-11-15张晶
张 晶
(奎屯市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新疆 奎屯 833200)
要讨论“单一空间电影”的叙事策略,就应对其做出较为清晰的界定。纵观近年来相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如“封闭空间电影”“禁闭空间电影”等概念被多次探讨,但这些研究同本文关于“单一空间电影”的研究,至少有两点不同:
一是概念的认定不同。本文关于“单一空间电影”的界定是:影片的叙事必须在单纯或唯一的空间内完成,且叙事空间未从内部被分割为多个明显不同的空间;而其他相近研究关于对象则并无此限制。
二是研究的重点不同。其他相近研究的重点在于“空间”,比如封闭或禁闭的空间在叙事、哲学或美学等范畴内的特征及作用,即“空间”是研究目的;而本文则是从整体上分析“单一空间电影”具有哪些典型的叙事策略,即“叙事策略”是研究目的。
综上,可以较为清晰地给出“单一空间电影”的概念:若某种影片,其叙事在单纯或唯一的空间内完成,且叙事空间未从内部被分割为多个明显不同的空间,那么即为“单一空间电影”。需要强调的是,此概念并非一种电影类型,仅为本文研究使用。
一、深刻立意下的人性揭示
因叙事空间的限定,“单一空间电影”难以形成复杂多样的情境,故常在深刻的立意下揭示人性之复杂,特别是人性的弱点,以激起观众的感性共鸣和理性思考,以确保影片的厚重感。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2007)是一部哲学思辨式的“软科幻”电影,其以深刻的哲学、新奇的假设、丰富的知识、单一的空间、严谨的逻辑为人反复称道,却鲜有论者从人性层面进行剖析。其实,人性的展现才是该电影的深刻所在。约翰对前来做客的七位学者敞开心扉诉说秘密,但因秘密有悖常识,其中四位学者恼羞成怒,甚至对约翰进行人身威胁。他们虽是人类中的顶级学者,却不无讽刺地符合“乌合之众”的特点:“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①
《终极面试》(2009)讲述了8位不同种族的精英在一间密室中参加某公司最终面试的全过程。4男4女在破解考题的过程中,由“合作—竞争”变成了“互助—互害”,生与死、善与恶发生激烈角逐。最后的胜出者的是一位冷静、机智、细心、警惕但又不乏善良的白人女性,她代表的人性善就是考试的答案。至于考试的谜题,正如CEO假扮的考生所言:“将你自己展现在你面前。”
在萨特的话剧《禁闭》中,三个人死后堕入地狱,地狱竟只是一间没有镜子的禁闭室。在这里,他们像生前一样尽情尔虞我诈、纠缠不清,无法和谐相处,却又只能通过对方的眼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剧尾那句“他人即地狱”成了存在主义的标志性观点,这句话若用来形容“单一空间电影”对人性的复杂特别是弱点的表达,不无贴切。
二、以人物为能指进行隐喻叙事
当叙事空间已被压缩到极限时,更多的表达只能在空间之外。“隐喻”作为表达言外之意的最常用手段,是“一种以彼物比此物并且隐藏含义的类比手法”②,必然成为“单一空间电影”的重要叙事策略。在单一的空间内,能作为“彼物”的无非是人物、有限的事物和叙事空间本身,其中,人物因身上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而成为表意最丰富的能指。
以《活埋》(2010)为例,男主角保罗对外界求助的过程,实际上隐喻着两层深刻含义:一是国家层面的战争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二是资本主义人际关系背后的利益本质。
从第一点看,保罗和伊拉克绑匪都是战争和国家意识形态双重冲突的产物。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却导致伊拉克普通贫民采用“恐怖”手段进行勒索和复仇,这是一种讽刺性隐喻,直指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激发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的直接原因。而一向对外输出西式民主和人权至上观念的美国政府,却在美国公民保罗的生死关头麻木冷漠,甚至反过来要求保罗保守秘密,以免国家形象受损,这种情节设置,再次揭示了美国政府的虚伪。
从第二点看,保罗多次强调自己身份低微,包括对政府工作人员说:“你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你说得简单。”对绑匪说:“我仅仅是卡车司机。”对救援行动的负责人说:“如果我是个外交官……我早就出去了。”在录遗嘱视频时对儿子说:“如果我是著名的壁球运动员,或者是穿西装上班的人……但是你能成为那类型的人。”甚至,在保罗的幻觉中也带有深深的底层认知——棺材盖被救援队打开了,保罗听见有人喊道:“平民已经找到了!”保罗对自身所处阶层的认知,代表着美国社会平民阶层的切身感受,他们在社会阶层固化的情况下很难打破阶层壁垒,但又侥幸地对政府、社会和下一代寄予希望。与保罗发生联系的各类人物隐喻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包括政府与公民的契约关系、熟人之间的淡漠关系、资本家与雇员的劳务关系等,都在各自的利益权衡中变得支离破碎。
“空间既可以具体的物质形式被感知、标示、分析、解释,同时还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的表征的观念形态。”③单一的空间以极简的存在形式隐喻了极复杂的社会,特别在人物上下功夫,以人物的身份设置、语言动作、人际关系等为载体进行隐喻叙事,令观众在无意识中产生认同或是开启思考,最终达到“文以载道”的目的。
三、以冲突和悬念的设置推动叙事
在空间环境几乎无变化的情况下,从视觉的奇观性上进行突破是相当困难的,只有尽量激发观众情绪的跌宕和脑力的思考,才有可能令观众注意力保持集中。冲突和悬念的巧妙设置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笔者将“单一空间电影”中的冲突和悬念设置归为四类:
1.以已知事实造成冲突和营造悬念。以希区柯克的悬疑电影《夺魂索》(1948)为例:两个年轻男子在住处杀死了一名同学并将其尸体放入箱子,之后邀请死者的亲友和师长来此聚会,还挑衅地将这个箱子作为餐桌使用。观众在以全知视角观看的过程中,会不断追问两个问题:箱子里的尸体会被人发现吗?是怎样被人发现的?这种悬念的巧妙之处在于倒置,把片中人物追寻到底的答案变成观众一开始就急于解决的问题,从而贯穿始终。
2.以敌对关系造成冲突和营造悬念。日本电影《红色密室》(1999)中,抽到王牌的玩家可以命令其他玩家在现有条件下做任何事,撑到最后的就是赢家。在单一的空间内,在几乎没有限制的游戏规则下,玩家必然会产生敌对互害行为,而那些有可能被变着花样呈现的日式血腥、暴力、性和死亡等情景就形成了一个个悬念,悬念破解的过程,就是观众内心深藏的肮脏欲望(如窥私、暴露、破坏、虐与被虐等)被电影白日梦所满足的过程。
3.以两难困境造成冲突和营造悬念。《梦想照进现实》(2006)中,女演员突然提出罢演,在宾馆房间与导演彻夜长谈。导演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果同意,那么自己无法向制片方交差;如果不同意,那么自己就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导演想方设法讨好和迁就演员,希望她能改变主意;后半部分,导演终于忍受不了她对自己的冷嘲热讽,进行了激烈的言语回击。导演身处的两难困境形成了贯穿始终的悬念:导演该如何是好?两人的意见能否达成一致?在微妙的独处氛围中,两人会不会坦白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4.以反常现象造成冲突和营造悬念。韩国惊悚电影《恐怖直播》(2013)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在一个狭小的直播间内营造出让整个国家陷入恐慌的大格局,每一分钟都令人提心吊胆”④。影片刚开始便以尹英华的视角设置了两次冲突:第一次是尹在节目中接到朴鲁圭拨打的热线,发现朴所言与节目话题不符,在引导对方无效的情况下,挂断了电话。第二次是被朴用技术手段强行连线,朴声称自己持有炸弹,尹当作是恶作剧并再次中断对话,随后听到了外界的爆炸声。这两次冲突都是由朴的反常行为造成的,从而成功地设置了一系列令人紧张的悬念:朴到底要说什么?他是不是真的有炸弹?出现爆炸事件后,尹英华会怎么做?
以上是“单一空间电影”中四种较为典型的设置冲突和悬念的例子。需要强调的是,仅在一个层面上保持冲突是不够的,冲突的强度或意义必须不断升华,如《恐怖直播》中尹英华与朴鲁圭的冲突最后升华为政府强权和公民尊严的冲突;仅设置一处或几处悬念也是不够的,悬念必须源源不断地出现,如《夺魂索》中,除了尸体在箱中形成的悬念外,还有主角与教授互相揣测形成的悬念等,这些悬念也促成了影片节奏不断变化,令观众始终保持关注。
四、“突转”的尾声与悲喜结局
“突转”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概念,“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⑤。在“单一空间电影”的尾部,往往会发生令观众意想不到的“突转”,一波三折地营造一个或悲或喜的结局。
《夺魂索》尾声处,在凶手认为万事大吉的时候,茹伯特教授突然又杀了个回马枪,通过假设和推理一步步揭露了凶手的罪行。一向宣扬“超人”哲学的他,在震惊之余,深深地为曾经持有的极端理念感到内疚,向窗外鸣枪引人报警。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尾声处,约翰与爱慕他的女同事在门外聊天儿,说出了自己的一个曾用名。之前扬言要将约翰送入精神病院的心理学家恰好从屋内出来,慌忙进一步询问,发现约翰竟是自己失踪多年的生父,一时激动猝死。经历丧子之痛后,约翰独自驾车离去。正当观众以为故事就此结束时,约翰在“坚守孤独”与“重新去爱”这两个选项中,选择了后者。女同事最终坐上了约翰的车子,两人在黎明的微光中驶向未来。
《活埋》尾声处,救援队负责人打来电话,激动地告诉保罗机器已经在实施挖掘工作了,令保罗重燃希望。突然,电话中机器的轰鸣声静了下来,救援人语气沉痛地向保罗道歉——他们找到的竟是马克·怀特的尸体——救援队负责人在之前口口声声保证早已获救的少年人质。在充满讽刺意味的道歉声中,保罗所在的棺材终于彻底被漏沙填满。
从观众心理的角度来说,“突转”有两点意义:一是“必需剧情的纠结逐场地继长增高,发展到最高度时轻巧地一下解掉。要纠结得难解难分,把主题重重封裹,然后再说明真相,把秘密突然揭破,使一切顿改旧观,一切都出人意表,这样才能使观众热烈地惊奇叫好”⑥。二是结尾的“突转”会加深观众的观影印象,可以有效地巩固其他叙事策略的效果。
同时,单一空间之外意味着另一个世界,主角最后必须做出两种选择:出去或是留下。若出去,意味着挑战新的苦难或是开启新的幸福旅程;留下则意味着永远承受普罗米修斯式或坦塔罗斯式的苦难。因此,“突转”的尾声之后,必然要形成一个或悲或喜的结局,不悲不喜的结局在这类电影中很难存在。
注释:
①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② 林骧华:《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
③ 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④ 陆姝:《调查韩国电影——产业篇:制作费票房全部公开透明》,腾讯网:腾讯娱乐,http://ent.qq.com/a/20140822/004062.htm?tu_biz=1.33.1.1。
⑤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页。
⑥ [法]波瓦洛:《诗的艺术》,任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