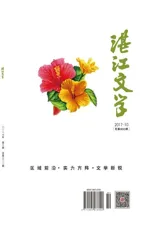山水相依
2017-11-14漆宇勤
※ 漆宇勤
山水相依
※ 漆宇勤
又想起了那个神话传说:赶着十万大山行走。
是的,有人手持鞭子,将十万大山像牛羊一样赶着在大地上行走。跨过岭南后,这法力无边的人突然愣了一下,打了一个盹,于是他所赶着的十万大山就如十万头牲畜蓦地停在了广西大地上。它们保持着吃草或行走的姿势,有的奇崛,有的呆萌,有的正扭头呼唤,有的睡意正酣。四蹄划拉着,一旁便多了条清凌凌的河流;双角顶碰着,前方便多了个洞穿的造型。
它们停驻得那么突然,那么随意。其中一些挨得太挤、跑得太偏,至今都只是草木的世界,重重叠叠的山岭中罕有人至。另外一些则更亲切很多,吸引着人们在自己的身畔或脚下穿行,观摩,安居。这些与人群亲近的山岭,主要集中在广西东北部的桂林。
这些年,我也曾见过一些山,涉过一些水。山水与城池,好像总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们相互隔离,相互疏远。但桂林不这样,桂林的山就是土著居民家门口的一块石头,就是放牧牛羊者帐篷旁的一头牛羊。这种感觉,在桂林的阳朔尤其明显。进入县城,迎面便是县城周边、县城内部耸立的石头山。游客在阳朔住宾馆,往往推门就是山,走上阳台,楼房背面竟然也是挨着石山。
似乎,是先人们由旷野里进入某处山峰林立中间穿插的空地,突然觉得累了,或者突然觉得欢喜了,于是就挨着大山的脚背歇一歇。到后来,干脆挨着山脚搭建个房子,长久居住下来,打渔、耕作,繁衍、生息。时间日久,一座寨子或城池便渐具雏形,一座与石山相互交缠依偎的城市便渐渐长成。这种城市与山岭相伴而生的地方,似乎并不常见。
不常见也没关系,有桂林作为代表就够了。这里的城市,这里居住的人们,似乎已经与山水融为了一体。他们可能一开始也曾抱怨山岭对生活的妨碍,也曾抱怨田土稀缺带来梯田耕种的辛劳,但渐渐就接受了现实、接纳了这无处不在的山和水。他们已经明白,是自己的祖先选择了这无数大小山峰之下的缝隙安居,而不是这无数大小山峰强行进入自己祖先的居所。
时间日久,他们渐渐又发现了自己司空见惯的山水,也有更多可爱之处。龙胜的梯田如同鳞甲披在壮家寨子的山坡上,漓江的清波正好养活着两岸以水为命渔猎的村民,而城池内外耸立的山岭,可以当作盆景罢。想到将屋前屋后顶着翠绿草木的石山当成盆景,桂林的人们就突然觉得自己身形高大起来,高大到随处可见的石山都只及自己的膝盖。这一刻,仿佛自己就是神话里那赶着十万大山行走的人,甩一鞭子,山就轰隆隆跑起来,有的调皮地跑远一些,有的撒娇地只稍微挪动一下脚步。
桂林山水的可爱之处,似乎更多地存在文字之中。那种旷世的美,几乎曾俘虏过所有对旅行稍有向往者的心。桂林山水甲天下也好,贺敬之的信天游也好,无论是教科书还是经典的语言里面,桂林都是一朵长盛不衰的旅游之花。但是它具体哪个景观哪个细节震撼着人心,似乎却没有一个很统一的说法。在我看来,桂林很好地切合了“山水”的组合,是可分可合合二为一的美丽“山”、“水”。仁者的山智者的水,在这里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呈现在你眼前,同时扑进你怀里,真实地体现了“山水”的本义。
我们乘着小小的游船沿着漓江行进。沿途总能见到孩子们在河边嬉水、女人们在河边清洗衣物,而老人赶着鱼鹰在竹排上、中年男人在浅水处甩开银亮色的渔网,钓鱼的人三三两两,青山绿水间安坐。一瞬间,我有些恍惚,似乎几百年前、一千年前,漓江两岸的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着吧。高强度的旅游开发这么多年,还没有将两岸在水里讨生活的人给改变掉,真好。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有个错觉,仿佛渔樵耕读的日子总是缓慢的,更像一种内心的历练,不急不躁,享受着大自然给予自己的一切:好收成、坏收成,甜蜜的果实、酸涩的果实。至于山水之外浮躁的城市生活,只要水面的竹筏还在悠悠划动,就离自己总会有那么三两米的距离。这种缓慢的生活参与,对于一个外来者,几乎不太可能真正进入。游客既然是游客,就成不了山水的主人。
——或许,有一种地方例外,那就是依托于旅游景区开设的风情街。在这些地方,游人本身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素不相识的人群里游走,累了就找个树下坐着,看其他的游人和店铺,没有谁会来打扰。丽江的古老街道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桂林阳朔的西街似乎也是这样一个地方。夜幕降临,住下来不急着赶路的人,将自己嵌入成为西街风景的一部分。闪烁的霓虹下,抬头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山已经在夜色里变幻了模样,而风吹来富有文艺情怀的音乐似乎可以弥漫到每个角落。最好不要扶老携幼,只和依恋着的人、知心的朋友,两两并行,沿着水边慢慢地走着。没有任何牵挂,也不为着任何一杯啤酒任何一种美食任何一件商品,兴之所至,行走驻足,整个人在夜色里柔软下来。
你不能不承认,跟着团队旅游的节奏与在城市里生活的节奏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时候的旅游并不是放松,更多地倒像是完成某种任务。似乎,来了这么一趟,带着长辈或晚辈来了这么一趟,便是一种义务的履行。真正的悠闲、沉浸之感,离得太遥远。
不怪你。整个世界都如此。前来旅游的人如此,在景区里生活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除了那些不参与旅游行业的农民与市民,那些稍与旅游相关的人们都是匆忙地谋生、仓促地表演,看见外国人来了,上前卖力推销的小商贩都多了许多,跑动起来的脚步也快了不少。但这个现象在桂林似乎并不如此明显。可能因为整个桂林社会都处于旅游大市场的缘故,也可能因为桂林旅游开发已久、早已成熟的缘故,这里更多了一些平和,没有外来者与本地人的明显区别。
这种冲突、对立的淡化,也体现在了当地的社会管理之中。十多年前我到桂林,朋友请我吃河鲜。在某处渔家乐遍布的河洲上,高大的宣传牌写着工整的告示:蚂蟥洲上的餐饮均未办理证件,也没有接受卫生检查,为了游客的餐饮卫生健康,建议大家不要到此类餐饮店消费。宣传牌就树在距离众多餐饮店几米远的河堤上,与食客爆满的渔家乐相安无事。
而这次到桂林,出了某个景点的溶洞口,又看见当地政府部门贴着大幅的告示:经核查,此处乞讨者均为职业乞讨人,建议游客不要给诈骗者施舍,以免上当受骗。在告示牌下,两个老人正安静地坐在那里乞讨。
这种社会管理的方式,有人会说是无能无为,但或许也会有人说是温和温馨。其实,骨子里,还是这个老牌的旅游城市,对冲突对立的某种自我调停与淡化吧。
在某种语境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定义一场旅行的来去前后:因为慕着某个场景图画,我们千方百计进入了其中,停留几日又离开,剩下这图景依旧在原处、在你生活之外停驻。
有很多城市或乡村,来之前你喜欢得不得了,抵达之后逐一赏玩的几日也依旧是乐在其中。几天之后回到自己的惯常住处,这曾亲近过的山水便又依旧变回了书本里的图画,并没有留下什么实质的东西。但你明白,在你回家之后,桂林龙脊梯田前的某株杂草因为你的踩踏和拔扯而断了枝叶,确实真实地存在。那草木折断处汁液的芬芳,有着天然的美好感,长久在半梦半醒间氤氲。
你知道,这茂盛的桂林,这水洇的桂林,这盛名之下的桂林,曾消纳你的三天时光、曾承载你的三天重量。
你曾来过,你曾由画外到画里。你曾触摸,你曾由远而近观照。
漆宇勤,在《诗刊》《星星》《人民日报》《绿风》《诗歌月刊》《青年文学》《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雨花》等全国500余家刊物发表文学作品1300余篇次,有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出版有个人作品集《无法拒绝》《向阳光微笑》《安源娃娃安源红》等8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