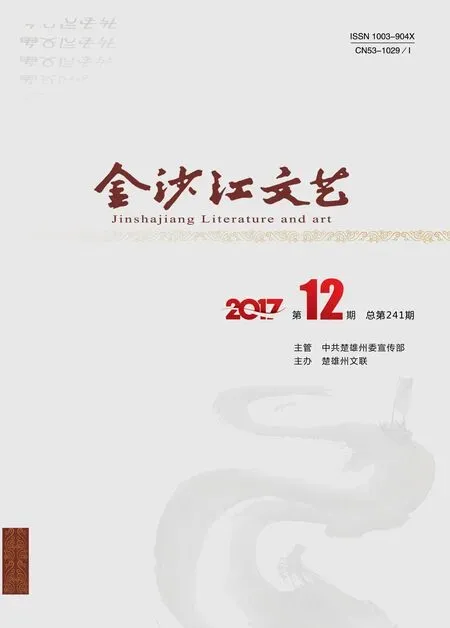右 耳
2017-11-14王雯君哈尼族
王雯君(哈尼族)
如果说左耳靠近心脏,为的是聆听爱人的甜言蜜语,感受爱情;那么右耳则是为了感受亲情。无论左耳还是右耳,爱情还是亲情,都需要用耳倾听,用真心感受,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
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入睡,耳朵里嗡嗡的,头脑一片空白,与父亲相处的最后时光就如电影,在脑海里回放。
那天接到母亲的电话,开口第一句问的就是“小二啊,你什么时候回来?”
彼时我刚参加完一个会议,准备吃过早饭就带着工作队进村入户开展工作。近一个月无节假日的连轴转,让我心里烦闷得很,没好气的回答:“我怎么知道,一会还要开会,要说什么快点说,忙!”
察觉到我语气中的不耐,母亲的声音低落了几分:“你爸昨晚意识又不清楚了,喊了好几遍你的名字,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你周末休不休息,能不能回来……”
这边办公室来人通知我开会,电话那头母亲听到了,忙说:“你忙我就先挂了。”未等我开口,电话里就传来“嘟嘟”的忙音,我只得怏怏收了电话,回会场继续开会。
中午,抽了个空打电话回家,听到我的声音,母亲很是欣喜,她说:“你阿爹昨夜跟我款话(聊天),说梦到脚好了,牵了一匹大白马,拉我回大庄赶集,走过小庙河坝,我问他水清么?他说清丝丝的……”母亲絮絮说着父亲的梦,语气甜蜜轻柔,像一个热恋中的年轻女子,在跟她的闺蜜述说往事。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帧画面,画中的父亲穿着白衬衣,卡其色的裤子,1米78的个头,微卷的黑发,皮肤很白,浓眉,典型的北方人身量,母亲梳着两条乌黑的辫子,戴一顶当时很是流行的解放军帽,穿着格子布衣服,五官不是很出色,笑起来却纯朴灿烂。他们身后,是最初的小庙河坝,不是现在的查姆湖,湖边也有垂柳、青草,没有那些一团团一簇簇娇艳灿烂的粉色樱花,也没有那些静谧忧郁紫蓝色的蓝花楹。情人桥边浅灰色的老医院是苏联时期的建筑,湖水是那种清澈见底的通透,阳光洒在上面,亮晃晃的,像金子一样。他们一定还有一匹马,父亲平生最爱白色,那马,一定也是雪白雪白的,没有一丝杂色,那一定是他们最好的年华。
我终于还是抽空回了家,还是因为工作,在开会的间隙到医院看看父亲。病床上的父亲身上挂满了各种管子,氧气管、心电监护、输液管、导尿管。花白的头发一寸来长,是我上次回家帮他剪了之后长出来的,浑浊的眼珠瞪得老大,张着嘴,“哎呦、哎呦”呻吟着,从他大张的嘴可以看见,他的舌头不正常的后缩着,脸色乌青,喉咙里好像藏了个风箱,呼吼、呼吼,艰难地呼吸着,感觉一口气呼出来,下一口气就吸不进去了。
我呆呆的站到床边,唤了他两声:“爸爸、爸爸”,他没应,我晃过神来,想起自己平时都是称呼父亲“我爹”的,怎么会忽然叫“爸爸”,我定了定神,收起心里的疑惑,加大音量叫了两声“我爹、我爹?”父亲浑浊的眼珠转向我的方向,喘得越发厉害了。
当护士的姐姐在旁边解释说:“爸爸已经看不见你了,但是能听见你的声音,”姐姐走到父亲床边,对着父亲的右耳大声道:“爸爸,爸爸,我妹妹回来了,你呢二姑娘回来了。”父亲对着我的方向眨了眨眼,表示知道了,就闭上了眼睛。
主治医生把我和姐姐叫到一起,交代病情,说父亲有肾衰的迹象,建议转到上一级医院进行透析。鉴于父亲的年纪和身体状况,姐姐和我决定让父亲暂时留院观察,待身体情况好转再转院治疗。
当夜,我换姐姐值夜陪护,炎热的夏夜,却冷得瑟瑟发抖,穿着外衣、加了毛毯、被子,还是觉得冷,眼睛里不停地有泪流下来。我告诉母亲:“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难受得很,一直流眼泪。”母亲让我不要多想,早点休息。
半夜,母亲睡着了,我走到床边用棉签蘸了水涂在父亲的嘴唇上,然后悄悄拉着他的手,轻声唤他“我爹,我爹”,他艰难的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含混的回了声“阿二啊”,又陷入了昏睡。
第二天一早,我在陪护床上睡的晕乎乎的,听见查房的护士说:“哎呀,老人家大便失禁了。”我忙和来接替我的姐姐一起,帮父亲擦洗了身体,更换了护垫,让他侧卧一会,以防褥疮。父亲以前病重的时候也有过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加上姐姐的职业就是护士,我们做起这一切来驾轻就熟。
侧卧着的父亲呼吸平稳了很多,我和姐姐说到单位办点事,让她照顾父亲一会,就走开了,谁知一走,就是阴阳相隔。姐姐打电话给我,让我快点回病房,我急急忙忙赶过去,没到病房门口,就听见姐姐撕心裂肺的嚎哭声,我的心咯噔一下,奔了过去,看见姐姐被两名护士搀扶着,一群医生护士围在父亲周围,做心脏复苏,父亲的头无力地耷拉着,再也没有了呼吸。
家里所有人都被电话召集到病房里面来,包括两个小孩子,在读幼儿园的宝宝不安的看着痛哭的大人们,惶惑的问我:“妈妈,你为什么哭?”我抱着他小小的身子,泣不成声,心底一个声音嚎哭着“因为我没有爸爸了啊。”
因为是退休职工,根据规定,父亲遗体是要火化的,当天中午,殡仪馆的师傅就把父亲的遗体接到了殡仪馆,我们则开始处理父亲的身后事。
定好开追悼会、下葬的日期后,首要任务就是张贴讣告,通知亲友,姐姐打电话给我说:“爸爸在世的时候就一直说你文采好,爸爸的讣告就由你来写。”我以一般情况下单位会起草撰写为理由草草回绝了姐姐,姐姐很是不满。她不会懂,我不甘心,自己那点被父亲培养出来的文学细胞,是用来宣告父亲的离去。
那时我的状态非常不好,感觉整个人被分成两半,一半是水,一半是火。太阳火辣辣挂在天上的时候,不管怎么烤,整个人都是冷的,心里空了一个洞,怎么也暖不起来,走在路上,太阳烤啊烤的,泪水就从眼角哗哗地流出来;天气不好,一雨成冬的时候,大家冷得直哆嗦,我的心里又有一把火在抓心挠肝的烧,不知道什么时候噌的一声就冒出来,把身边的人烧得体无完肤。
我和姐姐就像两只刺猬,把所有彼此的情谊忘得一干二净,好似仇人一样,用最恶毒的语言,把彼此刺得遍体鳞伤,仿佛只有不相见,才不会想起一起经历的那个人。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回到乡上,面对别人的目光,我都报以微笑,表示我很好,不用担心,对别人的安慰,我也会答上一声:“是的,我父亲病了那么多年,对他,是一种解脱……”
在一次文艺汇演上,因为是爱尼山乡专场,演艺公司特意添加了爱尼山乡最有名的民间小调“三月六”,“三月六”是流传于双柏县爱尼山乡境内的民间小调,以每句唱词后缀“三月六”几个字得名,整首歌曲哀怨婉转,以一个出嫁后回娘家女子的口吻,道出对父母、兄弟姊妹的感恩之情。
以前我分管文化,研究过“三月六”小调,知道当晚演出的伴奏音乐是经过后期制作加工的,歌曲开头这样唱到“阿表……我说么当家才知柴米贵,呀咿,实话相送么好朋友,养儿么才知父母呢恩……”随后的伴奏轻快婉转,歌词与本地乡土的相近,歌唱到最后一段,变得缓慢惆怅,“爹妈在世山成路么哎三月六,爹妈不在么咿呀路成山”一句歌词从右耳直撞入心房,刺得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当晚演出结束,我坐车赶回县上开会,一路颠簸,右耳疼得厉害,扯得整个头都是疼的,进城的时候,司机看我脸色难看,在查姆湖边停车,让我稍作休息,想起父亲去世前,母亲说的父亲关于查姆湖的梦境,心里戚戚,如鲠在喉,难受得不能自己,蹲在路边剧烈地干呕起来,恨不得把心肺都呕出来才作罢。
司机递了一瓶矿泉水给我,我接过,抬起头的瞬间,我愣住了,泪眼朦胧中,满树静谧忧郁的蓝花楹,蓝紫相间,如梦如幻,静静地在夜色中绽放,让人忍不住叹一声:“真好,没有错过这样的花期美景。”花开会落,但见过了,就印在了脑海里,就如父亲……
第二天,头疼得厉害,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两只耳朵里面都开始发炎,右耳尤其严重,问我近期有没有感冒,我回答没有,医生只好开了一堆的药,让我不适随诊。回到家,老公开玩笑说“你看,你脑子进水了,医生都没办法。”我生气瞪他,他拥我入怀,在我耳边轻声细语:“我知道,最难过的人是你,不要总把泪憋回去,如果想哭,不要假装坚强,只是记得,哭过之后,还要继续前行。”
我在他的怀中,泪流满面,泪水顺着脸颊滑进右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