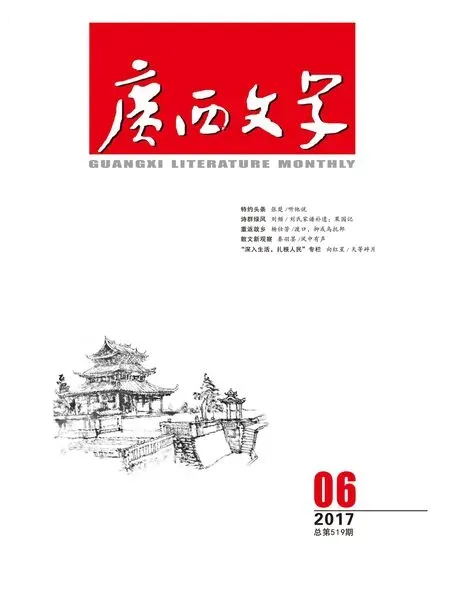散文新观察之秦羽墨篇
2017-11-14刘军/著
刘 军/著
马克思曾经说过:“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世界史的全部产物。”作为影响20世纪的三大思想家中的一员,他的发言具备了某种宏观性和整体性,即概括了人类从史前史过渡到文明史的总特征。而对于个体而言,五官感觉的形成,往往构成了初始经验,这些初始经验直接朝向了童年经验的区域。而每一代人的童年经验,其中最具个人性、鲜活性的内容,则由艺术家们提供给大众。家园情结的引导下,他们不自觉地将艺术之生成投向广袤富饶且无穷无尽的童年空间。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家不过是这样一群人,他为那些天赋条件和技能较差的人,构造了一条回归的旅程。童年经验的再现,不独带给人们初发芙蓉式的感受性瞬间,也带给人们相关根的认识。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既是普遍性的哲学问题,也是时刻困扰个体的生存问题,比较而言,梦境变形、意识跨越性流动,抑或真实再现,不过是不同艺术手段而已。这些手段殊途同归,皆会汇入寻找故园的河流。而对于散文而言,记忆性内容,尤其是童年生活的倒影,恰恰会成为这一文体之擅长或钟情之处。散文大家汪曾祺先生一辈子努力营造的就是纸上的高邮记忆,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让其流连忘返的则是沙湾童年生活。
本期散文新观察所推出的秦羽墨之《风中有声》,与其说是一篇乡土散文,不如说是家园情结下的童年回声。风暴和声音无疑构成了这篇作品重点钩沉的内容,而风暴也好,声音也好,皆由听觉而出。一个人的听觉史足够丰富,甚至奇幻,但构成尖锐性所在,且沉淀为经验者,大多集中于童年生活中的某些场景。在《风中有声》中,风暴具备两种含义,一种是时代的,一种是个体的。因为政策的调整,“我”的任教老师英琪,在事业和家庭的关键节点上被时代的大风吹上了岸边,成了被搁浅的鱼类。他本不是多余人,阴差阳错却充当了时代弃儿的角色。而他后来在田间的歌声,也成了荒凉存在的某种注脚。而对于叙事者“我”而言,湘南山地封闭的环境,放学路上来自山口处奇诡而阴森的大风,皆催生出主体逃离的欲求。这是一种对应时代大风反弹的结果,一阴一阳谓之道,相反与相成,皆依附于时代的大风之下。老子曾言:“扰万物者,莫疾乎风!”当代作家张炜则感叹道,在时代风暴的吹击下,做一根静止的芦苇是艰难的。好在帕斯卡尔业已为芦苇正名,作为思索的芦苇,恰是人的高贵性所在。就个体的风暴而言,它来自家庭内部,父亲的大嗓门以及家庭内部的硝烟,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刺激性记忆。作者在处理的时候,借助燕子筑巢加以隐喻性说明。而父亲的急躁、火爆与“我”的优柔、缓慢,也是一种“两极生四象”的关系。风暴具备某种摧毁性,而声音却具备了抚平的功能,母亲与“我”在声音上的感应关系,使得作者的童年获取了柔性的力量,并借此对抗冲撞、伤口、撕裂的力量,而声音的原初存在,正是童年的辉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