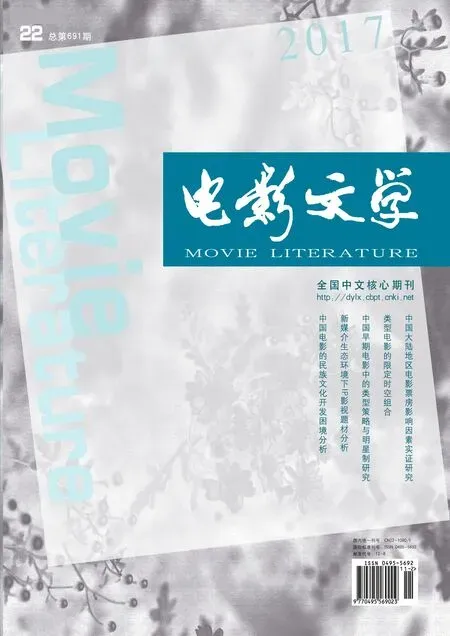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真爱》的叙事艺术
2017-11-14陈泳桦祁晓冰
陈泳桦 祁晓冰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电影《真爱》讲述的是新疆阿勒泰地区一个母亲与19个孩子的故事。通过第一人称的倒叙手法,为观众呈现了母亲阿尼帕和来自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汉族等6个民族的19个孩子一生的故事。影片以明暗两条线索,在时间和空间的相互交错中演绎着“真爱”的故事。
一、“离去—归来”模式
《真爱》大量采用了“离去—归来”的模式,其表达的正是“回家”的主题,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分别是“离去(形式)—归来”和“离去—归来(形式)”模式,这里所界定的“形式”是未达成的状态。
其一,“离去(形式)—归来”:这种以形式上的离去和实质上的归来为线索,代表的是一种欲离去终究没有离去的状态,而归来却是真实的。一是彩霞在阿尼帕的帮助下治好病后,想要去找哥哥。在去找哥哥的途中,她才坦白之前不敢把真实的情况告知阿尼帕,是害怕将她送回继父家。她的这种离去是一次欲向阿尼帕坦白而把哥哥接回来的尝试。当回到家,彩霞完成了她真正的回归,一个是家的形式,一个是有哥哥、有阿尼帕妈妈关爱的“家”。二是那然暂住在阿尼帕家后,要去远方亲戚那里,而后那然却跑了回来。他宁愿过着吃不饱的生活,也要沐浴着阿尼帕的爱。他的离去只是形式的离去,他的心从来没有从这个家里离开过,他的归来也是理所当然。而这两种情况都不遗余力地表明因这个家的温暖与关爱,孩子们找到了身与心的双重归属。
其二,“离去—归来(形式)”:这种以归来的形式和实质上的离去为线索,代表离去是真的离去了,归来却是形式上的归来。当阿比包爸爸躺在病床上,生命的气息慢慢消散,但他给予孩子的爱早已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他的精神也在孩子们的继承中得以回归。
“离去—归来”模式从两个方面表达出“离去”与“归来”的真正内涵:我们永远都在回家的路上,哪怕我们暂时离开了家,总有一天会回归;哪怕我们的躯体无法归来,但心早已经连在一起不分离。
二、矛盾的出现与转化
故事虽然发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各个人物都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但在情节的推动下,其内在气氛相对平和。之所以这种紧凑完整、张弛有度的叙述能够契合,是因为矛盾一经出现,就立即转化,自然而然呈现出平和的状态。矛盾通过两种形式转化,一是爱的升华,二是音乐的净化。
人物性格和行为的矛盾一经形成,就造成了故事情节的张力。矛盾最终能够升华为爱,实质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电影却在短暂的时间里,以人物之间共同的命运、不同的立场和由此所形成的共同的爱来构造。
阿尔曼作为阿尼帕的亲生孩子,也遗传了母亲善良的品质。作为孩子中年长的一个,他经常要照顾弟弟妹妹,为父母分担家庭重担,他本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却因为父母要把一双鞋子给王云辉,和妈妈大吵了一架。他因是长子而时常受到忽略,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然而矛盾一经出现,很快得到了转化。在运动会上,他和王云辉轮换着穿着那双新鞋,完成了比赛,鞋的传递也是矛盾释然后心灵的交换。正是基于阿尔曼的理解与善良,这个矛盾才在行为上得以转化。
当阿尼帕因操劳过度而生病倒下,丈夫阿比包打算将其中的几个孩子暂时送去亲戚家照顾。当阿比包念着要暂时离开家的孩子的名字时,他们像等着被宣判死刑一样。那些最终留下的孩子并没有松一口气,反而和即将离去的孩子们哭成一片。他们哀求着父母不要让他们走,他们主动请求“再也不嚷着吃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一顿只吃半碗”来作为让步的条件。父母也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泪流满面,说出“一家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分开”的话。因饥饿和贫困不得不离开与因彼此关爱不舍离开是一对矛盾,但矛盾立即得到转化,父母忍着一切艰辛答应让他们留下来。如果说阿尔曼和王云辉矛盾的出现和转化是爱的开始,那么19个小孩不舍分开则是爱的升华。爱的内涵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出现和转化,以及矛盾之间的对比中展开。
另一条矛盾的出现和转化的线索则是依靠音乐的力量。音乐的传达不像爱的形成那样漫长,它是即时的、轻松的、舒缓的。音乐正是在苦难日子里的一份希望以及一个民族在困境中乐观积极的民族情结。
那然是一个随身带着琴的维吾尔族男孩,镜头着重对他的三次弹琴进行描绘。第一次是当阿尔曼为了鞋子的事和妈妈大吵一架,他坐在毡房外面的地上怄气,那然在毡房里弹唱起来。阿尔曼脸上出现了淡淡的笑容,这是他从内心里想要消除母亲因对他关爱不足而造成的矛盾,这也为后面在运动会上他从行为上释然做了铺垫。音乐净化了孩子们的心灵,让他们彼此变得宽容与体谅起来。第二次是几个孩子在帮妈妈送杂碎的路途中,因为嘴馋而烧掉了父亲的打铁铺。打铁是父亲唯一的工作,也是这个家的重要来源,这就势必造成紧张感与危机感。父亲差点崩溃,那然却和几个维吾尔族邻居弹着琴消除紧张的氛围,毡房里奶茶和音乐都飘香起来。音乐净化着艰苦的生活,同时也表达出民族的乐观与坚强。第三次是当王云辉为了维护弟弟和同学打了起来,因伤害对方而被带去劳教所。对哥哥前途未卜命运的担忧使得孩子们在那一夜都没有睡着,那然拿起琴弹奏起来,琴声是有声的,思念却是无声的,通过琴声,思念也变得有声起来。音乐的出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牵挂,更凝聚着孩子与孩子的心。音乐净化的是在未知命运中所存的那一些希望和祈祷。
正是在爱的升华和音乐净化的表达中,矛盾的出现和转化才得到了一种解决的张力,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形式,才让故事紧凑有密度,富有节奏感,并且让情感层层递进。
三、叙事手法
麦茨曾经提到,其实正是当电影遇到了叙事问题以后,电影才在经历了连续的摸索之后产生了一套特殊的意指方法。和文本诉诸想象相比,电影所呈现的情节是经过挑选的,相对清晰与固定。也正是这样,电影的叙事手法一经确定便呈现在观众面前。电影作为时间和空间的综合艺术,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转换,在电影中有着无穷的潜力,而这正是电影叙事的重要条件和基本特征。《真爱》以一明一暗两大主线、时空交错两条线索共同构造出叙事的技巧。在形式上推进了情节的转变与发展,在内容上升华了“家”的主题。
在《真爱》里,一明一暗两条线贯穿前后。以阿尼帕第一人称倒叙的手法是明线,而暗线主要是由阿尼帕隐含的命运和孩子们的眼光来完成的。这两条线相互交错,诠释了长达几十年的“真爱”。
《真爱》的明线是通过母亲阿尼帕的视角展开的,这种视角是透过时间的流动来完成。以1974年、1984年、2010年、2013年4个时间点为界限,分为3个阶段。这3个阶段也是阿尼帕与19个孩子命运的交错。第一个阶段是1974—1984年,阿尼帕陆续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使得家里由9个孩子逐渐变成了19个孩子。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善举给生活增加了不少困难,但阿尼帕和丈夫阿比包忍受着一切艰难困苦,将19个孩子全部养大成人。这个阶段是整个电影的核心,也是最费笔墨的一部分,这是“爱”的萌芽。第二阶段是1984—2010年,孩子们慢慢成长,逐渐离开父母出去工作以撑起这个家,让操劳大半辈子的父母可以安享晚年。秋霞为了工厂的工作剪掉心爱的辫子,阿尔曼为了守住代表这个家的大锅意外去世,是这个阶段的高潮。孩子们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父母,承担起家的重担,这是“爱”的继承。第三个阶段是2010—2013年,阿尼帕的事迹使她被评为“2009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她去接受颁奖的时候,其丈夫在电视机前评价阿尼帕是“我们家上空的星星”,而“小家”的这颗星星,也成为“大家”的星星,这是“爱”的发扬。
《真爱》的暗线是先设置悬念,再通过细节去揭晓疑问。暗线弥补了主线只是“蜻蜓点水”却没有丰富故事内涵的缺陷。它悄然地解决了设置的疑问,不着边际却又清晰到位,将那些隐藏的点挖掘出来,将情感推至最高潮。一方面,电影的开头是以老年阿尼帕的独白开始,以呼麦作为背景音乐,以独白介入,将阿尼帕的命运和孩子的命运重合。这是一条隐形的线索,直到故事的末尾才并入主线,也即是在她做主让两对一起长大的孩子完婚后,望着河水回忆自己命运的时候一切答案才尘埃落定。她之所以要用一生去照顾无家可归的孩子,就是因为她的父母死在蒙古国,她虽然活了下来,却孤独一人。是阿比包的家人收留了她,而后他们也因为共同的苦难而惺惺相惜结为夫妻。这不仅诠释了为什么她要历经磨难收留那些孩子,并且做主让他们结婚,也回答了她作为维吾尔族人,电影开头背景音乐却是代表蒙古文化的呼麦的疑问。与此同时,也将她自己的命运和孩子的命运融为一体,虽然观众对她年轻时候的故事知之甚少,但孩子的命运也隐隐暗藏了她的命运。另一方面,故事的发展是通过孩子们的视角不断深入。比如阿尔曼由一个懂事的孩子变得任性,实则是因为自己的亲生母亲由于关爱其他孩子而忽略了他,借助于他的眼睛侧面烘托了母亲无私的爱。电影借助不同人的视角丰富了总体的视野,给观众打开了更多视觉的窗子。
《真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共同叙述、相互交错。时间线索简单明了,在空间上用转场的方式。常用的转场方法有运用语言、音乐、音响、人物动作转场,运用主客观镜头转场或景物镜头转场等。电影里多以景物镜头转场,包括以阿勒泰自然景物的转场和以连接家与外部世界的“桥”的转场。阿勒泰的自然景物是纯粹的景观,而“桥”已经具备了引申的含义,代表的不仅是实体,更是“通往心灵的路”。
故事的发展只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通过对自然景物的转场不仅是对时间的转换,更是为故事的推动设置了转点。阿勒泰常年寒冷,正是借助于春天冰雪消融、夏天绿树成荫、秋天叠翠流金、冬天白雪皑皑作为对比,暗示季节更迭。更为重要的是,自然风景的转场还让故事起伏有致。择一个典型的转场叙述:久未吃肉的孩子们帮妈妈送杂碎,馋嘴的四个孩子在经过爸爸的打铁铺时,秘密地切几段肠解馋,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家庭面临这样的变故,爸爸处于崩溃的状态。但是镜头又从这个家庭的苦难移向宽广的天空和大地,它似乎在说,人间的痛苦不管怎么更迭,大自然依旧岿然不动,它在审视人间苦难的时候,同样给予它们一些希望。而镜头紧接着又拉回到这个家庭,孩子那然和维吾尔族邻居弹着琴,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
对桥的转场,与自然景物的转场一样重要,只不过桥的内涵已经上升为另一种高度,它不仅是连接家和外面的桥,也是通向亲情和心灵的“桥”。桥的频繁出现,不仅暗示了时间的流动,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其一是由家通向外面的情节,孩子们去上学的时候,总会经过桥量一下身高,以见证自我的成长。其二是对归家的突出刻画,一次是全家参加完孩子的运动会,兴高采烈地回来;另一次是当孩子们都长大了,渐渐外出工作了,孤独的老两口加固着这座桥,等待着孩子们有一天能够全部回家团聚。将前者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和后者凄凉孤独的氛围生动地刻画出来,不仅加速了时间的流动,更是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家庭成员容量烘托出来。正是通过对桥的转场,将桥所能承载的重量和容量扩大,升华了“回家”的主题——桥连接着父母与孩子的心。
主线和暗线的起起伏伏、时间和空间的相互交错,是电影里特殊的叙述手法,通过这样的悄然设置,呈现给观众的是视觉的盛宴,具有无穷无尽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