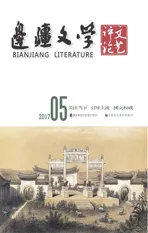峥嵘岁月的文学记忆
——评钟一夫长篇小说《红土谣》
2017-11-13黄光平
黄光平
峥嵘岁月的文学记忆——评钟一夫长篇小说《红土谣》
黄光平
一位伟人说过,随着历史潮流的淘洗,有些事情渐渐被人淡漠乃至遗忘了,有些事情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价值,却越发凸现出来。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可歌可泣的云南弥勒西山(月亮山)革命武装斗争,正是越来越凸现其深远意义和伟大价值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而且是有魅力的。作家钟一夫(钟鹤森)先生倾情投入,三易其稿,为我们奉上《红土谣》这样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既是红色土地的英雄史诗,亦是峥嵘岁月的文学记忆,更是红色文学的华彩乐章。
《红土谣》是首部以云南和弥勒西山(月亮山)武装斗争为背景和出发点的革命历史叙事作品。人物众多,纷纭复杂,慷慨悲壮是它的基调。作者从一滴水、一个角度、一个地区、一群人出发,经过艺术构思,发掘中国革命的某种整体性意义,塑造出一批可以感觉到鲜活地呼吸着甚或可仰视可触摸的艺术形象,它记述了弥勒西山(月亮山)武装斗争时期革命先驱者们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和云南儿女流血牺牲的伟大壮举,描写了黎明前撕破黑暗的西山风云,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史诗的宏阔和大时代的激情。从文学的层面看,《红土谣》是带有补充空白意义的悲壮史诗。
作者钟一夫先生长期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对云南弥勒西山革命史料有着丰厚的积累,但为了完成这一巨著,他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采访了大量的参与者和知情者。心灵深处一直萦绕着身为作家的使命和因崇敬前辈而生的“还债”夙愿。从本书准确的历史信息、细节与情景描述不难看出,虽然对人名、地名等进行了艺术处理,但真实、丰富、饱满,加之立体的全景式再现,相对于这一段峥嵘岁月来讲,是前所未有,下了大功夫、费了大气力的。可以说,没有作者对前辈革命业绩的由衷崇敬,没有作者开掘和弘扬前辈革命精神的巨大动力,就不会有《红土谣》的壮美。在作家的笔下,耿志英、石成林、滕俪芸、严子敬、陈思敏等,都是有血有肉、情感丰沛的人物。因此,在叙事中,作者非常注重时代特色的注入,洋溢着革命的浪漫主义豪情。比如受地下党省工委的派遣,石成林与女大学生滕俪芸假扮新婚夫妻,利用滕俪芸的社会关系,打入福甸县政警队,担承着敌人的怀疑、亲人的误解,在“妻子”滕俪芸的支持配合下,艺术地再现了率队起义、拖枪上山打游击的历史故事;比如简师学生耿志英受“满门忠烈”的革命家风熏陶,在地下党员、福甸中学图书管理员严子敬的培养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组织“洪流合唱团”,以柳若菁、晋文彬、耿志勤、陈思敏、郭兴华为代表的热血青年,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福甸县城宣传民主、自由,反内战、反“三征”的主张;比如伪县长任方元的无奈、政警队副队长潘金贵的作恶多端、中学教导主任鲁怀仁的阴险、奸细卫伯良狡猾的伪装等敌人性格特征的塑造;比如党的地下交通站联络员耿三娘、达昌嫂及“小洋芋”杨小玉至死不渝忠诚于党和人民、机敏地与敌人周旋的事迹;民运工作团那种青春的活力和才情,丰富的细节运用,使得这部作品人物生动、性格凸现,可圈可点的细节比比皆是,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月亮山”根据地人民在屠刀面前、围剿面前,走过的一条艰难曲折、英勇悲壮的反“三征”之路、胜利之路。作者把根据地起名“月亮山”,似在暗喻尽管黑云压顶,人民心中贮有光明的向往,黎明即将到来,太阳将会升起。鲜明地展现了革命者那种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联系群众、公而忘私、大义凛然的风采。
《红土谣》将历史上升为艺术,以严子敬、耿志勤奔赴“月亮山”组织民运工作团开展斗争为主线,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月亮山”武装斗争的过程,选取的切入点非常成功。尽管作品不能不照顾到那段历史时期艰苦卓绝的繁复斗争,不可能写尽众多的人物、事件和场景,不能不写曲折复杂的过程,不能不忠实于历史事实,但如何把这些事件、过程和事实变成文学,无疑是作者面临的最大困难。但作者克服了这个困难。钟一夫先生在结构的巧妙和详略安排方面狠下功夫,做到拿得起、放得下,展得开、收得拢;特别是以充沛的热烈的情感、丰富的艺术的想象,甚至是新历史主义的笔法,给那些事件和人物着色;让历史人物变成艺术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让事件与过程变成了跌宕起伏的情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思想变情致,情中有理,理中有情;最终将历史上升为艺术,转化为艺术,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能够感动人的优秀文学作品。
《红土谣》中,作者对耿志英等从青年学生到成长为革命者的历程,充满了牺牲情境的拓展,也展示着《红土谣》在观念层面的新意。“山茶花,紫丫丫,/生在红土坡,/长在石旮旯,/山茶花开红似火,/红满山,红满崖,/红遍穷人家……”青年学生们像山岩上的山茶花,在“月亮山”这块光荣的土地上,坚定地扎稳根子,开放出鲜艳夺目的花朵。这一群人从城市到山区,环境艰苦,疲惫不堪,语言不通,还要面对敌人挑衅、封锁和扫荡,但他们都是信念坚定、心灵闪光的人。他们学会唱的“红土谣”,是心声,是预言,是战歌,对情系劳苦大众的革命者来说,是附丽着殷红光芒的旗帜。他们为信仰而生,为众人而死,这样的灵魂是圣洁的火焰。作者多处运用“红土谣”这首歌,把他们的不同命运描画得惊天动地而又瑰丽无比,同样出色地折射出、聚焦了一段似乎被遗忘的历史,一段艰难的、残酷的革命斗争岁月的历史。
作者对于玛鲁寨遭袭、月亮山保卫战的描写,严子敬、滕俪芸、晋文彬、高峻峰、达昌嫂的牺牲,陈思敏、杨小玉的成长,伊洛村潘大爹的性格特征,乡长昂大刀对人民武装从飘摇至笃定的转变,昂大刀女儿阿梅的美丽、聪颖和对革命的倾向是非常悲壮的历史过程。所谓“红土谣”,所谓“月亮山”,指的就是无数烈士的流血和牺牲,书中无数感人的真实故事,像一颗颗发光的宝石,作者把它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宏伟的历史画卷,用文学的力量把历史的记忆镌刻成不朽的英雄群雕。也许,缺少了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场氛围,缺少了敌人的刺刀和机枪的近距离逼迫,他们所处的“月亮山”就显得不那么迫切、危急,但也正因此,这种献身选择才更为艰难,也才能承载坚定的政治理想,辉耀人类最美好的情操和最崇高的追求。他们的崇高就在于能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将生存和希望奉献给别人,奉献给革命的曙光和黎明,这种精神、行为和人格,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使一个有良知的人肃然起敬。
《红土谣》二十余万字,十一个章节,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以饱含深情的文字娓娓道来,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为我们打开了尘封的记忆,温婉细腻的文字和以小见大的描写,用浓郁的地域和民族色彩,演绎了一部“月亮山”革命武装斗争的艰辛历史,是英雄群体的概念浓缩。在享乐盛行,娱乐致死的当下,甚至历史事件发生地“革命烈士纪念碑”被挪移的今天,也许很多人对“红土谣”描述的“月亮山”革命斗争历史难以理解甚至没有了记忆,更不会意识到那些峥嵘岁月所包含的精神和价值。但是,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它最起码可以使人对历史有一种感动,对现实有一种满足,对未来有一种期待。
感谢作者对文学的忠诚,感谢作者为“月亮山”壮歌。读《红土谣》这一部将历史上升为艺术的震撼人心的革命史诗,我的内心百感交集。在一个信仰和理想匮乏的年代,《红土谣》的意义和价值就显得尤其重要。
(作者单位:红河州弥勒市文联)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