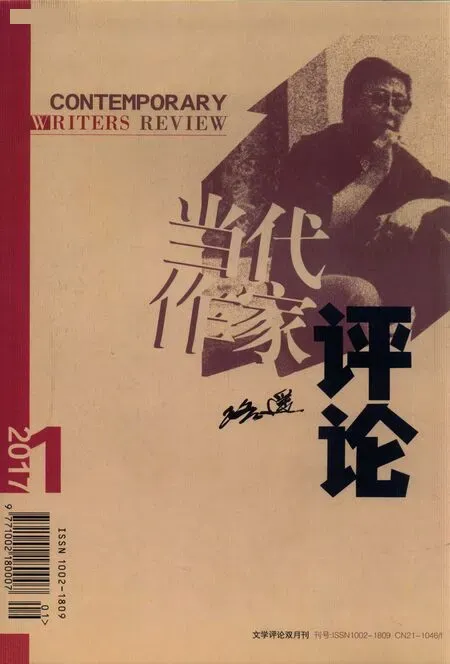越界的诱惑
——论王宏图的小说创作
2017-11-13郑兴
郑 兴

——论王宏图的小说创作
郑 兴
复旦大学教授、沪上作家王宏图的小说创作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迄今为止,他已收获了两部中短篇小说集《玫瑰婚典》《忧郁的星期天》以及三部长篇小说《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风华正茂》《别了,日耳曼尼亚》,加上批评集《东西跨界与都市书写》、对话录《苏童王宏图对话录》和随笔《不独在异乡——一个孔子学院院长的日记》等著作,其创作成果和格局已然相当可观。时至今日,我们有理由认真梳理他的作品,以求更贴切地走近他、把握他。
一、反常之性:身体的越界
探讨王宏图的创作,还是要从最早的《玫瑰婚典》说起。
这一中短篇小说集写于上世纪90年代,主要聚焦于婚姻与两性情感。这其中,短篇《最幸福的人》可视为整个小说集逻辑上的起点:“我”的同学玲玲一直是大家眼里“最幸福的人”,不料“我”见她以后,她却郁郁寡欢,原来她丈夫整日忙于事业,很少关心她——“最幸福的人”原来不幸福。小说至此戛然而止,悬置了一系列的疑问:何为美满的情感?婚姻的意义何在?婚姻中的人该如何安置自我,又将何去何从?
基于这些疑问,我们发现,这一小说集关注婚姻与情感,其中却没有两情相悦的幸福婚姻,也没有一见钟情后的佳偶天成,有的只是出轨、嫖娼或难觅伴侣的迷茫。《衣锦还乡》写宁馨出轨和弟弟宁德在性和婚姻上的困惑;《玫瑰婚典》与《蓝色风景线》都写女主人公厌烦婚姻,出轨后无路可走,终究弑夫或殉情;《我拥抱了你》中陈杰渴望与邂逅的蒙蒙成就感情,却意外得知对方是妓女,绝望中与她发生关系,尔后落荒而逃;《青灰色的火焰》写大半辈子循规蹈矩的男人利奇在初尝嫖娼经验后,长期压抑的欲望诡异爆发,突然开始疯狂虐待妓女。
如果说性是人类生活无法绕开的关键词,日常生活和道德习俗却规定了一系列基本的律令与禁忌,使性局限于稳定、单调的边界之内。即便如此,对禁忌的违反和对界限的逾越仍会发生。《玫瑰婚典》向我们集中呈现了各种反常的性,小说中的人物屡屡以身体的沦陷和出轨,越过日常规范的边界。王宏图对婚姻、情感的疑问和思考通过性的诸种面向折射出来,只是,他如此钟情于反常的、非婚姻的性,无论是性压抑、性变态、婚外偷情还是与妓女一晌贪欢,都不遗余力地加以呈现,偏偏对夫妻之性意兴阑珊,常态的性在他的小说中几乎隐身了。王宏图意欲何为?
法国哲学家巴塔耶的“越界”思想或许可以给我们启发。巴塔耶认为,人类以一系列的禁忌(如性禁忌、死亡禁忌和乱伦禁忌等)加诸自身,从而把自己和野兽区分开来,完成“从动物到人的转化”,禁忌也即边界。不过,也正是这一系列的边界,使人陷身于“乏味的、从属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有用法则和勤勉劳作,偏偏斫伤了人自身的总体性。巴塔耶因而在小说中肆意铺排污秽、色情和死亡,逾越各种界限与禁忌,再现人自身的动物性,从而在越界中重获为日常生活所压抑的“至尊性”。
借用巴塔耶的概念,王宏图小说中的种种“反常之性”也可视为一种“越界书写”——身体的越界。巴塔耶书写越界,是为丧失了总体性的现代人寻求解决之道,王宏图屡屡呈现身体越界,同样是为了凝视现代人的生存。以中篇《玫瑰婚典》为例:箐楠和师俊出轨后,师俊不过是逢场作戏,箐楠却沉醉了:
那是女人狂欢的时光,在痛快淋漓并非作秀的扭动尖叫中她品尝了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幸福……直到这时她才明白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本来她可能相伴一生尽管你有一股子不满意有那么一丁点怨气但日子本来就这么过。也正在这时,箐楠第一次感到了绝望,第一次切肤体味到了生命的不完满——像一件布满缺口无法修补的衣衫。
王宏图一再强调“这时”和“以前”的区别。其实,“以前”哪里有如此不堪。《玫瑰婚典》和《衣锦还乡》中,宁馨和菁楠的丈夫都很优秀,而且对其百依百顺。本该都是令人艳羡的生活,却让女主角感到无味、窒息,使她们轻松地沦陷于情人的勾引。明明是夫唱妇随的美满,明明是众人欣羡的幸福,偏偏都被王宏图宣判为“伪幸福”。物质丰裕意味着精神世界的空虚,举案齐眉暗示着按部就班的枯燥。
王宏图看来,人在物质生活外一定还别有所求,在日常生活的“沉沦”状态外一定还有着某种难以弥补的缺憾。于是,他让笔下的人物对此肤尝身受、辗转难安。只是,何谓“自己的幸福”和“自己的世界”,他只是点到即止,并未说透。“性伴侣的要求”这样的解释其实也太过简单。另一段与苏童的对话反倒道出了他的隐衷:
对于很完美的婚姻,我直觉地认为它要么是一种有意的伪饰,迎合世俗的道德感,也满足当事人的虚荣心,要么是双方性格都比较好,都乐于改变自己,这样尽管和谐,但缺少了生命中很多辉煌的东西。
原来,作为作家的王宏图,对婚姻这一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形态抱以怀疑态度的。所谓完美的婚姻本就不存在,即便表面和谐,也要以“生命中很多辉煌的东西”为代价。王宏图在告诉我们,婚姻,或者进一步说,以婚姻为表征的日常生活,其实是所有现代人的“界限”,因而也意味着压制和框范。如此看来,王宏图小说中的隐含意指其实是,出轨并非源自两个男人间的落差,嫖娼也不是因为妻子逊色,一切源于生命本然的缺憾。这无关乎婚姻是否“美满”,因为根本就没有“幸福”的婚姻,只要进入庸常的、按部就班的生活状态,残缺感、失落感便逐渐滋生。庸常的幸福再好,也是不够的,生命终究不圆满,存在即是缺憾。
如果以婚姻为代表的现代日常生活本然地压抑着我们,再光鲜的婚姻也是虚假的表象,行礼如仪的夫妻之性一定也是相互凑合乏善可陈,怎能让人提起兴趣。界限无处不在,越界也就成了王宏图的书写策略,他这才聚焦于反常的性,这样的性越是礼坏乐崩越是惊天动地,越能反衬出夫妻之性乃至婚姻生活的无味。越界,不仅意味着满足身体和精神的渴求,更意味着一种生命力的释放,一种跃出日常生活的渴望,一种在当前状态之外寻找另一种生存方式的祈求,一种让生命热力有所投射、让情感有所着落、让肉体为之颤抖的自我拯救。它既是刺向日常生活帷幕的利刃,也是照亮现代人生存暗夜的闪电。
于是,每当书写这些反常的性,王宏图不会横加谴责,而是携带着理解与同情,甚至敬意和感动。小说中,每当其发生,不仅是一种纵情的释放,却更像是枯木逢春,仿佛是等待了太久后的峰回路转,仿佛使沤烂的枯木重新焕发了华彩。钟情于反常的性不是诲淫,也非猎奇,而是不忍生命因沉沦于日常而枯萎,这才将跃出伦常的性刻意放大,成为甘霖,去滋润干涸太久的生命。
只是,王宏图又是清醒而悲观的,他看出现代人沉疴难愈,反常的性终究稀缺而不可靠,难成拯救的源头,他也不奢望越界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于是,他又让笔下的人物刚瞥见曙光,便戳破泡影。宁馨、菁楠出轨后很快发现,她们不过是对方的玩物,一切只是欲望驱使下的空洞表演。出轨的魅惑怎能一至于斯,只是在淤滞的生活里窒息太久,当迥异当下的情感状态猛然冲击,难免会眩晕、沉迷。试图在婚外之性中去填补存在的缺憾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幻觉,无异于抱薪救火,失望才是存在的命定结局。
《玫瑰婚典》看似是在说婚姻与情感,其实是指东打西,道出了创作早期的王宏图的生存感受:婚姻是日常生活的核心,它如此牢固、深入地切入到我们生命的内里,与之血肉相连,只是,差强人意的婚姻根本无法支撑起饱满动人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之内去寻找另一处栖息之所也绝无可能。早期的王宏图向我们决绝地宣告:现代人的生命里,完美是虚假的,不圆满才是永恒的。
二、辩证之法:风格的越界
在身体的越界之外,王宏图小说在风格上也呈现越界的特征。无论是写人物、心理,还是情境,王宏图皆以近乎偏执的精雕细作,以最高密度的形容词、名词,与笔下的对象正面遭逢。这样一种捕捉对象的精细、铺张、繁复,常常超过了对象所能承受的限度,使对象涨破了自身,这是细节的越界。巨细靡遗的笔法之外,更常见的是情绪的越界,文字背后蕴含着过分激烈的情绪,刺激狠绝的情感强度往往逾越常态,或躁狂,或忧郁,乐而淫,哀而伤,仿佛要刻意反写“发而皆中节”的古典美学原则。
细节的越界与情绪的越界互为表里,成就了王宏图小说的美学风格,也在在显示了他“穷形尽相”的冲动与努力。“穷形尽相”在今天是贬义词,意谓丑态毕露、怪象百出,不过,在词源学的意义上,它最初正是被用来形容文学家描画世界的不懈努力。晋代陆机在《文赋》中说,“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唐代卢照邻在《益州长史胡树礼为亡女造画赞》中写到,“穷形尽像,陋燕壁之含丹,写妙分容,嗤吴屏之坠笔”——“穷形尽相”原来是文学家眼中的理想境界。直至清代,陶宗佑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一文中说:“其所以爱之之故无他道焉,不外穷形尽相,引人入胜而已。”更是直接道出了,穷形尽相并引人入胜本就是小说的美德之一。
不过,“穷形尽相”与“引人入胜”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细节的越界仅仅是为了复现,情绪的越界又单单是宣泄,小说的“引人入胜”又从何说起?更大的疑问是,前文说到,王宏图在创作初期就已经奠定了对这个世界、对生命的基本态度:一种否定的、冷眼相看的、近于虚无主义的态度。可是,在否定的视角下,作家如何还能有“穷形尽相”的冲动与耐心,越界的动力机制从何而来?小说创作如何还能一直继续,而不会一声长叹就此搁笔?王宏图以他以此后的三部长篇,告诉我们,在否定的土壤里,也能持续结出绚烂的花,因为越界中自有其辩证法。
我们注意到,王宏图的小说中,一切光鲜亮丽的词都具有反讽的意味。比如他拟的小说标题:“衣锦还乡”——刚刚移民美国的宁馨当然有资格“衣锦还乡”,迎接她的却是自己成为别人玩物的残酷现实;“玫瑰婚典”——该会有多么郎才女貌、繁花似锦的婚典上演,小说却道出了一个以菁楠的出轨和死亡而支离破碎的新婚即景;又比如,“风华正茂”——青年学者刘广鉴年轻、敏感、有才气,真真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小说中他却受困于当前的学术机制,在高校的现行体制中寸步难行,有志难抒。
这样的反讽不仅仅一种修辞,更成为支撑小说的一种运行机制。既然繁花似锦意味着支离破碎,既然最华丽的外衣其实意味着最空洞的内里,既然肯定的面貌其实暗含着否定的态度,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将其颠倒过来:支离破碎可以用繁花似锦来表示,空洞的内里可以用华丽的外衣来包裹,否定的态度可以以肯定的面貌出现。反讽为隐含作者的态度和小说的语词之间拉开距离,形成一种张力空间,文本得以在这空间中自在地繁衍、铺陈。
一种既生动又诡异的机制由是生成,铺张、繁复的笔法捕获了对象的每一个细节,穷举了事物的每一种可能,道尽了世界繁华绚丽的表象,背后却隐伏着王宏图冷冷的注视和沉重的叹息,因为绚烂暗示着稍纵即逝,繁华指向着虚浮空无,不过,表象的生动并不因内核的虚无而被取消,内里的空洞也不因表象的繁华而被遗忘,短暂与虚无的内里越发印证着繁华表象的迷人,绚烂表象越发催生着对世界内里的清醒认知。读者既可沉醉于表象的繁华,也同时获得一种审美的间离——其内里还是虚无的啊。
于是,肯定的“表“与否定的“里”并不相互矛盾,反倒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辩证关系,二者相辅相依,相反相成。如鲍德里亚所说,假如没有表面现象,万物就是一桩“完美的罪行”,既无罪犯、也无受害者,更没有犯罪动机,不过,万物的虚无本质也正因表象而露出马脚,表象正是虚无的痕迹。鲍德里亚的本意是以此批判充斥着虚妄表象的当下社会,不过同样也启发我们,在文学的世界里,内在的“罪”和表象的“美”很难相互割裂,“罪”与“美”一体两面,前者必须借助后者才能表现出来,后者也指引着我们对前者按图索骥的领悟。
既如此,越界就不单单是为了复现,更不是宣泄,细节的侈丽和情绪的饱胀是为了给文本注入一种张力,唯有越界,反差才足够鲜明,张力才足够强劲。越界也不会真的无限延宕一去不回,而是时时返顾,让我们不可过分耽溺,提醒我们勿忘作家的此中真意。单纯的正写或反写、肯定与否定总归会有动力耗竭的危机,反倒是在辩证法的运作中,在正与反的碰撞、拉扯和交合中,供给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彻底释放了文本增殖与爆裂的可能,催生出迷人的风景。
这一辩证法的运作机制其实在文学史上早就存在。我曾在另一篇论文中称王宏图是“以赋为小说”,除了因为他的小说与汉赋有着同样的富丽细密的笔法,更因为汉赋也同样内蕴着越界的辩证法。在《七发》这一汉赋中,枚乘的多数篇幅都以铺张扬厉的笔法,力陈“七事”的动人,只在文章的最后挑明讽喻的旨归——劝太子戒除对“七事”的耽溺。如此费尽周折极力铺陈,文末却以简单的“曲终奏雅”将之前的努力一笔勾销。这样看似与写作意图极不相称的结构,这样在肯定中表达否定,正是一种书写的辩证法。
因为这一辩证法的存在,态度的否定不但不意味着写作动力的衰竭,反倒为小说提供了一种持续的动力机制。王宏图也因此不会越写越少,越写越涩,反倒越写越多,越写越密,以一部又一部的长篇,印证自身小说世界的蓬勃生机。
三、欲望之维:文本的越界
有了越界的辩证法,王宏图一面保持着对世界的清醒认知,同时尽可聚焦于他所关注的主题,落笔千言,恣肆为文,在文本的越界中,铺陈出动人的景观。进入21世纪以后,王宏图敏锐地感知到,我们正处于时代的节点上,这个世界正被一种新的逻辑所笼罩。于是,他把目光从家庭中移出、放远,开始认真打量上海这个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都市以及都市里的人。
王宏图看到,当下的都市已经充斥着欲望,欲望,正在成为都市、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上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超级都市,王宏图对上海又如此熟悉,那么,他将上海作表现欲望的舞台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玫瑰婚典》的多数小说也是发生在上海,但在这些小说中,上海只作为背景而存在,并不显得重要。只有从第一部长篇《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开始,上海真正与王宏图的小说产生了根本性的关联。
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开始,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便已经散发出太多的诱惑,也承载了作家们太多的想象。从上世纪30年代的张资平、新感觉派,到40年代的苏青、张爱玲,再到90年代的王安忆,已经有不可胜数的上海叙事,而且,早在穆时英等人的手上,欲望便已经作为上海叙事的关注对象,王宏图必须进一步寻找属于自己的书写上海、呈现欲望的方式,才能要真正使自己跟刘呐鸥、穆时英们区别开来。
王宏图也曾在论文中考察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都市叙事与欲望表达,但是,在他看来,这些作者要么对欲望的表现点到即止,将其作为一种新生的美学现象加以陈列,它逗引着主体的骚动,却又欲说还休,叙事往往隔靴搔痒,欲望无法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要么因为欲望作为对象太过动人,而作者自身的主体性不够强大,反倒被对象俘虏,因而难以穿透欲望的重重表象,小说便流于肤浅,立场混乱,无法达成对欲望的超越。对前辈的欲望叙事,王宏图抱以尊敬,却也是不满意的。
王宏图甚至面临着比前人更艰巨的挑战,因为无论从程度还是范围上,欲望对这个时代的宰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甚,如果说,在之前它还只是一个表象、一个征兆、或是一个特性,那么,到了当下,它已经侵入世界的每一寸肌理,成为这个时代的根本性症结。为了应对这个前所未有也难以捕捉的庞然大物,王宏图一方面将笔下的上海作为欲望的载体,点燃人们心中的欲望,更重要的是,他要聚焦于欲望与人的关系,让欲望成为小说背后的推动力,看欲望如何塑造着人、驱动着人,抑或毁灭着人。
回忆起沈大高速公路的过往,今年75岁,曾参与沈大高速公路建设的工程师王锡岩老人五味陈杂、百感交集。“当年经济发展急需改善路况来支持,但修建高速却面临建设规范、资金来源和认识水平三大困难,最难的是人的认识问题。”
小说中,上海这个超级都市为欲望的表现提供了无限可能,在这里,欲望的诱惑无处不在:物质、权力、身体、梦想、机遇等等,一切欲望的要素皆已具备,身处其中的人们怎能不遐想、躁动、甚至癫狂?世界仿佛进入了一个欲望的狂欢节,成功者的戏码天天都在上演,谁身处其中都会蠢蠢欲动;狂欢节又销蚀了既有的条框与界限,没有谁会真把规范、道德、底线当一回事,每个人兀自入戏,设计着自己的台词、动作、情节,排演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这里有在异国开空壳公司,并转移、套取国家资金的耀森;有先骗取女友信任,然后绑架其富有的父亲并讹诈钱财的阿龙;有在现行学术机制中游刃有余,虚造各种学术泡沫为自己积累升迁资源的张伟戈;有在国有企业中和领导串通,并贪污受贿、包养情妇的钱英年;甚至还有无名无姓、面目模糊却也都为一己私利亢奋不已的各色市民。这里面人物的身份各个不同,他们的手段也五花八门,却同样都是在追逐欲望的道路上奔走不息。
欲望席卷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唯有王宏图笔下的主人公成为难得的清醒者,注视着眼前的欲望都市。清醒的人因为是敏感的、向善的,这才看清欲望的伪饰与丑陋,因而拒绝投身于欲望的狂欢,主动将自己放逐到边缘处。可是,因为自甘边缘,他们必然在主流世界中处处碰壁,从而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因而又只能是孤独的、无力的,成为世界的局外人、多余人。
艾珉、刘广鉴们因而只能成为软弱的旁观者,他们要么连自己的婚姻问题都无从把控,要么连教授职称都望眼欲穿,在自顾不暇的窘境下还试图将欲望证伪,不注定是可笑的、徒劳的?于是,清醒者们焦躁了、愤怒了,他们经常会无来由地陷入忧郁、躁狂的情绪,他还会感到恶心,会不能自已地诅咒这个世界,可是,这样的焦躁与愤怒只会加剧自身的无力感、空洞感,相形之下,欲望却依然以自身的生机勃勃,招徕着一拨又一拨的追随者。
不过,即便欲望如此强大,清醒者又如此无力,王宏图却不会真的要让欲望在小说中奏凯,如此,他不会比前辈作家更进一步。正如前文所论,王宏图自有其“越界的辩证法”,将欲望置于这一运行机制中,其种种面目皆可自行呈现。
首先,王宏图尽可大肆铺排的欲望的表象,让欲望充分彰显自身的声色与光影,使其得到酣畅淋漓的表现。于是,王宏图经常在小说中不惮以大段篇幅,描画上海的景观,为诱惑的催生烘托足够的氛围,为欲望的好戏拉开大幕:
在这样五色缤纷的舞台上,各色人物鱼贯而过,在欲望的牵引下一路狂奔。他们往往在主流世界中如鱼得水,所欲所求皆已斩获。欲望的实现又如此迷人,让人沉酣,张伟戈年纪轻轻就评上了博导、副院长,在学界呼风唤雨;钱英年手握财富,虽然年事已高却可肆无忌惮地包养年轻情妇;连阿龙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相貌平平的穷小子,都能让艾琪这样的富贵出身、又相貌美艳的女人任自己玩弄。于是,他们志得意满了,有如站在了舞台的中心,相形之下,清醒者反倒成了既冥顽迂阔又自怜自艾的伶人。
就这样,欲望以自身的逻辑,仿佛在小说世界中颠倒众生、势如破竹,不过,恰恰就是在呼啸前进的旅程中,欲望耗竭了自身的动力,因为欲望是层层翻新的,一个欲望实现了,另一个更大、更动人的欲望于焉浮现,而投身欲望的人终究是有限的、欠然的肉身,面对着欲望的无底洞,他们难以一直维持同样的动力与激情,于是,在无限的欲望面前,他们迷茫了、疲惫了。
更重要的是,欲望大肆扩张的同时,也在自身体内埋下了崩裂的罅隙,就是这不起眼的裂缝,在某个偶然的契机,引发了自我的内爆与溃散:一直掌控全局、快要登上院长宝座的张伟戈,谁知就在一次偶然的嫖娼事件中,断送了自己的前途。阿龙把孟实绑架,眼看着就要大计得逞,谁知偶然见了艾琪,情感冲昏头脑的艾琪突然丧失理智,结果了阿龙的性命。就这样,王宏图写尽了欲望在城市中的活色生香,任其在小说中喧腾、绽放,却往往在小说的末端,让欲望为自身所反噬,走向衰颓与幻灭。欲望,被王宏图的辩证法拆解了。
王宏图以四两拨千斤的狡黠与冷静,击穿了欲望的层层表象,也揭穿了都市其看似丰裕实则匮乏、看似繁华实则窳败的复杂面目。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欲望蛊惑下的世间百态,看到了人和欲望的种种互动,也看到了欲望的迷人、繁荣、复杂、丑陋的复杂面向。也正因此,王宏图对笔下的人物保持着理解与同情,即便是张伟戈、钱英年们,在小说中也不是面目可憎的,人终究难以超越自己的有限性,王宏图对他们是不忍责备的。
四、创作之心:身份的越界
出生在文学世家,其后一直读书,再到进入高校,生命之于王宏图就是一条远离侵扰、波澜不惊的河流。也正因此,久受文学熏陶的他出手就比较成熟,最早的小说集《玫瑰婚典》便已在语言、主题和技法上游刃有余。那么,本文最后也即最大的疑问是:作家本人一生平稳、顺利,何以笔下流淌出如此激烈的文字,何以偏要塑造种种不圆满的生命,让他们的灵魂扭曲、颤栗,难以安妥、和谐地锲入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进一步延展“越界”的概念,抛开小说内容不论,王宏图的创作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越界:按照我们一贯的想象,大学教授本该专注学术,创作只是主业之外的嬉戏笔墨,王宏图偏偏以小说为志业,如此,小说家身份是对教授身份的越界;再者,安稳妥帖的个人生命本该导致小说风格的谨言慎行,王宏图偏不安于生命历程的束缚,不以小说向自身经历靠拢,反倒营造出耸人耳目的小说美学。这是写作风格对个人经历的越界。总之,小说创作成了作家主体自身的一次越界。那么,其中的矛盾该作何解释,作家主体的越界从何而来?
从王宏图的自述中,我们首先发现,越界来源于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不平衡性。王宏图说:
的确,乍看之下,我的人生道路并不曲折,虽然有些小小的波澜。但从上世纪80年代至当今,我的内心并不平静,常常处于与外部世界、与自我的剧烈冲突之中。一方面,这30余年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人们心头激发起难言的痛感,人们先前信奉的道德准则和价值一夜间崩塌。我有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和人生追求,但外部世界的变迁让人不胜惶恐。另一方面,我不是一个坚毅果敢的人,思想与行动间存在着很大的冲突,而且不善打理俗务,因而也在日常生活中给自己带来不小的麻烦。
这里所谓的“剧烈冲突”,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冲突,而是精神意义上的冲突。王宏图曾说,他们60后“这一代人”同时经历、见证了60、70年代的红色海洋、80年代的浪漫情思和90年代的消费主义迷狂,外界变化太过迅速、剧烈,因此,他们不断感到“震惊与眩晕”。
外部世界如此多变、迅速、诡谲,稳定的参照物不复存在,自己原先的一套逻辑和准则再也不能稳定地把握外部世界。个人经历再平稳,外部世界却处于动荡与剧变中,作家的内心世界也会随之震动,在“震惊”的体验中,自然难以维持平静。存在于此世的作家本人不可能真地隔绝于外部世界,纵使在主体实践上不被卷入外部世界的动荡与剧变,但动与变依然会映入作家的眼和心,最终投射于他的小说写作。
再借助其它的思想资源,我们进一步发现,越界更重要的来源其实是生命自身平衡的需要。不妨返观巴塔耶的论述。他在《色情史》中举例说:一个父亲在和女儿玩耍时,他可以温情脉脉,可他可能转身就去了不良场所,成了一个放荡成性的人;一个人在家里是一个安静的农夫,乐于助人,儿女绕膝,但到了战场上,却可能烧杀抢掠。巴塔耶认为,人人都有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一面和邪恶的、为所欲为的一面,看似毫不相干、互相抵牾的两面集于一人之身。我们之所以为后者的突然显露感到费解,是因为前者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协调一致的世界,为我们所把握,所习惯,后者却常常被我们遮蔽、遗忘。巴塔耶把前者称之为“思想世界”,将后者称之为“色情世界”,两个世界是相互补充的,没有它们的协调一致,主体的总体性就无法完善。
日常生活对作家而言,就是他的“思想世界”,但我们也一样要能理解,作家完全可以在笔下构造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色情世界”。巴塔耶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习惯于“思想世界”就遗忘了“色情世界”,也不必诧异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个体本就包含着“思想世界”和“色情世界”两个维度。两个世界看似截然相反,却完整地内在于同一个生命,作为个人的王宏图和作为小说家的王宏图只是一体两面,唯有同时把握他的“两个世界”,才是对他的完整理解。
齐泽克对“快感”的分析能进一步给我们启发。齐泽克说:
某个人可能婚姻幸福、事业成功、高朋满座、对生活十分满足,可同时他仍然恋上某种快感的特定形式(罪业),愿意为此而付出一切,而不是放弃它(毒品、烟草、某种变态性关系,等等),尽管在他的符号世界中一切都井井有条,这个绝对没有任何意义的入侵,这个倾斜把一切都搅乱,对此他无能为力,因为正是在这一“罪业”中,他的主体才接触到紧密的存在,一旦这一“罪业”被剥夺,他的世界从此就空无一物。
如果说巴塔耶的“两个世界”同时内在于一人,但二者并不对等,“思想世界”压抑了“色情世界”。齐泽克也区分了“符号世界”和“紧密的存在”两种概念:婚姻、事业和日常交际其实都属于“符号世界”,外部的符号编制成一张密密的网,牢牢地把主体捕获,使其不能动弹,使其无法接触“紧密的存在”。或者说,因为“思想世界”压抑着“色情世界”,使主体成为拉康意义上的“创伤性”存在,“创伤”又本然地询唤快感。
在齐泽克那里,“符号世界”和“紧密的存在”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只有当快感抑或罪业入侵了符号世界,在越轨的裂痕中和快感的尖叫中,鸿沟才被打破。快感是“非历史的”,它逸出了“符号世界”,是一种“倾斜”,是一种主体性的越轨,是既有格局的打破,对快感的渴求以“罪业”这一隐秘的形式得到纾解,“罪业”使主体重新找回快感,重新接触到存在。
这样看来,王宏图笔下的人物的其实本是处于一个过分“平衡”的世界,一个“井井有条的符号世界”,但王宏图一定要让这个世界“倾斜”,让“罪业”入侵。小说里的人大多在物质上是丰裕的,情感上也不缺伴侣和归宿,更没有具体的目标要去达成,却每每在失落与痛苦的心境中中苦苦挣扎,犹疑、忧郁、窒息、躁狂的情绪在小说中弥漫,不得纾解,文本呈现出一种紧张的拉锯,随时处于崩裂的边缘。这样的一种紧张感,不正是齐泽克所谓的“创伤性”?于是,王宏图只有屡屡借助某种“罪业”,借助笔下的不伦之性、变态、暴力甚至死亡,才能让人物逃出现状,冲破符号世界的层层包裹,重新感知自身的存在,王宏图也才能借此把握了人物、存在和世界三者的关系。
往深处看,我们更可以将王宏图笔下的人物看作是他自身的隐喻。写作,就是作家王宏图本人面对“符号世界”的一次越界。他何尝不是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处于过分安稳、和谐的符号世界中,既如此,写作,尤其是越界式的写作,便成了他的“罪业”:教授不必一定皓首穷经,偏偏投身小说不务正业;生活中行止有度,偏要在小说中执著纠缠歇斯底里;立身谨严,偏偏为文放荡,大写色情与暴力。
就在这样的越界中,作家在小说世界里翻江倒海为所欲为,一个过于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的生命借此打破了自己的符号世界,尽情地沉溺于“快感”,重新触摸“紧密的存在”。越界,既呈现于王宏图小说的内容,也呈现于他的风格,更时时诱惑着作家本人,以写作去平衡、圆满着自我。
(责任编辑 王 宁)
郑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