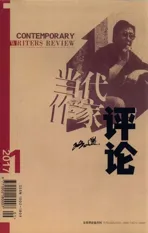古老文明之间的当代对话
——埃及汉学家、翻译家哈赛宁先生访谈录
2017-11-13黄学呈哈赛宁
黄学呈 哈赛宁

——埃及汉学家、翻译家哈赛宁先生访谈录
黄学呈 哈赛宁
哈赛宁·法赫米·侯赛因博士( Hassanein Fahmy Hussein),埃及汉学家、翻译家,精通阿拉伯语、汉语,熟悉法语、英语。是当今中埃、中阿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2016年8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哈赛宁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以表彰他对中华文化和文学海外传播、促进中阿文化交流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哈赛宁先生系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沙特阿拉伯沙特国王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在中国的学术身份有:鲁迅国际研究会理事,莫言研究会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世界研究》刊物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研究范围主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阿拉伯比较文学,汉语阿拉伯语著作翻译,当代中国社会。
近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吉林大学文学院学生黄学呈(以下简称“黄”)对哈赛宁先生(以下简称“哈”)进行了采访,对话实录如下。本文经过哈赛宁先生校阅。
黄:哈赛宁先生,您好!得知您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向您表示祝贺! 2013年34岁就拿到了埃及国家青年翻译奖,37岁拿到中国文化交流界的最高奖项,您多年的辛苦又一次得到社会的认可。今天想了解您的一些情况,代表中国的学生,分享您的经验和知识。
哈:谢谢。收到奖励当然高兴,这也是对我的鞭策,我需要更加努力工作。我非常乐意和中国朋友分享我的一切。
黄:哈赛宁先生出生在埃及什么地方?有什么特色?
哈:我是在埃及南方艾斯尤特省农村出生的,一个典型的尼罗河谷村落,阿勒·嘎纳耶姆Elghanayim城,一个叫阿勒·阿宰兹阿(Elazaiza)的村子,离开罗大约有400多公里,到卢克索古迹大约400公里,离最近的金字塔大约有250公里,到沙漠也不远。尼罗河从村子20多公里远的地方流过,村民灌溉和生活用水依靠尼罗河,尼罗河滋养着我们的一切。
记忆中的故乡,每天在宣礼塔呼唤中苏醒,开始一天的喧哗,大人们在田地里劳作,孩子们在树荫下、渠水中嬉戏。年复一年,那些养育我们的小麦、棉花、玉米、甘蔗、花生在烈日下顽强地生长。我们埃及人都是尼罗河的孩子,就像你们中国人是黄河长江的儿女一样。村子是个小社会,既有质朴的风俗和乡亲,也有复杂和纠结的邻里关系,人们为生存和生活,每天重复演绎着简单而又复杂的生活。
黄:中国人和阿拉伯人都重视家庭和亲情,能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和成长背景吗?
哈:我在这里要感谢我的父母、兄长,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亲人们的关爱和支持,是我取得一点成绩的主要动力。
我们的家庭是传统的穆斯林家庭,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不识字的。但我父母特别重视教育,想方设法让儿女读书。家中兄弟姊妹九人,我排行老三。由于过去经济条件有限,我两个哥哥当年只读了中专。父母和哥哥对我的生活帮助很大。现在父母亲都70多岁了,身体还好,父母故土难离,还在老家生活。
我妻子是开罗人,也是毕业于艾因·沙姆斯大学汉语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是位贤内助。我们自己的家在开罗。因为工作原因,现在我们全家人在沙特利雅得,算是客居他乡吧。
我们有两个孩子,大女儿Salma是我在北京读博的时候生的,现在8岁了,名字的阿拉伯语意思是“平和、尊敬、庄重”。小儿子Anas, 5岁了, 阿拉伯语意思是“陪伴、护佑、守望”。他们都非常聪明可爱,是我的骄傲,他们俩在利雅得的国际学校上学。他们也喜欢学习汉语,我希望他们长大后,也加入中阿文化交流的队伍。
小时候家境不宽裕,刺激我努力学习、改变自我、改变生活,艰苦的条件是我们生命的起源,也是我们成长的动力。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听说过省里的一些著名人物、知名学者和作家,于是暗自下决心,向他们学习,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如埃及第一任总统纳赛尔,埃及现代著名作家穆斯塔法·曼法鲁提、马哈茂德·巴达维等人。他们的事迹和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他们是我们少年时代的偶像和榜样。
黄:您是如何开始学汉语的呢?汉语可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哈:我小时候成绩好,在学校一直是第一名,是父母的骄傲。我小时候对语言特别敏感,学习英语和法语进步比较快,对外面的世界和远方充满了期待,看见外国人就主动搭讪。最早接触中国人是在历史名城卢克索,那一年我和几个同学在省里参加知识竞赛,获得第一名,继而又被安排到历史名城卢克索参加为期一周的全国知识竞赛。我在卢克索碰见一个香港旅游团体,主动和他们说“你好”,算是和中国人第一次交流,当时主要用英语交流。知道他们来自遥远的东方,那个李小龙、成龙的电影中描述的地方,那个使用针灸、筷子的民族,那个有长城和兵马俑的像埃及一样古老的国家。
我是1996年上大学,那一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埃及,苏伊士运河开发区开始建设,中埃外交关系出现一个小高潮。我拿到了艾因·夏姆斯大学在艾斯尤特省唯一的中国语言招生名额。入学后,最初感觉汉语太难学了,一度打退堂鼓。在父亲和两位兄长的鼓励下,刻苦努力,才逐渐找到乐趣。当年艾因·夏姆斯大学招生70多人,后来毕业的有50多人。在艾因·夏姆斯大学,我遇到了穆赫辛·法尔贾尼(Mohsen Fergani)老师,他和中文系的其他老师都对我的汉语学习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他是中国经典《论语》和《道德经》阿文版本的直译者,之前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是通过第三种语言翻译过来的《论语》和《道德经》,有些地方背离汉语原著。
2000年,我以全班第一名成绩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毕业,12月份留校做讲师,后来在艾因·夏姆斯大学攻读硕士。2002年,我被派往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近一年,从那时开始,对中国有了切身认识和系统了解。2005年,我获得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2005-2008年,我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师从高旭东教授,2008年获得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是北京语言大学的第一个阿拉伯博士。前后我在中国北京语言大学留学四年,游历中国诸多城市和地域,结识了很多朋友,也得到许多师长的关照。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艾因·夏姆斯大学是中东和非洲汉语人才培养的中心,有汉语专业博士点,在校学汉语的学生超过1000了。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大专辩论赛”上,艾因·夏姆斯大学代表队曾夺得过非汉语国家组的冠军。在历届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艾因·夏姆斯大学总有好成绩。2003 年我也曾参加过中央电视台国际大专辩论赛,进入了决赛。
黄:您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刘震云的《手机》,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宋岘的《中阿文化交流史》等经典作品。为什么选择翻译他们的作品?目前您在翻译中国作品吗?您的译作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哈:面对浩若烟海的中国文学作品,我们时间和人力有限,只能挑选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优先翻译,以保证向阿拉伯国家读者提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是经过母语读者甄选的,从文本、情节、人物和思想上有代表性,也被世界文坛广泛认可。这些作品写作技法可能是有借鉴他人的,但是素材和思想是一个民族独有的、有代表性的。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所书写的顽强卓绝的生命力、中国传统的吉祥色“红”、丰饶肥沃的土地、波澜壮阔的爱恨,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中的文学诠释。
目前我在翻译中国经济学家张卓元先生2014年出版的《经济改革新征程》,计划由沙特国王大学出版阿拉伯语版。阿拉伯人不仅想知道中国的文学和历史、情感和思想,也想从宏观层面即时掌握中国政府和国家治理的情况。作为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现实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能将国家治理到目前这个状态,中国必然有许多值得让人关注的地方。我想尽快把中国的一些现实情况介绍出去,让阿拉伯世界全面了解中国的当下。
文学作品方面,我最近在精读余华、迟子建、池莉的一些作品。希望最近能见到他们,想和他们交流读书体会,向他们学习,若有可能将翻译他们的作品。
翻译作品中,最满意的是《红高粱家族》。这部作品有历史的厚重和质朴的乡土气息,有土地、国家、民族、母性、生命等广阔的主题,描写的东西似曾相识。人物精神状态恣肆汪洋,笔法酣畅淋漓,情感淳朴真挚,充满了原始的力量。我是农村出来的,因为对土地和农村的熟悉,在共鸣中完成了作品翻译。
黄:您还翻译了哪些作品。您是怎么理解翻译工作的?铁凝在2014年8月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说作者和译者是 “失散已久的孪生兄弟或姐妹”,您怎么看?
哈:博士毕业之后,一边教书,一边翻译,这七八年时间,翻译的各类著作20多部。文学类的,除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透明的红萝卜》、刘震云的《手机》、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还有傅谨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导论》、张仲年的《中国实验戏剧》、阿舍的《逃奔的骨头》、《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收集了张洁、铁凝、残雪、迟子建等作家作品)、平原的《风往北吹》、回族作家了一容的《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回族作家马知遥的《静静的月亮山》、刘宾编选的古代维族学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的《〈福乐智慧〉箴言选萃》等。历史类的有,《中华5000年历史故事》、宋岘的《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生活类的有周玉奇的《扇之韵》、乔玢的《玉之赏——生活图赏》、谢定源的《中国饮食文化》。
这些年,先是在中国求学,后在埃及教书,2013年后客居沙特国王大学教书,作为一个学者和译者,生活比较简单规律。每天在宵礼之后,安顿好孩子后,开始读书和翻译。阿拉伯的夜是安静的、清凉的、阔远的,夜里是跟中国作家沟通思想的时刻,也是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的时刻。头顶上有我们的星空,身边有亲爱的家人,我常常工作到深夜。一个人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时,往往就不觉得疲倦,每天享受读书和翻译的时光。每每获得一点成就,就有一点喜悦,也发现一些问题,这所有的一切又继续鞭策我前行。
铁凝的讲文学作品的译者和作者的关系,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无论作者还是译者,都是基于对文学的热爱,对他人和自我的比较,对人、社会和历史的关注,向世界传达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翻译是一个学习和研究的过程,语言转化的前提是意思的深刻领会、对现实世界的了解和掌握,认真研读这些文本,仔细了解文本背后的故事,是整个翻译的过程。在研读文本的时候,译者就进入作者的世界,然后用母语将作者世界的故事传递给自己的族群。基于对作品的充分掌握和再次创作,所以我们和作者见面时,感觉很熟悉、很亲切,谈论作品时,有同胞一样的默契。
黄:我看有报道说您用开罗方言翻译中国小说,您翻译有哪些技巧?最近看到,中东大报《生活报》、阿拉伯语版《今日中国》同时对您和您的阿文版译作《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做了报道,这本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古汉语,您是如何翻译的?
哈:他们讲的是阿文版《手机》的意译,其实其他文学作品翻译时也有这类情况。有时候直译,有时候意译,用埃及方言翻译河南方言,尽可能让阿拉伯读者生动了解文本、人物和情节。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有25个,3亿多人口使用阿拉伯语,各地方言也不尽一样,因为阿拉伯世界文化的中心在埃及,所以埃及方言算是普及率比较高的,其他地区的人能看懂。还有沙姆地区、海湾地区、北非西部地区、苏丹地区也有各自的方言。有些地方的方言我也听不懂,这就像中国的北京话相对于广东话。
翻译的基本功在于熟悉语言、熟悉文本、多翻译、多思考,深入了解社会和背景知识。见多了就识广,熟练了就有技巧,在于日积月累,是个辛苦活、用心的活。
中阿翻译工作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两种古老文字的含义都非常丰富,文字的歧义比其他语言更加多。当今中阿翻译队伍中,中阿学者都有,视野各异、喜好也不一。从事中阿翻译的阿拉伯学者并不是很多,尤其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总体上是一个蓬勃的开端。中阿翻译语言尚需要一个验证、沉淀和习惯化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译著的积累。中阿文学思想交流、作品文本翻译和翻译工作自身,都有许多事要做。
《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阿文版是沙特阿拉伯国家层面主导和支持直译的第一部汉语作品。以往都是伊斯兰宗教经典往中国的单向输出,这本书是中沙图书交流的里程碑。翻译宋岘老师的《中国阿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的确比较辛苦。这本书中,写了很多关于丝绸之路的古代情况,引用了许多古汉语,地名古今变化也很大。经过查阅资料、请教他人、反复推敲,总算顺利完成了,这是我自认为最有难度的一部书籍。书中记载了阿拉伯的许多事物是沙特普通学者不知道的,书中讲述中国航海家郑和在600年前曾经去过麦加天方,激发了许多阿拉伯人对中国的兴趣。这部书籍出版前后,也适逢2016年初中国元首访沙特,在沙特学界引起关注,有沙特学者提出“我们究竟对我们的中国朋友知道多少”,提出加大“向东看”的力度,建议加大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研究。
黄:知道您接受邀请去过莫言的家乡,讲一讲您对莫言以及对莫言作品、莫言家乡的印象。莫言的故乡和您的故乡有何异同?
哈:我前后见过两次莫言,第一次是2007年11月,那次见面两个多小时,很短暂,就是简短谈论了翻译他作品的事。2012年10月,在我刚刚翻译完《红高粱家族》准备出版的时候,就听到莫言获得诺奖。11月,应莫言邀请,我到山东高密小住几天。乘坐火车到高密时,莫言亲自到车站接我,亲切如兄长一样。莫言对我的招待细致入微,令我非常感激。他知道我是穆斯林,依照穆斯林的风俗为我准备饮食起居。
他家人非常地质朴、热情,我见到他的哥哥、姐夫,一起吃饭,谈天说地。在高密见到了《红高粱家族》中描写的红高粱,有一种穿越到作品中的新鲜感。莫言带着我在街道上走,说“我小说中写的就是这些人、这些物,以及这些人物的故事”。在高密三天,傍晚的时候,我也独自在酒店附近转一转、走一走,莫言作品的“原产地”和母体给我熟悉、亲近的感觉。我在田地里看到了晶莹剔透的“透明的红萝卜”,回来之后,着手翻译了《透明的红萝卜》,2015年阿文版由埃及图书总局出版社出版。
有人说文学作品的译者和作者要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翻译出好的作品。我和莫言的交往,让我进一步跨越地理、民族和文化的鸿沟,更深刻地感知了作者、作品。目睹作品中提到的实物,我对许多原始素材,对作品、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高密,我的确想到我的埃及的故乡和土地,潜意识中有对比,两个古老文明在我的脑海中若隐若现、亲切会面。所有的农村都是那样地质朴亲切,越是底层的人越是勤劳勇敢,感觉到中国的百姓和埃及的百姓一样,淳朴善良坚韧,虽然生活的不容易,却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乐观豁达、顽强生活,环境不一样,历史不一样,存在形式不一样,但人心是相通的,情感是一样,生命力是一样的。到中国基层走一走收获还是很大的。
黄:和莫言比较,余华是“城里人”,你怎么看他和他的作品?
哈:余华的第一部阿文版小说《活着》是埃及著名汉学家阿齐兹教授翻译的。第二部阿文版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是由我翻译的,2016年1月在开罗书展上发布。
我和余华尚未单独见面,本来今年1月份要一起参加埃及国际书展,参加阿文版《许三观卖血记》的发布仪式,由于我当时在沙特参加中阿外事活动,两人最终没有见面。一直通过电子邮件联系,约了好久了,今年也许会实现期待的相逢。
余华的作品比较深刻,情节幽默,题材极端,选择生死、血肉、灵魂、生存、尊严、爱等关于生命的核心主题,写法上大量借鉴了西方的写法,现实批判性很强,读完之后令人回味,引人思考的东西比较多。
余华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写出一些违背常理而正义善良取向的事物,在笑声中让读者感知现实中卑微的普通人物。他的作品中能读出人性的善良,他在批判现实的同时给人们以希望和爱。
黄:2016年1月,第47届埃及开罗国际书展上,《手机》作者刘震云被埃及文化部授予“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颁奖理由是“旨在表彰其作品对埃及文学及阿拉伯文学带来滋养”。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哈:关于刘震云的作品,2015年阿联酋书展上发布了我翻译的阿拉伯语版本的《手机》,该书是2015年阿拉伯世界畅销书之一。还有艾哈迈德·赛义德博士(中文名“白鑫”)翻译的《我不是潘金莲》,以此为主要原因,中国作家刘震云被埃及及阿拉伯读者认识和了解。
刘震云获得奖励的原因:作品表述幽默,语句简短,表述直白,故事性强,传承中国本土叙事技巧,内容直面生活现实,即时反映生动活泼的城乡生活,埃及读者很容易阅读和接受。刘震云善于把琐碎的小事情串联后,做成历史和现实的镜子,映射当代中国发展进程。《手机》以通讯方式为基本线条勾勒过去中国人生活的百年,20世纪开始,中国人依靠诚信的口信传递亲情,20世纪中期是借助有线的电话传达真挚的爱,在世纪末,科技赋予人们现代化生活,却也带来了复杂的变化和层出不穷的烦恼。《我不是潘金莲》以“一根筋”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争取权利、不断上访为线索,描写了中国改革进程中妇女20年的维权处境和各类相关现实,荒诞中透露真性情。
我去过河南,在洛阳和开封有过停留,感受到中国人文的悠久、博大和复杂。驻留在街头看那些匆忙行走的使用手机的人们,也许小说中的故事正发生在他们身上。
曾经和刘震云会面也是两次,一次是2014年8月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时在北京见面,第二次在2015年5月在阿拉伯阿联酋国家阿布扎比国际书展《手机》发布会上。
相比之下,莫言、余华的作品比较厚重、深沉,非本土文化背景的读者需要再三回味才能了解人物、情节。在中东的几个书展上,莫言、余华、刘震云的书籍都是畅销书。今年1月,在埃及国际书展上,阿文版的样本都被人买走了,供不应求。当然,盗版的电子版在网上也开始流传了。
黄:我发现关注中国的埃及学者分为两个时期的两个团队。一个是新中国建立初“十七年”时期的访问中国的阿拉伯作家和学者。另一个时期就是改革开放后留学中国、1990年代后开始发力的新生力量,也是当今埃中文化交流的主力。在您的有关论文中提到,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埃及作家曾经访问中国。这些学者还在吗?他们近况如何?中国人总是关心老朋友的。
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世界学者对中国文化只是做了初步的了解,却是非常重要的开始,开启了阿拉伯世界对现代汉语和现代中国直接认识的大门。和中国的马坚、纳忠、张子仁、林仲明、杨朔、冰心一样,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先驱。
这些埃及学者、作家和诗人访问中国后,有人写了文章,有人立即出版了书籍,拉开了现代中阿交流文化的序幕。马哈茂德·伊勒·巴达维(1912-1986)出版了书籍《梦想之城》,生动记录了中国见闻。当时政治环境促进了这种交流,是“十七年”文学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国家惺惺相惜、合作发展的结果。
1956年前后访问中国的学者大都不在了,马哈茂德·伊勒·巴达维、萨阿丁·瓦赫巴、穆罕默德·哈赛宁·黑克勒、叶赫亚哈基、赛尔瓦特·阿巴扎、艾尼斯·曼苏尔、福阿德·卡尼德勒、哲迈勒·黑托尼,都已先后去世。在世的尚有优素福·莎鲁尼、艾哈迈德·射赫、法鲁克·舒莎、李副克·巴达维、艾哈迈德·阿卜杜姆·阿提何加兹、女作家伊克巴勒·巴尔卡。这些在世的文化交流的见证者和经历者大都年事已高、退休在家,偶尔也参加社会活动。
黄:去世的学者是中阿文化的损失啊。愿在世的前辈平安健康,欢迎他们再来中国。当代埃及的汉学家有哪些?他们都在哪些单位工作?埃及研究中国的机构有哪些?
哈:当代活跃在埃及的汉学家大多是“五○后”。“文革”时期,汉语教育在埃及一度停止。1977年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重新开设中文教育,当代汉学家和中国改革一起成长。
当代埃及主要的汉学家有:艾资哈尔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阿齐兹(Abdel Aziz Hamdi) 博士。曾在中国学习和工作过,在北京大学完成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翻译了艾青、曹禺、老舍、郭沫若、沈从文、田汉、鲁迅、铁凝、余华、莫言的一些作品。他曾先后用阿文出版了《中国的尝试》《中国的穆斯林》《中国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文革”文学初探》《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概述》等书籍。穆赫辛·法尔贾尼(Mohsen Fergani)博士,直接从汉语翻译了《论语》《道德经》等古典书籍,还有莫言小说《牛》《梦境与杂种》,正在翻译的经典有《诗经》,他翻译和创作了许多古代中国典籍和研究专著。今年初,他在埃及获得习主席颁发的“中阿友好杰出贡献奖”。
当然还有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的不少中国语言文学专家教授,他们通过其在汉语、中国文化及文学等有关中国方面的研究,在阿拉伯和中国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当今还有不少正在成长的青年才俊。
关于埃及研究中国和东亚研究的机构,目前成规模的主要是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开罗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赫勒晚大学、艾兹哈尔大学等。整体研究工作处于发展阶段,需要各方的支持。
中国在埃及设立的“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对中国文化在埃及传播有支撑性作用,目前有上海图书馆网络查阅终端,为埃及学者提供了信息和资料查询的方便。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工作人员和埃及汉学家、汉语学习者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黄:您不但翻译文学书籍,也翻译史学书籍和当代社会热点书籍,而且深度参与学术研究。你对翻译家、学者广泛参与社会实践是如何认识的?
哈:学术和生活、翻译和体验,都是相辅相成的,非汉语本土翻译人士,在学校里学习或教书,毕竟接触面还是有限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边学边实践,多参加社会活动,多了解新鲜的综合性信息,才能翻译出更好的书籍。
文学书籍表面上是讲故事,翻译语句似乎容易,但是要完整地表述意境和情节,这就比较难了。所以文学作品的翻译是需要生活的支撑的。不深入了解社会,难有精品译作。我主要有三种方式:体验中埃民众的原生态生活,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研读翻译当代中阿社会政治经济书籍,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
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经常参加一些中埃、中阿高层文化、经贸和政治交流活动。荣幸的是,2016年1月在沙特萨勒曼国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沙特阿美中国石化延布炼厂投产启动仪式时,我担任沙方同声传译。在见证重要事件的同时,使我更加认识到语言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黄:2015年,艾哈迈德·赛义德(白鑫)重新出版的阿文版《鲁迅精选小说集》,您为该书写了序言。当今时代,埃及和阿拉伯世界还需要鲁迅?
哈:艾哈迈德·赛义德博士重新出版鲁迅作品的目的不仅在于提高阿文表述的准确性和生动性,使其更接近原著,也在于又一次在埃及“呐喊”,这是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责任。鲁迅重视民族和人的自新,关注现实,启发民众,他的作品永远需要我们学习和阅读。鲁迅小说是镜子,它照射着我们的灵魂。每个国家,都有许多阿Q、狂人、孔乙己。
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启蒙者与呐喊者,鲁迅文学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世界经典文学的意义在于人物和思想的永恒性、普遍性。鲁迅在阿拉伯世界有着一定的传播,接触过鲁迅作品的阿拉伯国家的学者和外交官对于鲁迅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赞扬鲁迅为中国和中国百姓所做的一切。
现实社会一些地方的剧烈变化和动荡不安,使有良知的人非常痛心,使我们常常想起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我希望阿拉伯读者知道这些小说中的人物,看看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尽快自省自强,行动起来,克服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的短板,建设稳定繁荣的国家,让百姓过上和平富足的生活。希望连绵不断的“呐喊”声,唤醒民众从“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醒过来,打破自己身上的愚昧无知和落后状况,推动民众的启蒙、民族的发展,建设新的个体、新的文化、新的民族、新的生活。
黄:您怎么看埃及文学中民族主义存在状况?埃及民族主义发展和哪些作家或学者相关?
哈:从文学角度来讲,民族是文化多样化的基础,文化是民族的基因。要保持民族基因的存在和延续,就必须要有民族和民族主义。民族不独立,文化就不独立,就濒临亡国灭种了。中国作家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上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各民族的文学都是独特的,没有可比性,没有高低贵贱、落后先进之分 ,各民族的素材和母体是无法复制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翻译和交流的价值所在。
阿拉伯民族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之后,禁止使用阿拉伯文字、推广突厥文字,阿拉伯文明一度衰落,百姓生活在各种矛盾和压力之下,民不聊生,有些族群濒临消失。1798年拿破仑侵略埃及后,唤醒了阿拉伯民族,刺激阿拉伯人摆脱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文字。经过最近200年的发展,阿拉伯文化在阿拉伯人的努力下逐渐复兴。
阿拉伯和埃及近现代史上,出现了许多民族主义思想家和作家,他们或是反对土耳其傀儡和西方的统治,或是主张学习西方经验,或是坚持继承和发掘民族文化,或是批判自身文化和社会现实,推动了埃及和阿拉伯文艺复兴和民族振兴。他们立足现实,关注现实,是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的守护神和创新者。
他们主要有:叙利亚人布特鲁斯·布斯塔尼(1819-1883)、黎巴嫩人布希利·舒马伊尔(1860-1917)、埃及人穆哈默德·阿布杜(1849-1905)、埃及人哈穆德·萨米·巴鲁特(1838-1904)、埃及人艾哈迈德·邵基(1869-1932)、埃及人哈菲兹·易卜拉欣(1871-1972)、埃及人赫利赫·穆特郎(1872-1949)、埃及人阿卜杜·拉赫曼·舒凯里(1886-1958)、阿拔斯·迈哈穆徳·阿卡徳(1889-1964)、黎巴嫩旅美作家纪伯伦·哈利勒(1883-1931)、伊利亚·艾布·马迪(1889-1957)、埃及人穆罕默德·穆韦利希(1868-1930)、埃及人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1888-1956)、埃及人穆罕默德·帖木儿(1892-1921)、叶海亚·哈基(1905-1992 )、埃及人塔哈·侯赛因(1889-1973)、埃及人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优素福·伊德里斯(1927-1991)、著名思想家宰克·纳吉布·麦哈穆德(1905-1993)等人。他们对于埃及,就像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郑观应(1842-1922)、魏源(1794-1857)、林则徐(1785-1850)、严复(1854-1921)、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章太炎(1869-1936)、陈寅恪(1890-1969)、孙中山(1866-1925)、陈独秀(1879-1942)、鲁迅(1881-1936)、李大钊(1889-1927)、胡适(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冯友兰(1895-1990)、老舍(1899-1966)等学者作家之于中国一样。
黄:在近现代史上,埃及有哪些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埃及是个农业大国,写农民农村、关注社会基层的作家有哪些?
哈:阿拉伯社会和埃及的现实主义思想和文学,主要体现在阿拉伯文艺复兴进程中。是阿拉伯人的自我拯救和重新崛起,当然道路充满坎坷。
在文化上,思想家、作家书写百姓现实的生活,书写与现实相关的事物,引导社会“正视当下的生活”,为大多数百姓着想,用不同的方式关注、思考和研究现实的问题。埃及有自己的鲁迅,有自己的老舍,也有自己的丁玲、冰心,也有自己的莫言。
埃及最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有:塔哈和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日子》《鹬鸟声声》等作品。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和他的《开罗三部曲》《始与末》等作品。优素福·伊德里斯和他的《最廉价的夜晚》《罪孽》《法尔哈特共和国》。
埃及写农村的作家典型的是马哈茂德·伊勒·巴达维、阿卜杜·拉赫曼·舍尔卡维、优素福·伊德里斯。
埃及写城市的代表作家是纳吉布·马哈福兹马,我们称为他为埃及的老舍。他对开罗生活的文学描述,就像老舍对北京生活的描述一样。
黄:在近现代史上,埃及社会的“启蒙”是如何进行的?
哈:启蒙的主导思想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以法国为源头、伴随资本主义和现代化进程在全球推开的思潮。启蒙是人类发展的必经历程。具体到每个民族,过程又不一样。启蒙进程是需要相应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启蒙在各方因素的互动中提升和前进。
客观基础不成熟的时候,急躁和幼稚的启蒙适得其反,所培育的泛滥的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一盘散沙,当今中东社会有鲜活的样本。另外,启蒙也是当今西方一些组织主观上煽动暴乱、扰乱他国的工具和借口。
文学对埃及的启蒙作用当然是明显的,前面说过的作家和作品就是典型。这是一个庞大的命题,一句两句说不清,有机会我们再进一步详细切磋。不过我相信,阿拉伯人正在努力,和中国一样,在风雨之后,埃及一定会走向繁荣。
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翻译家、汉学家、学者,您是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距的?“落后的”东方该怎么办?
哈:从近现代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都受制于人,西方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引发了人类格局的巨大变化。
就学术方面,西方在资料积累、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等方面走在了前面,在绝大多数领域,我们被动地跟着西方在跑,西方具有绝对的优势。况且在殖民时代,西方营造了英语的世界语地位。目前西方几个国家掌握着全球学术的话语权,欧美等发达国家10亿人引领其它50多亿人的目光和思维。
但是,文化是民众精神的实践,文化、文学、文本和我们的广大的河流山川紧密相联系,和我们的历史传承相联系。这是最根本的东西,谁也不能从阿拉伯或者中国的土地上复制出一个美国或者欧洲。西方原创研究的素材和标本很多在亚非拉。比如,埃及考古,西方国家只能和埃及学者合作才能有研究成果;人类学方面,非洲社会就是丰富的活标本。
要想缩小和西方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借鉴西方有益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从原生态、基础层面着手,主动构建新的平台,设定新的维度,培育新的体系。亚非世界,有许多课题等待着我们去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走出去”是明智的,学界也要“走出去”,研究素材和视野的扩大,必然会带来丰硕的成果。
我们借鉴西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相信西方能做的,亚非国家也能做,只有行动才能改变。比如考古、医疗、生物、建筑、地质、文学、哲学、人类学、经济方面,发展中国家就有很大的合作和拓展空间。通过学者的交换、学术刊物的相互认可、大学资源的共享、科研和社会服务介入、企业和企业的对接,从官方和民间一起着手,相互扶持和切磋,也许就能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黄:您作为当今中阿文明的传播者和研究者,也是两个文明交流的推动者,您认为中阿交流的瓶颈在哪里?您对中埃、中阿交流有什么期待?
哈: 中阿文明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中国和埃及有相似的历史经历,面临同样的发展问题,特别是近现代社会的历程都令人嘘唏不已。当前中国和埃及都处于继承和发展的关键时刻。
中阿交流中,语言是中阿交流的瓶颈,需要双方积极克服。语言的隔阂导致文化的隔阂、人群的陌生。英语作为世界语言地位不可撼动,但不是老百姓的母语,不能创造水乳交融的感觉。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需要培养大量的语言人才,语言人才不仅仅是学校里培养的,更是在相互的交往和实践融合中锻造的。
从开拓丝绸之路到郑和船队访问西亚非洲,到今天的“一带一路”构想,从13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历元代中国,到目前大量阿拉伯学者出访中国,都说明,直接的生活交流才能带来更大的改变,全方位的交流会带来全方位的改变。当经济交流达到一定程度,文化和社会的交流需要全面跟上。
中阿交流中,文明的融合大于冲突。今年是中埃建交60周年,各界都在举办庆祝活动,相信中埃中阿文明交流肯定是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入。一切才刚刚开始,希望我们做得更好。
黄:谢谢哈赛宁先生!占用您宝贵时间了。阿拉伯先知说“学者的笔墨比战士的鲜血还要珍贵”,感谢您呕心沥血逐字逐句的翻译工作,感谢您对中阿文明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向您致敬。愿中阿、中埃文化在交流中共同繁荣,造福世界。
(责任编辑 李桂玲)
黄学呈,吉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哈赛宁·法赫米·侯赛因,埃及汉学家、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