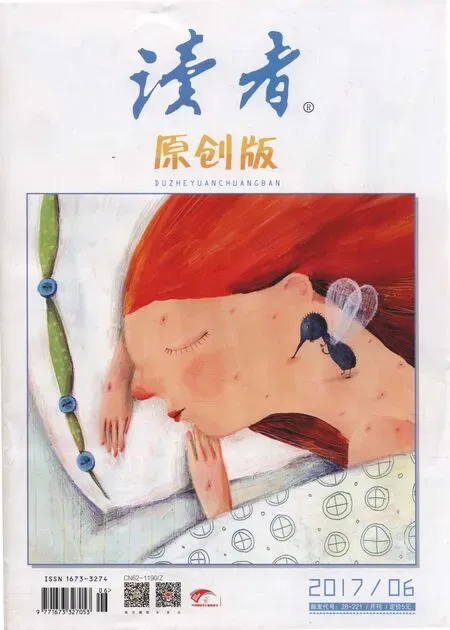陪护日记
2017-11-13文|王佩
文|王 佩
陪护日记
文|王 佩
2016年3月15日,父亲因病住院,我回故乡陪护了10天,直到他出院。
一
中午接到电话,父亲因急性心梗住院,需安放支架。我从上海乘下午的高铁赶往老家。车窗外,桃花盛开,我无心欣赏,亦无人可诉。他是我的锡安山,是庇荫我的翅膀,可不能有一点儿闪失。
晚上9点我赶到医院,支架手术成功,但父亲依然未脱离危险。我和堂弟、表弟几人轮流彻夜看护。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父亲从早晨5点开始心脏疼痛,自己吃了硝酸甘油,未缓解;8点去县医院求医时,因已难以行走,竟自己驾车去。到医院,医生一查心电图,发现是心梗,医院无法消融,遂用救护车将他送到50公里外的市医院。幸有贵人相助,立即住院抢救。经心脏造影,发现父亲的一条主动脉堵塞,要马上进行支架手术。
我守在父亲的床前,眼睛盯着心电图仪,要时刻注意上面的异常,有时候胸贴脱落,会有蓝字警告。
父亲刚硬要强,固执得像李尔王。他虽然已经68岁,但高兴起来,还动不动就要喝上八两一斤。有次醉酒后骑电动车摔得鼻青脸肿。这次心梗跟他前几天喝酒过量有关,但此时又怎么能埋怨他?
夜深了,窗外霓虹字闪烁,以商务宾馆的名义发出召唤,然而我必须守在这里,一如40多年来,父亲一直守护着他心中的那个少年。
二
夜里喝了一罐红牛,我又精神了。
刚才父亲醒了,为了消除尴尬,我给他讲了儿子在幼儿园的几件小事。他笑起来,声音很无力,但听得出发自内心的愉快。
随后谈起他的病情。由于血管堵塞了数小时,有的心肌细胞已死,搭上支架后会活一部分,但能活多少未知。他说起另外一个老干部,说他2002年搭了支架,一直活到现在。我顺着他的话说:“支架很安全,能用20年。”
我始终不敢看他的眼睛,有些手足无措。跟他谈起以后要过健康生活,平时要多注意。我不会说现成的漂亮话—懂事的孩子会笑着说:“孙子结婚还要你坐席呢!”
我说不出。
我一个人回到父母的家中暂做休整。来到父亲的房间,看到展开的被子,他看过的杂志,还有一对保定铁球。我想到差点就与他永诀,大哭。
哭罢,我在父母为我们一家三口预备的朝阳的房间里,安然睡去。
下午回到医院,给父亲放了我儿子用微信发来的祝福视频,他开怀大笑。我们只知道安慰病人,我们不知道,病人也在安慰我们。
三
凌晨3:30,病房的门被撞开,推车声、杂乱的脚步声、金属撞击声传来,是同一病房里的4床在抢救。后来仪器的嘟嘟声、除颤器一下下的按压声不绝于耳。最后4床被送到ICU(重症监护病房),凶多吉少。
在CCU(冠心病监护病房),这是常有的事。每个病人的心电图都在医生值班室内有显示,一有异常,医生会立即做出反应。夜里,医生监测到父亲心律不齐,专门过来为他做了心电图。
山东讲究礼仪,亲友免不了来病房探望。昨天来了一位家中的老友,他的到来给父亲以欢畅。因为他搭了3个支架,并且很平安地度过了6年。他的现身说法为父亲未来的康复提供了参照:不抽烟不喝酒,该凑的酒场、饭局依然凑,只不过人家喝酒你喝水。
我猜,在此刻的父亲看来,只要能够度过此劫,别说戒酒,断食也没什么。人,皮连着肉,肉连着骨,忘身外之物易,忘身难。
病人的心理是脆弱的,平时的权威尊严,在病床上面对一堆管子时顷刻崩塌。勉强维持自尊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忍受。忍受痛,忍受未知的命运。只有睡梦中的叹息透露出一点儿秘密,随着一个翻身,又掩盖住了。
父亲一生经历过几次大的挫折,有两次还是我给他带来的。这次肯定是最大的一劫,该轮到我为他清理麻烦了。
父亲跟我商量,给他房间里的电脑装上“游戏大厅”,以后打牌就在自己家里。之前,他是在院子里的老年活动中心打牌,人声鼎沸,二手烟缭绕。
我们做计划,有时并非真的为了执行,而是让自己心里好过一些。
四
在父亲住院的日子里,谈论他的孙子王元澄始终是他最大的安慰。死确实可畏,但是想到自己的生命在子孙身上得到延续,也就增添了可以战胜死亡的幻觉。
我终于向父亲发出了邀请,请他参加元澄君的大学毕业典礼。这个邀请并不真诚,因为连邀请者也不能保证到时候一定出席。元澄君今年才4岁。
随着陪护时间的增加,父亲抢救中的一些细节渐渐显露出来。例如,我通过母亲知道了他在被送去抢救的路上说的一句话:“生命真是脆弱啊!”
这话在舞台上说出来平淡无奇,但在拉着警报摇摇晃晃的救护车上说出来,就不一样了。
我如果是父亲,会在半夜似醒未醒之际,对自己说:“这是一场梦,醒来!”
醒来发现,一切都是真实的、血淋淋的。
对于病人来说,黑夜倘若不在睡觉,应是最难熬的—为自己的遭际埋怨,为自己的错误后悔,为未竟的心愿不甘,有苦不能诉,有叹息都咽到肚子里。这时,也许看到旁边面对电脑打字的儿子,想到不谙世事、嬉笑玩耍的孙子,会略有一点儿释然。抬头看看命运的重锤,嘴角微微一弯。
五
今天第一次跟父亲发生冲突,现在想来后悔极了。
起因是母亲要从县城来市里的医院送饭,但是她自己没有单独坐过长途车,也不会打的,我就说回家去接她。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允许。我习惯性地顶撞了他一句,同时说了一句很伤人的话:“好像你自己啥问题都能解决似的!”
这话一出口我就知道错了。父亲不再说话,但是我看见显示器上心率和呼吸频率都在增加。我赶紧服软,说不去接了,但是转过身去,看窗外雾霾中的朝阳,留给他的只有一个后背,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
我渴望母亲来医院,哪怕待一个小时,我也觉得有了主心骨。
但这都不是我顶撞父亲的借口。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内心一直住着一支起义军,而父亲就是统治者的肉身代表。当我的反抗被一次次镇压下去之后,父子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会爆发,更多时候是压抑。
少年心中的父亲总扮演一个“败兴人”。大学时候,我与一位外教关系不错,他春节期间无处去,我就想请他到我老家来过年。跟家里说了之后,父亲如临大敌。首先,父亲说外国人来小县城会引起轰动,根本无法接待;接着,父亲说春节对于一家人多么重要,外人来过年很不合适。我最后只好红着脸向外教撤回了邀请。但是隔阂已经种下,我觉得父亲太不可理喻了。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种焦虑。在小县城和小村庄,要想“安全”地生活,最好的方式是不出头,用我们当地话说叫“不脱俗”。“枪打出头鸟”,是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假如父亲当年开明到让一个美国人到家里过年,也许就没有他后来的事业发展和人脉关系了,而这两者也是生存必需品。
对于一个只知道索取的少年来说,只要我觉得爽,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跟父亲发生冲突后不久,母亲竟然自己打车来到了医院,而且是拼车,50公里的距离只花了20元。对于一位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从没有独自出过远门、从没有打过车的家庭妇女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奇迹!
父亲并没有责备她,我想他心里也是安慰和喜悦的。在不可知的灾祸面前,还有什么比家人的关爱更能慰藉人心呢?
从医生那里传来了好消息,经过综合诊断,医生同意父亲从CCU转入普通病房。父亲终于拔去了浑身的导线和管子。
他很开心,在新的病房里,还兴致勃勃地看了会儿电视。
这些年来,父亲没少陪亲戚们去看病,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北京。一陪就是十几天,从求医托人,到病房陪护;从发现病情,到病程结束。这固然与父亲的重情重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一种生存策略:生死互助。
我的故乡是贫瘠苦寒之地,要想在这儿生活下去,人不能各自为战,必须以血缘和亲族为基础,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
生老病死这样的大事,更不能离开亲戚的援手,尤其是兄弟姐妹这样的至亲。
从父亲这次生病就看出来了,父亲发病的第一时间我不在家,全指望父母亲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后代;第一时间前来探望的,请了年假或者逃了班在医院昼夜看护的,也是这些亲人。他们并没有义务非得这样做不可,如果不是由于父亲的好人品和多年积下的功德。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只有中专文凭;阅历不广,生活的区域从没跨出过县界;出身贫困,还背了个上中农的成分,无法参军;历尽挫折,有几次还是儿子带来的。但他身上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在荆棘丛中开出花朵,在虎狼包围下谈笑自若。他豁达、乐观、不屈不挠,从不当着家人的面长吁短叹。他知道自己资源有限,但珍惜每一次机会。
这么好的一个父亲,我竟差一点儿失去。
想到这里,眼泪不禁再一次落下……
感谢造物主,赐给我这样的慈父。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陪伴。
2016年3月25日,父亲顺利出院,进入漫长且不容掉以轻心的康复期。截至6月份,他已经去医院复查过两次,情况良好。父亲戒掉了烟酒,每天散散步,找老头聊聊天。他还惦记着参加区里的老年人乒乓球比赛,这恐怕是医生不允许的。
感谢家族和挚爱亲朋的关怀照料,感谢医护人员的仁心仁术。正是因为你们,才使得我父亲平安走过黑暗的幽谷,来到辽阔之地。
谨以此文,献给天下所有慈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