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时空观
——读王啸峰的小说集《隐秘花园》
2017-11-08小海
小海
小说家的时空观
——读王啸峰的小说集《隐秘花园》
小海
小说家常常像一个建筑师,他将自己的记忆像蜘蛛织网一样,编织出另一重时空,让读者深陷其中。在王啸峰的《隐秘花园》中,小说家的时间就是在苏州古城的大街小巷这个空间中铺陈,他是时间的捕手,让时间凝滞了,结晶了。同时又因了神秘与不确定元素的加入,使得他的小说虚实相生,玄机迭出,趣味盎然。这种虚虚实实,交错杂陈的情景,会让我想到他的散文写作。啸峰小说有散文化的意趣,比如说《抄表记》《炖生敲》《萤火虫》等,都是有故事内核的散文。多年前,读他散文时,我跟他说,你用了小说的笔法,这是好事,打通了两者的界限,文章就多出了不同的向度与味道。文无定法,随物赋形。所谓散文,也是姑且称之的,就是蕴含可能性的文体。可以说,他的小说是一种散文小说。这样的散文小说是一种混沌意义上的小说。他守候在散文与小说两种文体更开阔的可能性上,反而让我对他的写作存有更进一步的期待。这符合我对散文与小说这两种文体的一种诗意体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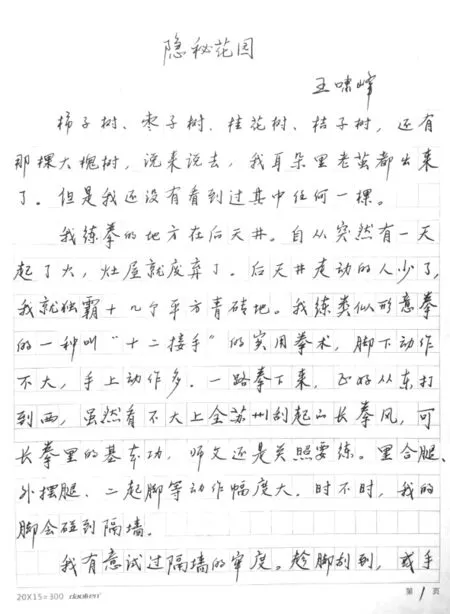
王啸峰手稿
我这种基于混沌意义之上的文本对应世界的文体认识论,与啸峰文本的不确定因素和开放的记忆相关。表现在他的小说中,就与江南迷离的梅雨季有关,与古城的幽灵和神秘传说有关。时空像处于一个压缩的透明气泡之中,像《井底之蓝》的渲染,《隐秘花园》的后花园,《角色》中的恍惚——他诱使你进入小说家精心营造的卷曲时空。感觉一个世纪前物理学家闵可夫斯基的这段话似乎是用来定义王啸峰小说的:“从今往后,空间和时间本身都将注定在黑暗中消失,只有二者的一种结合能保持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美]基普·S·索恩著《黑洞与时间弯曲》,李泳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16年1月,第118页)
汪政在《阴暗的魔法——王啸峰小说论》中说:“一般而言,小说家对时间的迷恋主要来自于对深度或者历史感的钟情,但王啸峰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嗜好,甚至,他会有意通过时间的平面化来消解深度与历史感,也就是说,不是什么历史的深度,而是时间之谜使作品变得神秘而幽暗。”(《隐秘花园》序言)王啸峰小说中的时间是从记忆的空间里面铺展与生发开来的,人世的沧桑、古城的变迁、时空的再造、灵异的谜团、艺术的魅力在他小说的时间轴上渐次展开,这都有赖于“回忆自己开口说话了”。回忆具有无孔不入的本领,让心灵变得异常敏感和丰澹,恰如走进古城千家万户的《抄表记》中的抄表人,也像《隐秘花园》中的外公,即使在肉身日渐衰败后,这种丰澹犹如智慧仍会累积生长。这是啸峰离开苏州到外地工作后,对古城最深的眷恋,甚至是用记忆对古城的一种“重塑”。这也让我想起果戈理说的:“我只有在罗马才能写俄国。”相信啸峰对这句话是心领神会的。热爱的对象所构成的回忆,如果心灵无法确认,又何尝存在过?这是古代诗人的“青山明月不曾空”(王昌龄《龙标野宴》),也是尼采的对大地说“是”。记忆如同一个建筑师,他会还你一座在匆匆赶赴现代化“盛宴”的路途中丢失的那座完美古城。王啸峰的记述与叙述,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城市史话。
时间之轴上的记忆对作家的重要性,不由自主让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繁复的记忆,琐细的记忆,是溺水者的那根稻草,是构筑文学梦幻宫殿的材料。记忆同时又是一个过滤器,一种澄清生命的过程。在普鲁斯特,记忆是一双翅膀,让他病弱的身躯脱离沉重的大地,成为他孱弱肉身一种精神介质。无论是记忆的大师普鲁斯特还是转型期的小说家王啸峰,在他们的笔下,有时记忆都像梦境,没有逻辑,关联现实的就是触发了他们痛点的那些碎片。记忆将他们曾经笃实相信的所谓真相还原为虚幻,记忆如打在黑暗舞台上跟随主人公的追光灯,他们是否清晰地知道这不是一场自我虚构的演出?对于他们来说,无法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就是不存在的记忆。每个词语都在开拓记忆的广阔时空,也将在卷曲的时空中重启自身的精神道路。
恰如《隐秘花园》中外公所言:记忆如同汉字,“读音变了,内涵没变。就像那些房子,多年之后,都会倒塌重建,但是曾经赋予的内涵不会变。所以打破平衡后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以前发生过的事件的镜像会不停地重复出现——只不过人类的显性,其他的隐性——等到回忆越积越多,现实与梦境就会互相影响,原本隐秘的世界越来越开放。”(第177页)在这里,回忆不仅能保存经验,回忆还更像内在本质,是与我们生命同在的一种共同命运体。
我愿用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l830-1886)的《如果记住就是忘却》来结束本文:
如果记住就是忘却
我将不再回忆,
如果忘却就是记住
我多么接近于忘却。
如果相思,是娱乐,
而哀悼,是喜悦,
那些手指何等欢快,今天,
采撷到了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