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可读性从哪里来
2017-11-01晓苏
晓苏
小说的可读性从哪里来
晓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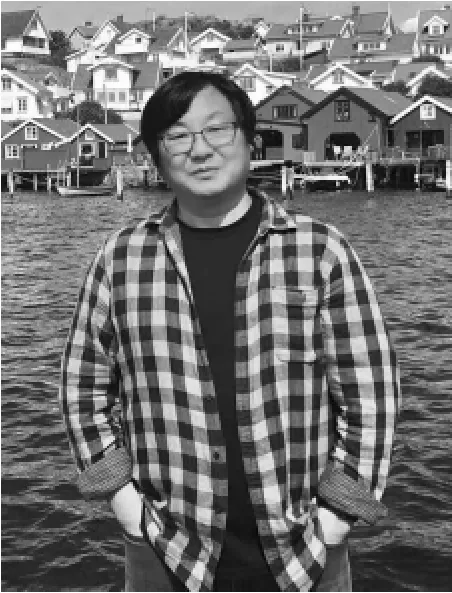
晓苏教授
一
小说写出来是让人读的,如果没有可读性,就没有人愿意读,没人读,那小说就没必要写,写了也是白写。因此,我一直把可读性视为小说的生命,同时也把它当成小说写作的最高追求。
小说的可读性,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看似浅显,实则深奥,完全可以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在我看来,小说的可读性至少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给读者初次阅读带来的吸引力和兴奋感;二是潜藏于文本深处的那种对读者持久的诱惑力,即那些能够激发读者再次阅读兴趣和反复阅读欲望的因素;三是文本暗含的可供读者进行多种解读的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把可读性狭隘地等同于通俗性、故事性和传奇性。这些只意味着好读,即浅近、易懂、有趣、好看。但是,好读并不完全等于可读,它只是可读性的一个方面。可读性的另一个方面还要求耐读,即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常读常新、百读不厌。它要求文本必须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参与意义建构的可能。
因此,可读性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好读,二是耐读。只有既好读又耐读,小说才具有真正的可读性。
二
小说的可读性从哪里来?无论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欣赏的角度来讲,我发现,具有可读性的小说,首先必须有意思。
有意思是相对有意义而言的。有意义指的是有思想价值,有意思指的是有情调,有趣味。最好的小说,当然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但是,这种小说却少而又少,十分罕见。我们经常读到的小说,有以下三种。一种是有意义没意思的,一种是有意思没意义的,还有一种是既没意义也没意思的。第三种显然是最差的小说了,这里不值一提。至于另外两种小说,我们见到最多的,无疑是有意义没意思的这种。可以说,这种小说几乎占据了小说的大半个江山。
坦率地讲,我不喜欢这种小说。原因是,它没有可读性。这种小说一味追求所谓的思想价值,要么卖萌,要么做秀,要么贴标签,要么喊口号,要么故作高深,要么假装正经,要么贩卖心灵鸡汤,要么兜售道德膏药。这种小说,读起来脸红,肉麻,恶心,头皮发痒,甚至浑身起鸡皮疙瘩,因此难以卒读。
有意思的小说则不同。因为它是从情调和趣味出发的,所以有着很强的可读性。它不求宏大,也不求深刻,只为渲染一种情调,传达一种趣味,显得很低调,很平实,有时候还有点世俗,因此读起来亲切,轻松,愉快,好玩,换句话说就是有意思。毫无疑问,我喜欢这种小说。
跟有意义的小说相比,为什么有意思的小说更具可读性?因为它不仅好读,而且耐读。首先,意义是理性的,意思是感性的,感性的东西肯定比理性的东西显得更直观,更形象,更具体,因此对读者更有吸引力;其次,意义是大同小异的,意思则是千差万别的,千差万别带来的美感显然比大同小异更加丰富和多样,因此对读者更有诱惑力;第三,意义一般是从内容中生发出来的,而意思却来自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所以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解读空间。
三
既然有意思的小说更有可读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小说怎样写才能有意思?通过比较,我发现有意义的小说和有意思的小说分别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形态。有意义的小说更倾向于庙堂意志,属于庙堂叙事;有意思的小说则更倾向于民间意趣,属于民间叙事。
庙堂主要指的是权力阶层,居于庙堂之高,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民间主要指百姓阶层,处于江湖之远,属于边缘文化形态。庙堂叙事的目的在于宣传庙堂意志,它当然更看重小说的意义,即思想价值。民间叙事的目的重在彰显民间意趣,所以它更看重小说的意思,即情调和趣味。这两种叙事形态的差异很大,突出体现在主题的表达上。
庙堂叙事形态的小说,在主题的表达上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它强调主题的教育性,要求对读者有教化作用,包括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伦理教育,属于说教化叙事;第二,它强调主题的明朗性,要求作家旗帜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热爱什么,憎恨什么,都必须明朗化,不能含糊其词,不能模棱两可;第三,它强调主题的集中性,要求一个作品只表达一个主题,不能有旁枝,不能有杂叶,也不能插科打诨。
民间叙事形态的小说,其主题表达与庙堂叙事形态的小说恰好相反。第一,它强调主题的审美性,要求小说必须渗透作家的审美意识,将感性与理性水乳交融,把情思和哲思融为一体,从而让读者得到美的体验与享受;第二,它强调主题的模糊性,追求含蓄,追求委婉,追求朦胧,叙事经常运用隐喻和象征,言此意彼,声东击西,闪烁其辞,模棱两可,似是而非,雾里看花,半明半昧,犹抱琵琶半遮面,给读者以极大的阅读诱惑;第三,它强调主题的多义性,叙述上打破封闭的格局,追求开放的状态,观念开放,故事开放,结构开放,语言开放,从而实现主题的开放,为读者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庙堂叙事追求的是有意义,而民间叙事追求的是有意思。显而易见,民间叙事无疑是小说可读性的重要来路。
四
弄清小说的可读性与民间叙事的关系之后,我想顺藤摸瓜,再来考察一下民间叙事形态的形成。任何一种叙事形态,都与作家的叙事立场有关。叙事立场是叙事形态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且是先决性因素。
所谓立场,指的是人们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与所持的态度,它与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小说而言,作家理应从纯正的文学立场出发去进行创作。遗憾的是,很多作家却秉持的是一种非文学的立场,要么是政治立场,要么是道德立场。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纯正的文学立场,纯正的文学立场应该是人性立场。
再回到民间叙事形态的小说上来。与庙堂叙事形态的小说相比,民间叙事形态的小说显然选择的是人性立场。
人性立场,就是要求作家把文学当成人学,尽力摆脱阶级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道德伦理学的局限与干扰,以人为本,把人性当作叙事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性的角度,用人性的目光,去观察、发现、捕捉那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不易察觉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往往是人性中最温柔、最脆弱、最潮湿、最疼痛、最神秘、最美妙、也是最有可读性的部分。一个小说家,只有从纯正的人性立场出发,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具有可读性的小说来。
那么,作家如何坚持人性立场呢?莫言曾以《文学照进人生》为题发表过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说:“中国文学要想获得世界读者的青睐,就必须打破过去局限的立场,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去表现普遍人性。”莫言所说的这种立场就是纯粹的人性立场,他要表现的是人类共同和普遍的人性。
人类共同而普遍的人性,有着共同而普遍的心理结构。从心理学角度讲,人有两个本能,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本能决定本性,它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最根本和最强大的原动力。生的本能表现为善良、慈爱、宽容、奉献、创造等积极正面的行为,死的本能则表现为恶毒、仇恨、狭隘、贪婪、毁灭等消极负面的行为。坚持人性立场的叙事,无疑应该对人的两个本能一视同仁,既要从正面去发现它的积极性,又要从负面去正视它的消极性。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写出真实的、复杂的、深刻的人性。
小说只有写出了真实、复杂而深刻的人性,才会对读者形成初次阅读的吸引力、持久阅读的诱惑力和多种解读的意蕴空间。换句话说,就是使小说获得了真正的可读性。
五
既然小说的可读性与人性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那我接下来就想谈一下小说如何看待和处理两性关系这个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性描写。因为,两性关系是人性中最核心的内容,同时也是最有情调和趣味的一种客观存在。寻找小说的可读性,两性关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两性关系指的是男女、公母、雌雄、阴阳等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种性别之间的微妙关系,其内容涉及到性器官、性征候、性需要以及性行为等与性有关的方方面面。两性关系是人类生活和自然生态中的一个最基本、最普遍、最持久、最神秘、最复杂的关系,既有心理性特征,又有生理性特征,并且与道德规范、伦理秩序和社会禁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对人们有着巨大而持久的吸引力,能激发人们无与伦比的兴奋与快感。因此,两性关系便成为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永恒母题,同时也是小说可读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源远流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从理论上讲,两性关系直接关乎到生命本身,不仅涉及到个体生命的存在,而且还涉及到族类生命的延续。但是,由于两性关系与性本能密不可分,所以庙堂叙事由于意识形态或道德伦理的原因,一般都不敢正视,在对待两性关系时总是忸怩作态、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只有坚持人性立场的民间叙事,才敢于正确看待和处理两性关系,进而去正面地、坦荡地、具体地进行两性书写。

晓苏教授在讲座中
性是社会人生的重要内容,作为反映社会人生的小说,不可能不涉及到性。夸张一点说,如果完全撇开性,小说就没法写,写出来也不真实,也不能全面展示出社会人生的本相与原貌。还有,我觉得性是人性中最幽深,最诡谲,最迷人的部分,如果要让小说具有人性的深度,闪烁人性的光芒,作家就必须去正面地写性,大胆地写性,严肃地写性,艺术地写性。
关键是要艺术地写性。我认为,艺术地写性有两层意思,一是用艺术的眼光去写性,二是写性中有艺术的部分。所谓用艺术的眼光去写性,指的是不能为了写性而写性,这性必须有它的艺术功能,要么是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要么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需要,凡是脱离人物和情节的性描写,都不是艺术的;写性中艺术的部分,意思是不能用性来刺激读者的感官。也就是说,不要过多地去展示性的细节、性的场面和性的过程,而是应该抓住性心理中那些有美感的部分,用文学的手法进行展示,努力给读者提供一种性爱之美的艺术享受。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小说而言,两性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只有艺术地写性,它才能转化为小说的可读性。否则,它将使小说的可读性大打折扣,甚至消失殆尽。
前面说到,小说的可读性,不仅要求好读,而且要求耐读。好读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耐读的问题,解决起来却十分困难。然而,这个问题再难也必须解决。否则的话,我们对小说可读性的寻找将会半途而废,乃至前功尽弃。
耐读的小说是不会过时的。它不是快餐面,不是一次性打火机,也不需要注明保质期。它不会人走茶凉,也不会时过境迁,更不会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说,他今天愿意读,明天还原意读。从不同读者的角度来说,今天的读者愿意读,明天的读者也愿意读。这么说来,耐读已经具有了经典的意味。是的,我们寻找小说的可读性,实际上是在呼唤小说经典。
那么,如何才能使小说耐读呢?我觉得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给小说注入现代性因素。
现代性是与传统性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方法论。现代性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前者萌芽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盛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虽然有阶段性的不同,前者侧重启蒙,后者侧重解构,但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即现代性。从哲学上来讲,现代性反对实用主义,反对本质主义,反对保守主义,强调自由,追求平等,主张开放,其价值观倾向于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认为价值具有相对性和多元性。
现代性也有阶段性的不同,可分为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如果说,前现代性的核心是建立一种现代文明新秩序的话,那么,后现代性就是要怀疑、推翻和打破已有的秩序。
当代学者周宪把前现代性称为启蒙的现代性,把后现代性称为审美的现代性。他说:“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以数学或几何学为原型的社会规划,那么,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则是对这种逻辑和规则的反抗;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秩序的追求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就是对混乱的渴求与冲动;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对理性主义、合理化和官僚化等工具理性的片面强调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正是对此倾向的反动,它更加关注感性和欲望,主张一种审美——表现理性;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当作一种对绝对完美的追索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则是一种在创新和变化中对相对性和暂时性的赞美。”我觉得,这番论述对小说创作极有指导意义,它从理论上回答了如何让小说耐读的问题。
一说到现代性,很多人都会以为它是一个极其高深、玄奥而晦涩的东西,将它划入意义的范畴,认为它枯燥、僵硬、干瘪、泛味,令人头疼。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和误会。事实上,现代性也是很具体、很实在、很形象的。它有情调,有趣味,严格说来应该属于意思的范畴。
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凡是具有现代性的小说,大都属于民间叙事形态,并且都是从人性立场出发的。它们常常运用象征、隐喻、反讽、夸张、变形、荒诞、错位和黑色幽默等现代技巧,同时还惯用德里达的解构思维和巴赫金的狂欢精神,从而变得异常生动,异常新奇,异常别致,读起来轻松、愉快、惬意,既好读又耐读,充满了真正的可读性。
晓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于湖北保康。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作家》《花城》《钟山》《天涯》《十月》《中国作家》《大家》《江南》《长城》《小说界》《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花》等刊发表小说五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五里铺》《大学故事》《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5部,中篇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2部,短篇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黑灯》《狗戏》《麦地上的女人》《中国爱情》《金米》《吊带衫》《麦芽糖》《我们的隐私》《暗恋者》《花被窝》《松毛床》12种。另有理论专著《名家名作研习录》《文学写作系统论》《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等3部。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刊转载40余篇,并有作品被译成英文和法文。曾获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花被窝》《酒疯子》《三个乞丐》分别进入2011年度、2013年度和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