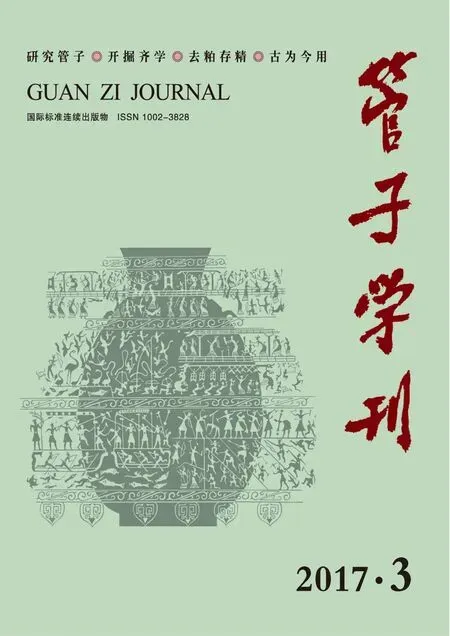清华简《系年》所见伍子胥职官考
2017-11-01刘光
刘 光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新出土文献研究
清华简《系年》所见伍子胥职官考
刘 光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其军事才能在著名的柏举之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中有关于伍子胥的新史料,其与传世文献最大的区别在于:《系年》记伍子胥在吴国所担任职官为“太宰”,而传世文献所载为“行人”。文章通过对春秋时期“行人”与“太宰”职责进行分析,并结合当时吴楚争霸的形势,认为:伍子胥在吴国所担任的职官应为“太宰”,其担任“行人”则属临时差遣。
《系年》;伍子胥;太宰;行人
伍子胥本为春秋时期楚国人,后因楚国的政治风波而逃奔吴国。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得到重用,展现了自己杰出的军事才能*对伍子胥军事才略及军事思想的研究前人多有涉及,如: 杨范中: 《从吴楚战争看伍员的军事思想》,《江汉论坛》1984 年第7 期;徐勇、黄朴民: 《关于伍子胥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92 年第3 期,等等。,为吴国入郢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关于其在吴国所担任的官职,以《左传》为代表的传世文献记为“行人”,而近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以下称“清华简《系年》”)则记为“太宰”,孰是孰非需要详作辨析。笔者不揣谫陋,结合相关文献对此问题略作探讨,以见教于方家。
一、关于伍子胥担任职官的不同记载与相关研究
关于其在吴国所担任之职官,传世文献所记载为“行人”,而《系年》所记载为太宰,相关记载如下:
《系年》第十五章谓:
伍员为吴太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诸侯,以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1]170
《左传》定公四年载:
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太宰以谋楚。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此事与《左传》有同有异,其谓:
王阖闾元年,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嚭亡奔吴,吴以为大夫。
《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所不同,然在叙述伍子胥官职为行人是一样的,这点与《系年》所记为太宰不同。
《系年》材料公布后,惟李均明先生撰文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在《伍员与柏举之战——从清华简〈系年〉谈起》一文中李先生认为“最大可能是伍员先当行人,后任太宰(尤其是阖闾九年之前史籍未见吴太宰任职的记载)”[2]83。而在《伍子胥的军事谋略与运动战理论——从清华简〈系年〉及张家山汉简〈盖庐〉谈起》一文中李先生的观点有所改变,他说:“所以,伍子胥先任太宰,后任行人的可能性很大,这两个职位对发挥其政治军事才能都是有利的。”[3]320李先生从历史事件的发展顺序上出发,得出上述结论,信而有征,言之成理。笔者认为,对于该问题,似可从另一角度来进行论证。笔者首先根据文献所载对春秋时期“行人”“太宰”之职掌作出分析,最后再结合吴楚政治形势,对伍子胥所担任之职官作出判断。
二、春秋时期“行人”职掌分析
行人之官见诸《周礼》者有“大行人”与“小行人”,其所载行人之职掌,曰:
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
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国之慝。
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凡诸侯入王,则逆劳于畿,及郊劳、视馆、将币,为承而摈。
由上述记载,我们可以将《周礼》体系下的行人之职掌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诸侯来访,行人负责行宾礼;其二,奉诸侯之命,聘问他国。
周代的行人在文献中还称为“行李”,《左传·僖公三十年》载: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
杜预注:“行李,使人。”孔颖达疏曰:“襄八年传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4]3974
“行李”又作“行理”,《国语·周语中》曰:
行理以节逆之。
韦昭注:“行理,小行人。”[5]72
西周金文未见“行人”字眼,但据学者研究,金文中“士”的职掌基本与“大行人”相同,当即文献之“大行人”[6]219-238。研究颇有理据,当可信从。
春秋时期“行人”于《左传》多有所见,从相关记载来看,春秋时期各国“行人”有如下特点:
第一,职掌与《周礼》所记大致相类,即行大宾之礼及奉诸侯之命行聘问之礼。
行大宾之礼者,如文公四年载: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
杜预注曰:“私,私问也。”《传》文言,宁武子来聘,鲁公与之宴,行人所行之职责即所谓大宾之礼。
行聘问之职者,如襄公二十四年载:
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程郑问焉,曰:‘敢问降级何由?’子羽不能对。”
《传》文所记,公孙挥奉命聘问晋国,正是行使行人聘问之职责。
第二,就《春秋》经传所见,行人为一时奉使,而非专官。
春秋时期朝聘是诸侯国间加强联系,巩固盟约的重要举措,有时候甚至关系国家存亡,因此,聘问人员的选择应当是非常谨慎之事。从《左传》的相关记载来看,行人多为临时差遣,而非专职。如:襄公十一年,《经》曰:
楚人执郑行人良霄。
同年《传》曰:

如上述推断不误,则我们可以知道春秋时期的“行人”只是一个临时奉使之官,并非常职。或者可以进一步说“行人”并非职官,而是临时差遣。
行人见诸《春秋》经传者凡18次*相关统计数据参看,顾栋高辑,李解民校点:《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73-1075页。,我们不惮其烦,将其细节具列于下,并将行人的职掌总结出来,列表1如下:
通过列表分析,春秋时期的行人之职,与《周礼》所记相合,皆行聘问或大宾之职,我们结合襄公十一年经、传的相关记载,可知“行人”之官为一时奉使之官,而非专官;进一步说,并非官职,而是临时差遣。
三、春秋时期太宰之地位与职掌
太宰之官见诸《周礼》,其所载太宰之职掌曰:
“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
“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诏王驭群臣”。
“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

表1 《春秋》经传所见行人表
“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
总而言之,太宰是辅佐王治理邦国各类事务,相当于后世“掌承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
周代的太宰又称冢宰,《周礼》题称为“天官冢宰”,杨天宇题解,太宰即冢宰[7]1;伪古文《尚书·伊训》曰:“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伪孔传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摄冢宰。”[4]344此处的冢宰与《周礼》所记载的“佐王治邦国”的太宰的职掌当相同。《礼记·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此处与《周礼》所载“以九贡致邦国之用”的太宰之职掌相同*关于“冢载为最高辅相说”的源流谢乃和先生曾有系统梳理,他指出:“春秋以降,随着权力结构的变迁,文献彝铭中的宰官职权在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呈现复杂有别的面貌,但冢宰在殷周时曾为君王最高辅相的历史之迹依然有端倪可寻。”详参氏著《古代社会与政治——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谢先生指出因时代不同太宰地位的不同,是很有见地的。。
“宰”之职官在殷墟甲骨文与商代金文中已经出现,如宰丰*见《甲骨文合集补编》11299反、11300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补编》,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3-1194页。、宰甫*《殷周金文集成》05395号有宰甫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殷周金文集成》(第四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得到,第146页。、宰椃*《殷周金文集成》09105号有宰椃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殷周金文集成》(第五卷),第305页。,西周金文中也有关于“宰”的记载,至于“太宰”一名在西周的金文中尚未出现。春秋金文中多次出现太宰之名:
齐昭公或懿公时期的素命镈(00271)*以下编号均为《殷周金文集成》编号,下不注明。器主素命是鲍叔牙之孙的儿子,因鲍叔“有成劳于其邦”,素命得以担任大工、大史、大徒、大宰,“余弥心畏忌,余四事,是以余为大攻、大史、大徒、大宰”。从器主兼任数职的情况来看,太宰非齐国所重之官,至少没有《周礼》所载如此权重。
春秋早期的鲁太宰原父簋(03987):原父铭文作邍父;由此可证鲁在春秋早期曾有人担任太宰之职,但从《左传》记载来看,春秋时期太宰并非鲁国所常设之官,也非鲁国所重之官。

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春秋时期的滕太宰得匜[10],铭文未体现其职掌,当与邾太宰相类。
综上所述,从春秋金文的实际来看,太宰并没有《周礼》所载的如此大的权力,斯维至先生对此曾有精辟的论断:“曩读《周礼》,觉其言冢宰制权能极尊,而细按所属,则凡庖人、官人、世妇、女御等殆皆王之小臣,可谓头大尾小,殊不相称,已疑其故,今由金文证之,乃知《周礼·冢宰》之职确有后人窜改。”*斯维至:《西周金文所见职官考》,转引自刘雨、张亚初:《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页。这是符合金文实际的正确见解。
太宰见诸《春秋》经传者,凡11次,从相关记载来看,各国“太宰”有如下特点:
第一,职权不若《周礼》记载重要,不为各国所重。
如襄公十一年载:
第二,太宰在某些国家设置非常制。
如隐公十一年载:“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公曰:‘为其少故,吾将受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弒之。”
孔颖达《正义》:“天子六卿,天官为太宰。诸侯则并六为三而兼职焉。昭四年传称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则鲁之三卿为太宰。羽父名见于经,已是卿矣,而复求太宰,而令鲁特设其官以荣己耳。以后更无太宰,而鲁竟不立之。”[4]3771由此可见,太宰非鲁之常设之官。
第三,太宰之官,可能为王或贵族的私臣,供王或贵族役使。
这些担任太宰的人,可能往往具有某些方面的特长或才干,满足王或贵族某种政治需求。这可以从《左传》所载伯州犁的事迹得出*《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伯州犁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担任楚王之侍,为楚王解答各类疑问,展现了自己的才能与见识。(“王曰:‘骋而左右,何也?’答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襄公二十六年,伯州犁平息楚王子围与穿封戌的争执,足见其才能;襄公二十七年,昭公元年,伯州犁随从楚王子围参加弭兵大会及聘问郑国,发挥了自己的外交才干。与聘问郑国同时,伯州犁为公子围所害,更验证了太宰之官为王之私人役使。。春秋时期太宰呈现的这种特征,可能也是由“宰”之起源于贵族之贴身侍御有关,可能是这种起源的孑遗。
太宰见诸春秋金文与《春秋》经传者,凡17次,我们不惮其烦,将所有细节列表2如下,以见春秋时期太宰的地位与相应职掌。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对春秋时期的太宰作出如下认识:
第一,春秋时期,太宰都非各国所重之职官。除少数小国之外,列国之太宰或为一般的职官,或是执政卿的泛称(然而这并非是职官)。
第二,春秋时期,太宰为王或贵族的私臣,可能为了满足王或贵族的某种的需求。太宰的这种特征可能是宰起源于王之近身侍御的孑遗。如楚之太宰伯州犁和吴之太宰伯嚭。
四、吴楚政治形势与伍子胥职官推测
(一)伍子胥的职官是太宰
吴国自寿梦时(公元前585年—前561年)始大,申公巫臣通吴晋之路后,吴国在晋国的扶持下暴兴,屡与楚国构衅,双方在淮北与江淮之间展开拉锯战,互有胜负,自吴王僚统治时期(公元前526—前515年),吴国渐渐在吴楚争霸中占据优势*吴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遂亡王舟,然遂夺回。吴王僚八年,公子光用谋(《系年》载用伍之鸡之谋)在鸡父大败楚国,攻取淮北重镇州来;九年,攻取楚国的居巢、钟离二邑,奠定了吴国在吴楚争霸中的优势。。

表2 春秋时期太宰列表
与吴国相反,楚平王即为后,楚国的内政渐趋腐败。好进谗言的少师费无极为构陷太子,连及伍奢及其子伍尚、伍员*据《系年》的记载,与伍员一起奔吴的尚有其弟伍之鸡,传世史书失载,而在今年公布的清华简第七册《越公其事》中也有关于伍之鸡,当有其历史来源。,伍尚为父被杀,伍员逃往吴国,《左传》昭公二十年详载其事:
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吾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杀之。
伍员因为楚国的政治风波,逃往吴国,其事发生在吴王僚五年(公元前522年)。伍员初逃吴,即向吴王进言,言伐楚之利,然未得重用。此事详见《左传》,其谓:
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雠,不可从也。”员曰:“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见鱄设诸焉,而耕于鄙。”
《史记·吴太伯世家》将《左传》的意思更为显明的表达出来,其载: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奔吴,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之季子。季子既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戮于楚,欲自报其雠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史记·吴太伯世家》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都交代的很清楚:公子光因对王位继承权有异议,阴求贤士,欲篡位。投奔吴国的伍子胥向吴王僚言伐楚之利,为公子光阻挠。伍子胥乃知公子光有他志,乃为光谋求勇士,公子光大喜,遂以伍子胥为谋士。
吴王僚十三年(公元前515年),野心勃勃的公子光弒杀了吴王僚自立,即王阖闾。阖闾即位,在稳定局势之后,即谋伐楚。并询问伍子胥所以伐楚之策,伍子胥言之,吴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阖闾四年(公元前511年),吴国即采取军事行动,用子胥之谋。相关记载,分别见诸《左传》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昭公三十年)
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于南岗而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昭公三十一年)
此时吴国的政治重心在于谋楚,《史记·吴太伯世家》则将此更显豁地表述为“光谋欲入郢”。伍子胥自楚奔,对楚国的内政了如指掌,其制定的伐楚之策,更为阖闾所重。这正是我们上文分析春秋时期太宰为王私使,其具有某种政治才干,满足王的某种政治需求的体现。此时阖闾的政治需求为“入郢”,伍子胥正可帮其实现这一政治需求,事实也确实如此,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楚几乎亡国。如上文我们对春秋时期太宰、行人职掌分析不误,则伍子胥在吴国所担任之职官,当是太宰,而非行人。《系年》所谓:
伍员为吴太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诸侯,以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1]170。
正是对太宰职掌的最好注脚。
至于伯嚭担任太宰,为吴王夫差所重,乃是与吴国政治重心的转移有关。入郢之后,伍子胥在“与越和成”“攻伐齐国”等重大问题上与吴王夫差意见相左,而被弃用,最终见杀。其事详见《国语》,不备列。而舍伍子胥而重用伯嚭,正是吴国政治重心由“谋楚”向北上争霸转移之故。伯嚭为太宰乃是由于其可以满足吴王争霸的政治需求,这与我们上文所述太宰之职掌若合符节,与伍子胥担任太宰的史实也不矛盾。
(二)伍子胥担任“行人”为临时奉职
春秋后期,列国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对小国而言,外交的结果有时候甚至关系国家存亡,因此,行人的选择应当是非常谨慎之事。由于战争的需要,这一时期出现了“外交与军事活动相配合之活动”[11]86,吴人入郢前的吴国的外交活动可谓这一现象的突出案例。《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世家》载:九年,吴王阖庐谓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吴越春秋》都记载吴国在入郢前联络唐、蔡的就是活动,其中尤以《吴越春秋》为详。《阖闾内传》记载吴王阖闾伐楚之前与伍子胥、孙武对话颇能体现此种现象。是篇谓:
九年,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将曰:“夫战,借胜以成其威,非常胜之道。”吴王曰:“何谓也?”二将曰:“楚之为兵,天下强敌也。今臣与之争锋,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吴王曰:“吾欲复击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孙武曰:“囊瓦者,贪而多过于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吴王于是使使谓唐、蔡曰:“楚为无道,虐杀忠良,侵食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举兵伐楚,愿二君有谋。”唐侯使其子干为质于吴。三国合谋伐楚。
伍子胥向吴王阖闾建议想要战胜强大的楚国,必须联络唐、蔡两国,从后文“吴王使使谓唐、蔡”的记载来看,吴王确实派人联络唐、蔡共同伐楚,而派出之人极有可能就是伍子胥。伍子胥的智能与才干,再加上其先椒举在中原各国中的良好声誉,使得伍子胥乃联络唐、蔡两国的最佳人选。这可能是文献所记“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的原因。
如前文分析,行人在春秋时期并非一个专任官职,而是一时奉使。换言之,行人并非职官,而是临时差遣。那么,伍子胥官职为太宰,奉吴王阖闾之命联络唐、蔡,并担任行人,也是符合春秋官制的合理现象。
综上所述,伍子胥入吴,所担任的职官为太宰。其担任太宰乃是由于其满足吴王阖闾“入郢”的政治需求;入郢之后,吴国政治重心由“谋楚”转而北上争霸,伍子胥失宠见杀,伯嚭为太宰受到重用,这与我们所分析的春秋时期列国太宰的职掌相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太宰的这类特征是其起源于王近身侍御的孑遗。由于入郢的需求,吴王阖闾命太宰伍子胥临时担任“行人”,联络唐、蔡,这是符合春秋时期“行人”非专官现象的。
附记:本文写作蒙导师李守奎先生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特此致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10&ZD091)结项成果。
[1]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上海:中西书局,2011.
[2]李均明.伍员与柏举之战——从清华简《系年》谈起[C]//罗运环.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3]李均明.伍子胥的军事谋略与运动战理论——从清华简《系年》及张家山汉简《盖庐》谈起[C]//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6.
[4]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吴雪飞.周代诉讼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罗新慧.
[7]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8]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9]谢乃和.古代社会与政治——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
[10]王人聪.新获滕太宰得匜考释[J].文物,1998,( 8):
[11]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二册)[M].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
2017-06-2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 项目批号: 10&ZD091) 。
刘光( 1989—) ,男,山西运城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史研究。
K877.5;K225
A
1002-3828(2017)03-0112-07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3.18
(责任编辑: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