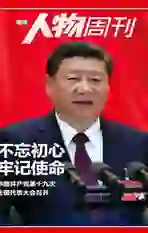生育迷思
2017-10-28陈竹沁
陈竹沁
“婚姻和孩子内在于任何一种人类繁荣的愿景。我们赞成以审慎的社会政策来鼓励和加强婚姻、生育和抚养。一个不欢迎孩子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
10月7日,欧洲十位保守主义倾向知识分子发布联署申明《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两天后,华师大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将其译介到中国。我在手机上划拉了几眼,继续埋首与同事静茹合作的“二孩”封面报道。
没想到交稿次日编辑也转发链接过来,《欧洲需要大量三孩家庭》,我随手戏谑了个“标题党”,与“二孩”稿中梁建章先生的专栏文章名相映成趣。
两地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当然大相径庭。不过,我总觉得“老欧洲”的恐慌,和中国学者对人口红利消亡、老龄化加速的担忧,有某种微妙的相似。原谅我视野所及都是“老男人”,非要具象的话,就是近期大热的美剧《使女的故事》里,黑衣主教站在高处训诫一群白帽红衣的使女。
这种联想可能失之极端,不过我想说的是生育决策中的话语权问题,它始终无可避免从私人领域被拉入公共领域。而其中的张力或冲突在于,父权与家国同构,而女权总是与个人主义合流。
易富贤很可能会批评我这个论断。在生多生少问题上与女权主义者的论争,他应该算得上“身经百战”。他把这些论敌称为“女残主义者”,而他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看得更为长远,他关怀的是老年妇女的养老问题——因为仅有社保可能是不够的。
如果问那些主动再生育的二孩妈妈们,你会发现“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明显回潮。许多受访者提到这几年大量“失独”家庭报道的刺激。站在两个孩子的角度,则是独生子女成长的孤单,和性格发展的弊端。我一度对后者有所认同,直到读了上海社科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包蕾萍所写的《独生子女神话:习俗、制度和集体心理》,我才重新审视上述观念的来源。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实证研究结果已经推翻这一“神話”:独生子女家庭的总体幸福指数常常高于“儿女双全”的理想模式,而孩子是否孤独、社交技巧的高下取决于父母花多少时间和心力带他们与外界沟通,与有没有兄弟姐妹无关。
不过我并没有将这些与我采访的二孩妈妈们分享。政府、企业、丈夫支持的多重缺位下,她们同时是优秀的职业女性和母亲,二孩让她们更强大,她们也从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儿女共同成长的快慰。
学者蒋莱告诉我,她访谈的近十位已生育二孩的高学历职业女性,都相对晚婚晚育,原生家庭经济水平和知识程度也较高,愿意做教育投资,尊重子女。在生育等家庭决策上,小家庭是核心,主导权掌握在妈妈手里,这样的家庭养育二孩的幸福指数较高。她们中没有人说“后悔生二孩”。这听上去不坏。
今年上半年上海多家产院分娩量较同期下降近两成。专家认为,主要是赶政策末班车的“70后”生育意愿已被释放,二孩全面放开后的“堆积效应”正在结束。这些家庭恰好是我们封面故事的开端。回过头来看,这一现象也恰好构成了我们这篇封面报道的隐线:今天的80后、90后,会怎样选择?
十位“老欧洲”把现代社会婚姻与生育的受挫归咎于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一种弃绝的文化剥夺了下一代人的身份认同感。”事实上,脱离具体家庭和个体经历的指责和说教,都毫无意义。
想来想去,还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最有趣——虽然物种有过度繁殖的原始能力,但资源的有限会使得生存竞争压力增加,最终实现物种数量的有效控制。而我们当下的生育环境,也无非是刚刚落回这样一个“自然选择”的钟摆。